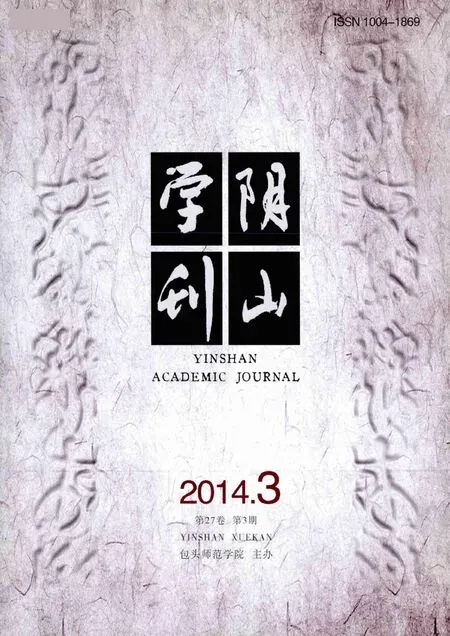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刘 云 飞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概念最早由德裔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进一步将“公共领域”一词概念化,从此形成了系统的公共领域理论。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和空间。在这其中,作为个体的公民,他们聚集到一起,共同探讨自己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一定的公论,并组织对抗无效的、专断的和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以维护公民的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此论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主流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学者的相关论著和论文层出不穷。而公共领域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也很快波及到了中国的史学界,并引起了极度关注和广泛讨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为:在西方各国,其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公共领域的发展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那么,在中国社会的演进中,是否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公共领域理论是否可以用来分析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①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有美国的罗威廉(William T.Rowe)、萧邦齐(R.Keith Schoppa)、兰金(Mary Backus Rankin)、史大卫(David Strand)以及中国的王笛和李长莉等。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有美籍华人孔复礼(Philip Kuhn)、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黄宗智(Philip C.C.Huang)、王国斌(R.Bin.Wong)以及中国的朱英和马敏等。集中反映这些争论的文章主要有:Frederic Wakeman,Jr.,The Civil Society Public Sphere Debate:Western Reflection on Chinese Public Culture;William T.Rowe,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in Late Imperial China;Philip C.C.Huang,“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以上文章均见Modern China ,19.2 (April 1993)。
但无论如何,有学者倾向于中国社会在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形态的主张。他们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剖析,认为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已出现某种形态的公共领域,并认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地方精英对社区公共事业的参与和管理上。②例如罗威廉通过分析19世纪汉口的商业经济和城市组织,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已出现了某种公共领域的形态。详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区(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笛也对晚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作了细致地分析,详见王笛《晚晴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李长莉对晚清上海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和演变也作了相关研究,详见李长莉《公私领域及私观念的近代演变——以晚清上海为例》,载刘泽华、张荣明等著《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长莉《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息”与“公共时间”》,《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此外,肖邦齐对清末民初浙江地方精英如何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进行了相关探讨,史大卫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公共领域的扩张作了一定的研究,参见赵红全《公共领域研究综述》,载《中国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笔者也认为,在明清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存在介于“私”与“官”二者之间的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事实。在今天,“公共领域”问题依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引入一种全新的理论模式来探讨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有利于拓宽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野和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对认识和反思我们的历史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因此,笔者将借用“公共领域”这一理论,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重点阐述在甘肃公共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甘肃公共领域创建中地方官僚与地方士绅的作用及关系
不少公共领域的创建是地方官参与推动的结果,甚至有些地方官将一些官办的慈善组织机构转移到地方士绅手中,从而使公共领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官方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过程。
清代甘肃为储粮备荒实行“仓储”制度。拿社仓来说,“乾隆初甘肃社仓有二,一为百姓公捐,自立正副经理,报官有案,不入官府交代;一为加工耗粮,内留五分为社粮,责成地方官经理,陕西总督岳钟祺所奏设。”[1](P15)再比如义仓,总督那彦成于道光五年(1825年)劝绅民捐谷建立义仓为甘肃建义仓之始。史料载:“(皋兰义仓)俱皋兰士民公举正副义长,在源源仓并寺庙民房收贮,县署有案。”光绪六年(1880年),新设义仓,“均在民房庙宇存储,公举绅董经理。”[2](P173)
上述皋兰社仓、义仓的创建实属地方官积极投入公共领域创建的一个范例。皋兰社仓由地方官员号召创办,并得到了官员和绅民的捐输,而且在社仓管理上由各社长自行经理,根据封建国家的惯例,社长、义长一般由“品行端正,家道殷实”的士绅来担任。这就说明,社仓、义仓的实际管理者是地方士绅而非官方。这表明近代甘肃的一些公共领域起初是由地方官倡建,而后把真正的经理权逐渐交到地方士绅手中,实现了权力的转化,而地方政府和官僚对一些公共领域所能做的就只有实施监督罢了。
在地方发生灾荒后,除了以地方士绅捐献为主要形式的民赈以外,主要的赈济方式是官方赈济和以士大夫和地方官捐献为主要形式的义赈。虽然官方赈济和有在任官员参与的义赈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公共领域的范畴(前所述以地方士绅捐献为主要形式的民赈属公共领域的范畴),但是地方官参与了各种形式的灾荒赈济活动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此以外,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甘肃的地方官员还建立了譬如栖流所、普济堂、育婴堂、养济院、恤嫠局、兰州同仁堂、兰州保节堂、恤老院、救孤院等公益慈善组织。而且,这些公益慈善组织起初大多由地方官员发起创建而后交由地方士绅管理。这方面的事例有:
兰州同仁堂,旧在鼓楼南,为施送棺木所,光绪二年兰州知府铁珊创置。原筹基金银三千一十四两,皆好善之士捐集,发商生息,又拨掩骼社廛肆九间并为局费,归绅经理。民国十四年,甘肃省长陆洪涛拨款五千元,仍归绅办。[1](P13)
兰州保节堂,旧在曹家巷,清光绪十二年兰州道饶应祺置。原筹基金银三千六百余两,发商生息,年久渐废。民国十四年,甘肃省长陆洪涛拨银一万元,归地方士绅经理。[1](P13)
育婴堂,在畅家巷,清嘉靖十六年总督那彦成置,收养孤贫幼孩。[1](P18)
恤嫠局,清同治十二年知县陶模置,每名月支小麦二斗,经费由无主荒地招垦取租。[1](P18)
再比如,在教育公共领域方面,以清代兰州府辖区*主要包括甘肃的兰州、榆中、临洮、临夏、渭源、夏河、皋兰、靖远等市县地,该行政区划于1913年被废。为例,清代兰州府辖区内共有书院16所,除爱莲书院和龙泉书院其创建者和创建时间不详外,其余14所书院中属地方官僚创建的有9所,士绅捐建的有3所,绅民共建的1所,公建的1所。[3](P44~45)显然,这些书院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20世纪初,为推行新学,甘肃省依学部规定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立学务处,成为主管全省学堂设立及其他监督工作的临时性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叶昌炽被省督府委派为“学务总理”,同时委派通晓教育的士绅参议教育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甘肃提学使依学部规定,通令各州厅县设劝学所和教育视学。劝学所以各地官长为监督,设总董一员兼任各地视学以视察当地学务,又在境内划分若干小学区,在每区设劝学员一名,并由“品行端正,留心学务”之士绅担任。劝学员负责讲习教育,统筹办学之策和推广新学,是一种职权较低的学官。按照清廷学部总务司统计,截止宣统元年(1909年),甘肃共设立劝学所75所,总董、劝学员分别达到了75人和381人。此外,为了倡导兴学育才的教育新政,辅助教育行政,推行教育普及,学部奏准各省设立教育会,推选会长、副会长各一人,聘任书记、会计若干人,并要求教育会须与学务公所及劝学所“联为一气”。于是,甘肃省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关于甘肃省教育会成立的时间,在傅九大的《甘肃教育史》一书中认为是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但在《甘肃省志·教育志》一书中却认为是成立于民国三年(1914年),笔者认为前者较为可信。因为中央的政令一下,地方不可能太过于拖延实施,必须尽快执行。在省城成立了教育学术团体——教育会。[4](P278~280)截止1938年,甘肃各个市县成立教育会达73处,会员超过1 098人。很多县市的教育会多数设在劝学所和教育局内,这些教育会后来由于机构不健全和经费困难,开展活动很少。[5](P493~494)由此可见,上述学务处、劝学所和教育会虽先由官方首倡设立,但地方士绅实际参与了每个机构在各方面的实际运作,尤其在发展地方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士绅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些教育会的会长、成员其本身就可能是地方精英,虽然甘肃教育会的活动有限,但它在讨论相关教育问题、社会疑点以及开通兴学风气等方面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此可见,地方官在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起了先导作用。地方官不但自身积极参与,而且倡导士绅积极捐助建立地方慈善公益组织和参与推动其他公共事业的发展,这很好地说明了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发展是地方官和地方士绅共同推动的结果。地方官僚和地方士绅二者彼此合作、相互依赖和利用,共同推动了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
二、创建公共领域的地方士绅与国家权力之关系
在创建甘肃地方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地方士绅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在基层社会的许多方面,例如道路、桥梁的修建,水利设施整修,灾荒救治,学校兴建,慈善事业的创办等方面地方士绅阶层几乎成为实际的管理者和主力军。关于士绅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独特作用,张忠礼先生有颇为经典的论述:
士绅作为一个具有领导地位和特殊声望的社会上层集团,推进和经理着众多地方和宗族的公共事务。他们的功能覆盖着广泛的领域,其中包括监督公共事项的财务、兴建和运作,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建立和经理地方和宗族的慈善机构,以及在和官府打交道时代表地方和宗族的利益。[6](P42)
甘肃地区内的士绅同样具有上述士绅的职责与功能,有关士绅单独修建以及士绅与地方官府合作修建桥梁、道路、水利等公共工程的事例如:
王钟灵,字世芳,皋兰庠生。……见义必为,凡修桥梁、建祖祠、置祭田,皆身任其累而出资亦巨。又别捐义田以赡宗族,设义仓以备凶荒,创义塾以诲邻里子弟。[7](卷八十九《人物七》P616)
迎善桥,在兴隆山,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八日被暴水冲去,至二十六年,官绅禀明上宪,由厘金项下拨银一千两,知县陈昌与绅士督工修建,更名“云龙桥”。[8](《建置·津梁》P677)
张廷选,字子青,狄道人,道光乙未进士。……狄道赴兰州路,旧由关沟门直入上摩云岭,沟深二十余里,细沙沮洳,夏秋雨水暴涨,路辄阻;冬季冰层立,多成深堑,车马倒毙无数,民甚苦之,廷选白诸大府,筹款该修新路,商旅赖之。……
狄城滨洮河南北皆旱田,廷选集众开渠溉田,费款巨万,三年始成。旋以土性不坚,复淤塞,廷选以忧劳卒。[7](卷六十九《人物志·群才一》P332)
很显然,上述的一些公共工程若没有地方士绅的支持而全靠国家之力是根本无力开展的。至于士绅与灾荒救治和地方慈善事业的创办,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1920年甘肃海源地震造成甘肃2 734 659 700人死亡,110 406 876 000头牲畜毙命,另据41个县提供的倒塌房屋的可靠数字统计,共造成590 635间房屋倒塌。[9](P386)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忍冻忍饥,瑟缩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为饿殍,亦将僵毙。牲畜伤亡散隅,狼狗亦群出噬人,实较本年北五省灾情为尤重。”[10](P40)此次地震是甘肃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之一。灾后,甘肃省当局成立“震灾筹赈公所”,后因效果不佳而撤销。在此情况下,旅外的甘肃籍人士“公举皋兰士绅刘尔炘专办赈务”,“尔炘桑梓攸关,文难逊谢,已于兰州设立‘甘肃赈灾筹赈处’,以士绅名义综理其事。”[11]筹赈处皆由士绅组成,“其他仁人志士闻风解囊者相望于海内,历时阅二十有七月,收款三十万两有奇。”[12]散赈时,“派素孚众望的士绅操办”,每县派二人,“遍历灾区,亲查亲放”,其“散放表册,受赈人员皆有手押。”[11]很显然,此次赈灾是以刘尔炘为代表的士绅来担当主角的。此次赈灾结束后,刘尔炘将所剩赈款用于甘肃各地创办丰黎社仓,以作为慈善机构来防患于未然。
此外,地方士绅还介入地方司法、帮办团练以加强地方防务和参与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由于受清朝官僚体制和地方官员职务繁杂、时间紧缺等因素的影响,地方官吏往往不得不借助地方士绅之力来处理包括地方纠纷在内的诸多事务。虽然清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而颁布了许多明令禁止地方士绅干涉地方社会事务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实际上形同虚设,地方士绅对地方社会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是实际存在的。对此,张忠礼论述道:“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士绅一般是不掌握司法权的,但是他们作为仲裁人,调节许多纠纷。有关士绅这类事务的例子不胜枚举,故人们下这样的断言,即由士绅解决的争端大大多于知县处理的。”[13](P66)对于甘肃的士绅来说,在地方社会中他们同样履行着调节民间纠纷的司法职责并受地方官委托帮办团练以维护地方治安,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比如:
周文,金县岁贡生。……生平善排解,乡里颂之。[7](卷七十三《人物志·孝义上》P597)
吴可读,字柳堂,皋兰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咸丰九年分校顺天乡试,丁母忧归,主讲兰山院,旋奉旨办甘肃团练。[7](卷六十四《人物志·乡贤上》P253)
当然,士绅武断乡曲、把持词讼的现象并不是没有。民初,秦安士绅巨子馥与地方士绅一道,介入地方防务、祭孔、举办公债、议会选举等事务,俨然凌驾于县知事之上。[14](下卷)西和县富绅“赵福海、何其慧两人操有甚大之帮会势力,为城中士绅藉势把持地方,协制官厅,并组织哥老会以养蓄势力,利诱各界人士参加,致无知者趋炎附势,入会甚多,其潜伏势力布满全邑,其著名而有力之爪牙为水南镇镇长刘宗向,长道镇镇长姬作礼、李永清、周维,兴国乡乡长柳效权,余如黄维岳、何应德等均供其驱策,故何赵二人实为该县士绅中之最有力者。”[15](P173)
三、结 语
通过前文论述,不难看出,士绅在各个方面干预地方事务,在地方公共事务当中,地方士绅通过兴建某些公共工程,举办一些公益性、救助性的慈善机构,并且一度介入地方司法领域,帮办团练镇压起义和维护地方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职能的缺失和不到位,让当地社会得到了更实际的裨益。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皇权势力一般只能达到县一级,对县以下的地区,国家权力相当有限。有学者称:“强大的皇权或中央集权国家的直接行政统治,从来未真正深入到县以下的社会中,广大农村及农民的直接统治机构和统治者,是作为皇权延伸物的家族和士绅。”[16](P181)此论述是不虚的,因为事实表明,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中,士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经营要远远多于地方官吏。士绅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弥补了官方管理的缺位,从而导致了非官方管理的膨胀,使得甘肃地区内的社会控制系统变成了官、地方士绅的联合体系。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地方士绅毕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以支撑地方公共事务的持续、长远发展,所以导致晚清以来有一些公共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17](P14)
总的说来,甘肃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和国家三者共同推动的结果。由前文我们看到,地方士绅、官僚和国家权力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密切的权力关系网络,这三者彼此依赖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国家为巩固自身统治,有时不得不转移部分权力给地方士绅,凭借地方士绅延伸自身的统治力量;而地方士绅则充分利用国家对发展公共领域的支持来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士绅把公共领域作为自身社会政治活动的基地。尤其从前文地方士绅的所作所为看,他们与官方行政机构所承担的职责有时候具有某种重叠的微妙关系。
通过前文论述笔者也得出,可能会因为地域的不同,环境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公共领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内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点和规模,但公共领域的共性只有一个,即不存在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公共领域,任何公共领域的创建、发展始终是地方官僚、士绅和国家权力三者共同推动的结果。
此外,笔者在思考一个问题,近代士绅的社会流动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绅商的出现,那么,甘肃的这些绅商阶层必然在甘肃境内建有大量的类似于商会、会馆等的商业组织。如果说晚清国家权力出现转移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甘肃境内的这些商会、会馆是否也像其他地区的商会、会馆一样开始行使过去由地方政府行使的职权,这些商会、会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了当地的政治,如参与地方征税、组织保甲、救济贫弱、筹集赈款、贮谷、管理育婴堂和孤老院等事宜。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再次把它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学人的注意,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1]甘肃通志稿[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总第28卷)[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00.
[2]重修皋兰县志[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方志(总第4册)[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3]高丽萍.清代甘肃书院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
[4]傅九大.甘肃教育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5]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6]张忠礼.中国士绅的收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7]甘肃通志稿[M].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四)[M].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8]金县新志[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总第34卷)[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00.
[9]刘百篪,张俊玲等.1920年12月16日海原8.5级大地震的伤亡人数再评估[J].中国地震,2003,(4).
[10]北洋政府内务部.赈务通告·公牍[R].1920,(8).
[11]甘肃赈灾筹赈处.甘肃省震灾筹赈处第一期征信录(手抄本)[Z].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1921.
[12]刘尔炘.辛壬赈灾记(手抄本)[M].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1921.
[13]张忠礼.中国士绅——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4]巨子馥.秦安巨子馥先生年谱[M].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1921.
[15]袁文伟.反叛与复仇——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6]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及其变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7]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J].历史研究,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