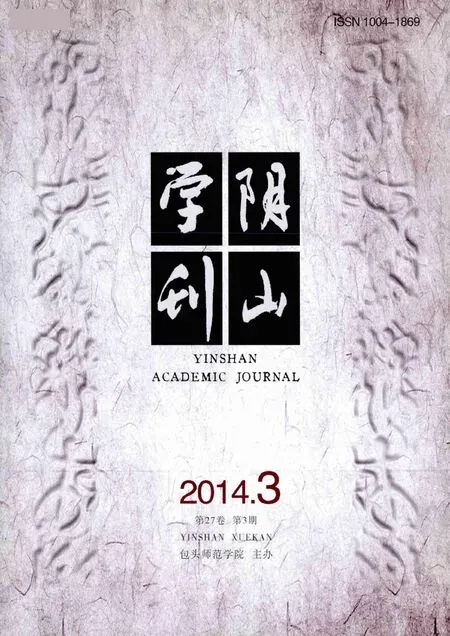“黑国语”
——包头方言中的隐语行话
胡 云 晖
(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内蒙古 包头 014025)
一
本文所谓隐语行话,是指某些社会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秘密交际语言,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黑话”,包头方言谓之“黑国语”。
汉语的隐语行话在古代文献中名称众多,有市语、隐语、切口、唇典、黑话、江湖话等说法,而其演变源流、形式种类,亦纷繁复杂,不可尽述。大概而言,则通谓之隐语,因为隐语的概念要宽泛一些,可以包括所有秘密语;而行话,则是指三百六十行中某一行业的内部秘密语言,古籍中谓之“市语”。《水浒传》第六十一回说燕青“不则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1](P632)诸行百艺的市语云云,也就是指的市井百业的行话。故隐语行话四字,似乎可以笼统地涵指所有的秘密语言了。
市语其名,唐时即已出现。据《秦京杂记》记载,“长安市人语,各有不同,有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折语,通谓市语。”所谓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折语等,是指不同形式的隐语行话。
宋元时期,由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达,隐语行话特别风行。圆社、妓院等都有行话,文人等日常绮谈,也以说市语为时尚,同时出现了关于市语的专集《圆社锦语》、《绮谈市语》。戏曲曲文中,行话词语更是屡见不鲜,几乎成为大众语言。
明清之际,隐语行话得到极大发展,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委巷丛谈”说:“(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2](P1097)清翟灏《通俗编·识余·市语》也说:“江湖人市语尤多,坊间有《江湖切要》一刻,事事物物,悉有隐称,诚所谓惑乱听闻,无足采也。”[3](P871)关于市语的专集、专著,还有《金陵六院市语》、《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行院声嗽》、《江湖行话谱》、《切口大词典》等,足见当时隐语行话流行之一斑。
而江湖话,则是建立在各种隐语行话之上的通用形式,吸收了众多行业市语的成分,为江湖大众所必知。过去相当多的一些行业或团体,例如耍把式卖艺、青红帮会等,因为其江湖性,所以其隐语就大部分采用了江湖话,主要是为了与江湖同道的交流。会说江湖话,可以通行于三山四码头,隔行也可交流;而只会说行业市语,则只能局限于行业内部。所以包头方言说:“江湖话走遍天下,黑国语寸步难行。”《切口大词典》序言也说:“夫吾人涉世,相接为缘,百业中人,熙往攘来,吾尝自命为聪睿矣,而以所业之不同,故术语互作,但见唇吻翕张,不辨声响,无论同帮族、同乡邑,相逢讶如异域,世间可怪之事,孰有甚于斯者?”[4](P1)可见自成体系的“黑国语”是有非常强的封闭性的。
二
清代的包头,原本是世居蒙古民族的游牧之地,乾隆初年,才有“走西口”的汉民逐渐垦殖定居,形成村落。之后,陆续出现了行商和小手工业者,直至发展到开设商号,商业趋于繁荣。尤其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托克托县河口镇因黄河溃堤而被淹,包头南海子渡口取而代之,以此为契机,一跃成为塞外河运主要商埠,到光绪末年,发展成了西北的“皮毛集散重镇”。
当时的包头,人口已发展到近七万人,车船辐辏,商贾云集,工商业形成了“九行十六社”,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靡不有之。对于那些走江湖、逛世路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码头。而由于治主不定,镇守官员的轮替极为频繁,更为江湖社会的形成,培植了土壤,奠定了基础。而军阀的来去,又如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今日方称奉军,明日已变晋系。或是土匪,独立队、不浪队,名目繁多,一经招抚,摇身一变,顿成官军;原系土豪,三相公、二少爷,杂色纷呈,拉起杆子,啸聚人马,就是山头。至于散兵游勇、哥老会、红枪会、乞丐帮,以及戏班、妓院、赌场、车行店脚牙、引车卖浆之流,更是应有尽有。其时的塞外包头,因为社会构成极为复杂,所以其社会语言也非常丰富,许多行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及生存的必要,几乎都有自己的隐语,江湖话也非常盛行。
如老包头梁上有著名的“死人沟”,本来是停厝棺材和埋葬倒卧死人的地方,后来一些乞丐等在沟的东西崖畔掏窑打洞居住,几十年间,形成了一个“讨吃窑”众多的贫民窟。而其人员构成,随着时间推移,越显复杂,或鼓匠、轿夫,或乞丐、流民,有江湖巨窃,也有剪绺小偷,藏龙卧虎,多达八百余人,逐渐发展成了名为“梁山”的帮会组织。“梁山”是丐帮性质的行会集体,属于江湖上的“锁家”和“里家”,有自己的祖师爷,其内部除订有帮规之外,还有极为严密的隐语行话。如小偷黑夜作案,叫“跑红条”,白天偷盗,叫“跑青条”,一早一晚行窃,谓之“打灯虎儿”,偷街上行人,叫“捏把子”,偷商店门市,叫“高买”,偷农民板车或毛驴驮子叫“滚轮轮”,站在房上巡风放哨,叫“登杆子”,进入院中升堂入室行窃,叫“跳池子”等。至于“梁山”内部日常交际所用的行话,就更为丰富,比如叫有势力的人为“碴儿”,称跟本家的女人通奸为“踩穷汉窝铺”,称捏造事实坏人名誉曰“唾臭”,乞丐头叫“鞭杆子”等都是。
牙行是旧包头商业贸易中的特殊行业,由于工作需要,不同的牙行,都有自己的行话,如老包头牛马桥上的“桥牙子”,除在“捏袖圪筒筒”时有诡秘的技巧之外,还有特殊的行话,例如数字方面,称一为流,二为戳,三为品,四为瞎,五为拐,六为挠,七为猴,八为桥,九为弯,十为挂,十一叫一大一小,五十五叫两拐;交易方面,称牛为叉子,驴叫鬼或尔直更,羊为绵绵,马为分耳,骆驼为铁面,卖叫射,买叫沾等,也是杂说纷陈的。其中称骆驼为铁面,称驴为尔直更等,是借用蒙古语,可见其词汇的灵活多样。
清末民初的包头,赌博极为盛行,东门大街至财神庙一带的闹市上,有好几家宝店,或者掏宝、推牌九,或者碰和、打麻将,呼幺喝六,勾引赌徒。其中有专门吃赌博饭的“白活”,输打赢要,闯汉子,充光棍,动辄以身体、性命相拼;也有“吃麻将”、“耍老千”的“高手”,在赌场上运用“搬肘子”、“打面相”、“推一门”、“下签子”、“捞海底”、“垛桃子”等技艺,赢那些不知深浅人的钱财,其隐语行话,则通谓之“吃空子”。
在过去老包头的大街上,还有一种卖故衣的小商人叫提猴的,既无店铺,又无大资本,零星淘些衣物,提溜着在街头喝卖。此类人也有黑话,其数目,依次为一喜二道三挺四飞五口六抓七谢八胜九满,十为喜子,十一则为重喜子,关于衣物等,自然也有非常详细的隐语。
包头理发业的历史较为久远,相传清康熙年间,就有了第一家剃头铺兰喜堂,之后发展壮大,并组建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净发社”。
旧时理发工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被列入“下九流”,为了生存,行业内部非常讲究团结互助,江湖义气浓厚。尤其是为了应付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免受欺侮,他们也创制了自己的隐语行话,并规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只在行业内用作互通信息和交流暗示。如称难伺候的顾客为“道啃子”,军警宪特叫“嚎天子”,小偷叫“王顶托儿”,大胡子叫“大盘子”或“海碟子”,技术不精的二把刀叫“月点清”,理发不给钱叫“漂活”,钱叫“棍儿”,茶叶叫“水上漂”,油叫“漫水子”,炕叫“温台”等等,不仅词汇量极为丰富,而且不断创新补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词汇系统,据笔者调查统计,其种类可以分为身体门、器物门、人物门、居住门、姓氏门、动作行为门、性状门、理发门、饮食门、数目门等。其一至九数,分别是一溜二月三王四则五中六升七心八张九爱十足。这一计数法,属于江湖话的借用,清翟灏《通俗编·识余·市语》曰:“江湖杂流,一留二月三汪四则五中六人七心八张九爱十足。”[3](P871)包头理发业行话在借用时,因受地方方音影响,与之发音稍有不同,如四,有时念直,有时念斋;九,有时也念耐;十则念为局。
旧日包头理发业的从业者,虽然以陕西榆林人为多,但其传承,则受山西长子县理发业影响甚大,所以其隐语行话在长子县理发人足迹所至的山西大部、河北张家口、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宁夏的银川等地的业内都可以通行使用,而且如上所述,其中也掺杂了相当多的江湖话因素,从而使其行业具有了江湖的性质。
所谓江湖,其本义是指四方各地。因为过去有相当一些人,专门游走四方,浪迹天涯,以流浪谋生,称之为走江湖,所以江湖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含义,专指因之而形成的社会氛围。
在旧日,因为时局和社会的动荡,造成频繁的人口流动,从而为江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所以当时的走江湖者,各色人等无所不包,即如“走西口”的江湖人中,既有撂地摆摊、耍猴变戏法的艺人,也有走方郎中、占卜卦师;有江洋大盗,也有小李白钱;有散兵游勇,也有落魄文人;有云游僧道,也有祖传乞丐。三教九流,无不混迹其中。这些人背井离乡,冲州撞府,拜山门,闯码头,在颠沛流离与险恶环境之中,既需要别人的帮扶,也乐于助人,逐渐形成为江湖规矩,而江湖话,正是这些人用以语言沟通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旧日的包头地区,凡是具有江湖特点的行业,其隐语行话,都与江湖话密切相关。其中受江湖话影响最大的是戏剧行业。
各地的戏剧界基本都供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唐明皇,而且无论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戏剧种类,都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团体性较强,其从业性质,则主要以流动演出为主,所以更具有江湖的特点,其隐语行话,也就以江湖话为主。在包头地区的“二人台”艺人中,因为受地域因素的影响,所以其行话虽然说的是江湖话,但也有一些方言、方音的特点,具有地域性,从而有别于通用的江湖话。例如火扇子(酒)、躺子(枚)、杈杖(筷子)、捏捏(唢呐)、妥条(睡觉)、斗花子(姑娘)、草条儿(香烟)、扑尘子(面粉)、踢土子(鞋)、老斗(傻子)、操皮(打鼓)、草盘(扬琴)、流水子(四块瓦)、扇子(镲)、皮(鼓)、太皇(梆子)、圪喘子(笙)、筛(锣)、正皇(师傅)、帘子(钱)、还巢(回家)等。
旧日的包头地区,土匪多如牛毛,而匪患的猖獗,与哥老会的兴起密切相关。关于其结会及隐语行话情况,民国《萨拉齐县志》引于孔昭《土匪记》曰:“先是,(民国)十年冬,哥老会传会甚力,有秦人小五杨者,名杨万祯,为龙头,绥西各县皆设有码头,会中分清洪水两派。清水派曰秋子行,又曰顶门垫户;洪水派曰杆子上,又分忠义、五福等堂名,暨峨眉、终南等山名,以别尊卑次序礼。一般劣绅、土棍、无赖、流氓,争先入会。有驻包头甘军统领蒋辉若者,早已在会,助杨甚力。萨、包、固、五、安、东等县,均已会化(称清水,或云汇通),在邑境传会(称栽培)者,二、四、五区等均有首领,夜间三五成群,相率焚香结会,白昼聚集一室,练习会语(称团条子)。乡人有反对或不赞成者,立遭横祸。凡在会者,所有财产与匪共有,任何糟踏不敢启齿,如帮码头(称斗份子)款,业经派定,即倾家荡产亦得完纳,故筹措十万八万,极为容易。杨既拥有巨资,乃权门奔走,官僚往来,竟有山西国会议员贾述尧(平鲁人)拜为门徒,而土劣等更是群蚁附膻,称子称孙者迹踵不绝。”[5](P785)之后哥老会沦为土匪,时而被招抚为官军,时而又落草为寇,对地方民情风俗以及语言习惯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在妓院、旅店、饭馆、鼓杠房、当铺、占卜星相、阴阳、浴池、煤矿以及百工技艺等行业,也都有自成体系而不相通用的隐语行话。这些形形色色的行话,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也不是流行语言,但在一些特殊交际场合,却是不可或缺的。
在包头民间,还普遍流传过一种叫做“露八分话”的隐语。所谓“露八分”,是指将言语隐其二分,露八分于人,以惑乱听闻。其方法,是于正字之前,冠以该字同声eng韵之字,故增一字,连带说出,使旁听者仿佛能懂,而仓猝间又莫能明辨,起到隐语的作用。如大坏蛋一词,以露八分话说出,则成“等大亨坏等蛋”;露八分,则说成“冷露本八粉分”,余此类推;如果正字声母是j、q、x者,则前冠之字韵母变为ing,如“机器人”,则说成“井机请器仍人”;先生,则说成“醒先省生”。用这样的方式说话,自然是具有一定的隐秘性的。
三
隐语行话作为一种行业、帮会语言,具有极为强烈的封闭性,但作为一种语言形态,又必然具有交流的属性,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有开放的一面,日久天长,自然有一些词语就进入了方言系统,成为地方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包头方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是来自于江湖话或行业隐语。
例如称受伤为挂花、挂彩,称踩点为踩盘子,称绑票为请财神,称走为扯活,称匕首为七子,称形势危急为风头紧等,就都是来自于土匪黑话。其中踩盘子,来源甚早。《水浒传》第二回:“叵耐史进那厮,前日我去他庄上寻矮丘乙郎,他道我来相脚头踩盘,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六部成语·刑部》:“踩盘,踏看某地某家以便行动也。”《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语言类·方言俚语》则说:“各县指结伙行劫者曰独立队,绑票勒索曰请财神。匪中类多隐语,以掩耳目。其最通行者,如谓官军来捕曰水洪,受伤曰挂彩,子弹曰鱼子,暗报官军曰改水。”[6](P108)为大众所熟知,也就丧失了隐语的隐秘性,成为特殊的方言词了。
又如称讨吃货为道啃子,称看为扳沙,是来源于理发业行话;称傻子为壁龛,称男妓为相公、为老五,是来源于戏剧行话;称妨主货为白头牛,是来源于哥老会行话;而捞毛,则是来源于妓院行话,等等。
另外,据老艺人口传,一些在文字资料上无可考证其源头的方言词,也都是来自行话,如睡觉叫掸活,说话叫谝啦,吃饭叫抿咂等都是,我们如果细加考察,必定还能发现更多属于隐语行话的方言词。这些词语的进入,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方言词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严格地说,“黑国语”并不属于方言的范畴,而应归类于社会语言。只是因为其在流传使用的过程中,有一些词语进入了方言,而这些词语在方言中的归类,只能称之为“黑国语”。所以,本文题目所谓方言中的“黑国语”云云,仅仅是一种狭义的说法。而真正的“黑国语”,只在其行业或帮会的内部流传,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其具体情形,并不为局外人所知晓,是名副其实的秘密语言,与地方方言不可混为一谈。
但毫无疑问地,隐语行话也是一种民俗语言现象,它与产生这种语言的历史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搜集和整理这些虽然已经过时和即将消失的语言,哪怕是只言片语,东鳞西爪,对于研究和了解“走西口”以来包头各行各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如实反映当时的风俗民情、社会风貌等,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非常希望有这一方面的知情者和热心者,能够留心一二,予以抢救记录和归类整理,若如此,则不仅可填补历史空白,也是地方语言文化之大幸。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中国方志丛书之四八八号[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3]翟灏.通俗编[M].台北:大化书局,1979.
[4]吴汉痴.切口大词典·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5]萨拉齐县志[M].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八[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
[6]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七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