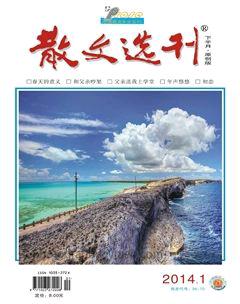年声悠悠
赵畅

过年的脚步近了,记忆中小山村的年声也渐渐响起。那年声一如春天破冰,河中湖间经了温煦春日的照耀,那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在厚厚的冰面上撕开一道道裂痕,直抒胸臆,喷薄而出。
40多年前,我曾寄养在浙东四明山麓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是祖父祖母的家。即便以后回到了城里生活,读书放寒假我还会回小山村过年。与城里相比,去小山村过年才听得到真正的年声,透过年声才真正感受得到那浓浓的年味、酽酽的年景。
过年的氛围,总是从猪叫声开始的。只要听到猪叫声,我们总会循声而去。要知道,杀猪是小山村的大事,似乎也只有过年时节才能看到这样的场面。赶到现场时,那里早被围得水泄不通,猪还未开肠破肚,可等着买肉的人则开始与主人嚷嚷着要买这买那、讨价还价的。那年头,家家经济拮据,大伙也只是象征性地买两三斤猪肉回家。是的,似乎只要有了猪肉,家里做菜就有了底气,过年也就滋润了。
祖父祖母家人多,经济条件相对也好点,所以总会多买点肉。于是,其中一部分便会被用来做红烧肉。单单烧做红烧肉,似太过奢侈,通常会加入几倍于猪肉的油豆腐。每每往锅里放油豆腐时,祖母总是将一只只油豆腐像新疆羊肉串一样串在竹筷上,待满筷了再将其一只只拨入锅中。问其故,则曰:“便于肉卤进去。”此时,灶膛的火正旺,应和着火苗的扑哧扑哧声,锅中猪肉和油豆腐之间的交合也始发出咕咚咕咚声。从田间地头回家的叔叔婶婶们,推门听到这样的声音,也便发出会意的笑声。
除了杀猪,养了鸡鸭的人家,也会开始宰杀鸡鸭。要知道,猪肉与鸡肉、鸭肉是小山村过年最传统亦是最高档的菜肴。而自酿的米酒,更是断然不能少却,否则,这年等于没味没劲没过。祖父家的米酒,是由祖父亲自制作的。从烧糯米到拌和酒曲,从洗酒瓮到封瓮盖,祖父一人给包了。而今想来,米酒该是生命的“尤物”,每个环节都深蕴于生命之中。从稻米变成琼浆玉液,实现华丽蜕变,这是集日月光华于一身的上苍的恩赐。启瓮盖的前几天,祖父总是会让我用耳朵贴着瓮身听。起初,我什么都听不到,祖父说:“要专心、用心去听。”慢慢的,我终于听闻到了瓮内的声音,心愈静则声愈大,那是翻江倒海的发酵声,那是胶着合体的欢叫声,那更是凤凰涅槃的飞舞声。小山村之所以流行米酒,是因为其兼众酒之长,少去了白酒的刚烈,弥补了啤酒的清淡,汲取了黄酒柔和的绵长。当瓮盖被开启的那一瞬间,蓦地,酽醲的清香扑鼻而来,并刹那调动起我们周身的味觉。“好酒,好酒哪!”祖父连声夸奖,为自己的酿制手艺,也为过年的佐餐助兴。
年夜饭,是每家每户年末最隆重最丰盛的一顿饭。午饭以后,祖母与大婶小婶早已开始筹备菜单。每年,祖母总会创制一只新的菜肴,她说:“老是传统菜,我会被下岗的。”祖母的幽默不是没有道理,大婶小婶都想露一手哩!因为创新,祖母依然每年掌勺。在我印象中,祖母的新菜颇有创意,至今难忘。比如煨煲猪蹄、鸡爪加香菇,比如蛋花、咸菜、鱼丝羹。用柴灶烧尽的炭灰煨煲食物,虽不见火苗,但煨瓮内若有若无的声响,自将食物煮了个熟透。那稠厚的汤汁滑过每个人的舌尖,香浓、缠绵,看着家人惬意的神情,祖母快慰极了。而那清清淡淡的羹,因了丝丝缕缕蛋花的悬浮,恍如袖珍荷叶的咸菜的铺绣,如纤柔银鱼般的鱼丝栩栩如生地穿梭,这羹味道当是好极了。吃年夜饭时,烧菜的祖母是最忙碌的。每上一个菜,她都会叮嘱端盘子的大婶小婶:“叫他们趁热吃,抓紧吃,后面还有哩!”只有等到菜上齐了,她才肯落座,只可惜,菜冷了,给她留着的菜其色香味多少也走了样。然而,祖母依然乐呵呵的。经了祖父的提议,我们集体向祖母敬酒。于是,碰杯声、欢笑声飘出窗外,与其他家庭的欢声笑语相接,构成了小山村一年最后时光的幸福图景。
除夕夜,也是守岁夜。我曾问祖父:“为什么一定要守岁呢?”读过书的祖父是这样解释的:“时间如白驹过隙,不管过去的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精彩还是遗憾,无论幸运还是无奈,这已然成为我们过往人生的一部分。它就要离去,也正在离去,想到此,我们总觉得有些难舍难分,所以古人要‘守着它。”哦,原来守岁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我感慨万千——守岁就是在为属于自己的时间站岗,替属于自己的生命情感守护。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刚才还在表达要坚持与祖父祖母一起守岁意愿的我,渐渐的终于招架不住瞌睡虫的诱惑,始沉沉睡去,即便是后来的炮仗声也无法将我从酣梦中拉回来。倒是两位老人信守着承诺,通过长长的守夜完成了对一个年俗的礼拜,而年俗“就这样完成了岁月的转换,以‘辞和‘迎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天地一年一度的‘天人合一”。
大年初一的清早,我总是会被一阵阵的鞭炮声吵醒。换作平日,我会记恨,可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自是高兴。我知道,今天可以穿新衣,可以拿压岁钱。想着想着,便再也不想赖在被窝里。穿上新衣下得楼去,祖父祖母和叔叔婶婶一齐将目光转向了我,他们一边夸奖着我的新衣一边给我递上红包。此时此刻,我恍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走在T型台上的模特、走上领奖台去的获奖者。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则是最好的音乐伴奏。
毕竟是小山村,气候也明显比城里低,过年更是时常碰逢大雪天。但在我看来,只有下雪,满山遍野披上银装,这才有年的气氛,才像是过年的样子。每每下大雪,总是在傍晚时分。“大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晶莹的雪花像柳絮,像芦花,远看大有纷纷扬扬之姿,近听更有窸窸窣窣之声,她是仙女撒下的碎玉,是月宫桂树的缤纷落英,是翩然起舞的白色蝴蝶。这形、声、情并茂之景之境,恍如搔痒的无形之手,把我的心搔得直痒痒。早晨起来,推开窗户,雪已停辍,村道则早被皑皑的白雪淹没,唯有几只大黄狗留下的一串串脚印才提示人们脚印下面就是村道。早餐过后,除了零星的鞭炮声,便是大人和孩童打雪仗时发出的嬉闹声。你扔我躲,你追我赶,更兼雪末飞舞,远远望去,这场面成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里唯一的动感画景,一如童话里的故事。
过年看戏,当是小山村最为隆重的年事。开演当晚,挂着汽油灯的戏台前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一阵紧锣密鼓之后,胡琴一拉,帮腔完毕,女旦便碎步而出,腰随脚扭,手随头舞,未等开口行腔,这袅袅娜娜、款款有韵的亮相,早已赢得满堂喝彩。行腔连故事、故事连行腔,随着故事情节的陆续展开,各路人马始一一登场。于是乎,“一腔一调,韵里藏情;一举一动,巧中孕美”,“吟到悲处,观者便回肠九转,泪流涔涔;念到喜处,看客则前俯后仰,乐不自禁”。传统的戏曲艺术,其故事并未有迷局般的复杂,且人的忠奸褒贬、性格特征,都被描画在了脸上。然而,观众却能在那唱腔身段的表演中如醉如痴,在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正义逻辑中陶然怡乐——这或许就是“曾经支撑了传统戏曲生长发展的最大多数普通观众关于生活的美好期待,以及由此形成的欣赏习惯”。戏曲终了,散场后,总有人捏腔拿调地学着哼唱起来,有的竟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苦苦记着戏中人物,真可谓“听唱入唱,看戏识戏”。
在小山村,过年吃请之于我则又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风景。因为我还是孩子,所以通常总是被请去吃早饭。早上是我赖床之时,但只要听闻楼下或隔壁大伯大妈大嗓门的叫声,我总会在第一时间起床,我知道这是乡里乡亲的好客之情,我不可推却更不能迟到。在常人眼里,吃早饭定然简单或只是为了应付,可不管进哪家门,我发现桌上摆放着的显然是他们全家过年最为丰盛的小菜,从中可见他们的真诚好客。我知道,按村里的习惯,有几个菜诸如整条的鱼、猪肘子等一般是凑凑碗头而已,轻易不去碰它,只有等到重要客人光临,才会动它。可好,我不动筷,主人竟会毫不犹豫下重手撕裂并屡屡夹给我吃。而今想来,他们是将我当做上宾了的。
每次过完年,就要回城里去了。临别前,亲朋好友们总会拎着粽子、年糕、鸡蛋、糯米之类的东西送我,弄得我收也不是不收也不好。我知道,那些年里,他们自己也并不富余,可他们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送我。进退维谷里,每每又总是祖母出来打圆场:“我看,拿是要拿的,这是大家的一份心意,但只拿一部分,太多了恐怕也吃不完。”即便如此,有时相互间也还是嚷嚷着不肯退步,不明真相的人,远远听见还以为是在吵架呢!可莫要小看了这些小年礼,在我心里其价值远比今天的燕窝、人参、虫草要贵重许多,因为乡亲乡情无可替代、弥足珍贵。
小山村交通不便,凌晨四点多我就得起床赶车。告别祖父祖母、叔叔婶婶,我早已泪流满面、哽咽不止。穿过弄堂,告别声、哭叫声不小心吵扰到了周围住户。随着送我去车站的小叔和我的脚步声的响起,弄堂人家的楼上窗户便次第打开,“慢慢走,明年过年时再来”“莫难过,马上又要过年的”,一声声,是告别也是欢送,是邀请也是欢迎,是呼喊也是慰藉,是离去也是归来。
年声,不是别的,是笑得最甜、睡得最踏实的时刻,是说不完的家长里短,是喝得最干的酒、燃得最亮的灯,是春联、灯笼和爆竹的炸响,是一个流淌在血液、深入到骨髓里的长长的符号……
这悠悠的年声里,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