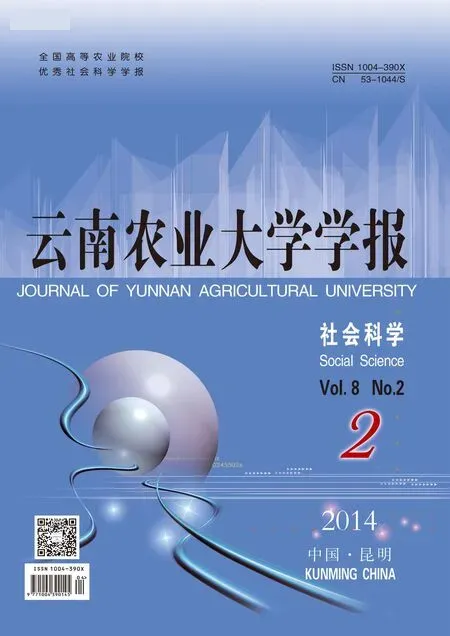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对秘书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
杨晓雁,李荣兴,莫晓萍
(云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我国秘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黄帝时代的史官,其后经过历朝历代的改革,秘书的职责分工越来越清晰明确,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但不管哪朝哪代,从事秘书工作的人都是古代文人中的一分子,他们的文化背景、心理态势、思维方式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任何文化、道德都是历史具体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时代、民族、阶级的不同内容,原始时代不同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资本制度,各种知识观念、道德标准和艺术趣味都在不断变迁。然而也就在这种变迁运动中,却不断积累着、巩固着、持续着,形成着与动物相区别的人所特有的心理结构、能力和形式。”[1]这就是文化心理结构。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秘书群体的情感意志、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塑造。
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是构建秘书群体文化心理的基石
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伦理,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它的形成经历了从孔子、孟子到汉代董仲舒的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孔子提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仁”,孟子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仁、义、礼、智,董仲舒则提出了“信”。至此,形成了一个以“仁”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人一部分的秘书群体,不仅以此为自身立人行事的准则,更将其泛化到秘书工作的方方面面。
首先,“仁”是统领一切的根本原则,它框定了秘书群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中国古代的秘书们是从对己对人两个方面来践行“仁学”思想的。对己,是指他们把“仁者爱人”作为最根本的道德情感贯穿在生命活动的始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那里,“仁”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以“爱人”为核心,包含了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引者注)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这是从人的行为方面规定了怎样才能行“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是论述了“仁”在道德情感方面的表现。而“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其言也讱。”(《论语·严渊》) “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学而》)这是“仁”在语言仪表方面的表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论语·里仁》) “仁者不忧。”(《论语·子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罕》)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是求“仁”的方法。可见,孔子以“仁”为核心而构建的道德范畴体系,“既包括有人的认知心理、语言仪表、道德情感、行为动机等主观因素,也包含有人的道德行为的客观因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2]几千年来,“仁”的标准就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对“仁”的追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执着追求。
不仅如此,孔子还把这种“爱人”的思想扩展到治国理政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更将其阐发为“仁政”学说,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方方面面论证了“仁政”的方法,要求统治者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仁政学说对作为为统治者服务的秘书来说,提供了一个高于服务对象本身的道德标准。统治者的言行不符合“仁”的标准,就会换来秘书们的犯颜直谏,甚至死谏。例如,唐朝的魏征,每进切谏,虽几次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明代的海瑞,为人正直刚毅,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深得民众爱戴。
其次,“义”是由“仁”申发出来的秘书职业道德,主要表现为君臣关系中对君主的忠诚,以及秘书职业活动中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什么是“宜”?就是合适,也即符合周礼。“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大戴礼记·盛德》)“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记·乐记》)孔子也说:“名出以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可见尊卑有礼,各得其义,就是“义”。因此,“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作为直接为君主服务的秘书,恪守臣子本分,谦卑有礼,忠诚不贰是其职业操守的第一要义。这种德能兼备的人臣历来是受到统治者赏识的,《旧唐书》就是这样评价唐太宗的能臣魏征的:“其实根于道义,发于侓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
我国古代的秘书往往还兼有史官的职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秉笔直书”、“君举必书”、不虚美、不掩恶的职业道德,这些也是“义”中应有之意。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这样的典范。
第三,礼是仁的具体体现。在秘书活动中,“礼”表现为外在的伦理规范和制度规范。所谓“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中庸》)说明谦逊、礼让、宽容是符合“礼”的要求的,而“礼”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使人际关系协调和睦的手段。封建君臣关系又是等级分明、君尊臣卑的上下级关系,这就要求作为臣子的秘书不仅要谦逊、礼让,更要对君始终怀有敬畏之心,恪守君臣之道,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像杨修、祢衡就是因恃才傲物、言行无状,冒犯了君主,实际是违背了“礼”的要求而丢了性命的。
第四,“智”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思考问题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于秘书来说,“智”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在解决问题的智慧上。辨是非靠的是“仁”、“义”,完成的是对事、对人的评价,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切入点是方法论问题,显现的是个性特点。而在君尊臣卑的等级关系中,秘书工作要收到实效,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智慧了。中国古代秘书往往还兼有史官、谏官的角色,直言犯上,固然能青史留名,但因此而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毕竟,昏君、庸君是多数。象冯谖那样深谋远虑,象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象魏征那样迂回婉转……只有洞悉君主心理,通达人性世故,讲智慧,讲方法,才能最终达成目标。
第五,“信”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的基本道德。对秘书而言,谨守“信”的道德规范,就要做到,在心性的层面,把“正心诚意”作为“修身”的前提;在言语行为层面,努力做到敬事而信、言而有信、诚实笃信。即“言忠信,行笃敬”。作为秘书,从古至今,只有当你被证明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时,你所辅佐和服务的人才会把大事托付给你。唐代魏征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不仅在于他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更因为他对太宗“忠”,对国事“敬”。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要影响。
“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也。”(《孟子·诰子上》)“仁、义、礼、智、信”从道德原则、情感旨趣、行为规范等方面架构起了秘书群体文化心理的基本框架。历代统治者在选拔秘书时,也是把德性品行放在首位。例如汉武帝时期选拔秘书的标准是:“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元典章吏部》记录选拔秘书官吏的标准是:“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计月日多少为优。”
“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文化伦理,在几千年的文化演进中,形成了秘书群体文化心理的基石,对新时代的秘书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在继承中创新,把它与以人为本、大局观念、现代礼仪、商业信用等现代观念结合起来,转变为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思想与职业修养,塑造现代秘书职业精神和职业人格。
二、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是秘书群体实现生命价值的内在动力
中国古代的秘书群体同其他士人一样,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群体。儒学不仅是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包括内在精神的追求和外在躯体的实践两个方面。在道家那里是通过逍遥无为来实现的,而儒家则提倡内圣外王。
儒家把“内圣”作为完善人格的内在规定。“‘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3]具体来说,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基本的道德体系是人超越于自然人之上而成为君子、贤人,乃至圣人的前提。
儒家的理想人格还表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实践人格,即将“真实的关切系于国事民瘼,以匡正社会人生为目的,”[4]在外王事功中实现理想人格。
内圣外王的另一种表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经世济民的事业相统一。夫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这是将君子的社会活动赋予了天命、天道的理论支撑,而孟子更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舍我其谁”的高度。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个体生命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时候,他的内心就获得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纵观古今,中国传统秘书文化的主流昭示的依然是秘书群体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历朝历代的那些冒死直谏、视死如归者彰显的就是这种追求对家国负责的高尚的价值旨归。阿谀奉承、一心为己者毕竟是少数。支撑古代秘书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正是内圣外王的精神动力。其实,即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精神动力机制依然是秘书成长的动力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个人价值只有与社会价值相联系、相统一才会最大限度得到实现。秘书从业者,在发展个性的同时,要把握社会大势,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与奉献社会的共赢。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范式是秘书群体消极心理的根源
分析秘书群体的文化心理,除了上述积极的层面,还存在这一些消极的心理因素,比如唯上思想、法制意识淡薄、缺乏独立人格等。究其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范式有关。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血缘情感、宗法制度之上的文化体系。“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延伸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等级关系。”[5]父子关系延伸为君臣关系,家庭中的孝悌延伸为朝堂上的忠君爱臣,加之宗法制度的渗透,于是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君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为人臣者,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在这样的体制下,形成了唯上唯大、唯命是从的心理态势。历史上当然不乏敢于犯颜直谏的士人,但也有大量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泯灭了独立人格的碌碌之辈。
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表现出重伦理、轻法制,以理代法,道德规范高于法律原则的倾向。长期以来,以儒家的“礼”代替了事实上的“法”,以感性情感统领了严谨的逻辑思维,有“治人”而无“治法”。这样的文化传统再与森严的等级观念和愚忠思想结合起来,把“犯上”和“作乱”相提并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位高就意味着权重,权力大于法律,那么,历史上有那么多阿谀奉承、一心唯上、瞒上欺下的文臣,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伦理范式,对今天的秘书的消极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领导者把秘书视为自己的家奴、仆人、保姆,必须言听计从;有的秘书对领导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唯命是从,甚至溜须拍马,扭曲了领导和秘书的关系,也助长了一些领导者目无法纪、武断专制的作风,有的甚至由此坠入腐败的深渊。有鉴于此,现代秘书,一方面要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范式的合理因素,建立互相尊重的、和谐的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按照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根据现代管理的需要,摒弃其中的糟粕,主动给领导当好参谋助手。在尊重领导的同时,要敢于、善于“直言进谏”,体现现代秘书对事业负责、对法律敬畏、对领导尊重而不盲从的职业品格。
四、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造成秘书群体智能结构的偏向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道德伦理泛化至一切领域,就连自然现象都常被用来论证说明道德规范、政治主张。在治学传统上,也是以经学、史学为主线而展开。人才选拔、教育思想无不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比如学术传统,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都是以经学为主流。又如教育和人才选拔,注重的也是人伦道德标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太宗品评大臣“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断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把科学排斥在外,抑制了科学的独立。
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反映在秘书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表现为智能结构的偏向。在知识背景上,是人文知识优于自然科学知识;在思维方式上,是重感性、轻理性,重整体感知、轻逻辑分析。在古代社会,大多是文人为臣(秘书),事农事工者难以入朝。虽然与整个文化传统有关,但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重治人、轻治事的原因吧。
现代秘书,则应该从这种学术偏向中走出来。在当今时代,科学与人文并重,学科交叉融合,各种知识相互渗透,领导与管理要求科学化和综合。单一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秘书工作的需要。现代秘书要跟上时代要求,既要成为秘书职业的行家里手,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秘书技能;又要成为知识全面的“杂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古今中外的文化常识都应该有所涉猎,用丰富的知识结构支撑立体的多维的思维方式,培养全面的理性的判断能力,成为工作上的多面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履行好秘书职能。
五、官、私两条途径形成了秘书群体一雅一俗、一显一隐两种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的秘书职业从周代始就一直存在着官、私两种形式。所谓“官”,是指食朝廷俸禄,有官职,直接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朝臣,即所谓“公臣”。另一种形式是存在于官僚体制之外的“私臣”,又称为幕友、幕宾、师爷。这种形式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养士之风。著名的四公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再如名士吕不韦,相传其门下食客三千。主人自己出资食养门客,奠定了二者之间的主宾关系。到秦汉时期,除了官方选拔秘书(僚属)的“辟属制度”,在官僚体制之外,则形成了幕友制,即幕主出资聘用幕宾,幕宾为幕主出谋划策,草拟文书,经办具体事务,实际就是充任幕主的私人秘书之职。以后历代,这种体制外的幕友、师爷一直与体制内的官僚秘书同时并存,相辅相成,弥补了官僚体制内秘书人才的不足。直至清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时俗称师爷,而又以绍兴师爷最为有名。
秘书职业的这一“官”一“私”两种形式形成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种文化。官僚秘书大多为中国古代士人中的精英,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如前所述,他们把内修圣贤品德,外致帝王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人格主体上来说,他们追求的是“超我”的实现。而体制外的幕友、师爷们,大多是下层文人,官僚体制的大门毕竟很窄,要挤进去不容易,于是厕身有名望、有权势的官僚,不失为一条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幕主与幕友之间的雇佣关系,使幕友对幕主有较强的人身依附色彩,加之幕友之间的竞争又十分激烈,多重因素作用下,儒家那种殿堂文化逐渐退居其次,市民文化、俗文化因其较强的实用性而逐渐成为主流。例如清代专门培养师爷的“幕馆”,除了传授处理文书文案和官衙日常事务的技能,最主要的就是教士人如何揣摩社会风气,揣度幕主心理,谙熟官场应酬规矩。
幕友、师爷“在辛亥革命后,作为一个群体虽已解体,但其影响却继续存在,与当今千千万万从事辅助领导工作的秘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当代秘书与‘师爷’有承继关系。”[6]幕友文化、师爷文化中俗文化的成分也沉积在秘书文化心理结构中,作为“隐”的部分和主流文化一起共同作用于秘书群体。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秘书,分布范围已十分广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资和私人企业都有秘书岗位的存在。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秘书,本质都不同于古代的公臣和私臣,其表现是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所处的法律道德环境的一致性。作为现代秘书,要按照这种一致性的要求,自觉剔除上述两种文化心理的不良积淀,无论是在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无论是在任何一种性质的单位,都要把服务领导、服务单位的职责延伸到社会,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不能孤立,更不能对立。否则,秘书就会沦为私人工具而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操守。
六、结语
秘书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职业,几千年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秘书群体的情感意志、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无不深深地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对秘书群体心理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构筑了“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规范,形成了“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由此而形成了“秉笔直书”、“忠君爱国”、廉洁自律等等秘书职业道德。当然也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对秘书群体心理形成了消极影响,诸如唯上是从、缺乏个性、庸俗圆滑等等,均可从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觅得踪迹。因此,作为现代秘书从业者,必须厘清传统文化对秘书传统心理结构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成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秘书人才。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41.
[2]葛荣晋.孔子论“仁”及其现代价值[G]//方铭.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首善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世界传播.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3]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22.
[4]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72.
[5] 陈子典.传统道德与现代精神文明[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69.
[6] 钟小安.幕友师爷秘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