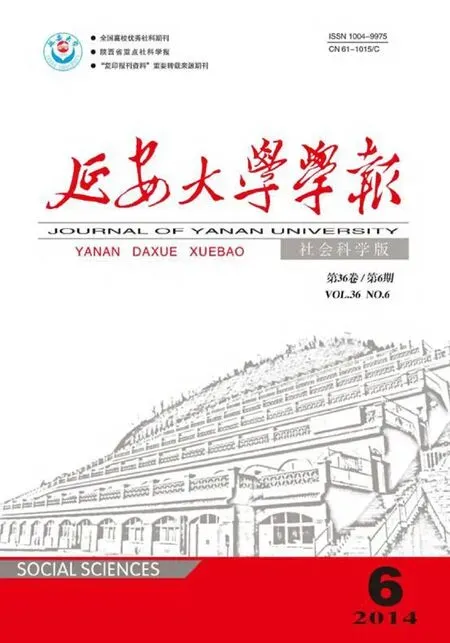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杨 会 敏
(宿迁学院 中文系,江苏 宿迁 223800)
在6世纪中叶新罗真德女王(公元647-653年在位)的五言诗《太平颂》之后,慧超、金乔觉等人的少量作品勉强延续了新罗汉诗的命脉,直到9世纪宾贡及第生们才创作了大量汉诗作品。《太平颂》和宾贡及第生们汉诗之间的统一新罗汉诗作品几近空白的现象,与其说没有专职从事汉诗创作的文人或者说这些文人的汉诗作品未保存下来,还不如说新罗在统一后,在国内实施发展壮大汉诗的奖掖制度直至后期才成效显著。
新罗后期,汉诗才被来唐留学的新罗学子们所崇尚,并形成了一支稳固的汉诗队伍,也由此奠定了朝鲜汉诗正式发展的基础。这些新罗留学生主要是宾贡进士。据党银平先生考证,“宾贡最初仅泛指上古宾荐之礼或外邦朝贡方式,唐穆宗长庆年间以后乃特指入唐游学应试的异域贡士,其进士及第者便称作‘宾贡进士’,以此区别于唐本国进士。唐代并未特设宾贡一科,宾贡进士仅是唐代进士的一种类别称谓,并非科目名称”。[1]高丽著名文人崔瀣(1287—1340)在其《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一文中称,到唐朝灭亡时为止,新罗宾贡进士人数达58人,五代时期又有32人。入唐登第的并且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新罗时期的宾贡及第生们,杰出者首推崔致远(855—?),其后崔匡裕、崔承佑、朴仁范,皆以诗名,以这四人为主要代表的宾贡及第生们可以说是新罗时期汉诗队伍的主体。在本文中,为方便论述,将由崔致远、崔匡裕、崔承佑、朴仁范等为主要代表的新罗宾贡及第生们或新罗宾贡进士所组成的诗人群体简称为宾贡诗人、宾贡诸子或宾贡诗人群。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由宾贡诗人群所引领的汉诗风与其学习接触的晚唐诗风关系紧密。
一、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
从诗歌题材内容来看,新罗宾贡诸子的诗歌具有晚唐诗人的“感伤”格调和底蕴。晚唐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虽然古、今人对晚唐诗歌流派的划分见仁见智,但无论何种流派划分,似乎都不否认以李商隐、温庭筠为核心的“温李诗派”、以贾岛、姚合为核心的“姚贾诗派”以及陆龟蒙、皮日休等皮陆诗人群的诗歌都被蒙上一层哀伤的格调,其思想内容与情感底蕴以“感伤”来概括最为恰切。而宾贡诸子的诗歌不管是感时伤事,还是咏物写景,都带有程度不等的感伤色彩。如果说宾贡诸子所抒写的思乡别离之伤、爱而不得之伤更多地是从生命本体角度透视“感伤”,即个体生命中的遭遇和悲欢离合,具有个体性与偶然性,这类感伤往往由一些纤微、敏感的生命触感所构筑,而不是由一些宏大的、抽象的文化形态所激发出来的共鸣,那么若感伤能超越本体生命的阶段,上升到民族文化层面,这种感伤将更具深度。被派遣的宾贡诸子主要来唐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而唐朝以儒学作为立国之主导思想,对释、道二家也兼收并蓄,在这种跨文化背景下,新罗宾贡诸子的思想也像唐代文人一样自由开放,多出入于儒、道、释之间,但从其人生价值的最核心取向来看,儒家积极用世、关怀现实政治的精神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以儒为主、又杂以佛道的思想构成使其汉诗所表达的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
(一)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
新罗宾贡诸子汉诗的感伤格调中所蕴含的儒化色彩主要体现为强烈的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无论是他们直接抒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情感,还是借古讽今、托物讽喻、感时伤事,或是对晚唐、新罗的昏聩政局的愤慨和直接批判,都是其郁结在心中的难以实现的用世情怀的注脚。
三国时代末期,儒学已传入新罗,并被定为官学。至统一新罗时期,又采取派遣大量留学生入唐朝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文化、在礼部设立主要教授儒家经典著作的国学、制定“读书三品科”的考试选拔制度——以视儒家经典的学业成绩等级作为选拔官员的衡量标准、创制“吏读”法——用本国语言训解儒家经典和其他汉籍等各种重要举措加大儒学传播的范围和力度。甚至许多帝王都亲临国学视察,这更是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学习儒学的激情。由于新罗的统治阶级特别热衷和重视儒学,极大地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
宾贡诸子自幼研习儒家经典,当科举及第、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遭受挫折、难以实现时,报国无门的忧患意识应运而生,这种忧患意识自然在他们的汉诗创作中有所表现。以崔致远为例,他来唐历经六年艰苦的求学生涯后于公元874年在礼部侍郎裴瓒门下科举及第,一举成名,后因黄巢农民起义,长安沦陷,无法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才转投到握有军事大权且又颇有诗名的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下,并受到重用,但也因此招来了其他同僚们的嫉妒和排挤,再加上后期高骈迷信方术,拥兵自重,与崔致远自幼受到的儒家思想相悖,感到绝望后崔致远才选择归国。归国前崔志远写给高骈的《陈情上太尉》一诗表达了其复杂情感:
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
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为身。
客路离愁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
济川幸遇恩波广,愿濯凡缨十载尘。[2]
在回顾自己身为异国人问津无门的境况后,诗人说出了忍受客居他乡的愁苦和对故园的思念,只为光宗耀祖、建功立业,而不为一己之私利,尾联引用“濯缨”的典故感谢高骈的垂青,表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定会坚持高洁的操守。其“迷津懒问从他笑,直道能行要自愚。壮志起来何处说,俗人相对不如无”[2](《辛丑年寄进士吴瞻》)这两句流露出在黑白不分的世道可谓壮志难酬,可以与《陈情上太尉》一诗进行互证式解读。崔致远写给友人的惜别作品中,也不忘匡时济世的志向,如“好把壮心谋后会,广陵风月待衔杯”[2](《酬杨赡秀才送别》)、“荣禄危时未及亲,莫嗟歧路蹔劳身。今朝远别无他语,一片心须不愧人”[2](《酬吴密秀才惜别二绝句》)等。
另外,朴仁范在唐期间作了《上殷员外》、《上冯员外》、《赠田校书》等几首干谒诗。作者极尽全力地美化和赞美对方,甚至有些阿谀奉承之嫌,作为文人,内心应该是非常苦涩。但为了能早日功成名就,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应念风前退飞鹢,不知何路出鸡群”[3](《春日送韦大尉自西川除淮南》),崔承佑将自己比作“鹢鸟”,道出了迫切希望出人头地的远大抱负。
虽然新罗宾贡诸子希望能匡时济世、建功立业,但日益腐败、衰退的晚唐社会却很难提供让其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的不少咏史诗、怀古诗常常借古讽今,感时伤事,希望有所作为的济世情怀可见一斑,如崔致远的咏史诗《汴河怀古》、《熊津公山城诗》等诗。
当然,宾贡诸子另有一些汉诗直接揭露社会弊端。如崔致远的“处处烟尘满战场,年年荆棘侵儒苑”[2](《奉和座主尚书避难过维扬宠示绝句三首》)表现出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晚唐时局极为忧虑。对晚唐上层社会的腐化堕落,崔致远也极为忧愁,《江南女》最具代表性。其实,崔致远选择离唐归国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对政局腐败、奸臣当道的晚唐感到绝望,其诗句“危时端坐恨非夫,争奈生逢恶世途”[2](《辛丑年寄进士吴瞻》)直斥时局危殆、感叹生不逢时,其拳拳的济世之情让人动容。
然而归国后的崔致远面对的新罗也是政治腐败、弊端丛生,其政治抱负仍然难以实现。他再一次陷入痛苦失望的深渊,并写下讽喻名篇《古意》:
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
谁知异物类,幻惑同人形。
变化尚非艰,操心良独难。
欲辨真与伪,愿磨心镜看。[4]
诗人把一些表面上是谦谦君子、实则虚伪狡诈的封建官僚比作狐狸,讽喻了颠倒是非的世态人情。其另一首《寓兴》中的两句“争奈探珠者,轻生入海底。心荣尘易染,心垢正难洗”[3]嘲笑了那些为了得利而不顾生死的封建官僚们,也表现了诗人对这些争权夺利者的极度厌恶和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自惭生地贱,堪恨人弃遗”[4](《蜀葵花》)、“深避鹰鹤投海岛,羡他鸾鸾戏江潭。只将名品齐黄雀,独让衔环意未甘”[2](《归燕吟献太尉》)、“可惜含芳临碧海,谁能移植到朱栏”[2](《杜鹃》)以处在恶劣环境中的蜀葵花、黄雀、杜鹃花自喻生不逢时、处世艰辛的自己。崔致远甚至将自己比作“聚散只凭潮浪簸,高低况被海风吹”[2](《沙汀》)的柔弱无力的沙汀。无独有偶,晚唐诗人罗隐的“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5](《柳》)以柳的特征慨叹借随风飞舞的柳丝,慨叹自己生活漂泊不定,功名未成。而崔致远的似雪花飞舞的沙汀的“聚散”、“高低”全凭“浪潮”和“海风”的随意捉弄,隐喻自己生逢乱世而命运不由自己做主,其诚挚无私的济世情怀溢于言表。
崔致远的《江南女》、《古意》、《寓兴》、《归燕吟献太尉》等讽喻诗不仅蕴蓄着忧念苍生、兼济天下的广阔胸怀,也体现了儒家诗论中的“美刺”思想,即通过“美刺”、“比兴”对社会问题有所美化或有所怨刺,且明显地继承了从《诗经》、《楚辞》而来的优良传统。崔致远不仅用具体诗歌创作践行了儒家的“美刺说”,且将对这一儒家诗教说的理解上升到理论层面。崔致远在《徐州时漙司空》一文中所言“永言有义有礼,惟在知和而和”[4]即继承了《毛诗序》的“止乎礼义”的文艺思想,并进一步引申出了诗歌应“知和而和”的理论主张,其实质是主张诗歌既可“美刺劝惩”,但又不能违背礼义。崔致远对儒家“美刺”思想的接受与创作实践可能直接源于晚唐皮陆诗人群的影响。崔致远与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的晚唐皮陆诗人群中的罗隐、杜荀鹤都有交往:罗隐与崔致远两人相互赠答的诗歌虽未留存下来,但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云:“(致远)始西游时,与江东诗人罗隐相知。隐负才自高,不轻许可人,示致远所制歌诗五轴”,[6]可推测两人之间应该有过一些诗歌交往;而杜荀鹤与崔致远的好友顾云及张乔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为崔杜二人进行直接的诗文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且《东文选》、《全唐诗》中收录了两人的赠答唱和之作。据此,可推测崔致远的讽喻诗创作可能与罗隐、杜荀鹤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经过比较发现,崔致远与罗隐、杜荀鹤等人的讽喻诗具有题材、主题旨趣的相似性,而且大都选择以咏物为主。罗隐继承了杜甫所开创的、经由元稹、白居易等人发扬光大的感时讽世、干预朝政、干预社会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讽喻诗传统,大都选择一些愤世嫉俗的象征性物象,创作了《金钱花》、《牡丹花》、《残花》、《汴河》、《黄河》等具有愤激讥刺意味的咏物类的讽喻诗,极大地拓展了讽喻诗的现实意义。而杜荀鹤也创作了《山中寡妇》、《自叙》、《自述》、《雪》、《蚕妇》、《田翁》等具有强烈地批判现实性的讽喻诗。崔致远与罗隐、杜荀鹤等人的讽喻诗创作对于纠正晚唐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华靡绮丽的诗风具有积极意义。
崔致远创作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色彩和济世精神的讽喻诗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心仪儒家正统的诗教观,非常注重诗歌干预社会政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和功能。崔致远在《幽州李可举大王》一文中曰:“博采圣人之书,用光君子之道”,[4]主张发挥儒家礼乐教化的积极入世作用,用诗文来宣扬儒家思想,这与皮陆诗人群所倡导的诗歌应该具有积极反映社会、干预政治的功能的诗教说是相近的。崔致远在写给中国友人张乔的《和张进士乔村居病中见寄》一诗中曰:“不唯骚雅标新格,能把行藏继古贤”。[4]张乔的诗歌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赞誉,关键一点是它与儒家所推崇的《诗经》风诗、雅诗的社会内容和教化作用及传承了这种现实主义诗歌精神的《楚辞》相吻合。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人也积极提倡《诗经》风雅的精神和传统,要求诗人的创作应该关心政治、关心社会,有益于教化,且与崔致远有交往密切的杜荀鹤、张乔等人也亲身实践这种主张。尽管这种诗教说不是晚唐诗坛主要的诗歌理论,且在创作实践中也未形成主流,但可以推测崔致远的诗歌教化说及其创作实践极有可能是受到杜荀鹤等皮陆诗人群的影响。而让人遗憾的是,皮陆诗人群及受其影响的以崔致远为核心代表的宾贡诗人群的文学倾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大背景有些格格不入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弊政将已经苟延残喘近半个世纪的晚唐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皮陆诗人群有来自新罗的宾贡诗人群体的倾力加盟,但是他们所共同倡导的诗教主张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二)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
虽然匡时济世的儒家入世精神对新罗宾贡诸子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这种信念也驱使他们寒窗苦读数载,但衰落腐败的社会使他们深感壮志难酬、却又不甘心轻易放弃理想,而他们在出国前和出国后所涉猎的道家的离宦退隐、遗世高蹈思想则提供了另一种生命维度。于是,他们徘徊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痛苦中,其诗歌难免带有浓厚的无可奈何的感伤色彩。表现这种意向的典型诗作如崔致远的《赠梓谷兰若独居僧》一诗。另外,崔致远的《泛海》、《山顶危石》、《石上矮松》、《海鸥》、《石峰》、《寓兴》、《和张进士乔村居病中见寄字松年》《和李展长官冬日游山寺》等诗也表现自己想要避开人世间的烦恼和无奈,遗世高蹈之意向。
佛教在朝鲜三国时代已从中国传入并逐渐被接受。在统一新罗时期,上升至国教地位,在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新罗宾贡诸子入唐的晚唐时期,佛教的流传比初盛中唐更为兴盛,参禅礼佛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作为佛教影响的输入国——新罗对佛教的跨文化受容与到佛教影响的输出国——中国的切身体验这两股合力使新罗宾贡诸子顺理成章地选择用佛教思想去化解因壮志未酬而造成的内心的苦闷与伤感。如朴仁范的《径州龙朔寺阁,兼柬云栖上人》:
翚飞仙阁在青冥,月殿垄歌历历听。
灯撼萤光明鸟道,梯回虹影到岩扃。
人随流水何时尽,竹带寒山万古青。
试问是非空色理,百年愁醉坐来醒。[3]
面对“翚飞仙阁”、“月殿垄歌”等美景,不觉感叹人生短暂、万事皆空,而自己又何必太过执着于尘世、计较个人的得失呢?再如其《和金员外赠曦山清上人》:“海畔云庵倚碧螺,远离尘土称僧家。劝君休向巴蕉喻,看取春风撼浪花”[5]一诗中以佛教经典中用来比喻众生躯体之不坚的芭蕉喻应远离尘世的纷扰与喧嚣。另有崔致远的《赠云门寺智光上人》一诗:
云畔构精庐,安静四纪余。
筇无出山步,笔绝入京书。
竹架泉声紧,松灵日影疏。
境高吟不尽,暝目悟真如。[4]
诗人愿像僧人一样隐居深山,静观松竹,凝听泉声,求得心灵的至境,并体悟“真如”。“真如”一词是佛教表示本体的概念,即宇宙事物的真相或本然状态,这显然受到禅宗审美意识的影响。天籁之声、寺庙清净的环境,都容易和某种寂灭意识相合,以便感悟禅意,这也是包括新罗宾贡诗人在内的许多东方来唐学诗者常常追求的至高境界。
二、淡雅明畅为主导的多样化风格
宾贡诗人的诗歌取法多家、不拘一格,总体风格以淡雅明畅为主。为何其主导风格是淡雅明畅?究其原因,崔致远等人入唐留学时,唐朝所出的科诗都是典型的格律诗,这使得崔致远等人没有创作五言、七言古体诗或是大型的组诗,而是创作了以七律、七绝为主的近体诗。据保存最为完整的成均馆大学大同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影印本《崔文昌侯全集》,崔致远诗歌现存诗歌合计100题108首诗。其中,五言古诗仅4首,五言绝句2首,五言律诗5首;近体诗以七绝与七律为主,共计93首,另有其他缺字七言诗4首。相比之下,朴仁范、崔匡裕、崔承祐的诗作保存至今的较少,保存较完整的《东文选》中,其中收录他们创作的七言律诗各10首。宾贡诸子的这一诗体取向,与晚唐大多数诗人相同。比如晚唐主导诗派温李派以七律见长,而皮陆诗人群中的罗隐、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的诗歌也以五言、七言律绝为主。这种体裁上的选择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创作具有奇峭风格的作品。因为大凡奇峭风格的作品篇幅较长,讲排比铺叙,押险韵,喜用偏僻的生字和典故,以逞才为能事。而篇幅短小的近体诗适宜写景抒情,少铺排和夸张,体裁和题材的因素决定了宾贡诗人的创作易形成淡雅明畅的诗风,这一诗风与罗隐、杜荀鹤等人诗风相近。
另外,宾贡诸子的汉诗语言都直白通俗,很少用险僻生硬的字词,喜用叠字,甚至将口语、俗语入诗,通俗易懂。当然,他们也力求诗意新颖,构思新巧,但往往只是语句的新奇,缺乏宏大的气象和格局。崔致远艺术成就和艺术感染力最高的两类诗——思乡诗和写景抒怀诗大都清新自然,语言流畅。兹举佳句如下:“幸得东风已迎路,好花时节到鸡林”[2](《和友人除夜见寄》)、“客路离愁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2](《陈情上太尉》)等。其他诗人也不乏此类佳句,如朴仁范的“清如水镜常无累,馨比兰荪自有春”[3](《赠田校书》)、崔匡裕的“林含落照溪光远,帘卷残秋岳色高”[3](《郊居呈知己》)等。
虽然宾贡诗人汉诗的主导风格是淡雅明畅,但也不乏清健俊丽之作。如崔致远的七律《登润州慈和寺上房》的颔联“画角声中朝暮浪,青山影里古今人”[4]将画角声、古今人分别放置在大海、青山的壮丽背景下,营造出空阔辽远、浑融清劲的诗境,这句诗深得唐人喜爱和传播。另外,朴仁范的“尊前有雪吟京洛,马上无山入塞云”[3](《关中送陈策先辈赴那州幕》)、“人随流水何时尽,竹带寒山万古青”[3](《径州龙朔寺阁,兼柬云栖上人》)等诗句,都写得俊逸清新。
当然,宾贡诸子也不乏气势磅礴、笔法雄劲之作,典型之作如崔致远的两首海景诗:
骤雪翻霜千万重,往来弦望蹑前踪。
见君终日能怀言,渐我趋时尽放牖。
石壁战声飞霹雳,云峰倒影撼芙蓉。
因思宗悫长风语,壮气横生忆卧龙。[4](《潮浪》)
挂席浮沧海,长风万里通。
乘槎思汉使,采药忆秦童。
日月无何外,乾坤太极中。
蓬莱看咫尺,吾且访仙翁。[4](《泛海》)
前者铺天盖地的雪浪、大如霹雳的撞击海岸的鼓浪声、如芙蓉一般美丽的高耸入云的山峰的倒影与宗悫的远大志向、诸葛亮的豪壮气概相映成辉,表现出崔致远的宏大的人生抱负和激昂的入世精神。后者作于诗人归新罗乘船航行于浩淼的大海时。首联从李白《行路难》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7]化出,颈联大有曹操《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8]的恢宏气象。再如崔致远的《石峰》中前两联:“巉岩绝顶欲摩天,海日初开一朵莲。势削不容凡树木,格高唯惹好云烟”,[2]陡峭的岩石迫近高天,海上初升的太阳如白莲花绽放在水中,异常壮丽,山岩陡峭,容不得平凡树木,格调高雅自有蓝天白云相伴,描画的境界高远开阔,不似人间。还有崔匡裕的“红暎蜃楼波吐日,紫笼鳌极岫横霞”[3](《送乡人及第还国》)等诗句也写得雄浑壮阔。
由此可见,宾贡诸子的汉诗创作不拘一格,在淡雅明畅主导的诗风下呈现多元化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古代诗评家们虽然对以崔致远为代表的宾贡诸子所作出的贡献大加赞扬,但批判其将在唐朝学到的晚唐诗风传到新罗诗坛。具有代表性评价如下:李德懋在其《论诗绝句》中曰:“三崔一朴贡科宾,罗代词林只四人。无可奈何夷界夏,零星诗句没精神”,[9]他认为这些主导诗坛的宾贡及第生们所写的诗没有盛中唐的气魄和精神。李奎报在其《白云小说》中也云“然其(笔者按:指崔致远)诗不甚高,岂其入中国,在于晚唐后故欤”?[10]许筠言:“崔孤云学士之诗,在唐末亦郑谷、韩偓之类,率佻浅不厚”,[11]又言“及罗季,孤云学士始大阙誉,以今观之,文菲以萎,诗粗以弱,使在许郑间,亦形其丑,乃欲使盛唐争其工耶”,[11]贬抑崔致远诗像晚唐诗人郑谷、韩偓、许浑之流的诗一样佻浅、粗弱。
以上各家评价都一致把以崔致远为代表的宾贡诗人的诗歌与“气格卑弱”的晚唐诗歌相提并论,其实晚唐诗歌也不能以“气格卑弱”一概论之。虽然与盛中唐诗歌相比,晚唐诗歌的气势和力度削弱,但并不意味着诗歌本身的格调低下纤弱,而主要指诗歌体式更加纤巧精细,这在中国学界已达成共识。可见,朝鲜诗评家们对晚唐诗歌也存在一定的误读,这也导致他们在评价宾贡诗人的诗歌时也有失偏颇。
三、对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艺术技巧的借鉴
从艺术技巧来看,虽然宾贡诗人大都崇尚平易明畅的诗歌风格,所追求的诗歌境界为自然天成、不加雕饰,但他们对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还是有所借鉴的,这也使宾贡诸子的诗歌在力图通俗化的同时也能做到精工雅丽。
温李作为对仗的高手,不仅仅在律诗中间两联使用对仗,且有意识地在诗歌的各个单元——句子、短语、语词之间使用对仗,使对仗成为贯穿全诗的重要手法。这种“泛对仗”现象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当句对”。当句对的手法可追溯到《诗》、骚,温李之前也曾为诗论家所提及,但首次得到普遍运用是肇始于温李。李商隐曾作诗《当句有对》,从诗歌题目来看即为一种自觉的尝试。从这首诗本身来看,每句都有两个词语形成一组对仗,可谓是李商隐使用当句对的一个范例,他的其他诗歌也广泛而自由灵活地使用当句对,且形式多样。
宾贡诗人也热衷于使用当句对。如崔致远的“东飘西转路歧尘”[4](《途中作》)、“秋去春来能守信,暖风凉雨饱相谙”[2](《归燕吟献太尉》)、“繁花压柔枝”[3](《蜀葵花》),朴仁范的“红莲丹桂共芳芬”[3](《关中送陈策先辈赴那州幕》),崔承佑的“纷纷舞袖飘衣举”[3](《邺下和李秀才与镜》),崔匡裕的“白醪红脍虽牵梦”[3](《忆江西旧游,因寄知己》)等。而崔致远的“海内谁怜海外人”[2](《陈情上太尉》)一句中,“海内”、“海外”为有一个字相同的当句对,《文镜秘府论》称之为“双拟对”,李商隐也善用双拟对。这种当句对的优点是工整流畅,具有回环婉转之美。
另外,朴仁范的“祢衡词赋陆机文”[3](《关中送陈策先辈赴那州幕》)、崔承佑的“汉南才子洛川神”[3](《邺下和李秀才与镜》)等句使用了前为四字词组、后为三字词组的对仗(姑且称为“前四后三”式对仗),表面上看起来不对称但却为偏正式名词词组的当句对。最让人称绝的是朴仁范的“芸阁仙郎幕府宾,鹤心松操古诗人”[3](《赠田校书》)一联,上句使用了前四后三式的当句对,而下句“鹤心”、“松操”两两对仗,且“古诗人”又与“芸阁仙郎”、“幕府宾”构成“鼎足对”。所谓“鼎足对”即一句中两个词语形成当句对外,也可与本句或下句的另外一个词语形成对仗,也即三个词语间的“鼎足对”,具有排比连对的雄健气势。
从上述当句对的例子来看,宾贡诸子作诗时同温李派诗人一样,单句之中有对,两句之间成对,全诗内在结构上环环相扣,丝丝入微,给人以工巧密丽之感。
温庭筠、李商隐还有意识地采用了复辞手法,即通过相同字词的重复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典型的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暮秋独游曲江》、《赠司勋杜十三员外》等诗。宾贡诗人中,崔致远所用复辞手法诗句摘录如下:
“窗前三更雨,灯前万里心”[3](《秋夜雨中》)、“不是不知归去好,只缘归去又家贫”[4](《途中作》)、“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为身”[2](《陈情上太尉》)、“既传国信兼家信,不独家荣国亦荣”[4](《行次山阳,续蒙大尉寄赐衣段,令充归觐续寿信物,谨以诗谢》)、“悲莫悲兮儿女事”[4](《酬进士杨赡送别》)。
温庭筠、李商隐的律诗尤其是七律对仗的两联注重用虚字。宾贡诸子中崔致远诗歌所用虚字不胜枚举,不论何种体裁,几乎每首诗歌不离虚字,典型的如七律《汴河怀古》一诗后三联六句都用虚字。另如朴仁范的“志操应将寒竹茂,心源不让玉壶清”[3](《上冯员外》)、崔承佑的“疮痍从此资良药,宵旰终须缓圣君”[3](《春日送韦大尉自西川除淮南》)、崔匡裕的“同离故国君先去,独把空书寄远家”[3](《送乡人及第还国》)等。温庭筠、李商隐运用虚字可谓匠心独运。李商隐步杜甫后尘,善用“自”字。宾贡诗人中朴仁范最喜用“自”字,如“翩翩穷鸟自哀鸣”[3](《上冯员外》)、“馨比兰荪自有春”[3](《赠田校书》),崔致远也有“风暖金陵草自春”[4](《登润州慈和寺上房》)。实字与虚字构成巧妙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诗歌意蕴的传达既要依靠实字的支持,也须有虚字的灵活周旋,实字与虚字的配合,使诗意层层推进又层层递转;另一方面,虚字的运用使诗歌语调轻重相间、起伏不平,吟咏之际,抑扬顿挫、风神摇曳,可谓“虚处传神”。
综上,当句对、复辞、虚字等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得宾贡诸子的诗作产生悠扬婉转、徘徊不尽的美感效果,如果说诗歌语言的表层结构是诗人心理深层结构的外化,那么,这些手法的运用也将这些诗人委婉而细腻的情感世界和深层的心理体验凸现出来了。
晚唐诗人力主用典,温庭筠、李商隐以善用典故著称。在温李诗派主导晚唐诗坛的情形下,作为学作格律诗的新罗宾贡诸子来说,自然要受到这种这种创作手法的影响。
崔致远学习温庭筠、李商隐正典反用,即从人们熟识的典故的反面着笔,类似于咏史诗中的“翻案法”,使诗歌警新明快又余味无穷,常用于诗歌结尾处。如其七律《归燕吟献太尉》最后一联“只将名品齐黄雀,独让衔环意未甘”,[2]“衔环”这一典故出自《后汉书》,喻指报恩,而诗人借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不甘心仅仅像黄雀一样以衔环报恩,还想实现匡时济世的宏愿。另外,其《山顶危石》最后一联:“纵饶蕴玉谁回顾,举世谋身笑卞和”。[2]“卞和泣玉”的典故的寓意为只要坚持真理,终被认识。而诗人借此典故想讽刺有才之人不为所用的世道的浑浊。诗人对典故的反用比正面批判更为沉痛有力。
宾贡诸子还善于学习温庭筠、李商隐将两个典故合并至一处使用,如崔致远的“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3](《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借用春秋时期鲁国的颜回和战国时期鲁国的孟子以明心志,崔匡裕的“拔剑城前独问津,渚边曾遇谢将军”[3](《忆江西旧游,因寄知己》)连用了《论语·微子》中“问津”和《世说新语》中寒士袁宏被谢尚赏识的故事。
在普通名词前加上人命或地名,使其变成专有名词,这是温庭筠、李商隐惯用的一种用典方式,宾贡诸子也化为己用。如崔致远《海鸥》中“漆园蝴蝶梦”、[2]《石上矮松》中“栋梁堪入晏婴家”[2],朴仁范的“孔明筹策惠连诗”[3](《上殷员外》)、“陆家词赋”[3](《上冯员外》)、“祢衡词赋陆机文”[3](《关中送陈策先辈赴那州幕》)等。
当然,还有直接从神话传说、典籍或成语中化用典故,兹不举例。相比较而言,宾贡诸子能根据所表达内容和感情的需要,恰切自然地用典,将心中复杂的心理通过典故表现得简练又透辟,而温李诗人则将情思熔铸在典故中,使诗意显得曲折深婉、似是而非,乃至隐晦、生僻难解。
总而言之,宾贡诸子对温李诗人的受容集中表现在格律诗的对仗、声律、用典、用字等语言形式技巧层面上。其实,这些创作技巧可用“以骈文为诗”一语来概括,因为骈文形式整齐华美,讲究对仗、声律、用典、辞藻。而温庭筠、李商隐作为骈文大家,他们将骈文的特长移置于诗,便形成了“以骈文为诗”的独特现象。如前述的当句对、特别是七言律句前四字的当句对,本身就类似于骈文中的四字句。至于正典反用、两个典故甚至多典连用等用典方式,更是鲜见于骈文。温庭筠、李商隐致力于语言形式的精雕细琢,可以说是“以骈文为诗”。宾贡诸子的诗歌创作技巧除了受到温李诗人的“以骈文为诗”的影响外,还与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好的教材和诗文集范本——《文选》有密切关系,“在朝鲜,在盛唐诗文和宋代欧苏传入并被消化、模仿之前,文选体——以美句骈俪为特色的六朝文风一直在这里居统治地位,长盛不衰”。[12]以崔致远为例,从古代朝鲜至现代韩国,不少评论家指出其文章具有六朝的绮丽:如成伣在其《慵斋丛话》曰:“我国文章始发挥于崔致远,虽能诗句而艺不精,虽工四六而语不整”;[13]而现代一些著名的韩国学者也沿袭了这一观点,如金台俊先生言:“他的文风极具六朝时代的绮丽而少有盛唐的雄伟”,[12]另外李家源先生也称:“其文风却未脱六朝绮丽之四六体”。[14]可见,宾贡诸子极容易像温庭筠、李商隐一样将六朝文风化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由此我们明白为何从朝鲜古代诗评家成伣直至近现代诗评家们都用“六朝绮丽”来概括崔致远的文风、诗风,实质上就是针对其语言形式风格而论的,而不是针对其思想内容的。因为崔致远并没有沿袭六朝乃至晚唐描写男女情爱的艳情诗题材。由此我们也明白,前述的诗评家们将宾贡诸子的诗歌与“气格卑弱”的晚唐诗歌一起批判,实际上主要针对其精细雕琢的语言形式,这一批评对于刚刚学习近体诗的宾贡诸子们来说有些苛刻。因为对这些技巧的掌握是步入近体诗艺术殿堂的必经之路。而宾贡诗人对温李派诗歌主要表现内容——着重表现的不是具体的事件或明确的情感,往往是个人内心世界隐约幽微的复杂情感,而这一点也是造成温李诗朦胧深婉的诗境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也看出宾贡诸子借温李诗歌外在语言形式表达特有的思想内质,继而形成不同诗境的创新之处。
四、结语
综上,统一新罗时期的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具有浓郁的“感伤”格调与思想意蕴,不论是他们直接抒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情感,还是借古讽今、托物讽喻、感时伤事,或是对晚唐、新罗的昏聩政局的愤慨和直接批判,都表达了其郁结在心中的难以实现的儒家用世情怀。尤为可贵的是,他们不受晚唐空洞绮靡的主流的文学环境的羁绊,继承了儒家以诗文积极干预社会、反映现实的文学传统,创作了不少讽喻现实且充溢着济世之志的作品,即使后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魏阙之想而转向佛道去化解心灵之痛,也都是因昏暗时政而哀、因壮志未酬而伤的一种延续。在艺术风格上,宾贡诗人的诗歌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在艺术技巧上,他们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这也使宾贡诸子的诗歌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1] 党银平.唐代有无“宾贡科”新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1):157.
[2] [朝鲜]崔致远.崔文昌侯全集[M].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2.403,208,208,404,403,208,403,404,404,405,403,404,403,403,403,403,404,404,405.
[3] [朝鲜]徐居正,等.东文选[Z].汉城:太学社,1975.569,588,568,568,568,569,568,566,588,569,570,570,569,570,568,664,569,569,566,569,568,665,570,568,569,569.
[4] [朝鲜]崔致远.韩国文集丛刊(1)[Z].汉城:景仁文化社,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150,150,41,44,152,151,152,126,152,151,151,125,126,152.
[5]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7553,127.
[6]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十六·列传第六·崔致远传[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528.
[7] 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5.
[8] 孙明君.三曹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
[9] [朝鲜]李德懋.韩国文集丛刊(257)[Z].汉城:景仁文化社,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190.
[10] [韩]赵钟业.韩国诗话丛编[Z].汉城:太学社,2000.17.
[11] [朝鲜]许筠.韩国文集丛刊(74)[Z].汉城:景仁文化社,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357,226.
[12] [韩]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M].张琏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24,35.
[13] [朝鲜]成伣.慵斋丛话[Z].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71.1.
[14] [韩]李家源.韩国汉文学史[M].赵季,刘畅,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