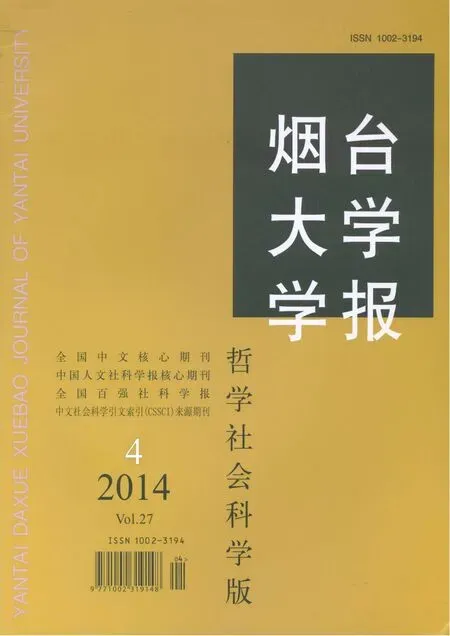对“认识的另一半”的开拓性研究
——《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读后感
叶峻
对“认识的另一半”的开拓性研究
——《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读后感
叶峻
人的认识本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认识方式的有机结合,但我们以往的认识论研究因受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往往只注重研究人的理性思维和理性认识能力,而不提及甚至也不敢提及非理性认识问题。若有人提出尚需认真地研究非理性认识的话,则会被误解或曲解为是在提倡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想主义而妄加指责。这种在理论上的极“左”思潮,曾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在认识论方面的理论探索,也严重地阻碍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若不彻底纠正,将会使我们在实践中重蹈历史覆辙,犯与以往相同的错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我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承担起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应当认真地去研究过去被遗忘了的非理性认识论问题。使我们的认识论研究逐步深化,使我们的认识论能够日臻全面、系统、完整、科学。基于上述,为了拓展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浩研究员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写出了《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这部长达57万余言的学术专著。
在认真地拜读了这部著作之后,我觉得作者对非理性认识论的探索是积极的、有效的,它填补了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空白。该书打破了近些年来认识论研究方面的沉寂,并为认识论研究的复兴提供了一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颇具新意,现仅撮要如下:
首先,它深刻地剖析了理性认识的局限性,阐明了研究非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作者在充分肯定理性认识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作用的前提下,同时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理性认识所把握的只是事物的共性、普遍性和统一性,而忽视了事物的个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它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同时,在进行判断和推理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概念的歧义而产生错误,一旦前提有误,不管推理是否合乎逻辑,都会推导出谬误。“它忽略了事物的可变性和历史性,如在进化论产生之前,人们根据既有的认识,就不相信猴子会变成人。”表现在一定的认识结构或思维模式的消极作用中。一定的认识结构是在以往认识过程中形成的逻辑结构内化、沉淀和凝结成的心理结构,它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然而,人们在认识问题时,往往会被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所左右,以旧思路去思考新问题,从而陷入思维定式的陷阱。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非理性认识论呢?作者认为,这是时代的呼唤。因为任何哲学思潮的形成,都不是某些天才哲学家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作者看来,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后,使人变成了抽象理性动物。这种全智全能的理性必然产生独断论,引发了诸多社会弊病。非理性主义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思,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新觉醒。对非理性问题的全面探索,是对主体认识结构和认识能力研究的深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相对的,不完善的。这就彻底打破了以往的科学神话。非线性科学的创立,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原有的观念。它必然会在更深层次上审视人们的思维认识能力,变革着人们的思维认识形式。研究非理性认识,是知识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因为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特征,从方法论视角看,就是人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而这些都属于非理性认识论研究的范围。
其次,我认为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对非理性认识论作了系统的建构,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作者认为,人们要想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首先就应该去寻找人类认识的原始动因及认识选择性的客观依据。为此,只有到主体自身的欲望、需要、情绪、情感、兴趣、爱好等非理性认识的基本要素中去寻找。而人的认识和实践成功与否,又和人的理想、信念、意志等非理性或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诸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再则,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文学艺术的创作,也离不开联想、想象、直觉、灵感、顿悟和潜意识这些非理性的认识形式。鉴于此,作者在该书中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非理性要素、非理性认识的主要形式、非理性认识形成的主客观基础、非理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非理性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非理性认识与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中的非理性认识问题,从而把我们的认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三,深刻地阐明了理性认识与非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上世纪90年代的非理性认识论研究,对理性与非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一般认为是理性因素在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非理性只起辅助性的作用。该书作者对这一观点有了更深刻的新的理解和把握。他认为理性和非理性认识是互为主导的,“因为在现实的认识活动中,由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不同,由于每个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差异,在人们的每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中,确实是非理性和理性各有侧重、互为主导的。”(第297页)该书作者还认为,非理性认识可以向理性认识跃迁,理性认识也可以向非理性认识沉淀。并用大量的事实证实了这一观点。很显然,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无论在深度还是在材料的充实性上,该书都具有很大的新进展。作者在非理性认识论研究的深度上的挖掘,还有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或创见。比如,他明确指出:“潜意识是人犯错误的根源之一”(第294页)、“诡辩是以理性形式出现的非理性认识”(第297页)、“把理性绝对化必然走向非理性”(第286页)等等。
其四,该书在非理性认识论研究上的新进展,突出地表现在其拓展了非理性认识论研究的诸多领域。以往的非理性认识论研究,主要是探讨非理性因素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个传统认识过程和认识阶段中的作用。该书不但在这一传统认识过程、认识阶段和认识类型的意义上论述了非理性认识的作用,而且把非理性认识作用扩展到网络时代和虚拟世界,探讨了虚拟实践和虚拟认识;扩展到决策认识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和日常认识。此外,作者在该书中不只分析了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也分析了非理性因素在实践中的作用,探讨了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多种功能。这些都足以说明,同以往非理性认识研究相比,在研究领域上有了更广的拓展。
总之,我认为在当前认识论研究处于低谷和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作者能拿出这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是难能可贵的。它对推动我们的认识论研究,特别是非理性认识论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学术界关注。当然,对非理性认识论的研究正像人的认识本身一样永无止境,就非理性认识论研究来说,还有许多突破口值得学者们去认真研究。比如文化和价值、资本和市场、民生和幸福等领域中的非理性与非理性认识,或许就是非理性认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甚至可能是非理性认识论乃至整个认识论大有作为和大显身手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