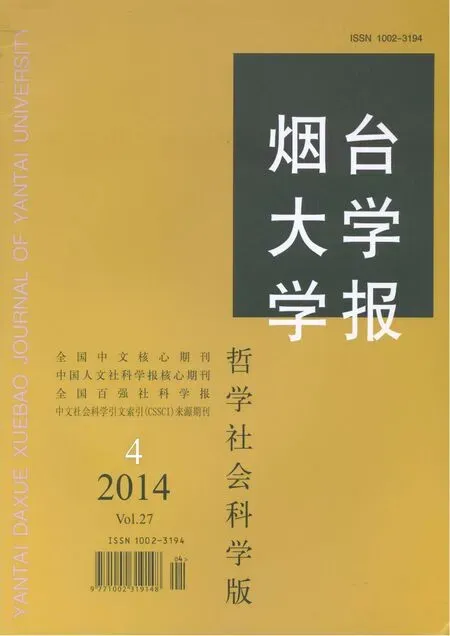东汉的私谥问题
沈刚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12)
东汉的私谥问题
沈刚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12)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东汉;私谥;士人;儒学
谥法是统治者对特定群体死后给予的称号,用以总结其一生之行状。这一制度发端于先秦,到汉代发展完善,皇帝、诸侯王、列侯均有资格获得谥号,并且在谥号的名称、授予程序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东汉时期,因为时局变动、士风转变等,在公谥之外,还出现了私谥,即私人加赠谥号。①汪受宽先生界定私谥的概念为:除正式可称为天子的朝廷赐给的谥号,其他一切给谥都是私谥。参看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对于谥法中的这一特殊现象早已为人所注意。在石刻文献中屡屡出现私谥现象,所以最早金石学家就此曾有议论,如洪适云:“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词,谥之曰元儒先生,犹陈寔之文范,法真之元德也。《隶释》又有忠惠父鲁峻碑,亦非谥于朝者。群下私相谥,非古也。未(末)流之弊,故更相标榜,三君八顾之目,纷然而奇祸作矣。”②《玄儒先生娄寿碑》,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页。明郭宗昌《金石史》:“古者生无爵,则死无谥,而谥法作自周公,私谥昉于春秋,汉末尚节义,故尚不废,苻秦既已非古,犹谥及隐逸,唐朝臣尚加山林之号,……”③郭宗昌《金石史》,转引自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651页。这些都是对私谥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评价。另外一些经学家和礼学家也从这个角度对私谥予以置评。④汪受宽先生曾对自汉至清的私谥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可参看汪受宽:《谥法研究》第八章《私谥》,第206页。现代学者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余英时先生从东汉士阶层的分化角度来观察私谥这一特殊现象。①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汪受宽先生则在《谥法研究》一书中列出《私谥》专章,从私谥的定义、对象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近年,徐国荣、盖金伟、何如月诸先生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②徐国荣:《汉末私谥和曹操碑禁的文化意义》,《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盖金伟:《汉唐“私谥”文化简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这些成果显然为认识东汉的私谥问题提供了帮助。本文在此基础上,重新检核相关史料,以补前贤所未及之处。
一、私谥对象的身份
公谥是国家针对特定对象而赠予的谥号。与此相对,私谥发生于民间,其赠予的对象也应很庞杂。不过,在东汉时代关于私谥有限的记载中,我们发现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汪受宽先生曾将中国古代的私谥对象分为造诣高深的学者、隐逸之士、德高望重的地方贤达、忠义节烈之士、孝悌子弟、贞洁妇女等六类,③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08-212页。其中前三类与东汉私谥相关。不过,如果针对东汉的具体情况,从仕与隐的角度观察更能体现出时代特点。
一是隐逸之人,这类情况所占比例最大。《玄儒先生娄寿碑》称,娄寿:“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霭,遁世无闷,……郡县礼请,终不回顾,高位厚禄,固不动心。”④洪适:《隶释·隶续》,第103页。这在叙述娄寿生平时,说明他亦是未曾步入仕途的处士。另外还有李休,对于郡守、司空的屡次辟召,却“辞此三命”;⑤严可均:《全后汉文》卷75《玄文先生李休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81页。另一位谥主杨厚更是多次推辞了三公的征召,甚至是皇太后的礼聘。据《后汉书》卷30上《杨厚传》:“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车特征,皆不就。……本初元年,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⑥史籍记载还有:荀靖,“靖有至行,不仕。”(《后汉书》卷62《荀爽传》)法真“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后汉书》卷83《逸民法真传》)蔡邕之父棱,“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发,人爵不升”。(《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李贤注引《蔡携碑》)众多的隐士、逸民被私自赠予谥号,与东汉时期推崇隐逸成风有一定关系。《后汉书》卷83《逸民传》序曰:“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皇帝如此重视,加之这一行为亦被视作耿介守志之举,因而为士林所推誉。
二是去官或致仕者。范丹,曾“以处士举孝廉,除郎中,莱芜长,未出京师,丧母行服,故事,服阕后还郎中……辟太尉府”,后“太尉张公、司徒崔公、前后四辟,皆不就”。⑦严可均:《全后汉文》卷77《范丹碑》,第891页。鲁峻则有更丰富的任职经历,据《司隶校尉鲁峻碑》:“始仕,佐职牧守,……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丞,丧父如礼,辟司徒府,举高第侍御史,东郡顿丘令,视事四年……以公事去官,……为司空王畅所举,征拜议郎、太尉长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隶校尉,……遭母忧自乞,拜议郎,服竟,还拜屯骑校尉,以病逊位”。⑧洪适:《隶释·隶续》,第101页。又如陈寔,曾为太丘长,但自罹党锢之祸后,“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不过,这些去官者多与党锢有关,有明确记载的除陈寔外,范丹也曾“用受禁锢。君罹其罪,闭门静居,……乃鬻卦于梁宋之域”。⑨严可均:《全后汉文》卷77《范丹碑》,第891页。此外,司徒掾梁休“光禄主(缺)昭德塞违,(下缺)光翳燿,隐身殉道,隘穷不闷,……禁防既释,辟司徒府”,一度也仕途中断。所谓“禁防既释”,洪适解释为“其云禁防既释,则钩党也。又有韬光翳耀,隐身殉道,隘穷不闷之句。铭则云遐罻罔退潜伏,皆谓党事”。(10)《司徒掾梁休碑》,洪适:《隶释·隶续》,第297页。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士阶层与宦官集团斗争的标志性事件,参与到此事件中的儒家士人被士林尊崇,所以身后被加私谥也在情理之中。
三是在任官吏。卫尉衡方,“仕郡辟州,举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胶东令,……州举尤异,迁会稽东部都尉,……扎服祥除,征拜议郎,右北平太守,……迁颍川太守,……征拜议郎,迁太医令,京兆尹,……本朝录功,入登卫(缺二字),……建宁初政,朝用旧臣,留拜步兵校尉”。①《卫尉衡方碑》,洪适:《隶释·隶续》,第90页。夏恭,“王莽末,盗贼从横,攻没郡县,恭以恩信为众所附,拥兵固守。独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迁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欢心”。②《后汉书》卷80上《文苑夏恭传》,第2610页。这些在任官吏之所以有机会获得私谥,也和其行善政关系颇大,除了夏恭“和集百姓,甚得其欢心”外,衡方任颍川太守也“修清涤俗,招拔隐逸,光大茅茹”。
不过,这些官吏无论在朝在野,他们皆通晓儒术。相关的碑传在叙其生平时,也多有此类记载:
法真,“体兼四业”,李贤注曰:“谓《诗》、《书》、《礼》、《乐》也。”③《后汉书》卷83《逸民法真传》,第2774页。
陈寔,“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④《后汉书》卷62《陈寔传》,第2065页。
范冉(丹),“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⑤《后汉书》卷81《独行范冉传》,第2688页。
朱颉,“修儒术”。⑥《后汉书》卷43《朱穆传》,第1461页。
张霸,“七岁通《春秋》,……后就长水校尉樊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⑦《后汉书》卷36《张霸传》,第1241页。
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⑧《后汉书》卷80上《文苑夏恭传》,第2610页。
李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详纬”。⑨严可均:《全后汉文》卷75《玄文先生李休碑》,第881页。
娄寿,“捥发传业,好学不厌”。按:所谓传业,当为其家学,碑云“曾祖父攸《春秋》以大夫侍讲,至五官中郎将,祖父太常博士,征朱雀司马”。(10)《玄儒先生娄寿碑》,洪适:《隶释·隶续》,第103页。
衡方,“耽《诗》悦《书》”。(11)《卫尉衡方碑》,洪适:《隶释·隶续》,第90页。
鲁峻,“治鲁《诗》,兼通《颜氏春秋》,博览群书,无物不刊,学为儒宗,行为士表”。(12)《司隶校尉鲁峻碑》,洪适:《隶释·隶续》,第101页。
以上这些记载,显示出这些人或传家学,或受业名师,或游于太学,或兼通数经,都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精通儒学,以至于“学为儒宗,行为士表”,成为儒生的典范。而谥法是儒家用以正名的重要手段,因而他们死后获得赠谥自然是对这一群体表达敬意的合适方式,如《卫尉衡方碑》所言“谥以旌德,铭以勒勋”,即赠谥和勒石做铭一样,都是死后昭显德行的必要形式。
二、命谥者、给谥程序与谥号
公谥是由国家按照一定程序来命名的,其命谥者是汉代国家政权。私谥不在国家谥法范围内,所以命谥者也来源于民间,通常认为它是由门生故吏为其业师或府主赠谥,比如范晔在《后汉书》中说:“时人多不行妻服,虽在亲忧犹有吊丧疾者,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13)《后汉书》卷62《荀爽传》,第2057页。周天游先生也指出了这一规律:“东汉中期起,门阀世族开始形成。由于名节道德观的确立,以及荣辱与共的政治利害关系,门生故吏对举主座师,莫不竭诚相报,虽死不辞。其形式繁杂,私谥即其一。”①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01页。这一规律固然不错,并且也有实例予以支持,如:鲁峻死后,“于是门生汝南干(缺)沛国丁直、魏郡马萌、勃海吕图、任城吴盛、陈留诚屯、东郡夏侯弘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子夏之徒,作谥宣尼君,事帝则忠,临民则惠,乃昭告神明,谥君曰忠惠”。②《司隶校尉鲁峻碑》,洪适:《隶释·隶续》,第101页。王稚死后,“门人录其本行,谥曰宪父”。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751页。在门生故吏和其业师府主之间依附关系日益强化的东汉时代,将私谥发生的场域设定在此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我们重新排比这些史料,发现除上述情况外,命谥者最多者为官吏。首先是获谥者籍贯所在地的郡县长吏。如《后汉书》卷62《荀爽传》李贤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荀靖“及卒,学士惜之,诔靖者二十六人。颍阴令丘祯追号靖曰玄行先生”。荀靖为颍川颍阴人,故当地县令为其赠谥。又李休死后,“时令戴君,临丧命谥,郡遣丞掾,冠盖咸至,既定而后罢焉”。④严可均:《全后汉文》卷75《玄文先生李休碑》,第881页。所谓“时令”,大约就是指时任李休所在县之令。能够命谥的长吏还有郡太守,如《司徒掾梁休碑》:“太守安平赵府君,嘉厥高藐(下阙)尼父之美,宋叔三命之伐,存有立名,死宜见旌,(下阙)守节曰贞,博闻曰文。请谥休为贞文子。”洪适云:“郡将至于累行论谥,宜不在夏恭、范丹之下。”⑤洪适:《隶释·隶续》,第297页。称郡将者,在汉代文献常和他所管辖地域联系在一起,如东汉会稽郡,“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⑥《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第1397页。赵府君自然就是梁休所在郡之太守。还有郡守、县令等同时参与命谥。范丹为陈留外黄人,“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张公、兖州刘君,陈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刘君,佥有休命,使诸儒参案典礼,作诔着谥,曰贞节先生。”⑦严可均:《全后汉文》卷77《范丹碑》,第891页。地方官吏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对辖境内声望卓著的儒生命谥,以示尊崇儒学、尊敬乡望,在东汉社会推崇名士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达到稳定地方统治的作用。另外,兖州刘君不清楚为何人。太尉张公,即张延,中平二年为太尉。张延之所以参与对范丹命谥,是因为“太尉张公、司徒崔公,前后四辟”,也就是说三公曾经辟举过,即使没有就任,二者也可形成人际结合关系。
不仅如此,范丹被命谥还有外戚何进参与的背景。《后汉书》卷81有《独行范冉传》,据本传李贤注:“冉”或作“丹”。并且范冉的字、籍贯、行状与《范丹碑》完全相同,因而可以肯定二者为一人,《范冉传》在记述这件事时说:“于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吊。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李贤注:“《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好廉自克曰节’也。会葬者二千余人,刺史郡守各为立碑表墓焉。”也就是说,范丹被地方长吏命谥,是何进的意旨。不仅如此,何进还遣自己的属吏为人命谥,据《后汉书》卷62《陈寔传》:“(陈寔)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根据李贤注引《先贤行状》曰:“将军何进遣官属吊祠为谥。”也就是说,命谥是何进的个人行为。何进之所以给二人命以私谥,因为二人在当时为士林所推重,陈寔为当时名士,范丹亦为李固之知己。⑧《后汉书》本传曰:“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外戚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常有合流之事,一方面,二者有共同的敌人——宦官,而且,外戚有时亦兼具士大夫之身份。士大夫并不完全排斥外戚集团。就何进而言,尽管他和士人的结合不能和窦武同日而语,但也可以“以一时利害相结合”。①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第291页。
另外,还有一类命谥者,称为国人、乡人。如娄寿“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禄,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谥”。国人虽然在传世文献中找不到合适的解释,但从娄寿碑阴题名看,除籍属南郡和汝南两人书写籍贯外,其余皆无籍贯,洪适认为“余盖南阳人也”。②《玄儒先生娄寿碑》,洪适:《隶释·隶续》,第103页。乡人,从字面理解,似为乡党之辈,如杨厚,“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③《后汉书》卷30上《杨厚传》,第1050页。然而这其中也有上述地方长吏和门生参与的身影,虽然是乡人命谥,然而却有门人立庙,郡属吏祠祀,说明虽由乡党命谥,但和门生、地方长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娄寿材料记载简略,或可视为隐而未彰。
为了显示私谥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赠予原则也模仿国家公谥。首先要总结其一生行状,如前揭王稚:“门人录其本行,谥曰宪父。”范丹,“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所谓“累行”,指平素所为,如《淮南子·齐俗训》有“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虽然这徒具形式,只有善谥,无恶谥,但至少在程序上和公谥保持一致。其次,要依据礼书经典给予谥号,朱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④《后汉书》卷33《朱穆传》,第1473页。所谓“考依古义”,同样的意思在东汉石刻文献中称为“按典考论”“参案典礼”。这些古义、典礼等表示的都是谥法中的经典。据汪受宽先生研究,汉代所用谥法经典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谥法解》,他说:“西汉以后,《谥法解》为历朝礼官所珍藏,作为议谥的依据。”⑤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29页。唐宋人也认为如此,如“贞宣先生”一词,《后汉书》卷33《朱穆传》李贤注《谥法》曰:“清白守节曰贞,善闻周达曰宣。”这正是《逸周书谥法解》的内容,同样的还有“贞节先生”“贞定先生”等,皆是如此,即对于死前未仕者多用“贞”字。另外还有不见于《谥法解》的谥法,如“及(朱)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所谓“文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曰:“蔡邕议曰:‘鲁季文子,君子以为忠,而谥曰文子。又传曰:忠,文之实也。忠以为实,文以彰之。’遂共谥穆。”文忠之称,引自《国语·周语下》,这是据事给谥,在《左传》中有很多例子。又如鲁峻被谥为忠惠,是因为其门生认为“事帝则忠,临民则惠,乃昭告神明,谥君曰忠惠”,⑥《司隶校尉鲁峻碑》,洪适:《隶释·隶续》,第101页。也可作如是观。这些虽然不是来源于东汉官方所用之《谥法》,但亦有古例可循,当可看做“考依古义”的另一种形式。但无论是何种方式,都和儒家经典密切相关。⑦据汪受宽先生考证,儒家经典《大戴礼记》中之《谥法》袭自《逸周书谥法解》,参看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23-234页。所以在议谥法时,多有儒生参与,比如夏恭,“诸儒共谥曰宣明君”;在范丹卒后,太尉张延等“使诸儒参案典礼,作诔著谥,曰贞节先生”。让儒生定谥,亦有保证所谥符合礼典的意味在内。
在公谥中,谥号赠与都遵守一定的程序,所以有规律可循,臣下只有王、侯有谥号,所以称其身份时为谥号+王或侯。但私谥的谥主身份庞杂,显然无法整齐划一排列,且无成例可循。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从仕隐角度将谥主的身份和谥号等联系起来,列制表格,隐约显示出一定的规律。
通过下文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如果谥主在死前已经归隐不仕,那么他被称为“先生”,这其中的含义,清人郑学业曾有一段话解释:
《檀弓》:“鲁哀公诔孔子曰:呜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为之谥。”疏:“尼则谥也。”《蔡中郎集》:“有朱公叔谥议云:‘本谥曰忠文子。案古之以子配谥者、皆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与诸侯并,故以公配。府君,王室亚卿也。曰公犹可,若称子,则降等多矣。惧礼废日久,将诡时听。周有中山甫,伯阳嘉父,优老之称也。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可于公父之中,择一处焉。’据此则碑所云‘忠惠父’者,谥而系之以
‘父’,当时所谓尊崇之至矣。”①郑学业:《都笑斋金石文考》,转引自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54页。
先生是儒家对业师的尊称,如《论语为政》:“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不仕之人,常门徒众多,有门生给上谥号,故称先生。

私谥谥号与仕隐关系表
而谥主死前为在任官员,则称为“子”“君”,或不具名。称“子”,按上引《蔡中郎集》所言,其根据是“古之以子配谥者、皆诸侯之臣也”。称君,按照先秦礼书,有地者皆可称“君”,《仪礼丧服传》:“天子、诸侯及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夏恭“再迁太山都尉”,宰治一方,诸儒况之古义,以“君”作为其身份的代称。这些名词的混称是因为儒生所凭借的儒家经典各不相同,同时礼书中的制度对于私谥这种特殊情况,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明。从身份角度所显示出的这种两分规律尽管没有明文指示,可儒生要以礼制建设为己任,那么这其中自然也不会草率从事,要遵循一定的规矩。
三、私谥形成原因
一般认为,东汉后期私谥的流行与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斗争密切相关,是政局混乱之下的产物,如汪受宽先生说:“(东汉后期),幼帝即位者多,实权掌握在外戚、宦官手中,朝政黑暗,社会混乱,由此造成了功臣们功成名就即隐退山林,以保持名节避除祸患,一般士人则隐居丘壑,待价而沽,或羞与宦官为伍。这种背景,造成了东汉宗室外戚得谥者多,宦官也开始给谥,而文武大臣却很少得谥,私谥重新流行。”①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8页。余英时先生从私谥所反映的业师弟子之关系角度看待:“从私谥之事可推知当时士大夫群体自觉之观念并不限于与其他社会集团之相区别之士大夫集团一层,而已进而发展为内在之分化。盖门生弟子既推尊其师,则群体之自觉亦必存在于各家之间,可不待论矣!”②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第300页。也就是说,私谥和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分化是互为表里的。这些固然是不易之论。然而,如果我们将私谥问题作为考察的焦点时,还应发掘出更多的背景。
首先是汉代谥法本身封闭、刻板的制度性缺陷和东汉混乱政局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如汪受宽先生所说,东汉宗室、外戚、宦官得谥者多、大臣却很少得谥。确切地说,是士大夫群体得谥者少。其中的机制在于汉代给谥资格是诸侯王和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等。《续汉书礼仪志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大鸿胪奏谥,天子使者赠璧帛,载日命谥如礼。”③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52页。东汉只有宗室近亲才有资格分封为诸侯王。其他人能够得谥,只有封侯一途。而东汉中后期却是外戚宦官专权的时代,他们以此为基础,获得了封侯的机会,特别是宦者封侯,始于东汉郑众,他因诛窦宪,“遂享分土之封”,延熹二年更是一日封宦官五侯。④《后汉书》卷78《宦者传》,第2520页。这样他们就因侯爵身份而顺理成章的获得谥号。而东汉时期少有像西汉时期对匈奴那样的大规模战争,造成普通的士大夫“人爵不升”,很难获得封侯的机会,自然就得不到国家谥法的眷顾。但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士大夫,却对身后留名非常重视,所谓“昭其功行,录记所履,著于耆旧,刊石树铭,光示来世。”⑤严可均:《全后汉文》卷77《范丹碑》,第891页。因而通过私谥的方式,在旧的制度框架内寻求同样的结果,并且也能显示出其与宦官集团区别。官方谥法流于形式,也是造成私谥盛行的制度因素,清人朱彝尊曾论曰:“易名之典,礼官主之,太常博士议之,廷臣得以駮正之。其后但请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谥,失制谥之本矣。”⑥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卷二,转引自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65页。
其次,和东汉士人分外重视声誉的氛围相关。一方面东汉时期选举制度和乡里清议有密切关系,唐长孺先生谈及此时名士主持乡里清议情况时说:“人伦臧否本是当时名士专业之一,名士清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臧否人物,像汝南那样有组织的每月升降品题虽然不见他郡,但诸郡通常由名士主持乡里清议,品题人物是无疑的。”⑦唐长孺:《东汉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这种对关系士人切身利益的仕进与清议密切相关,自然会为士人所关注。另一方面,东汉桓灵以后,士风转变,范晔在《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中有一段很准确的总结:“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也就意味着士大夫对在朝在野之人皆予以题拂品核。在这种风气之下,作为总结人一生功过的私谥自然会被重视起来。《后汉书》卷43《朱穆传》李贤注引张璠论曰:“夫谥者,上之所赠,非下之所造,故颜、闵至德,不闻有谥。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议之。”我们对私谥发生大致时间可考者进行统计,共有15例,其中有12例是在桓帝以后(公元147年以后)。
再次,私谥在东汉后期兴盛,也是西汉末期士族势力发展的结果。余英时先生说:“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的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强宗大族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大家族的财势。这二方面在多数情形下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①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载《士与中国文化》,第220、222页。我们从私谥者的身份看,亦多为士族,如朱穆祖父朱晖“家世衣冠”。②《后汉书》卷43《朱晖传》,第1457页。荀靖父荀淑,“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③《后汉书》卷62《荀淑传》,第2049页。是皆以宗族相交接。即使未仕之处士,他们亦有宗族作为社会基础。娄寿未尝出仕,碑文称“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谥”,然而据宋人洪适统计的碑阴题名54人里,“其间姓娄之可见者十有二人”。④《玄儒先生娄寿碑》,洪适:《隶释·隶续》,第104页。可见亦有宗族势力做支撑。这些士人和以财势为基础的宗族结合到一起,必然在政治上有其诉求,其出路自然是以进入国家政权,担任国家各级官吏为主,而从私谥角度取得名义上的社会认可也是士族势力伸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此外,东汉政权对私谥这种与国家立法相悖的行为,似乎并未禁止。早在东汉初年夏恭被“诸儒共谥曰宣明君”;其子牙“早卒,乡人号曰文德先生”。⑤《后汉书》卷80上《文苑夏恭传》,第2610页。政权没有对私谥进行打压,这也为私谥在东汉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四、余论:私谥与东汉晚期的政治生态
本文所讨论东汉时期私谥,更多是从政治因素来考量的。私谥在东汉出现,特别是在晚期的盛行,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集中反应。这一点除上述所论之外,尚有两方面可以补充论之。
在给谥者中,有一类是获谥者籍贯所在地的郡县长吏,这有稳定地方统治的意义。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当时地方长吏的行政环境。汉代社会中的豪强从西汉时期开始发展,他们通过担任郡县右职,实际拥有了在本地的控制权。如东汉“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⑥《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6页。因而太守只有“画诺”“坐啸”了。作为地方长吏对这些以宗族为依托,集财势、文化优势于一身的地方士族亦有倾慕之心,徐干《中论》卷下《谴交》云:“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这些宾客、儒服就是地方的士族,州郡牧守宁愿与之交接,也不恤王事,所以对私谥者命谥也就持积极的态度。作为获谥者而言,他们虽然已经获得地方社会的实际支配权,但是以地方长吏来命谥,可以视为私谥取得正当性的一条重要管道。
谥法作为国家礼典之一,却能够被士大夫集团转化成私谥的形式,显示出他们与皇权的离心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源于和宦官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这一点很多学者皆有专论,毋须多谈。表现出这些离心倾向的人物,不仅是得谥者,也包括命谥者,以及其他的参与者。如范丹卒后,不仅被何进命谥,而且“三府各遣令史奔吊”。所谓三府,即三公府,说明私谥并非个人行为,这和名士卒后,动辄海内数千人吊丧相呼应,⑦《后汉书》卷68《郭太传》曰:“(郭泰)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成为士大夫集团与被宦官集团所控制皇权之间发生疏离的表现形式。所以从政治史角度观察,私谥问题不仅是礼法问题,而且也是东汉社会政治生态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曹鲁超][责任编辑:诚 钧]
The Problem of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 Privately in Latter Han Dynasty
SHEN Gang
(Institute of Document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 privately was in vogue in latter Han dynasty.The person who was given the posthumous title included hermits,retired officers and officers.They were proficient in Confucianism.Except disciples and reserve officials,local officers,relatives of empress and local people also can confer the posthumous title.The principle of conferring the title was confusion documents or ancient example.The title was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identity.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 privately was in relation to the inflexible system of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thinking highly of reputation in the scholar group,and the developing of noble.It reflected the eccentric prone between the scholar-bureaucrat group and the power of emperor.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 privately;latter Han dynasty;scholar group;confucianism
K 234.2
A
1002-3194(2014)04-0093-09
2013-08-26
沈刚(1973- ),男,辽宁宽甸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秦汉史。
吉林大学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魏晋国家统治方式演变与社会变迁”(2012FRLX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