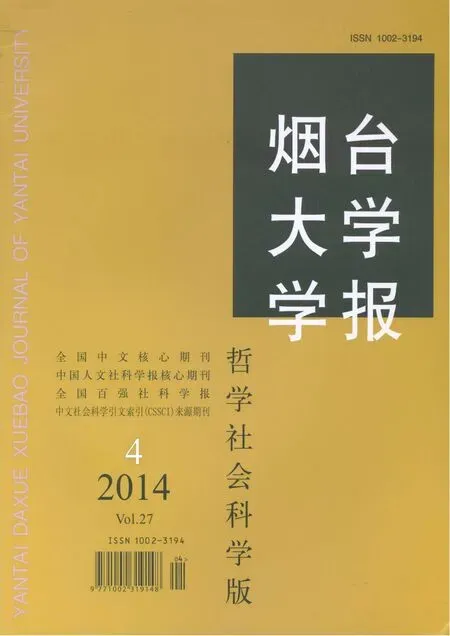晚清“新小说”中的少年形象及其形式症候
——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冯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晚清“新小说”中的少年形象及其形式症候
——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冯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晚清“新小说”是近代知识分子应对时代危机的产物,它着眼于对大众情感进行整合与教育,其目的在于想象和构建一种新的主体。在除旧布新之际,“少年”表征了新的时间起点,而“少年”之“成长”则意味着将线性时间注入进步历史观念之中,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基本母题与形式结构。“新小说”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第一人称少年主人公形象,通过讨论其中所呈现出的多种形式症候,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时代危机下半殖民国家面对现代转型时的难题与困境。
新小说;少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一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洋务初期李鸿章还自信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甲午战争以后在康有为看来整个局势已是“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①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1页。,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危机感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开来。对于世纪之交的晚清最后一代精英知识者而言,一方面,依靠清廷推行自上而下改革的设想随着戊戌变法的流产而宣告失败,另一方面,义和团等下层民众的反抗与暴动不仅无力回天,反而充满偏畸和愚昧,梁启超甚至视之为“极奇特的病态”。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8页。在这种情况下,“兴民权”、“开民智”成了绝大多数知识者的首要目标,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再三强调“建国”与“立人”的急迫性与同一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③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5页。基于这种共识,晚清知识者们着眼于构建“社会”这一中层力量,试图通过讲学、办报、集社等方式来教育、激发、整合民众,而本文所讨论的晚清“新小说”便是这种新的文化——政治实践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严格说来,尽管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振臂一呼为“新小说”定下了基调,但“新小说”形形色色的创作实践却并不能完全被梁氏的理念所涵盖。甲午战争以后,趋新求变日渐成为知识文化界的内在诉求,身处时代前沿的小说家们纷纷以“新”自居、喜谈改良,但具体到创作中,对于“旧”的切身理解以及对于“新”的具体想象,比之梁氏的明晰果断却要复杂得多,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多有前后矛盾之处,正因如此,对“新小说”的研究不能止于理念,而应努力深入文本机理乃至形式结构之中。“新小说”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迅速占领报刊市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趋新”时潮以外,还在于小说家们善于利用新兴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有意识地调整文风文体以适应报刊连载的新要求,并针对西洋译介小说中新的叙事类型与叙事方式积极加以模仿和尝试。这一时期谴责小说、官场小说层出不穷,正是小说家们汲取传统世情小说的题旨风格并进一步加以类型化的结果,这种种方面都显示出“新小说”绝不只是政治的传声筒,同时也有力地介入了时代文化与阅读趣味。
尽管对“新”的理解未必全然一致,但“新小说”背后的启蒙目标及其大众化的指向却是分外明确的,有论者将其比附为儒家传统“文以载道”的近代版本,然而文学并非“手段”与“目标”一分为二的简单结合,更何况,转型危机之下的所需承载的“道”也非昔比。倘若我们更为整体地联系时代语境,便会发现“新小说”背后的大众视野已经初步蕴含了现代情感政治的雏形。早在梁氏明确将“新小说”与“新民”联系在一起之前,来自西洋的译介小说、尤其是那些围绕人物与世界来展开的长篇小说,如《拿破仑》、《俾士麦克》,甚至《茶花女遗事》等,已经从各方面启发着晚清翻译界、文学界的知识人,促使他们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去理解西方小说中个体与世界的紧密关系以及个体所展现出充沛的行动能力与情感力量,并视之为中西文学观念的根本差异所在。在写于1897年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里,严复、夏曾佑用了大量篇幅考察论证“性情”如何从根本上联结起了各种事件和事理,并得出结论,“性情”不仅无需抑制,反而因其具备“古今中外一也”的普遍性而值得被大书特书。尽管这种对于“性情”的重视在儒家文学传统中并不陌生,并常常用以矫正名教的虚伪或道学的僵化,但在儒家的天理世界观遭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极大冲击的转型时期,“性情”所联结起的便不再是天道与个人,而是亟待通过行动与实践进入历史、书写自身的广大庶民。反过来,对于性情与人心的重视,又在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正名:“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近日人心之营构,几位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①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27页。这种以“人心”来构建历史的信心,大胆翻转了传统史学的虚实之辩,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执着进取的能动观念,也前瞻性地指明了文学想象在后发国家追寻现代的过程中所将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康有为期望“新小说”能通往传统的六经、正史、语录、律例所不能达到的领域②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29页。,梁启超希望借助“新小说”传播“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人心”、“新人格”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其目的便不再只是文学与政治的简单叠加,而是借助小说充沛的情感召唤力量重新想象一种人与世界的积极关系,从而敏锐地把握住了通往共和、民主的时代脉象。
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中更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是时间。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严复便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思考时间观念如何决定了今日中西方人学术政化的强弱格局,他认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①严复:《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这一思考在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译介中得到了强化。同样,在梁启超眼里,晚清帝国被想象为是一座更历千岁的巨厦,一个在停滞的时间中逐渐风化的非生命体,线性时间的引入既是一种压迫性的、异质性的毁灭力量,同时也包含着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契机。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②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里,梁启超乐观地用“少年”来比拟亟待进入世界民族国家之列的中国,少年成长的“自然性”对应着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唯有经由少年之“新生”亦即主体力量的介入,中国方有可能重新进入现代时间秩序,在“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未来中重新书写“老大帝国”的辉煌。
在“少年中国”的倡导和动员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以“少年”自诩的小说家,以及以“少年”为主角的“新小说”。梁氏本人便非常喜欢并亲自翻译了讲述少年英雄的《十五小豪杰》,这本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经过晚清语境下的译介转换,被明确地赋予了教育大众的任务,松岑在《新小说》第十七号上曾评论道:“吾读《十五小豪杰》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险独立,建新共和制于南极也?”③松岑:《论写情小说于社会之关系》,《新小说》第17号,1905年。通过跨语际的阅读,晚清少年被赋予了探索国泰民安的政治新建制的任务。此外,“新小说”还涌现出一类少年革命者形象,比如陈天华创作的《狮子吼》中自称“新中国之少年”的小生,以及《恨史》、《新聊斋唐生》等写情小说中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爱国青年,后者在梁启超“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④梁启超:《新小说社征文启》,《新民丛报》第19号,1902年。的要求下,不再沉湎于花前月下,而是以自我牺牲、以一己“私情”成全爱国“公情”为至上目标。
本文并不拟从文本的内容层面来探讨晚清“新小说”中的“少年”形象所寄予着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诉求,而是将少年及其成长视为“新小说”的一种基本形式结构,从“少年”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出发,探寻新小说家如何想象民族国家的主体,以及如何想象主体与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此前陈平原教授等研究者已经针对“新小说”的叙事形式做出了若干开拓性的研究,但这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小说叙事形式与社会文化生产之间的关联⑤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也即文本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事实上,叙述形式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生产意义、呈现症候的“有意味的形式”。与此同时,在一再“重写文学史”的今天,针对吴趼人等晚清新小说家的批评既不能停留在诸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等“先进”或者“落后”的僵化框架内,也不能在“被压抑的现代性”等论述中放弃晚清小说回应现代危机的历史维度⑥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通过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⑦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本文试图探索一种更能够容纳中国近现代整体历史进程的、更为历史化的晚清小说的批评方法,以期求正于方家。
二
1903年10月,《新小说》从第八号开始交由吴趼人主持,同一期开始,吴趼人连载三部长篇小说,分别为《痛史》、《电术奇谈》、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下简称《怪现状》)。《怪现状》连载了前八十回,最终集结一百零八回,交付梁启超所主持的广智书局出版,公认为是晚清“谴责小说”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吴趼人算得上晚清最具文体改革意识的小说家,他乐于尝试和探索各种篇幅体裁与叙事方式,同时也是最早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作者①吴趼人使用第一人称的小说目前可见的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大改革》、《平步青云》、《黑狱冤魂》、《预备立宪》,后四篇皆为短篇,其中《预备立宪》为文言小说。,这些文学形式的探索本身除了有来自西洋小说的启发以外,更为内在的动力恐怕是为了更好地为创作与思想赋形。《怪现状》中异常醒目地出现了第一人称叙事主角“我”,“我”的出场意味着叙述者主动放弃说书人的权力,从“幕前”走到“幕后”,这其中显然隐含着一种主体的姿态。与此同时,与全知视角相比,“我”更容易与读者相互亲近,从而引发读者感同身受地进入“我”的世界,如果联系捷克批评家米列娜(Milena Delezelova)所指出的,“新小说”的核心目标正是为了“把读者从对于小说的朦胧不定的理解逐渐导向要模仿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强烈愿望”②米列娜等:《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页。,那么,毫无疑问,从“我”的内视角所展开的叙述可以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并有助于小说家塑造出一类内在情感丰富的主人公,从而激发起读者内在地认同与“模仿”。
在《怪现状》一开始时,我们会发现,第一人称确实有意识地运用了内视角的优势,作为少年的“我”初到上海,被亲伯父拒之门外,孤苦无依,偶遇同乡吴继之,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这些都经由读者视角与主人公视角一致,起到了感同身受的效果。“我”一出场时遭遇的第一次挫折来自“我”的亲伯父,“我”将父亲过世后的一笔遗产交给伯父存放在钱庄里,屡次写信支取利息却没有回音,逼不得已“我”只好去找伯父,却被用各种手段推脱相见,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却仍旧蒙在鼓里,此处吴趼人故意安排了除“我”之外的其他当事人——包括读者——都对伯父的卑鄙行径心知肚明,唯独“我”偏偏看不明白(同乡吴继之也屡次告诫“我”,“他说这话时另外有个道理,你自己不懂,我们旁观的是很明白的”),这里叙述视角的全知与第一人称“我”本来应该具备的限制视角产生了偏移,这或许是由于吴趼人对第一人称叙事的使用尚不熟谙,但也恰好暴露出“我”的年少幼稚、不通世事为后文埋下了“成长”的伏笔。
然而,随着“我”的旅行的开启,短暂的内视角很快便被外视角的观察眼光所取代,更值得我们重视和讨论的是,从小说行进到一半开始,“我”的声音便大大地减弱,小说后半部分实际上出现了两个以上的叙述声口,也即热奈特所谓的“故事内叙述者”与“故事外叙述者”③热奈特:《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随着越来越多“故事外叙述者”的出场,小说竟然“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传统第三人称叙事的老路子上④小说第70-72回、第80-84回、第87-95回,这三段故事都是经由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完整地讲述出来的。,诸如“看官听我叙来”或是“你道”等说书人向听众道白的口吻在小说七十四回之后便屡见不鲜,第一人称叙述者甚至还屡屡介入他人的心理活动之中。就连吴趼人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全知叙事者与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之间的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在接连用长达三、四回的篇幅借第三者之口讲述同一个故事后,“我”居然跳出来直接⑤小说第52回,督办被夫人质问娶妾一事时,叙述者就介入了督办的内心活动:督办被夫人问得哑口无言,暗想:“难道这些枝节,也由电信传去的?”面对读者解释道:“我这两段故事,是分了三四天和子安们说的,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那些节目,我又懒得叙上,好等这件事成个片段罢了。”简而言之,在小说行进的过程中,第一人称“我”不仅没有如小说一开始所呈现出的那样逐渐进入读者的视野,尽管吴趼人有意识地赋予笔下的这位少年主人公一系列开阔的性格特质,比如好奇、爱冒险、喜欢收集见闻、广交朋友等等,并特意为他设置了一个需要四处旅行的职业,相反,小说呈现出来的却是“我”的逐渐缺席,更出人意料的是,小说最后一回在陡然呈现的全面颓势面前,“我”几乎连解释的能力都不再具备,小说戛然而止,叙述者甚至无法提供一个结局。关于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固然可以批评吴趼人没有充分地自觉到第一人称主体性视角的优势,这一“内置”的视角并没有帮助他去更好地想象、塑造一种情感丰富的主体,但是,更需要解释的是主人公的逐渐退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第一人称无法“从一而终”?小说为什么在叙事方式与叙事对象上遭遇了无法协调的两难?这些文学形式表征出了怎样的历史困境?
显然,叙事技巧的不成熟以及叙事意识的欠缺并非是主要的原因,换个角度我们或许应该承认,恰恰正是因为吴趼人秉持了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意图,塑造主体的任务必然会让位于对“怪现状”的揭露,这一急切的目标使得他不可能、也无暇塑造一个充沛的、或者在“个人意义”上丰富的主体人格,主人公的性格面向必须是单面的、整体朝外的,其个人日常生活无足轻重,也正因如此,小说中即便主人公父亲过世也只是一句“一场痛苦,自不必言”,三年婚姻生活更是一笔带过。从人物与世界的关系上来看,与叙述者的消隐互为因果的,是叙述者外部空间的压缩,这里并非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均质、单一的空间,而是与个体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激发出行动、生发出意义的有“内容”的空间。不难看出,这一空间——也即小说中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怪现状的杂乱纷呈而自动浮现,相反,这一“世界”伴随着叙述者的缺席而更加零散、杂乱、并最终失去其整体性的意义,此中恰能见出鲁迅对这部小说的批评:“杂集话柄”。①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主人公与空间之间的整合能力对应着主体参与世界的可能性与能动性,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将《怪现状》与同样流行于二十世纪之交的西欧侦探小说做一个比较,尽管侦探小说里足智多谋的主人公同样只是出现在事件(案件)发生并完成之后,但是,经过侦探主人公有效的行动与理性的思考,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能够被再次去魅,并在清晰有序的因果链条中得到梳理与解释,也即是说,主体强大的理性与行为能力足以穿透迷雾般的事件,并获得重新讲述这一故事的资格。反观《怪现状》,主人公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总是迟到地出现在“怪现状”的外部,经由“目睹”或更为被动地听别人“讲故事”,无法提供对当前事件的整体性理解与把握。伴随着“我”逐渐丧失进入世界的行动能力并最终失去了叙事的资格,小说只能重新回到全知视角,尽管后者可以更“方便”地呈现事件,但正是由于缺乏主体的贯穿与联系,这一空间成为了一个无意义的场所,并最终被一桩桩千奇百怪的、零落无机的怪现状所占据乃至肢解。
与主体视角从内到外的转移所紧密联系的,是这一视角背后情感经验的匮乏,伴随着“怪现状”的深入,后者逐渐被一种单调冷峻的讽刺与愤懑所占据,恰如鲁迅所批评的“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②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3页。这里所讨论的“情感”无需窄化为私人情欲或自我意识,而是应该放置在前文所提及的“新小说”的情感政治的目标下加以理解。事实上,晚清文化政治所亟待召唤的情感,并不是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二分的前提下对前者的深度挖掘,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在迅速变换的外部危机面前不断生成的对于现实境遇的切身反馈,并反过来从这一新的时空体验中获得历史进步的动力。对于一个身处危机中的后发民族国家而言,只有在调动起这种情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想象一种现代主体的内面以及从内而外地凝结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然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目标的难度所在:梁启超们所构想的情感政治必须同时伴随着行动和实践才能真正地调动起批判的力量,并在现实层面构成克服危机的资源,然而,当个体所目睹的世界无以为继、个体所倚靠的价值信念无法激发出一种有效的回应时,情感的力量如何能在抱怨、失落、焦虑以及恐惧之外,继续承担起超越现实、想象未来的任务?事实上,我们知道,伴随着“新小说”落潮后大量泛滥的正是一双双窥视的眼睛与沉溺于虚空之中的感伤与失落,从“谴责小说”到“黑幕小说”或许只有一步之遥。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外部世界,“少年”主人公如何进行其思考与认知?换句话说,个体如何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成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指向了什么?
三
批评家米列娜在分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主人公的认知过程时认为:“主角自身的故事具有一认知过程(a cognitive process)的特征,即认知的故事(an epistemic story):从‘错误的信念’(a false belief)出发,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主角获知其伯父人品、地位、行为等的‘真相’(a true knowledge)”。①米列娜等:《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第523页。但是,在本文看来,米列娜的解读更符合欧洲“成长小说”的特征,与《怪现状》的特定语境颇有出入,这一区别值得我们细加讨论。
《怪现状》一开始时吴趼人有意将十五岁的“我”设计为一个纯洁的、好奇的外来者,与周围见怪不怪的其他人(比如吴继之)形成对照。“我”第一次坐轮船去南京,目睹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去做贼,感慨“扮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污了官场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观察并且合乎“常理”的判断,然而当“我”随后与吴继之谈及此事,却恍然大悟那人“的的确确是一位候补县太爷”,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官场之恶在于名实不符。自此开始,“我”的成长任务便被锁定为拨云见日,弄清常理被颠倒后的“真相”。每当“我”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时,吴继之总是及时出场,指出我的短视:“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继而由他来告诉读者真正“怪”在何处。也即是说,小说实际上呈现出的认知情形并非如米列娜所说的经由“错误”发展到“正确”、并最终获得对事件“真相”的理解,恰恰相反,这里的“真相”只不过是常情常理堕落后的颠倒,并不具有任何真理性价值,叙述者在意的与其说是呈现出一种从错误到真实的认知上升过程,毋宁说是在批判一种从常态到变态的道德下降的过程。
如果将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做一对比,即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种认知模式的重要区别。歌德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威廉·麦斯特出身于商人家庭,但他并不满足于小市民阶层的世界观,而是在游历了广袤的祖国、结识和跨越了各个阶层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有意义的教育,最终矫正了先前的自我认识,超越了小市民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念,实现了与他人更高层次的互动互助,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体。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威廉·麦斯特的成长历程既是个体深入特定社会历史的具体实践,又是个体对于普遍的价值意义系统的体验与感知。这位少年的“学习时代”始终围绕着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历史的交汇互动,这使得他的认知过程包含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即从“错误”到“正确”、从低级到高尚、从褊狭到普遍,最终与歌德所说的“伟大真理”合一。而反观《怪现状》,同样是少年游历,同样是结识和跨越不同人群,所不同的是,晚清少年并没有获得“学习”的机会,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剧烈扭曲的现实世界无法提供一种稳定的环境供主人公认知与探索,一切所见所闻在令主人公震惊之余,都无法构成新的“知识”。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尽管小说中出现了层出不穷的怪现状,但叙述者显然并没有打算为主人公设置任何价值观念上互相碰撞的“他者”,整篇小说中叙述者迫切想要呈现的,并不是认知过程中主人公自身意识的修正,而恰恰是在严肃的、一元的儒家道德评判标准之下所目睹的颠倒与堕落。尽管在成长之路上叙述者设置了另一位主人公吴继之充当“我”的保护人与“导师”角色,然而这个导师同样是“不尽职”的,这不仅由于吴继之本人在面对动荡世事也常感无力,甚至在大多数时候只不过寻求明哲保身,更重要的是小说中“我”与吴继之实际上仍然共同置身于一个封闭的儒家士绅共同体以内。显而易见,尽管这一共同体背后的天理秩序在晚清危机下已然遭受巨大的冲击,但叙述者仍然高度维护和认同这一共同体背后同脉相连的儒家文化教养,“我”与吴继之的交往也始终贯穿着评诗、赏画、猜谜等古典文人活动。可以预见的是,吴继之与“我”(以及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姊姊”与“我”)之间不可能出现任何价值观念上的真正碰撞,在叙述者的视域里,少年之未来与今日之“吴继之”是可以想见的同一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步的时间维度并没有如期进入小说,“我”的成长也并没有在小说内部真正地展开。
在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看来,歌德的这篇小说代表了欧洲“成长小说”(Erziehungsriman或Bildungsroman,也译作“教育小说”)的典范,尽管我们无需将这一小说类型从其自身的文化历史中抽象出来与转型时期的晚清小说做一简单的高下比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通过讨论与西欧成长小说密切相关的历史范畴,恰可以清晰地对照出晚清“新小说”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在对“成长小说”的讨论中,巴赫金同样注意到了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以及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深刻作用,在巴赫金看来,歌德小说里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时代主体”,其先决条件是他自觉到了“自身己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时代的过渡”,与此同时,通过将时间作为一种价值纳入到自身内部,主人公得以克服自身“作为统一体的静态性”以及“稳定不变性”,在有意义的时间中不断地累积实践与经验,成为一个“动态的统一体”。正因如此,巴赫金认为真正的成长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局限,主人公不再处于一个静止的世界和历史中,而是“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并由此进入了“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①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0-233页。这种对于个体与时间变动关系的理解内在的契合了黑格尔所设想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史,正是在不断地将异质之物转换为他者的动态过程中,主体辩证地在差异和对立中确认自身。同样的,梁启超在批判封建史学“四弊二病”、提倡“史界革命”时,也在思考着如何将进步的旨意注入历史之中,他主张:“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页。,通过将一切混乱无序的无规则变化排斥在历史之外,为个体即将开启的进步、成长的历程赋予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说,以认同这种新的历史时间观念为前提,个体才能获得介入历史。
然而,回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们会发现,尽管吴趼人同样意识到了除旧布新的迫切性,也尝试着以一种更为积极、更为开放地姿态去迎向“未来”,但是进入历史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吴趼人对时代危机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儒家伦理框架以内,这表现在小说主人公从始到终都在用一种道德的眼光去贯穿和衡量周围所处的世界,正因如此,即使身处转型时代的高速变迁的洪流之中,主人公的内部与外部世界仍然呈现为一种停滞的状态。在混乱、堕落的场景下,线性进步的时间并没有轻而易举地进入这部小说,人群只不过在私利私欲的驱动下如同走马灯一样纷纷上场,而主人公在虚实颠倒、举步维艰的外部环境中却无法获得成长所必须的经验和动力,叙述者也并没有为其留下反思与自省的空间。为了匡正摇摇欲坠的纲常法纪,吴趼人赋予了主人公一个坚定的道德立场,然而,小说在叙述层面却悖论性地呈现出这一立场无法回应历史难题:从19世纪中叶沦为半殖民地开始,晚清帝国在半个多世纪内所遭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毁灭性打击已经一再证明了传统以道德为本位的儒家文明在应对帝国主义船坚炮利时的无效,这种无效反过来加速了社会道德沦丧与价值虚空,但是,对于转型时期的个体而言,来自传统的思想资源与知识结构却是人们理解现实时的唯一立足点。如何将这种资源加以革新和转换,如何获得身处“两个时代的交叉处”的自觉,这意味着必须在中与西、全球与地方、帝国与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知识与价值等等复杂的维度中结构性地洞察社会、反思历史,这也决定了针对“少年”及其成长的想象与叙事将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不断回响的主题,身处历史断裂之际的个体还将在持续的危机与挫折中不断地上下求索。
[责任编辑:诚 钧]
The Youth in the New Nove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On Bizarre Happenings Witnessed Over Two Decades
FENG Ni
(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The New Nove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the product born to respond the crisis of the time. It aims at educating the masses through an emotional way,with calling for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ubjects as its final purpose.During the changing periods,the youth in the novel represents a fresh start of time and the growing of the youth represents a modern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There is a youth with first person in the masterpiece of the New Novel On Bizarre Happenings Witnessed Over Two Decades.Through the discuss of the youth in this novel,I will show how it is combined with the crisis of the late Qing.
New Novel;youth;On Bizarre Happenings Witnessed Over Two Decades
I 206.5
A
1002-3194(2014)04-0058-08
2014-03-15
冯妮(1983- ),女,辽宁营口人,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项目(2014M551386);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科研创新计划青年培育项目“爱情叙事的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从晚清小说到‘五四’新文学”(13QN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