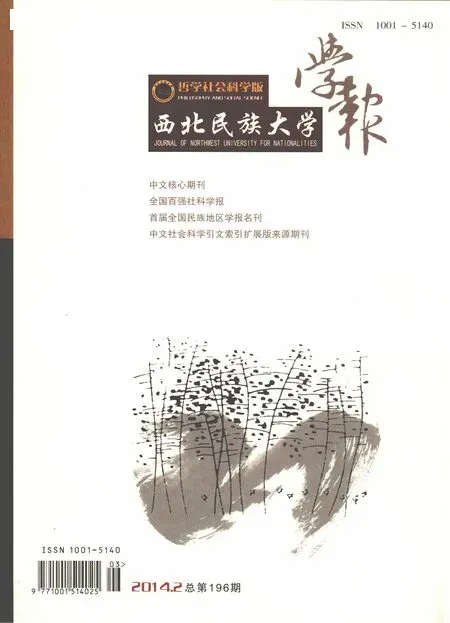论早期密教对佛教主流思想的吸收与改造——以持明密教佛顶法为核心
张文卓
(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710062)
密教起源于大乘佛教陀罗尼,其核心理论与大乘佛教主流思想,如中观思想、瑜伽唯识思想、如来藏思想、陀罗尼思想、净土思想等有密切关系。这些思想被密教吸收并与其繁复的神灵体系、庞杂的实践体系融合为一,从而形成了佛教密乘,成为晚期佛教的主流。但是密教吸收、融合大乘佛教思想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期发展。佛顶法正是这一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中可以看出主流佛教思想逐步进入密教并被其吸收、改造的理论痕迹。
佛顶法是以佛顶类神灵为核心形成的一类密法体系,作为早期密教陀罗尼密教和中期以金胎两部密法为核心的密教的过渡阶段,它上承陀罗尼密教,下启金胎两部密法,融合了大乘佛教主流思想,又大大发展了陀罗尼密教确立的以陀罗尼为核心的理论特色,并在陀罗尼密教“语密”的基础上增加了“身密”,大大推动了密教的发展。其在教相上继承佛教核心思想,诸如中观思想、菩提心思想、如来藏思想、禅观思想、净土思想等,在事相上则建立起曼荼罗法、画像法、坛法、印咒法、护摩法等较为完备的密法体系。作为密教早期发展阶段的佛顶法,其思想体系并非杂乱无章,而是繁中有序、乱中有纲,也即密教经典的作者有意将佛教主流思想引入密教体系,并力图使二者合二为一,从而使密教获得正统佛教的承认,扩大其流传。本文拟就佛顶法中所见佛教主流思想做一探究,以期厘清其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对后来密教理论体系的影响。
一、佛顶法的兴起及其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状况
密教的形成经过了长期酝酿,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更有适合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广泛的群众基础。密教起源于陀罗尼(梵文Dhārani)[1],而陀罗尼思想在佛教中源远流长,尤在大乘佛教时期发展迅速,各主要大乘经典中大多都专列《陀罗尼品》,论说陀罗尼的功能、功德等。早期陀罗尼密教就是沿着这一发展逻辑继续演变的结果,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印度教、印度民间宗教的影响,但佛教陀罗尼思想的演变是根本原因。陀罗尼密教大约在3世纪前后就开始流传[2],这是密教的最初阶段与形态。这个时期的密教主要发挥和突出了陀罗尼的功能与功德,它依附于大乘佛教,缺乏理论体系,其密法体系也尚处于萌芽阶段。继陀罗尼密教之后,随着《持明咒藏》的编纂,密教进入持明密教阶段。较之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除了强调明咒(梵文Vidyā)的作用之外,增加了印契,密教 “三密”此时已经具备其二。佛顶法则是持明密教时期新出现的一类神祇体系、密法体系,起源于对佛三十二相之一——无见佛顶以及佛灭度后对佛顶骨舍利的崇拜,佛顶最终从佛陀身体的局部脱离,形成一类独立的神祇——佛顶佛,继而又产生佛顶轮王等一系列神灵。产生了一系列经典,诸如《一字佛顶轮王经》《一字奇特佛顶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字顶轮王瑜伽经》《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等,逐渐建构起了较为完善的密教理论和实践体系,为金胎两部大法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佛顶法的兴起
佛顶法是以佛顶类神灵为主尊或核心形成的一类密法体系,密法体系较为完备,属于持明密教晚期的一个密法体系。佛顶类神灵的产生以佛顶佛的出现为标志,之后又相继形成了三佛顶、五佛顶、八佛顶等不同体系,又与轮王思想相结合衍生出佛顶轮王类神祇,最后又产生一字佛顶轮王,形成了一字佛顶轮王法。一字佛顶轮王法是持明密教发展的顶点,对金胎两部密法均有影响,与金刚界密法关系尤为密切。
据《历代三宝纪》记载,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就出现了佛顶部经轨的汉译本,即阇那耶舍译一卷本“《佛顶咒经并功能》一卷(保定四年译,学士鲍永笔受)”[3]。但是,此经现已不存,内容难以详考。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汉译佛顶部经轨是永徽五年(655年),阿地瞿多所译《陀罗尼集经》,其中明确出现佛顶佛,且在该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原文载:“座主即是释迦如来顶上化佛,号佛顶佛”[4],又说“时佛世尊为诸会众说佛顶法,广此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5]。此中明确说“佛顶法”,可知佛顶思想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流传,因为从一尊新的神祇——佛顶佛的出现到一类修行法门——佛顶法的形成必然经过一个过程。又,地婆诃罗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680年,佛陀波利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683年。据《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记载,《佛顶咒经并功能》、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地婆诃罗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三经是同本别译[6]。可知,564年译出的《佛顶咒经并功能》今已不存,在佛教史上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到680年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则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这大致说明佛顶法在汉地的广泛流传也经过了百余年的酝酿。
吕澂先生认为,从一部佛经在印度开始流传到译成汉文,大致约100年[7]。那也就是说至迟450年前后,印度西北部、中亚一带已经流传着与佛顶法相关的经典,到550年前后佛顶法则广为流传。吕建福先生指出,陀罗尼密教发展到4、5世纪,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就是在陀罗尼的基础上配上了手印,又增加了曼荼罗法、像法、供养法等,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密法体系。他认为3~4世纪《持明咒藏》编纂形成,到5~6世纪持明密教已经广为流传[8]。佛顶法作为晚期持明密教的重要内容,兴起于4世纪前后,5~6世纪则非常兴盛。
(二)佛顶法流传的时代背景
4、5世纪大约是笈多王朝统治印度的时期,①笈多王朝从旃陀罗笈多一世继位的(319—320年)纪元,到5世纪末开始衰败,遭到嚈哒人的大规模入侵。详细内容可以参考:K.查克拉巴尔蒂著《笈多王国》,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52—154页;亦见:王治来著《中亚通史》(古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该王朝从5世纪中叶开始陆续遭到嚈哒人的攻击,“最后的打击发生在五世纪末期,当时匈人(嚈哒人)成功地闯进了北印度”[9]。虽然 “匈人对印度的政治影响后来就消退了。但是,在北印度政治变化中起了催化剂作用的匈人到六世纪中叶目睹了笈多王国缓慢的腐朽和最后的解体。”[10]从“塞建陀笈多(约454—约467年)死后,笈多人未能抵抗住匈人反复入侵的浪潮,中央权威迅速衰落。以后诸王的继承顺序不很确定……说明这一王朝末期相当混乱。”[11]约从7世纪初开始,塔内萨尔的普世亚布蒂家族的曷利沙伐弹那(戒日王,606—647年)在位期间,他们才成功地对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确立了政治主权[12]。
可知从5世纪中叶开始,笈多王朝由盛转衰,频繁遭到匈人的入侵,陷入负隅顽抗的境地,这种纷乱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大约7世纪初。5、6世纪正是佛顶法在中亚一带流传的时期,这种纷乱的政治格局以及频繁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为密教的流传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且此时虽然“佛教(大乘和小乘)在笈多印度很昌盛,但是外部和内部的一些因素导致它逐渐衰弱”[13]。“而且笈多王朝支持多种宗教,包括婆罗门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更倾向于婆罗门教,到塞建陀王时逐渐改变了宗教政策,对佛教开始重视起来。这可能与国势日衰有关……借以鼓舞人心”[14]。这一情况也间接反映在后来的佛顶类经典中,①吕澂也有类似观点,“(《大涅槃经》)前分流行于笈多王朝初期,统治者对佛教疏远,也包括其时小乘不信大乘,所以,《大涅槃经》就认为这些人是‘一阐提’。后来笈多王朝信仰佛教的多起来,小乘也有转向大乘的,《大涅槃经》后分的说法也相应地变化了,认为‘一阐提’也可以成佛,给这些人开放门户,对自身学说的发展也更为有利。”见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如《一字佛顶轮王经》载:“以忿怒诵根本真言,能禁止象马车轮。即此印乘象结遥掷,能禁止他敌。”[15]亦载:“书一字顶轮真言,并画轮王……对军阵前,即彼军众如盲迷乱,一切器仗彼手而落,并皆禁止。又法欲令他军堕落,令医人五支取血,于炉于护摩,瞬目顷,彼军皆得堕落,则随意缚。”[16]又载:“结根本印,入军阵,能禁一切,刀兵所不能害。”[17]类似的说法在佛顶类经典中不胜枚举,因为这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当然也与佛教的传播息息相关。佛顶类经典之所以重视王族及战争,与其争取统治阶级的支持和信仰是密切相关的。整个持明密教时期流传的神祇、密法,都有很强的现实性,对个人而言,流传各种成就法,能够满足普通信众的需求;对统治阶层而言,又流行降伏、增益法,能够满足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
(三)佛顶法兴起前后西北印度、中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
这一时期,除了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之外,中亚还流行着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以及民间宗教等多种宗教形态,宗教信仰繁杂而活跃,不同宗教为了争取信众不可避免暗中较量、相互借鉴,甚至不免互相贬低。《陀罗尼集经》记载说:“不得轻慢我等正教。”[18]这是佛教自身的说法,带有贬低其他宗教的意味,但确也说明当时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有许多证据证明,西北印度在贵霜人到来前夕盛行湿婆崇拜。”[19]还有“在巴克特里亚,贵霜钱币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琐罗亚斯德教诸神,不过两个阿梅沙·斯潘塔(圣神)——沙赫里瓦尔(王国)和瓦赫曼(善思)——与希腊和印度神祇的关系,提供了证据,说明有一种把不同宗教融合在一起的很明显的倾向。”[20]另外,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熟悉许多宗教,特别是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曼达派(Mandaeism)和佛教,宣称建立了一宗世界宗教以取代当时存在的一切宗教。他从它们的信条和实践中借用了许多内容,因此,摩尼教从其所有特点来说,是一种融合各种不同信仰而成的宗教。”[21]甚至东方摩尼教的忏悔罪恶观念很可能是取自佛教,拜火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教义和宗教实践,密教的护摩仪式有可能就来自琐罗亚斯德教或者受其启发。总而言之,可知这一时期中亚地区多种宗教信仰并存,而且各种宗教之间的互相影响与相互借鉴乃至融合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
中亚在密教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密教经典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如密教的核心经典之一——《大日经》就产生于西北印度、中亚一带。而且“出自巴乔尔(Bajaur)、蒂拉赫(Tirah)、斯瓦特(Swat)、吉尔吉特和罕萨(Hunza)的许多佛教朝圣者留下的佉卢文石刻铭文和圣物箱上的铭文证明,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持续了很长时间,从贵霜时代一直延续到穆斯林征服为止。”[22]而这一地区可能与密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是密教流传的主要地区之一[23]。西北印度之所以是密教经典的发源地,这与佛教发展与传播的历史有关。“自孔雀王朝亡后,印度的佛教中心地区本已从恒河流域转移到印度的西北部,佛教也很快传到中亚各地。如康国即‘奉佛为胡书’。吐火罗国‘俗奉佛’。故这个时期到中国传播佛教的僧人,中亚各地人反而多于天竺人。嚈哒的统治也可能是促使大批中亚僧徒前往中国的原因之一。将佛经译成汉文的也多是中亚人,并且有许多从西域胡语转译而来,而非直接译自梵文。中亚各族对于佛教之东传起了很大的作用。”①中亚在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亚也是一个东西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的大熔炉。东西文明在这里交汇,所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传播到东西方,其中宗教文明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密教的形成与此背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亦可参见:王治来著《中亚通史》(古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这也就不难理解中亚在佛教向中国传播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原因了。
二、佛顶法对主流佛教思想的回应、吸收与改造
任何思想绝非孤立出现,必然处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它既是对之前或同一时期某种思想的回应与扬弃,也必然对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佛顶法的兴盛也正是继承了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在陀罗尼密教的基础上走得更远,顺应了时代潮流。佛顶法兴起之时面对的是怎样的佛教发展状况,佛顶法吸收继承了哪些传统佛教思想,又做了哪些改造与发挥;佛顶法的出现期望解决何种宗教、哲学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有何意义。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抑或才能更好地理解佛顶法的兴起在佛教史、密教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5、6世纪流传的佛教思想除了佛教一以贯之的基础思想之外,以般若性空思想为核心的早期大乘佛教思想也非常流行,另外这一时期兴起并逐渐突出的中期大乘佛教思想包括佛性思想、如来藏思想、瑜伽唯识思想、中观思想,净土思想等。“中亚出土了大量大乘经文,可以勾勒出一幅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占据优势的佛教派别的图景。在诸派中,信奉《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教派占有最突出的地位。”[24]《陀罗尼集经·释迦佛顶三昧陀罗尼品》亦载:“其佛左边安净箱子,盛《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日日读之。”[25]可见般若思想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思想依然被佛顶法强调。《一字佛顶轮王经》亦载:“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愿欲修行菩萨大行,坚固信向,一心正愿,常乐书写大乘经典,读诵供养,解其义味。若见斯人则为解释,如《宝雨经》一一法门,修学菩萨加行法行则得成就。是故密迹主!咒何所成,要从身心勤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定慧、清净,一心修习,方得成就。”[26]这里透露出对大乘佛教经典的强调,直接提到《宝雨经》;也有与大乘佛教相似的六度,但是缺般若,改成了“清净”,《陀罗尼集经》也有六度,“波罗蜜多六度行”[27]。《一字佛顶轮王经》说:“印砂佛塔随力印修,并转大乘诸余经典。”[28]可见大乘佛教仍是持明密教的主要理论来源。此外,“对西方极乐世界(Sukhavati)教主阿弥陀佛(Amitabha)的崇拜在中亚诸民中特别普及。”[29]
佛顶法流传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而且为了自身发展,它也必须吸收佛教主流思想,才可能发展壮大,否则甚至有被指控为“外道”的危险,可见大乘佛教思想自然是佛顶法可以吸纳的重要思想来源。那么佛顶法中主要吸收、改造了哪些佛教主流思想,下文展开论述。
(一)佛顶法与涅槃佛性思想
笈多王朝时期,《大般涅槃经》已经开始流传。关于该经在汉地流传的版本主要有三个,起初有义净从天竺取来,共觉贤译出的六卷本《佛说大般泥洹经》,这只是全经的一部分,即《大众问品》,即吕澂所言前分,后有昙无谶译出的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也就是现在所称“北本”,吕澂称为后分,再有慧严、慧观与诗人谢灵运等汇编而成的《大般涅槃经》,称为“南本”[30]。《大般涅槃经》提出法身具有“常、乐、我、净”四德,真实不虚。为何不虚,因为佛性是常,而且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众生和佛有何差别?众生佛性被无明烦恼所遮蔽,隐而未显,只有经过修行,去除烦恼,才能使佛性显现,成就佛果。《大般涅槃经》载:“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31]在描述佛性的时候,“《大涅槃经》中的佛性也用了‘如来藏’的名字”[32],但是《大般涅槃经》中的如来藏尚未广传,所以说“我今亦尔说如来藏,是故比丘不应生怖”[33],透露出如来藏应为新说,尚未取得认可,故有此说。如来藏在《大般涅槃经》中也称为“如来密藏”或“如来秘密藏”。
持明密教时期的佛顶轮王法对《涅槃经》思想的回应与吸收主要体现在对“一阐提”是否有佛性的问题的探讨上,说明佛顶轮王法也参与到了当时主流思潮的探讨中,而且也说明这一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佛教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影响极大。如《陀罗尼集经·释迦佛顶三昧陀罗尼品》说:“若有受持此法轮印陀罗尼者,一切诸法三昧陀罗尼,法自在力速得成就,令佛正法久住世间,常行菩萨摩诃萨道,起大慈心,教化众生,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名转法轮,灭除一切罪,一阐提等皆悉消灭。”[34]这里明确说到一阐提,虽然没有明确说一阐提可以成佛,但是说可以使一阐提灭除罪恶。既然罪恶灭除,成就善根,也就有了成佛的可能性,此中论述与北本《大般涅槃经》关于一阐提能否成佛的观点一致。无独有偶,该经同一品又说:“此印陀罗尼,若善男子善女人至心作印诵陀罗尼,随诵一遍,百千万亿俱致那由他恒河沙劫四重五逆一阐提罪一切罪障悉皆消灭。若能一生日日常诵,千遍万遍,能令行者无始以来一切罪障悉皆消灭。”[35]这也说明密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广泛关注佛教当时流传的重要理论问题,并有积极回应,虽然以陀罗尼能够消除一阐提罪恶的方式阐述这一问题,但这确实反映出密教不光单纯吸收传统佛教理论,也做出自己的判断与回应。
(二)佛顶法与菩提心思想
菩提心思想源远流长,也是密教的核心思想。①吕建福先生对菩提心思想的渊源有详细考察,认为菩提心思想是密教的核心思想。见吕建福《密教哲学的基本议题及其重要概念》《密教论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93页。菩提心思想在密教中的发展有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密教陀罗尼经典中并没有多少菩提心的内容,但是在持明密教时期的佛顶法中,菩提心思想已经被吸纳,并多有阐述。《一字佛顶轮王经》说:“释迦大师子,无量菩提门。理趣自在行,当为最上使。见苦迫有情,乐修行此法。天人共戴仰,当成无上尊。修习是深法,称叹大妙咒。信乐于大乘,心行应菩提。”[36]
佛顶法也非常强调菩提心,把发菩提心作为修持的前提和成就的必要条件。《一字佛顶轮王经》:“当世咒者得复如汝坚固精进发菩提心,怜愍有情,修此一字顶轮王成就法者决定成证。”[37]又说:“我为一切苾刍、苾刍尼、信男、信女等持此不可思议一字顶轮王印咒乐成就者,说所修行三昧耶门,应各持清净戒,发菩提心。”[38]亦载:“密迹主是故一切咒者心常寂静,坚持六念,系修咒法,发菩提心,则得成就,离菩提心外毕无成办。何以故,假菩提心大威力故。”[39]可以看出非常强调菩提心在密法修持中的作用,称有大威力。《陀罗尼集经》也说:“若作法时,深心发于无上菩提心,平等怜愍一切众生,发是心者随意得验,若不尔者不得验也。”[40]又说:“是真言能助成般若波罗蜜多,令一切众生皆发无上菩提之心。”[41]《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中菩提心与大圆镜智联系起来,说:“此名发菩提心真言,亦名大圆镜智。速令发菩提心,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即是法身之义。”[42]《金刚顶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时处念诵成佛仪轨》载:“种种开示已,教发菩提心,授与佛性戒,金刚坚固禁,当引入轮坛,灌顶受职已,令瞻覩圣会,告示三么耶,从今至成佛,莫舍菩提心。”[43]到了后期的密教中,菩提心与满月结合起来,与瑜伽密教的月轮观有直接关系。《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载:“云何名菩提心?诸佛告言,汝观心中字门本性清净,如净满月。”[44]
(三)佛顶法与般若性空思想
般若性空思想亦贯穿佛顶法。《陀罗尼集经》载:“作般若三昧禅印,先观四大色毕竟空,无有真实,次观五蕴,知其性空,不可得,即心寂灭三昧,观色性不可得,即色寂灭三昧。若证此三昧时,心生大欢喜,或见诸境界,不得取着,灭除一切诸重罪障。若见他障,为彼作印,诵陀罗尼,即得除灭一切罪障。”[45]相似的说法亦出现在佛顶法后期经典《一字佛顶轮王经》中,说:“观照四大色毕竟空,体无真实。复观五蕴,其性亦空。如法界性无我无人,亦无受者可得之法,心则寂静。复观静心,心亦无住。咒者诵咒每时数毕,常作斯观。若见种种神变境像,特勿取着,自静见心,即得灭除一切罪垢。”[46]此中说到无我、无人、无受者,也即无我无我所,能所具泯,取消了主客观二元对立。在克服能所对立之后,又反观自心,此时的心称为静心,亦即清净之心,接着又说此静心亦无住,破除对此静心的执着。这里的空观是彻底的,并没有停留在顽空的地步,对空亦破,达到一种不住空、不住有、空有之间亦无所住的宗教境界。般若经是最初形成的大乘经典,旨在阐明“性空假有”的中道实相,其理论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小乘佛教思想,诸如对于小乘法有我空的破析、对于只追求自我解脱的超越、对于出世隐遁的突破等,俨然标明佛教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般若思想作为最初兴起的大乘佛教思想,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一字佛顶轮王经》载:“密迹主!此一印咒名如来般若波罗蜜三摩地门,所有三世一切如来诸大菩萨独觉声闻等皆从此般若波罗蜜印咒三摩地门生,成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地。是知此印咒有大威德,名主三世一切如来诸大菩萨一切金刚独觉声闻之母。”[47]此段论述与《大波若经》极其相似,只是般若波罗蜜三摩地变成了咒,类似的论述在佛顶类经典中还有很多,这也反映出密教对大乘经典的吸收和密教化的改造。
《陀罗尼集经》载:“掌中画作七宝经函,其中具有十二部经,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藏。”[48]这里提到十二部经,十二部经亦称十二分教,其就是佛经编写的十二种题材或者说十二种不同形式。十二分教是随着部派佛教逐渐形成的,起初有九分教的说法,十二分教是后来的说法。吕澂说:“十二分教是新说,在此之前还有九分教的旧说,旧说就不包括‘方广’。”[49]也可以看出,十二分教是大乘佛教产生之后,为了把自己的经典体系纳入“佛说”的范畴,从而扩展了小乘佛教九分教的说法。而密教则吸收了新的理论,并没有选择九分教的说法,而且明确说到“般若波罗蜜多藏”,也即般若类经典,可见般若经影响极大,直接被密教吸收。但是在继承大乘佛教思想的同时,也做了符合自身理论的改造,使其密教化,为自身密教体系服务。如《陀罗尼集经》载:“若欲修行般若波罗蜜者,一食斋戒,香汤沐浴,着新净衣,入于道场要当先诵此陀罗尼,并作此印,满百万遍。然后修行余般若法,决定成就,是故名为般若根本。此陀罗尼印悉能照了一切般若波罗蜜法,故名般若波罗蜜眼。此陀罗尼印悉能摧灭一切障碍,悉能住持一切诸佛菩萨功德,故名金刚般若心也。”[50]明显可见,佛顶法虽然吸收了般若思想,但是增加了陀罗尼、手印,进行了密教化的改造,为我所用。
(四)佛顶法与净土思想
净土思想在持明密教时期的佛顶法中也有反映。净土思想萌芽于原始佛教,公元前3世纪(至晚公元前2世纪)弥勒兜率净土信仰兴起,稍晚弥陀西方极乐净土也起源,两种净土信仰大致皆流行于西北印度、东北波斯、中亚、西域这一区域,随即沿丝绸之路进入于阗、河西走廊,最后传至内陆,影响愈大,并最终形成中国佛教净土宗,蔚为大观。①相关内容,亦可参考张文良《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2期;汪志强《印度佛教净土思想研究》,2006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普慧《略论弥勒、弥陀净土信仰之兴起》,《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唐以后中国佛教逐渐成了“户户阿弥陀”的情景,也可见净土思想之影响。净土信仰之所以如此兴盛,流传不绝,主要原因在于净土是信仰者的最终归宿,无论普通信众还是高僧大德,无一例外都希望命终之后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据经典描述,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至极。
密教兴起之初,尤其在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时期(大约藏密所说“事续”时期)虽然主要以获得现世利益为目的,实现通常情况下难以达到的欲求,包括生命、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命终之后的存在形式与状态仍是密教思想关注的主题,当然,无论是弥勒兜率净土还是弥陀西方极乐净土都提供了很好的选择,所以净土思想也被佛顶法吸收。
《陀罗尼集经》卷三载:“若有行者日日作此印法并诵咒者,能除一切四重五逆恒河沙等罪,皆悉消灭,十方净土随意往生,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51]又说:“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常见诸佛。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为一切众生令好念佛故。”[52]同经卷八载:“次发愿云……若命终时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常见诸佛,一切众生亦复如是。”[53]亦载,“若人日日作此印法种种供养者,即得大验,死生阿弥陀佛国,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54]可以看出往生净土也是密教信仰的最终目标,但这里说“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可见净土并不仅限于弥勒净土或弥陀净土,而是十方净土。之所以是十方净土,这与“十方三世诸佛”有关。《陀罗尼集经》载:“从今已去,若在人间,常闻大乘甚深经法陀罗尼藏十方诸佛大悲名号,不见恶事,不闻恶法,不遇外道,不遭九横八难八苦,若命终时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常见一切诸佛。”[55]这里明确说“常闻十方诸佛大悲名号……命终时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可知十方净土与十方诸佛有关。相似的记载亦见与该经他品,说:“此是十方三世诸佛大三昧陀罗尼咒印,若人至心受持读诵……周遍十方一切净土。”[56]这更证明了十方净土的由来。有时也说“诸佛净土”,可知每个佛都有自己的净土。如经所说:“若欲生诸佛净土者。昼夜各三时诵二十一遍,满三七日,如其所欲,即于梦中或见佛金色形象及菩萨形象,此是先相,即知当生净土。”[57]这里说“诸佛净土”就意味着净土并不唯一,不同的佛都有各自的净土世界。
可见《陀罗尼集经》所说的净土,首先,强调往生净土是命终之后的最佳选择,其次,净土并不局限于弥勒或弥陀净土两种,再次,相比较而言,在各种净土中较为强调弥陀净土。《陀罗尼集经》卷五载:“是一法印,能除一切水火风贼刀及王难。夜叉罗剎一切鬼神毒龙毒蛇系缚等难,若人日日常作供养,得观世音及诸菩萨等皆生欢喜,命终得生阿弥陀佛国,又复十方净土随意往生。”[58]可见虽强调弥陀净土,当并不排斥其他净土。
在佛顶法中,关于弥勒的论述并不多,且基本上以菩萨身份出现,全经仅有一处称为弥勒佛,而且在佛顶部早期经典《陀罗尼集经》中并没有提及兜率净土,可知弥勒及其兜率净土在经中影响并不大,但是对阿弥陀佛及西方净土却有大量详细阐述,明显可以看出极为强调阿弥陀佛[59]。同时也反复出现应诵持《阿弥陀经》的说法,如说:“当发心诵《阿弥陀经》”[60],又说:“若人日日香汤洗浴……诵《阿弥陀经》……一切罪障皆悉消灭。”[61]
《陀罗尼集经》中有《阿弥陀佛大思维经序分》,集中讲述供养阿弥陀佛的功德以及如何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等内容。载:“尔时观世音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四部众及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众生修行善法,得生阿弥陀佛国,并见彼佛,云何而得?佛告观世音菩萨言:若四部众欲生彼国者,应当受持阿弥陀佛印并陀罗尼及作坛法,供养礼拜,方得往生彼佛国土。”[62]观音菩萨发问如何往生阿弥陀佛国,佛告大众应当受持阿弥陀佛印并陀罗尼,还要做坛法,供养礼拜,如此才能得生阿弥陀佛国,也就是西方净土。又说到以众华散阿弥陀佛有十种功德,其中第九就是生阿弥陀佛国。接着又说了多种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途径,包括好心布施阿弥陀佛、燃灯供养、以香布施供养、恭敬礼拜、念阿弥陀佛功德、诵持阿弥陀佛陀罗尼等。诵持阿弥陀佛陀罗尼是密教的创造,而且前一个引文可以看出不仅诵持陀罗尼,而且结合了手印,这是持明密教的一大特点,较之陀罗尼密教有很大不同。“陀罗尼密教发展到4、5世纪,密教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就是有人取手印(mudra)与陀罗尼相配”[63],密教三密此时已具备身密、语密,意密的出现则更晚一些。“密教的手印就是改造大乘佛教中的手印法,并直接吸取世间印法而形成的,《持明咒藏》的编纂者最先把手印引入到密教中。”[64]这一重大变化在《陀罗尼集经》中也有反映。
《陀罗尼集经》中出现阿弥陀佛曼荼罗法。中央自然是阿弥陀佛,结跏趺坐,持阿弥陀佛说法印,阿弥陀佛右厢为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左厢大势至菩萨,又依次介绍阿弥陀佛大心印、护身结界印、坐禅印、灭罪印、心印、阿弥陀佛顶印、轮印、疗病法印,如此等等。总之,可以看出阿弥陀佛在《陀罗尼集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反复强调的仍是如何往生阿弥陀佛国,出现了阿弥陀佛曼荼罗,也可以看出密教吸收显教内容并使其密教化的痕迹。该经中也说到阿弥陀佛造像,载:“安置阿弥陀佛像已”[65],“置阿弥陀佛像”[66],“中心安置阿弥陀佛像”[67],此类说还有很多。当然所谓“阿弥陀佛像”可能是画像(密教中非常盛行)、塑像、造像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另有记载完全可以确定此时阿弥陀佛泥塑像已经盛行。《陀罗尼集经》卷二载:“又若欲得生彼国者,亦更以泥作阿弥陀佛像十万躯灭罪,死生阿弥陀佛国。”[68]此中说到“以泥作阿弥陀佛像”,可知此阿弥陀佛像并非仅指画像。①普惠认为,“弥勒造像在西北印度、东北波斯、中亚、西域非常盛行,而弥陀造像则是在中国内地发展起来的。”(见:普慧《略论弥勒、弥陀净土信仰之兴起》,《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第147页。)通过本文粗浅的研究,可以看出,起码泥塑阿弥陀佛像在中亚地区早就盛行。佛顶是《陀罗尼集经》新出现的神祇,此中也出现阿弥陀佛顶。
(五)佛顶法与金刚神崇拜
金刚神发源于早期佛教,经过《密迹金刚力士经》《华严经》等经典的传扬,逐渐突显出来,成为新兴的一类神祇,在密教尤其瑜伽密教中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金刚藏菩萨,梵文vajragarbha[69],也是金刚神家族的重要一位,其在《陀罗尼集经》中也非常突出。金刚藏神与《华严经》及其眷属经《十地经论》有直接关系,正是通过《华严经》进入佛教核心神祇体系,而早期密教如《陀罗尼集经》正是受其影响。“何故名金刚藏?藏即名坚,其犹树藏,又如怀孕在藏,是故坚如金刚,如金刚藏。是诸善根,一切余善根中其力最上,犹如金刚。亦能生成人天道行,诸余善根所不能坏故,名金刚藏。”[70]《十地经论》解释了金刚藏的含义。在有些经典中,阿閦佛也被称为阿閦金刚藏,如《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载:“稽首一切薄伽梵,及以东方金刚部,雄猛阿閦金刚藏……”[71]而且金刚藏与密教中的秘密主、执金刚有时亦混用,如《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载:“南面秘密主执金刚藏王菩萨”[72]。与此相似,金刚藏亦同密迹金刚混同,如《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有“密迹金刚藏王”的说法[73],《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亦说“南面画执金刚藏王秘密主菩萨”[74]。在一些经典中金刚藏即是虚空藏,如《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说:“金刚藏者即虚空藏也”[75],《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也说“五者南方第一虚空藏大菩萨摩诃萨,号名金刚藏王”[76]。从上述引证可以看出,金刚藏、密迹金刚、秘密主及执金刚关系密切,很多时候混用,并没有明确区分,而这也正说明了作为金刚神家族的神祇有共通之处,而且在经典中更强调的作为金刚神这一类所具有的共性。正如吕建福先生所言:“持明密教中的金刚藏,即是早期密教中的金刚密迹,后来密教中的金刚手,手持金刚杵是其特点,但也有同执拂尘的例子。”[77]
三、结语
就佛顶法流传来看,发挥了对佛三十二相之一——无见顶相及灭度后佛顶骨舍利的崇拜,迎合了大乘佛教信仰主义盛行的潮流,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多种宗教并行的信仰状况,为佛顶法的流传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佛顶法自身又有意吸收、改造大乘佛教以来流传的主要佛教思潮,融合佛性思想、净土思想等信众最为关注的信仰问题,又极力宣扬曼荼罗无论在宗教修行还是满足日常需求方面的特殊功用,使佛教主流思想与密教实践结合,构建起较为精致的密教理论体系与宗教实践体系,把密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金刚界、胎藏界密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源泉,因此在密教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同时,密教的发展也折射出佛教其他派别发展的过程,比如佛顶法吸收了弥陀净土而不是弥勒净土,又比如佛顶法承认一阐提亦可成佛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思想史发展的阶段特征。但是佛教哲学作为宗教哲学,其与世俗哲学根本的不同在于一切宗教哲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也只是为其宗教信仰服务,佛教哲学也不例外。作为哲学层面的佛教(或佛教哲学)毕竟只是为了给作为宗教的佛教提供理论依据,密教的兴盛正是佛教作为宗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1][2][8][63][64][77]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4,32,36-40,36,39,259.
[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正藏(第49卷)[Z].100(中).
[4][5][18][25][27][34][35][40][41][45][48][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5][66]
[67][68]陀罗尼集经.大正藏(第18卷)[Z].[唐]阿地瞿多译.888(中),785(下),885(中),786(上),787(中),790(上),791(下),977(中),809(下),787(下),805(中),806(下),806(中),811(下),857(中),823(上),892(中),788(下),826(中),828(上),800(上)-803(中),802(下),823(中),800(上).
[6][唐]明佺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卷)[Z].396(下).
[7][14][30][32][49]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5,152,157,159,156.
[9][10][11][12]K.查克拉巴尔蒂.笈多王国[A].B.A.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三卷)[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152-154,154,154,155.
[13]B.A.李特文斯基,张广达.历史导言[A].B.A.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三卷)[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4.
[15][16][17]一字奇特佛顶经.大正藏(第19卷)[Z].[唐]不空译.288(中),295(中),288(中).
[19][22][24][29]B.A.李特文斯基,M.I.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宗教与宗教运动(二)[A].B.A.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三卷)[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364,374,380,380.
[20][21]Ph.吉纽,B.A.李特文斯基.宗教与宗教运动(一)[A].B.A.李特文斯基主.中亚文明史(第三卷)[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342,350.
[23]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349.
[26][28][36][37][38][39][46][47]一字佛顶轮王经.大正藏(第19卷)[Z].[唐]不空译.233(中),236(中),237(下),254(中),261(上),233(上),236(上),245(下).
[31][33]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第12卷)[Z].[北凉]昙无谶译.407(中),407(下).
[42][71][72]尊胜佛顶修瑜伽法仪轨.大正藏(第19卷)[Z].[唐]善无畏译.371(中),368(中),368(中).
[43]金刚顶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时处念诵成佛仪轨.大正藏(第19卷)[Z].[唐]不空译.320(下)321(上).
[44][69]失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真言.大正藏(第19卷)[Z].391(中),385(中).
[70]十地经论.大正藏(第26卷)[Z].[后魏]菩提流支译.124(上).
[73]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大正藏(第19卷)[Z].[唐]金刚智译.28.
[74]慈氏菩萨略修瑜伽念诵法.大正藏(第20卷)[Z].[唐]金刚智译.597(上).
[75]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大正藏(第19卷)[Z].[唐]不空译.615(下).
[76]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大正藏(第20卷).[Z].[唐]不空译.3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