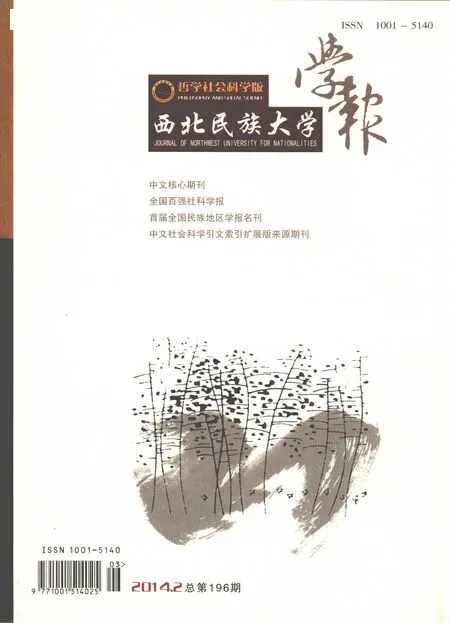《安娜与国王》——后殖民时代好莱坞电影的一次表意实践
杨 伟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
从1930年代美国银幕第一次出现中国题材电影浪潮之后的80年间,好莱坞电影一直在做多元电影题材的尝试,电影时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政治的温度计。20世纪末的政治大变动为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安娜与国王》恰是这一背景下好莱坞华语题材电影的又一次新浪潮。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好莱坞针对华语世界电影策略的改变
1.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好莱坞电影把尚未饱和的华语电影世界作为新世纪电影开发的新战场。二战之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在理论上常常表述为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依照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观点,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文化被不断沦为他者化的时代,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
随后殖民主义时代裹挟而来的电影文化奇观,在好莱坞电影市场开拓过程中越来越凸显着它的重要性。“东方”“落后”一度成为好莱坞电影中重点叙述的对象。而这种叙述很大成程度上带有好莱坞东方学意味的。自1978年萨义德发表《东方学》一书,东方学成为人文学科注目的理论。萨氏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划分,其意图与原始人划分花草一样,是为了把东方文化放在西方人觉得安全的秩序里[1]。在这个安全的臆想系统秩序里,东方文化(弱势文化)总是不免被西方文化(强势文化)所重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可以通过文化输出淡化甚至融化和改写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及文化,从而创造出西方意义上的新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电影文化在国家与民族,东方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非基督教世界,文明与野蛮,强者与弱者的意识形态大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大战中,电影机器俨然成为美国国家推行意识形态的有效机器。法国《电影手册》的编辑让—路易·博德里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一文发表了一篇极富实践性的论文—— 《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2],探讨了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他认为,电影的摄、放操作使电影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光学仪器隶属于科学实践的表面现象,及它们的技术性掩盖了它们本身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效果。与人眼相似的摄影机(意识形态附着于摄影机所采用的中心透视法)依据定点原则将视觉化客体组织成影像(远离现实的幻觉世界),视觉化客体也标明了先验“主体”(摄影机、人眼)的位置(那个必须被占据的点);而放映操作24画格每秒的放映速度,模拟人视觉的运动方式及速度,掩盖了摄影机所具有的特殊机械性,让非连续影像以原样而连续运动。同时,隐藏摄放机器造成的观影情境与镜式情境的相似使观影主体既认同于影像(中间透视的空间)中那个虚幻的世界,又认同于占据先验主体位置的摄影机;观影主体自觉地把想象投射到那个也是被自己的眼睛组织起来的具有统一含义的连续体上(误认),从而建立起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二元世界。这样,电影通过对一个中心位置的幻觉式界定而构造出“主体”的同时,又在无意识状态中“询唤”出意识形态效果。“它是一种注定要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3],“它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模型相辅相成”[4]。因此,摄影机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电影文化通过其特殊的观影模式,让人们忘记了现实,活在了电影创造的当下意识形态中。
好莱坞已经太深地融入了美国文化,无法逃脱美国政治的影响。在好莱坞向国外推销电影作品的历史上,美国这架国家机器,可以说从开始就扮演着护卫和先锋的角色,将电影当做一种商品来推销,这架国家机器的功能不仅引导电影拍什么(历史上的海斯法案不但规范了好莱坞电影、强化了基督教信仰,对于好莱坞电影所到之处社会文化的影响更大)和如何拍电影,并且为电影的拍摄、发行、放映、输出创造有利条件。为了给好莱坞市场准入创造条件,美国不惜采用一些不同凡响的外交手段甚至政治和贸易惩罚手段来扩展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美国政府一直是美国经济和美国文化全球化的有力后援。美国政府与好莱坞之间形成稳固的互惠关系,好莱坞成为传递美国文化的有效途径,而美国政府帮助好莱坞扩大其传播范围①好莱坞与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商业和进口谈判的关系。美国在外国的各种政府机构还专门负责收集各国的电影市场的情报,撰写大量调查分析报告,以供电影商参考。甚至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将电影议题纳入了与其他国家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之中,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业在美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外交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以至于美国政府肯为这个一百年前被喻为小玩意的东西架桥铺路。。
崇尚自由、爱好和平、打击邪恶、拯救人类、英雄救美等这些被普同化的叙事内容被好莱坞类型电影无数次地搬演,而这样的循环搬演却屡屡成功。人们在欣赏好莱坞大片的同时,也在接受着好莱坞电影带来的文化大餐。这个包含有基于西方的、督教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电影在华丽的外包装下,进入到它可以想到的任何区域,其作用远甚于漂洋过海、长途跋涉的传教士。在这里电影凌驾于个性特色之上,发挥着社会仪式的功能。全球化背景之下东方的中国必然是美国电影意识形态重要的实践之地。
2.好莱坞电影内容由早期外形上的他者奇观化进入到他者客观化时期。对“美国电影里的他者形象”这一课题,美国学者陶乐赛·琼斯早在1955年就曾向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附设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提供了一份名为《1895—1955年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印度的演出》调查报告,但是在21世纪以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并不太关注,相关论文寥寥无几,较有价值的文章有李一鸣于1997年发表于《大众电影》第7期上的《银幕谎言:好莱坞电影中妖魔化的华人形象》,进入21世纪,伴随国内学者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课题的关注,“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也开始为人注意,出现了张英进的《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论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周宁的《双重他者:(落花》的中国想象》等较有影响的论文[5]。“他者”的概念是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早期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积累了许多有关“他者”的记述和认知。一大批传教士,殖民官员,探险家乐此不疲的进入这些“他者”文化中,在与他者的不断接触中人类学诞生,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观、种族观出现:“西方人把新大陆和非洲等为代表的‘他者’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这一与‘他者’相对应的西方被认定是理性和文明的世界。”在对“他者”的种种历史表述中,电影无疑是千年来最成功的。这种表述也由早期赤裸裸的、无遮拦粗俗的奇观化呈现进入到安全、隐秘的状态中。《安娜与国王》恰是新时期后殖民主义时代“他者”暗语在电影中的一次有效实践。
二、《安娜与国王》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
这部由20世纪福克斯投资,安迪·坦纳特(Andy Tennant)执导,拍摄于1999年的电影《安娜与国王》,迄今已经15年。电影是1946年的好莱坞经典歌舞片《国王与我》的翻版,两部电影都取材于同一个真实的故事《安娜的日记》。由个人传记改编成小说,又由小说改编成电影。故事讲述了寡居的英籍女教师安娜·里欧诺文与暹罗(泰国旧称)国王之间著名的爱情故事,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主题 。两部电影不同时代换汤不换药的改编方式中蕴含着好莱坞叙事策略的改变。1946年版的电影当中启用了丽塔·莫雷诺、尤伯连纳、德博拉·克尔、艾伦·莫布雷、查尔斯·欧文等主演,所有的主演都以西方人的面孔为主;1999年的电影《安娜与国王》启用了华人影星周润发,就演员阵容而言叙事策略的改变可见一斑,老牌的福克斯电影公司在同一内容不同版本的电影叙事策略上可谓费尽心机。
在早期西方电影史上当影像中的西方人要遭遇非西方人时,电影叙事中一定是耻于与“他者”为伍的,所有的西方文化寓意当中的“他者”都由西方人自己来承担。好莱坞早期电影叙事中的有色人种都是由白人来扮演的,电影理论家罗伯特·史达姆认为这样的扮相带有三种侮辱①1.你不值得自我表现;2.你的群体中也没有人能够表现你;3.作为电影生产者的我们也根本不在乎你的愤恨的感觉,因为我们有力量,而且你对我们的做法没有任何办法。参见罗伯特.史达姆.文化研究与种族[M].郭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社,2006.326.,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白人对非白人社会的一种想象性征服。这种让人难以理喻的电影现象,缘于西方人无法接受作为“他者”的非西方男人对于种族秩序的颠覆和对西方社会的象征性入侵。非西方作为他者,不仅是西方自我的对立面、扩张的疆界和否定与征服的对象,同时也可能是威胁着西方文化价值并导致西方文化毁灭的致命危险所在。也因此,无论叙事的类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非西方的形象始终无法逃脱作为被虚构和想象的他者。
从1946年到1999年世界将要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在这短短的五十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从地域上隔离了西方社会对“他者”的主观臆想。把对他者的主观臆想转入到客观化的时期,在尊重“他者”文化的基础之上重建”他者”系统,由“他者”奇观化进入他者叙述的隐秘、客观化阶段,在电影叙事当中呈现为:“他者”由幕后走到台前;由小丑、奸雄到英雄、王者;发生由《华人洗衣铺》《破碎的花朵》《阎将军的苦茶》到《花木兰》《功夫熊猫》《安娜与国王》的嬗变。
影片《破碎的花朵》是默片时代的电影大师格里菲斯在1919年的一次电影实践,其实践跨越了时代的潮流,讲述了一个非白人男子对西方女子的异性追求。这样的实践,在彼时的西方人眼中显然是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产生过分的争议,格里菲斯无奈地让这对异色恋人双双死去。影片结尾的这样一种处理无疑是关于白种人与他者之恋最温婉的表述。格里菲斯被誉为是默片时代最早对非西方文化有比较正面刻画的电影人。异族相恋、通婚这一敏感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有声片中继续得到延续。1932年的影片《阎将军的苦茶》中,中国军阀爱上了一位西方女子,西方女子也钟情于这个东方男人,跟《破碎的花朵》一样,死亡是解决这个难解之题的唯一办法。到了世纪末的《安娜与国王》虽未以死作为结局,但这种与“他者”的恋情是修不成正果的。
历史学者姬虹在其学术研究中《美国移民跨族婚姻的历史与现状》[6]一文中翔实地记载了美国历史上他者之恋的艰难之路:1661年的马里兰最早产生反异族通婚法,禁止自由人—奴隶或白人—黑人通婚,违者处以重罪。到20世纪20年代,共有38州有禁止白人/黑人通婚的法律。反异族通婚法始于美国南方,但随着移民进入和开发西部,该法律也延伸到此地,并且得到完善,涉及的对象也不仅仅在于白人—黑人,而是扩展到来西部“淘金”的亚裔,在亚裔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人。持续将近三百多年反异族通婚法最终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垂死挣扎,最后北卡罗来纳州于1998年、亚拉巴马州于2000年11月通过公投废除了该法。但事实证明,跨种族婚姻的道路并没有因为解除了法律上的禁令,而变得平坦。影片《安娜与国王》作为20世纪末的影像,以一种暧昧温情的叙述一笔带过这段历史,但怎么也跳不出300年遗留的烙印,安娜与国王无论怎么互相欣赏都不会走到一起,究其原因是深刻的。
综观好莱坞电影历史,影像中的女性大底以弱者形象出现,女性常常成为影院中男演员和男性观众欲望的对象、拯救的对象。①美国学者劳拉穆尔维在其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深刻讨论了电影中的女人在观看癖的驱使下被电影院中满足男观众及影片中的男人的欲望,女人在男权文化的电影文化中只能是被拯救,帮扶和欲望的对象。而在影片《安娜与国王》中,一反常态的让安娜这个寡居携子的女性成为其所处异文化空间的主宰者、自我命运的救赎者。影片处处刻意强调安娜的女性身份,在泰国东方式的古老而传统的王宫中,来自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弱女子无所畏惧地与暹罗王对峙,发表自己的高见并要求他人接受。在一大群匍匐在地的棕色人种中卓然傲立,坚持不跪。其勇敢的行为让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们大为快意。影片不遗余力将安娜对暹罗王室的“卓越贡献”进行了描写: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挽救了国王的生命间接保存了泰国王室,甚至她的思想对未来国王的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在西方文明社会中羸弱的小女子改换空间后在异文化中顺势变得无比的强大。好莱坞的深层话语机制,难道真的只是在影像中单纯地塑造这样一位坚强、独立、勇敢的女性吗?《安娜与国王》实际通过温和而且动人的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爱情故事构建强大的西方文化征服并拯救传统的东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好莱坞电影英雄救美版本的一个异化,只是在这部电影中完全颠覆了西方电影传统叙事中的英雄施惠者的男性形象。完美的包装之下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再一次通过电影文本自恋式的肯定了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用隐秘的手法将东方文化安排在了自己臆想中合适的位置。
《安娜与国王》世纪末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意识形态电影实践的成功范本,它折射出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复杂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后殖民主义时代多元文化交融沟通、甚至碰撞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观影群体心理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复杂。东方文化或者“他者”文化必将成为好莱坞缓解影视资源枯竭和观众审美疲劳危机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安娜与国王》这样的东西方文化汇合成就的好莱坞电影的成功表意实践只是转入新世纪好莱坞的一个开始,不仅因为文化资源、电影市场,更重要的是因为意识形态。
[1]王铭铭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M].天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22-123.
[2]路易·博德里.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A].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547.
[3][4]让—路易·博德里.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A].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564,564.
[5]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221.
[6]姬虹.美国移民跨族婚姻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3):5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