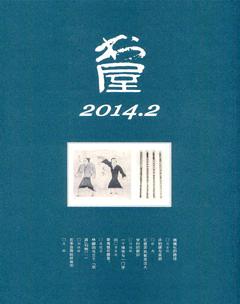记忆·思考·审美
孙德喜
2007年夏天,在上海同济大学的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结识了年过八旬的来自北京的毛宪文先生。会后他不顾酷暑炎热来到扬州游玩,我一路陪同,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并且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几天前,毛先生给我寄来了他新近出版的三十七万字的巨著《甲子集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我为毛先生在耄耋之年出版著作再次深深感动,于是花了几天时间通读了这部厚实的著作,觉得这是他自1952年大学毕业以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体现了他在这一个甲子年里的记忆、思考以及对艺术美的审视。
毛宪文先生,蒙古族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至今已过一个甲子。六十年来,毛宪文先生勤奋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思考,写下了为数可观的文学评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现在他将这些结集出版。在他的这部著作中,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历史记忆。毛宪文先生出生于1926年,不仅见证了六十多年来共和国的历史,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时代的风风雨雨,而且由于他长期在鲁迅文学院工作,接触到许多著名作家,因而,他的历史记忆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丁玲、邓刚、乐黛云、刘绍棠、马烽、黄秋耘、废名、乌尔热图、李发模、赵本夫、胡正等数十位作家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丁玲的回忆。我们对丁玲的坎坷人生与创作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但是对她创办文学研究所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则了解较少。毛宪文先生在书中详细叙述了丁玲在辅导教育青年作家方面的具体事情,从而让我们了解到作为文学教育家的丁玲。这样,丁玲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更加全面、具体和丰满。与此同时,毛宪文先生还记述了丁玲与新加坡作家的交往以及她对新加坡华人文学的深刻影响,为中新文学交流史、比较史提供了非常具体而珍贵的史料。至于其他作家大大小小的逸事不仅让我们了解到生活中的作家,而且对于研究这些作家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甲子集粹》中,毛宪文先生还写了长篇文章回顾自己从“九·一八”到“八·一五”的人生经历,从个人视角叙述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毛宪文的这些回顾性和怀念性的文章虽然并不系统,比较零碎,然而无疑是最具体鲜活的历史呈现。
毛宪文先生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学者,他不仅研究作家作品,而且善于对各种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高洪波在《甲子集粹》的序中借用陈建功的话说,毛宪文先生的书中“不乏独到见解”。而这“独到见解”显然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晶。从毛宪文的思考来看,他着力于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具体地分析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使他有别于一些人玩弄概念,在空洞的理论间钻来钻去。所以,他由思考提出的意见还是给人以亲切感,很容易让人接受。在谈到青年学者赵焕亭论丁玲的问题时,毛宪文先生觉得赵焕亭在研究中“没有尖锐地毫不留情地指出:所谓丁玲晚年丧失创作个性特色的妄说,其目的是希望丁玲这样的大作家不应该这样去写,而应该违心地迎合某些人的趣味”。毛宪文先生的这个看法虽然不一定为人们认可,却也符合丁玲当时的心态。
在《甲子集粹》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对古今文学作品的评析。毛宪文先生的评析都很短小精悍,要言不烦,一语中的,揭示出古今文学名篇的思想内涵、文化意蕴以及艺术特色。毛宪文先生写这些评析文章很可能是他在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和中学任教时的讲稿。而他的这些文稿写得非常朴实,就同他的为人一样,厚道而中肯。因而,他将自己的人格理想和人生追求融入到文学名篇的审美当中来,从而使他的审美别具一番风味。
毛宪文先生的《甲子集粹》让我们看到与共和国一道成长的作家的信念和追求,个性和风采。从他的人生来看,他既受到极左政治的迫害,感慨于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不幸,更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他以真情真意投入写作时,我们看到了他的独特姿态。而且,我们还注意到,毛宪文的写作显然不同于那些大作家的自我表现,主要是他作为铺路石的写作,他无论是回忆历史,还是思考问题,抑或是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评论,都是为了启发青年,提携后学,甘为他人作嫁衣,确实令我们敬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