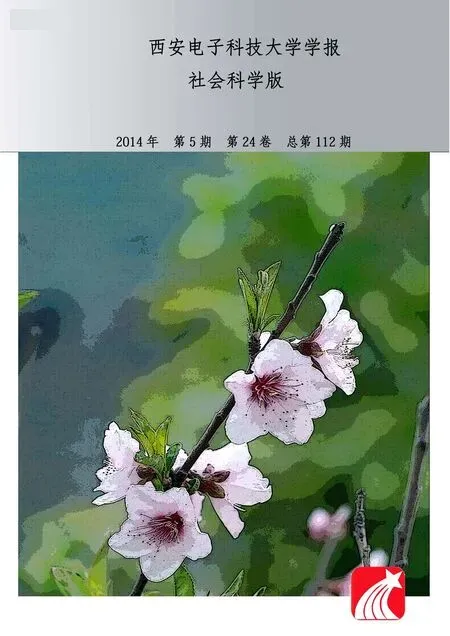折翼在现实“围城”中的纯真情爱
——透析《边城》田园梦幻背后的悲剧意蕴
田丰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文学
折翼在现实“围城”中的纯真情爱
——透析《边城》田园梦幻背后的悲剧意蕴
田丰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充满魔力的爱情虽然足以征服青年男女炽烈的心,却时常无法挣脱现实的羁绊,因而即便是纯真的爱情也难免会在现实的“围城”中折翼。在《边城》中诚然有着非常浓厚的田园牧歌情调,但同时又对现实给予了或隐或显的关注,这在翠翠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中有着明确的体现。究其实质,翠翠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既非外在的暴力迫压所致,也非盲目的命运观念使然,而是更多地体现为爱情和包括身份、地位、习俗、责任等等在内的现实因素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
沈从文;《边城》;悲剧意蕴;现实“围城”
在以往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中,《边城》往往被视为一方未曾沾染尘俗的乐土,一个充满世外桃源意味的理想化的世界,这里人美景美,给人一种亦真亦幻如入梦境般的感觉。然而就在牧歌情调掩映下却不时跳动着不和谐的音符,并由此触发起我们对小说中人物命运浮沉的关切和哀叹。翠翠母亲、父亲和翠翠、傩送两代人原本为世人艳羡和翘盼的琴瑟和鸣却最终化成凄婉的不绝哀鸣。面对如此惨剧,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情人无法两情相悦反倒要生离死别?
一
从翠翠母女两代人爱情故事牵涉到的人物来看,无论是老船夫、翠翠父亲、杨马兵,还是顺顺、天保、傩送等都不是极恶之人,小说中生活窘迫的老船夫清贫自守、为人忠厚,自不待言,即便饶有家资的船总顺顺非但不仗势欺人,反而急公好义、为人慷慨,因而以往常见的滥施封建家长淫威横加干涉子女婚姻的叙述套路在《边城》中踪影难觅。那么既然悲剧的主角是母女,是否跟她们的性格有关呢?我们知道翠翠母亲幼时虽然也曾“乖得使人怜爱”①,但她敢于大胆追求爱情,不仅通过对歌为自己选定如意郎君,而且还背着忠厚的父亲与恋人发生了暧昧关系以致未婚先孕,直至为了爱情付出自己的生命;而翠翠虽然也在风日里长养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但给人的整体感觉却更像一个乖乖女,对于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在爱情的追求上也始终是腼腆、被动的,在她身上已几无其母亲刚烈性格的遗存,甚至连对歌的能力和勇气也已经丧失殆尽,生命力显得极度弱化。既非人为暴力迫压造成,又非人物性格使然,那么是否是偶然的命运造成的呢?这在文本中似乎也有据可循,老船夫不是已隐约感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吗?然而深究其实,以“命运”二字来概括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不免显得大而无当、过于笼统,既无助于我们理清爱情悲剧的精神实质及其真实成因,也无法解释为何在大老求婚时老船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而一到翠翠喜欢二老不爱大老时就认为可能重蹈翠翠母亲爱情悲剧的覆辙。退一步讲,既然有翠翠母亲的前车之鉴,而且老船夫在大老求婚时已经担心翠翠是否能够接受,为什么不在征询翠翠的意见后再作决断呢?要解开这些疑团,我们还需把翠翠父母、翠翠和傩送间的爱情悲剧综合起来以便找寻真相。
以往论者往往将笔墨集中在翠翠身上,对翠翠母亲却少有论及。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与《边城》故事情节的安排有关,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俩间的爱情纠葛无疑是作者论述的焦点,而在长达 21节的故事文本中只有6次提到翠翠母亲,字数加在一起也不过600左右,但这些文字却均匀地分布在故事的各个部分(分别出现在第1、7、11、12、13、21节),“从头到尾,翠翠父母的故事都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1]150。故事刚刚开始,作者便向我们介绍起翠翠父母的恋爱悲剧。十七年前身为老船夫独生女的翠翠母亲和一个屯防军人通过对歌心生爱慕而私定终身,在怀有身孕后两人约定一起私奔,却因翠翠母亲不忍心抛下孤独的父亲作罢,最终军人服毒自尽,翠翠母亲在生下翠翠后也寻了死路。故事听起来并不复杂,但也恰由于过于简略不由得让人疑窦丛生。从苗地的风俗来看,“勾勾伞‘勾’幸福,边边场上定终身”是其婚恋常态,男女间“以歌为媒”通过对歌自由婚恋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他们为何不能正常结合而偏要选择为爱殉情呢?究竟是什么阻碍着他们无法成婚?
以往曾有论者提出翠翠父亲是汉人,由于苗汉不通婚方才导致悲剧的发生,粗看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早在乾嘉年间,清廷为镇压苗民起义曾调集七省十余万兵力血洗了此地的一个个苗寨。事变平息后,清王朝在重兵驻守的同时,还采取“以苗治苗”的方略,“设苗兵控制苗人,设屯兵控制苗兵,设绿营控制屯兵,保境息民”[2],在防地划分上则让苗兵驻在各乡,屯兵驻在各县以便层层控制。茶峒作为处在三省交界地带的军事重镇成为清朝实施“苗防屯政”的协台治所,嘉庆七年相当于师级的永绥协即驻守在此,其招募的士兵全部是汉人,驻防官兵多达一千余人。翠翠父亲既然身为驻守茶峒的一名屯戍兵,而且文中特意交代“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翠翠父亲也的确是“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那么基本可以肯定他是汉人。有清以来对于苗汉通婚曾数度开禁后又再行禁止,康熙四十三年颁布禁止苗汉通婚法令;雍正五年又经湖广总督奏请发布禁令,苗汉结亲者要“照违制律,杖一百,仍离异”,甚至媒人也要“杖九十”;雍正八年又准许民苗兵丁结亲,令其自相亲睦,以成内地风俗;乾隆二十九年为化遵苗民,以苗人向化日久,准与内地民人姻娅往来;乾嘉起义期间苗汉亲戚往往互通消息屡屡泄露军机,清廷有感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再次禁止苗汉通婚。但因边地艰苦,加上戍卒众多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因而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大打折扣。当地汉族上层人物为了延续子嗣或有将苗族婢女收房纳妾者,在生下男丁后再将苗女远嫁他乡,假称已死在本地做一假坟供子孙祭拜。沈从文的亲祖母即是在生下二子(即沈从文的父亲)过继给沈宏富(沈从文的爷爷)后被嫁到远方,直到他二十岁时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从小祭拜的正是其苗裔祖母的假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有着苗族血统的孩子不仅会遭受歧视,也不准许参加文科武举。然而上述情况大多只发生在类似沈家这样的上层汉族家庭之中,对于下层士兵而言却基本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顾忌,通过同为屯戍兵的杨马兵也曾追求过翠翠母亲这一事实就可证明汉人身份并不足以成为翠翠父亲与翠翠母亲正常结婚的阻碍。而且在小说中,也确已点明“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这些住户中,除了一部分……小资本家外,其余多数皆为当年屯戍来此有军籍的人家)”。由此可见,汉人戍兵在当地成家已然成为常态,且在成家后大都已经脱离军籍。那么究竟如何方能对此做出合情入理的解释呢?
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基本认定翠翠父亲的汉人身份,但因翠翠母亲是苗人,而他们又身处苗人聚居地区,因而在婚恋问题上更多地还是要遵从当地的苗俗,而且从他们对歌相恋也可以看出翠翠父亲对于苗人习俗不仅完全熟习,他也确然是按照苗人礼仪展开爱情攻势的。我们知道湘西苗族虽然婚恋比较自由,但到了谈婚论嫁之时却也有着一系列的仪式,“无论自由婚或包办婚,从婚约的缔结到成婚,苗族有自己的风尚、礼仪和规矩”[3]327,其中比较关键的环节就有男方必须向女方家登门求婚,而且按照习俗“亲要多求为贵”,即男方要多次到女方家央求,得到女方家父母同意后方才算正式订婚。虽然老船夫只有一女,按照苗俗家中有女无儿者要招入赘女婿,但还是要男方登门求婚的,在杨马兵代大老求婚时也曾提到“这件事照规矩得这个人带封点心亲自到碧溪岨家中去说,方见得慎重其事”。那么是否是因老船夫有意阻挠而无法成婚呢?有学者就曾大胆推测说老船夫应该对此悲剧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其论据是“老祖父是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当兵的,因为当兵的人要开拔的……矛盾的是女儿爱上了一个要远走的人,而且又爱得那么深,杨马兵不是说,我也唱过歌的,可是她始终不理我,但当兵的一唱歌,那个女的就跟他好上,不仅好上,而且有了孩子”[1]151。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其中的一个明显疏漏,因为照这句话的意思显然认为杨马兵不是当兵的,但在文中已经明确说明杨马兵(谐音即“养马兵”,绿营兵按照兵种可划分为马兵、步兵和守兵,又因步兵和守兵都无马,通常也以马兵和步兵来划分绿营兵,因而杨马兵极有可能并非是其本名,而是以此来借指杨姓马兵,在小说文本中“特为证明那马兵所说的话有多少可靠处”这句话事实上也的确含有此意)年青时即在军营做马夫,在老船夫死后他照顾翠翠时还需先“回城去把马匹托营里人照料,再回碧溪岨来陪她”,三天后船总过来接翠翠时因翠翠不愿进城“只请船总过城里衙门去为说句话,许杨马兵暂时同她住住”,由此可见杨马兵“原本和翠翠的父亲同样当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翠翠父亲是否一定要开拔,对此我们要特别指出翠翠父亲是屯戍兵的这一特殊身份。因为湘西屯戍兵是在实行“苗防屯政”后才出现的,而此前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湘西来的绿营兵的确有固定的驻防年限,一到期满便可返回故乡。在实施屯防新政后保存下来的《苗疆屯防实录》中我们看到关涉茶峒所属永绥厅的这样一组数据:“永绥厅屯丁二千名……永绥厅老幼丁八百名、残废丁三百名”。而且事实上并非永绥一厅如此,凤凰、乾州、永绥、古丈坪、保靖县等五厅共有屯丁七千名,但仅凤凰、永绥二厅就共有老幼残废丁二千三百名[4]。这一点从杨马兵身上也可得到证实,因为直到老船夫去世时年近六十岁的杨马兵还是一名老兵,在得到消息后他也是“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岨去了”。由此可见,屯田新政实施后绿营的屯戍兵基本上固定驻守在某个地方,这些人即便是年老或残废后也都由屯田税赋供养起来,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翠翠父亲和杨马兵要追求当地的苗姑而不是等转移防地后再与汉族姑娘成婚。
此外,虽然翠翠父母间的暧昧关系是背着老船夫发生的,但从老船夫在为翠翠讲述起其父母的故事时也已经表明他对于翠翠父母的相恋是知情的:“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到了”。通过祖父讲述故事时的神态、情境及其内容都不难看出他对于翠翠父亲是比较满意的,对于他和自己女儿对歌生情也未加阻拦,显然持默许的态度,在文中也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表明老船夫直接反对过翠翠父母的婚事。
那么是否是因为翠翠母亲未婚先孕有违礼制而无法成婚呢?文中翠翠父母也确是“有了小孩子后”方才商定要一起私奔的,而且在事发后虽然老船夫只当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一样“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但翠翠母亲却“怀了羞惭”,以致在生下翠翠后故意寻了死路。然而,实际上苗人男女青年未婚即行野合多出自汉族文人的主观臆测,因为现实生活中“苗族青年男女通过对歌,谈情说爱,自订终身,一般都十分注意礼节,行为是很有分寸的,否则就会受到对方的鄙视和社会舆论的责难”[3]336。依照苗俗,尚未结婚的男女青年忌行房事,因而翠翠父母“野合”乃至怀孕在身的确是于礼不合的,而且“处女与人私通有孕,常吃水银打胎,有私生子则常溺毙”[5],况且他们也的确是背着老船夫发生的暧昧关系。但问题是未婚先孕并不会像已婚的萧萧在受到花狗引诱怀孕后那样面临“沉谭”或被发卖的危险,事实上,只要处女不是在怀孕后被人抛弃也还是有补救措施的。湘西地区原本就有“打三早”的婚俗,青年男女在以歌为媒私定终身后如果无法得到双方父母认可的话,他们也可以冲破家庭阻力结合在一起,待生下孩子后双方父母还得认账并重新补送嫁妆举行结婚仪典。因此其根节点恐怕并不在此,而是仍然出在为何“结婚不成”上。
这还得从翠翠母亲的独生女身份说起。按照苗俗,男子招赘后要居住女家,永远上门,而且在湘西“赘婿本人无财产权,一切主权概归女方,故入赘现象并不多”[3]222。在老船夫死后,杨马兵赶来料理丧事时曾对翠翠说:“爷爷的心事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对得起你爷爷。我会安排,什么事都会。我要一个爷爷欢喜你也欢喜的人来接收这只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在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杨马兵为了老船夫的何种心事以至于到了不惜以命相博的程度。如果爷爷的心事是指要促使傩送和翠翠完婚的话,似乎不必拼命也可以得到顺利圆满的解决,船总顺顺不是在刚过四七后就派人请杨马兵进城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的事了吗?这难道不是已经表明顺顺已经同意傩送和翠翠的婚事,只待傩送回返后便可完婚吗?但为何杨马兵在转达顺顺的意见时非但不主动促成反倒“又为翠翠出主张,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予以回绝呢?显然爷爷的心事应该另有所指,那么其心事究竟是什么。其症结恰出在渡船上,杨马兵要拼命完成的老船夫的心事其实是要找一个爷爷和翠翠都欢喜的人来“接收”这只渡船。此处要未来新郎接收的“这只渡船”并非单纯地与碾坊相仿佛的“陪嫁物”,而是要迎娶翠翠的人必须终生以撑渡船为业。既然是要依礼招入赘孙女婿,在孙女尚且懵懂无知之时老船夫本人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的,就连颇懂老船夫心事的杨马兵也说过“人家以为这件事情你老人家肯了翠翠便无有不肯呢”这样的话。惟有渡船相伴的老船夫并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产,但对渡船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别无他求,却偏偏想要招一个愿意接续自己以撑渡船为终身职业的女婿,这一点在文中是有据可查的。大老在与二老谈论自己的打算时就曾说过:“二老,你运气倒好,作了王团总女婿,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在大老死后不久,二老到川东办货经过渡船后脚夫询问他时也说:“你当真预备作他的孙女婿,接替他那只破渡船吗?”显然要得到翠翠是必须以终生操弄渡船为条件的,同为“陪嫁物”的碾坊却并非如此。文中借老船夫的口说过:“听说你们中寨人想把河边一座碾坊连同家中闺女送给河街上顺顺”,由此可知二老是迎娶团总女儿上门而非倒插门,而且碾坊也无须亲自动手操弄,婚后完全可以雇一个长年来打理,老船夫也正是借此来试探二老的口气的。
我们藉此可以梳理出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成因。在小说文本中,人人各司其职、忠于职守,都有着极其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即便是妓女也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老船夫几十年如一日,“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就连他养的那只黄狗也“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翠翠第一次偶遇傩送埋下爱情的种子是由于她看过龙船后在河边等待爷爷接她回家,但爷爷却迟迟未出现。老船夫之所以没能按约定接她,却是因为临时找来代替他守渡船的人醉倒了。虽然他也心急如焚地牵挂着翠翠的安危,但“为了责任又不便与渡船离开”,由此不难看出,渡船摆渡的职责在老人心目中是近乎神圣的;而翠翠虽然很生爷爷的气,但在看到家中醉倒着的另一个老人后便顿时消了气。由此可见,自幼受到爷爷行为耳濡目染的翠翠对于渡船的职责所在也是同样看重的。她在爷爷疲倦时总是代替他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也唯如此她才马上原谅了爷爷。当年翠翠父母之所以为了爱情双双殒命,正是由于老船夫、翠翠母亲、翠翠父亲三人各自担负的职责间的不可调和及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力量合在一起终而导致惨剧的发生。这要换成别人比如杨马兵或许还不至于如此,但翠翠父亲偏偏“又要爱情又惜名誉”,他无法在渡船和从军之间做出抉择。如果选择渡船则必然要退出行伍,这有违于他立志从军的志向,当逃兵私奔更有悖军人的荣誉;如果继续从军则无法接过渡船到女方家生活,这既违背了当地的习俗,也不符合老船夫择婿的条件,因此他无法与翠翠母亲按正常途径结合在一起。那么为何翠翠父亲这么看重军人的荣誉呢?这得从当时绿营兵的社会地位和薪俸待遇说起。绿营兵完全由汉人组成,在清代前期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承平日久、军纪松弛,战斗力极度萎缩。清代晚期,清廷为提高绿营兵的战斗力,在采取裁撤冗员,提高军饷等等举措的同时,还有意强化军队纪律以及增强军人的荣誉感。为稳定边境,清政府对远离故土的绿营士兵给予了特殊的优待,以便使他们能够安于职守。当时苗兵的薪俸极低,嘉庆二年湖广总督毕沅在迟至一年后方才得到朝廷批复的给予苗弁基本口粮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苗守备每名每年给银十六两……苗千总每名每年给银十二两……苗把总每名每年给银八两……苗外委每名每年给银六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名苗守备每年所得饷银十六两“尚不及各营战兵一年饷额”[6]。我们知道老船夫摆渡是由公家拨付钱粮的,但如果翠翠父亲接过渡船年收入却只有“三斗米,七百钱”,按照1两银子换1000钱,大约可买1石米,而1石是10斗折算的话共计1两银子,这也难怪老船夫的生活异常窘迫了。因而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等各方面来衡量,我们都不难理解为什么翠翠父亲难以轻易下定决心按照苗俗入赘女方家了,但身为独女的翠翠母亲却又不愿意抛弃孤独的老船夫和他一起私奔,因而才会在“结婚不成”翠翠母亲又已有身孕的情况下做出自杀殉情的选择。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绿营士兵都像翠翠父亲这样极端重视军人的荣誉,如同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军士已经自动放弃军籍而与当地的百姓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到了翠翠长大之时“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也正因此,杨马兵在事隔多年后回忆起翠翠父亲时还专门强调翠翠父亲既要爱情又惜名誉这一造成爱情悲剧的症结所在。
三
面对如此凄惨的现实,老船夫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必然会有所警觉,这直接表现在他对翠翠择婿问题态度的转变上,他一反以往凭其自然、听之任之的做法转而事必躬亲、关怀备至。天保和傩送兄弟两个虽然同时爱上翠翠,但首先正式展开爱情攻势的却是天保,老船夫对于他也是很满意的,他“记起前一次大老亲口所说的话,知道大老的意思很真,且知道顺顺也欢喜翠翠,故心里很高兴”,只不过为显得庄重些他想让天保按照本地规矩带封点心亲自上门求婚,因此才提出或走“车路”或走“马路”来“正正经经”地求婚。不难看出,老船夫还是很看好这门亲事的,实际上对他而言,天保无论是“车路”也好还是“马路”也罢都无关紧要,他唯一担心的是翠翠是否能够满意。为了打消男方的顾虑,他还特意同杨马兵说:“我若捏得定这件事,我马上就答应了”。当他一旦意识到“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后却马上联想到翠翠很可能会步其母亲的后尘,并为此感到害怕。那么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喜欢二老就会重蹈爱情悲剧?难道两情相悦的二老和翠翠就不能成婚吗?为何在大老求婚时老船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呢?
这也需从苗地的习俗说起,“按习惯,小儿子不出门,随同父母居住”[3]222,因此在分家时往往对小儿特别优厚,相应地小儿也要承担起赡养年迈的父母的义务。况且在船总顺顺看来,大儿子行为做事和自己最为相似,将来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创立家业,因而由着大老离门出户到老船夫家撑渡船过活;对傩送则不然,不仅要让他将来继承家业,还特意为他选定了有碾坊作为陪嫁的团总女儿。为人豪爽的大老对此泰然自若,他还向二老描述自己未来的打算:
二老,你运气倒好,作了王团总女婿,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我欢喜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一片大南竹,围着这一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但碾坊作为陪嫁在当地来说毕竟是极为罕见的,即便是对人事尚还懵懂的翠翠在偶然听到别人对碾坊和渡船的议论后也不禁心潮起伏:
翠翠到河下时,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是生气了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
从老船夫这方面来看,深谙当地习俗的他当然更看好的是大老而非二老,早在杨马兵代大老求亲之前,他就假借开玩笑对翠翠说过:“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在大老过溪时,心直口快的大老当着老船夫的面夸赞翠翠长得标致,老船夫不仅不恼,反而“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由此可见,他一心想要成全的是大老和翠翠的婚事,也正因此才会在得知真正唱歌打动翠翠芳心的人是二老后却并没有向翠翠挑明。事实证明,老船夫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二老在和大老对歌竞争时本“有机会唱歌却从此不再到碧溪岨唱歌”,在大老主动退出后原本志在必得的他却打了退堂鼓,而在大老死后中寨人又来向他求婚的关键时刻说出的却是那样模棱两可的话,他说:
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它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这在他其实也有着难言之隐,选择碾坊就意味着要永远失去翠翠,选择渡船又无法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而在大老溺水身亡后已成独子的他在“碾坊”“渡船”之间摇摆的太平已经更多地开始倾向后者。对于当地习俗了然于胸的老船夫显然对此也是早有预料的,他非常明了傩送面临的两难处境,因而才会显得那么急迫,不仅多次当面询问顺顺和傩送的意见,还急切地向中寨人打听情况。但也正因此,原本忠厚的他言语间便显得绕来绕去,这并非他故意要像文明人那样讲究,而是因为他充分了解这件事情的棘手之处,但为了孙女的幸福他又不得不说,因此才会一反常态,显得欲说还休、拖泥带水而不够爽快。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恰恰因为他“太小心了,太想把这件事做好”[1]152,反倒使得顺顺和二老都对他产生误会,非但求婚未果反而使得事情陷入僵局。
总而言之,翠翠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从根本上讲既非外在的暴力迫压所致,也非由于盲目的命运观念使然,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爱情和包括身份、地位、习俗、责任等等在内的现实因素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究其实质,正符合于王国维先生所总结的悲剧之大者:“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7],此事古难全,《红楼梦》如此,《边城》亦然,这也正应合着沈从文在文中所特意说明的:“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爱情的魔力之大足以征服青年男女那炽烈的心,却又时常无法摆脱现实的羁绊,从而引发起无数的人间悲剧,但也正因此种永恒存在而又始终难以超越的矛盾纠葛吸引、打动着无数读者去为之唏嘘感叹,洒上一掬热泪。在苦苦追求甚至以死相逼终于如愿以偿赢得美人归却又移情别恋于高青青的沈从文在蜜月期创作出具有悲剧意蕴的《边城》恐怕也绝非偶然,在某种程度上《边城》或许恰是深陷在现实“围城”中难以自拔的沈从文唱出的一曲哀歌。
[注 释]
① 文中所引《边城》中的文字均见于《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91.
[3]伍新福.苗族文化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4](清)佚名.苗疆屯防实录[M].扬州:江苏扬州人民出版社,1960.
[5]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00.
[6]谭必友.19世纪湘西“苗疆”屯政与乡村社区新阶层的兴起[J].民族研究,2007(4):70-79.
[7]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66-67.
本文推荐专家:
李慧敏,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及影视文学。
贺仲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及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
The Pure Love is Held Back by the Reality ——Dialysis of the Tragedy Implication Behind the Rural Dream of “Border Town”
TIAN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Border Town is marked with idyllic style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The love tragedy of Cuicui and her mother reflects that Border Town is not a pure land which is fully far away from reality. It also infiltrates blood and tears behind the rural dream. The beautiful natural scene of Border town is not completely isolated from the painful loss of life. The magical love can easily conquer the fiery heart of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but always cannot get rid of the fetters of reality. As a result, the pure love is unavoidably held back by the reality.
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gic connotation;Besieged by Reality
I207.42
A
1008-472X(2014)09-0095-06
2014-01-20
田 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