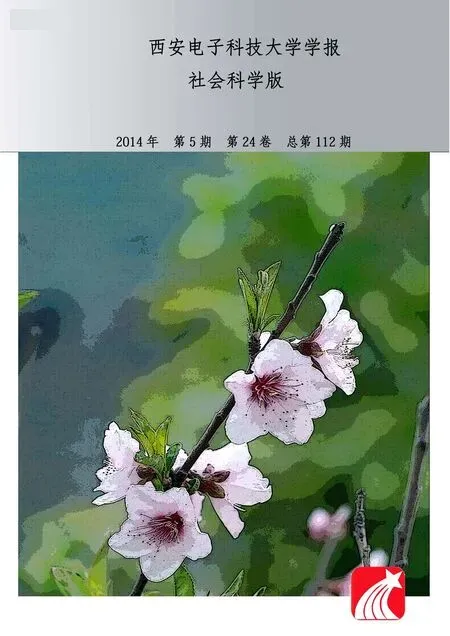企业低碳竞争力视角下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相关研究综述
刘鹤
(四川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1)
一、引言
快速工业化、商业化与CO2大量排放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困扰人类。2013年9月27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专门报告,进一步确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并指出气候变暖是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确认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95%。近年来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气候屡见报端,彰显着人类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多数科学家把气候异常归结于碳基能源过度使用造成的CO2大量排放。虽然碳排放缓慢的影响着全球环境,但正是因为它缓慢的特点而易被忽略,其潜在威胁更大,理应受到人类的高度关注。
缓解CO2过度排放已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共识,世界各国正采取措施减少生产经营及和普通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量。2012年12月的多哈世界气候大会,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十八大报告把资源节约、能源节约、再生能源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事项统一为“生态文明”,并把这些内容作为整个报告十一部分中的第八部分单独强调,环境资源保护、节能减排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从国家层面意识到发展低碳战略已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国家低碳竞争力概念应运而生。它衡量的是国家或区域在低碳未来为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低碳竞争力是国家或区域整体低碳竞争力的根源和具体表现,即提升国家低碳竞争力主要靠提高区域内的企业低碳竞争力来实现。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愈发受到强制削减碳排放及碳税等因素的约束,这意味着企业低碳竞争力将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1]。一般的说,企业低碳竞争力是指企业通过低碳生产和发展方式,在经营过程中及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有更好的低碳表现,从而在与其竞争对手竞分资源上具有更强的优势,以使企业获得利润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
关于企业低碳竞争力来源问题,Jonathan Lash和Fred Wellington认为在气候变暖的形势下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需要注意开发碳资产[3];独娟进一步指出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构建企业竞争力,因此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核心是资源低碳配置能力[4]。也就是说企业有效识别对低碳经济有贡献的资源,进而合理配置、经营、扩张这些资源可保持对竞争企业的低碳竞争优势,因而企业开发、经营碳资产有助于提高企业低碳竞争力。
企业低碳竞争力的载体是碳资产,“碳资产”的概念目前尚有争议,曾任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中国区首席代表的江苏布鲁斯达低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新认为碳资产是一个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合于存储、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林辉认为是碳资产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和无形资产[5];万林葳等认为碳资产指企业由于实施具有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的项目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而获得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6];王璟珉等认为碳资产是与碳排放相关的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和间接利益的资源[7]。以上对碳资产的认识有共同之处,即有低碳价值的资产,比如某空调生产企业将厂区内的照明灯具全部改装为低耗能率的优质节能灯,这不仅直接降低CO2排放,同时因为少消耗电能而间接降低了全社会的CO2排放,该批次的优质节能灯可认定为企业碳资产。
碳资产可划分为“有形”碳资产和“无形”碳资产。诸如像低碳建筑、低碳设备等碳有形资产的成本和价值容易准确计算和评估,但它只能说明企业低碳竞争现状,更多反映的是企业与其竞争对手在低碳表现中低碳静态竞争力;而企业低碳发展战略、碳循环机制、节能减排发展策略、电子商务应用水平等则通过各种社会影响和效益影响,促成股市增值或资产评估值上升。这些不易识别且难以量化“无形”碳资产决定企业与竞争对手未来的低碳表现,反映的是低碳动态竞争力,真正维系着企业低碳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同时碳无形资产是碳有形资产能够高效运行的有力保证,它真正体现了企业产品或服务在与其竞争对手相比的优势低碳表现。因此,企业低碳竞争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是企业识别、积累并经营碳无形资产。
伴随着人类生活从社会自然空间延伸到互联网空间,以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互联网资产(主要是互联网无形资产)价值逐步受到企业的重视,基于互联网资产为主的生产经营相对于传统线下无疑会降低CO2排放,使企业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有更好的低碳表现。把有低碳价值的互联网无形资产视为碳无形资产中特殊的一类即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这类型资产同其它类碳无形资产一样将通过节能减排对企业低碳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由于企业越来越多的生产经营活动依赖互联网,致使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未来必将承载更多的企业低碳竞争力信息,愈发成为企业在低碳未来致胜的重要因素。
二、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概述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是碳无形资产中重要的一类,它是指具有CO2减排效果,能支撑申报CDM项目或使得企业CO2排放总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的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揭示了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同时拥有互联网属性和低碳属性,前者把它同其它类的碳无形资产区分开来,后者是它和其它类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本质差异。互联网属性意味着其更高更模糊的边际收益,而低碳属性支撑着其对企业的直接贡献:在自由碳交易市场尚未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申请CDM项目获利;在碳排放自由交易和给定碳排放额度的环境下降低碳排放量,如果企业碳排放总量低于给定额度,冗余碳排放量可通过自由交易获利,如果企业碳排放总量仍然高于给定额度,则减少的碳排放有助于企业减少从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的资金。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价值绝不仅限CO2减排效果,更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关系改变着企业竞争优势,这些网络化关系包括:社会机构、合作伙伴、供应商及客户等。在低碳消费方面,“碳标识”会激励外部客户低碳消费行为,并对企业低碳行为的认可,进而增加其产品的消费欲望;在关联企业关系方面,可绕开上下游合作伙伴,特别是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相关公司的“碳壁垒”;在政府关系方面,可获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倾斜和优惠。总之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价值更多的通过客户响应、社会价值等外部因素来实现。
三、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及评价研究
(一)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
在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研究方面,鲁明勇认为互联网无形资产是由企业或个人所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具有收益预期的网络经济资源[8];蒋秀莲认为互联网无形资产指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具有较高的获利能力,而且随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其价值也随着扩大,不具有传统会计意义上实物形态的资产[9];童华晨认为互联网无形资产指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包括域名、网站、网络软件、企业网络客户、企业网络知名度、网站及其他业务访问量、网络品牌形象等,还包括企业用于上网的机器设备等。并明确上述资产中的绝大部分虽不符合传统意义上无形资产的概念,但应纳入无形资产的范畴[10];汤洵明确指出互联网资产一般就指互联网无形资产,并系统论证了互联网无形资产本质上是无形资产,并进一步指出它的特殊内涵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互联网无形资产可以是多种资产的组合;由于互联网无形资产是信息化的产物,故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对其影响程度高[11]。2009年的“互联网资产保护与优化”会上,与会专家倡议将互联网资产正式纳入无形资产体系,即互联网资产就是互联网无形资产。文献分析显示:尽管学者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定义阐述不完全相同,但互联网无形资产的内涵和范畴均较为清晰,争议不多。
(二)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价
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价主要集中于财务视角。董延安为把域名的价值分解为补偿价格、平均价格、超额价格等三部分,从而建立了域名价值评价的一般模型,并运用实际成本法、现金净流量现值法、预期净收益现值法等财务方法计量域名的价值[12];鲁明勇比较了历史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在评价互联网无形资产方面的优缺点,但并没有给出哪些方法较为科学的结论[8];王帧等在鲁明勇基础上建议针对不同的互联网无形资产分别采用成本法、收益法、市价法,并讨论了每种方法对各种互联网无形资产的适用性[13];汤洵采用收益现值法首次对互联网企业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并运用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互联网企业整体无形资产进行分割,仍成本收益等财务方法评估出各类互联网无形资产价值[11]。文献梳理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价研究,国外研究极少,国内的研究进度较为超前,同时学界倾向分割互联网无形资产后,单独使用财务方法评价,事实上互联网无形资产之间彼此关联,且可相互组合,定性和定量结合的系统性评价方法会成为未来评价研究方向。
四、碳无形资产定义及评价研究
(一)碳资产定义
从环境污染的角度看,代表温室气体的CO2及排放不仅没有任何价值,且由于环境排放容量限制而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但CO2减排和CO2吸附活动因其减轻了人类对环境伤害而极具价值,“碳资产”应运而生。林辉认为碳资产指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和无形资产[14];张鹏认为碳资产是地球环境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容纳量通过相关制度的分配而被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一种环境资源,随着二氧化碳排放,资产会被消耗。这使得国内企业可通过实施节能减排来申请CDM项目实现盈利[15];仲永安等认为碳资产是人类通过法律建构,把碳排放这样一个实质的人类活动就变成一种抽象的、可分割、可交易的法律权利,由此出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被视为一种有价产权[16];谭中明认为碳资产指在碳排放权交易成为现实后,拥有碳减排能力的企业也就因此获得碳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价值属性,具备了资产的性质,形成碳资产[17];洪芳柏认为碳资产是以企业(或行业)为对象,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这种具有价值属性,体现或潜藏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进一步解释,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18];上述碳资产定义有些侧重于碳排放权分配,有些偏重于碳减排量,也有些开始注意低碳设备、低碳技术、低碳策略、碳标签、互联网应用技术等企业碳资源。也就是说,额定碳排放权和碳减排量固然属于“无形”碳资产,企业以减少CO2排放量为目的的那些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生物减碳排放等碳资源也应归属于碳资产。万林葳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碳资产指企业由于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而获得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19]。
(二)碳资产相关领域
相关领域包括碳资产交易、碳资产延伸产品:碳金融、碳信用、碳标签、碳中和、自愿减排等。Cameron Hepburn通过分析京都协定书下的三种灵活的碳资产交易机制,提出了未来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19];谢怀筑等总结了碳金融、碳信用的典型特征[20];王留之等提出了八种碳金融的创新模式: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 CERs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融资租赁、保理、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化和碳交易保险[21];周飞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了基本理论探索,通过对碳排放权的含义和性质分析,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和特征,同时讨论了我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必要性[22]。
(三)碳无形资产最新研究成果
前述文献中提到额定碳排放权、碳减排量、碳标签、低碳策略等大多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属于碳无形资产的范畴。Takashi Kanamura探索性的对作为商品的碳资产的进行分类,提出可把碳无形资产从碳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高喜超认为碳无形资产指具有低碳价值的无形资产,并把碳无形资产分为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八类,运用AHP-ANN模型系统评价这些碳无形资产,最后进行了实证研究[23]。文献分析显示,碳无形资产研究刚刚起步,其分类和评价工作也不够成熟。
五、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研究
(一)企业低碳竞争力内涵
该领域研究经历了企业绿色竞争力、企业环境竞争力等概念后,企业低碳竞争力内涵研究逐渐成熟:崔健认为企业低碳竞争力是指在碳约束的背景下,为实现碳排放削减目标,企业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低碳技术和清洁生产方式,率先生产、开发、利用比竞争对手具有更低污染、更低排放、更低能耗的产品与服务,从而持续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24];高喜超等认为崔健的观点忽略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低碳表现,他们把企业低碳竞争力理解为通过低碳生产和发展方式,在经营过程中及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有更好的低碳表现,从而在与其竞争对手竞分资源上具有更强的优势,以使企业获得利润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3];独娟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认为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核心是资源低碳配置能力,即以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对化石能源等高碳能源的依赖,形成以低碳能耗、低排放为基础的资源配置能力[4];徐建中等提出企业低碳竞争力网络的概念,认为企业低碳竞争力是开放动态的完整系统,它不仅根源于企业内部,还与外部的多种组织和制度有关,企业与这些相关组织和制度的相互影响与互动被定义为企业低碳竞争力网络,其构成要素包括:参与者、低碳能源开发、低碳技术创新、低碳发展资金、低碳管理和低碳文化等[25];2013年超越环境商务咨询公司出版专著《企业低碳竞争力战略》认为企业低碳竞争力是传统的企业竞争力附加因素,是企业通过减少产品与服务的碳强度等措施所获得竞争力的“增量”。从上述分析可知,关于企业低碳竞争力内涵的研究尽管角度不尽相同,但分歧较少,且研究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扩展。
(二)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
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文献相对较少,例如,张伟娜等从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三个维度评价了企业绿色竞争力[26];王皓构建了企业低碳竞争力的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三个一级指标(经济能力、生产能力、低碳能力)和六个二级指标,并采用神经网络法进行评价[27];陈红喜基于价值链视角设计了评价企业绿色竞争力的5个层面,分别是企业绿色设计能力、企业绿色供应能力、企业绿色生产能力、企业绿色营销能力及企业绿色处理能力,18项二级指标通过这 5个层面系统评价企业绿色竞争力,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28];朱利明认为可从运营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资源竞争力、管理竞争力4个维度评价企业低碳竞争力,并通过建立模糊评价矩阵计算并综合评价,但没有对该评价方法进行实证研究[29];黄山等认为企业提高低碳竞争力的驱动因素遵守监管规定、服从制度规范从而维护企业声誉、满足消费者低碳消费需求、最求政策激励收益、获取低碳竞争力优势和良好的长期效益等,并基于此动因提出了企业提高低碳竞争力的途径[30]。文献分析显示: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研究尽管已为学界所关注,但评价理论和方法研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六、结论与展望
企业低碳竞争力视角下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的相关研究领域包括互联网无形资产、碳无形资产和企业低碳竞争力研究等方面。文献综述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方面相对成熟;企业层面的低碳竞争力评价研究不够丰富和深入;而碳无形资产定义、分类及评价研究特别薄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虽然已有研究中涉及到了碳无形资产评价,但尚无文献涉及各类碳无形资产评价,特别是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
(二)虽然已有不少文献涉及到了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且有文献在碳无形资产视角下的评价企业低碳竞争力,但暂无文献通过探讨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的路径和程度,并在企业低碳竞争力视角科学评价互联网碳无形资产。
据此,通过研究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机理及程度、科学评价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理论意义:作为企业低碳竞争力的主要来源的各类碳无形资产日益增多,研究互联网类的碳无形资产与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关系,据此建立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模型,形成了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的新思路,完善和丰富了碳无形资产评价理论研究体系,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实际意义:企业一般比较重视低碳建筑、低碳设备等硬资产或“可见”的额定碳排放权、碳减排量、低碳技术等碳无形资产,而忽视低碳战略、低碳组织体系、减排政策等“不可见”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而极具低碳价值的互联网类碳无形资产却常被企业忽视,其主要原因是未能明晰该类型资产对企业的价值和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贡献。同时,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与其它各项碳无形资产共同组成生态系统,彼此密不可分。现实却是企业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低碳竞争力的价值和贡献基本不了解,这极大的束缚了企业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机理及程度、科学评价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是企业面临的紧迫任务。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激励企业发掘、经营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并提高其在该类资产的配置效率,从而保证企业在低碳未来中的竞争优势。
除了上述研究领域以外,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的其它研究方向至少还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碳盘查过程中如何准确核算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CO2减排量。
(二)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外部性机理,以及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减少这种外部性,以保证政策激励公正性和有效性。
[1] 赵云君.低碳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J].经济纵横,2011(2):103-104
[2] 高喜超,范莉莉.企业低碳竞争力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3,278(2):136-141.
[3] LASH JONATHAN,WELLINGTON FRED.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a warming planet[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7,85(3):94-102.
[4] 独娟.论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形成要素及构建路径[J].求索,2012(5):193-194
[5] 林辉.未来低碳趋势下的企业竞争[J].销售与市场,2009(11):36-38.
[6] 万林葳,朱学义.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我国企业碳资产管理初探[J].Commercial Accounting,2010(9):68-70.
[7] 王璟珉,聂利彬.战略视角下企业碳资产管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31-134.
[8] 鲁明勇.网络虚拟资产的会计研究[J].商业研究,2006,19(7):153-156.
[9] 蒋秀莲,蒋晨,蒋陈杰.Internet上企业无形资产问题研究[J].电子商务,2011(9):24-31.
[10] 童华晨.浅析网络经济下企业网络资产管理[J].当代经济,2012(15):56-57.
[11] 汤洵.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7-8.
[12] 董延安.企业网络域名价值评估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4:29-38.
[13] 王帧.阮萍.对网络虚拟资产价值评估的探讨[J].中国商界,2010(7):101-102.
[14] 林辉.未来低碳趋势下的企业竞争[J].销售与市场,2009(11):36-38.
[15] 张鹏.碳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研究[J].财会研究,2011(5):40-42.
[16] 仲永安,邓玉琴.中国大型电力企业碳资产管理路线初探[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1,36(11):166-171.
[17] 谭中明,刘杨.对碳资产财务会计处理的探讨[J].Commercial Accounting,2011(11):51-52.
[18] 洪芳柏.企业碳资产管理展望[J].杭州化工,2012,42(1):1-4.
[19] CAMERON HEPBURN.Carbon Trading:A Review of the Kyoto Mechanisms[J].Environment and Reasources,2007,32(11):375-393.
[20] 谢怀筑,于李娜.碳金融: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1):29-40.
[21] 王留之,宋阳.略论我国碳交易的金融创新及其风险防范[J].现代财经,2009,29(6):30-34.
[22] 周飞.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5-10.
[23] 高喜超.碳无形资产视角下的企业低碳竞争力系统评价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4:29-126.
[24] 崔健.日本产业低碳竞争力辨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9):105-110.
[25] 徐建中,袁小量.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企业低碳竞争力网络运行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24):92-95.
[26] 张伟娜,王修来.企业绿色竞争力的评价模型及其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0(20):43-45.
[27] 王皓.企业低碳竞争力的研究—以机电制造企业为例[D].无锡:江南大学,2010:19-50.
[28] 陈红喜,刘东,袁瑜.低碳背景下的企业绿色竞争力评价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2):1-5.
[29] 朱利明.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商贸,2013(13):105-106.
[30] 黄山,吴小节,宗其俊.中国制造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来源及提升途径[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5):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