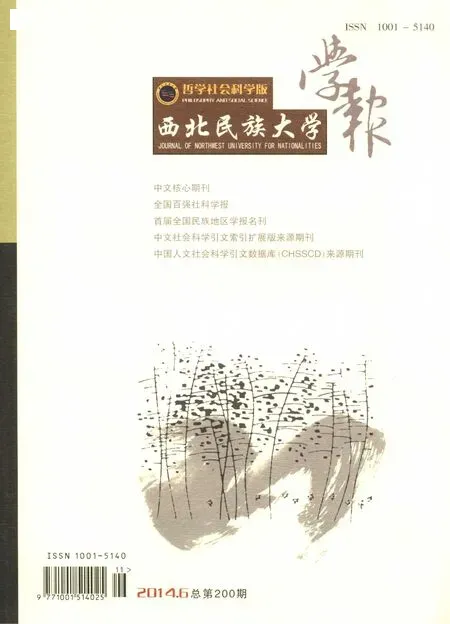从西南到西北——历史时期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考释
唐旭波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武都郡在历史时期的区域归属变迁问题较早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但学界对武都郡区域归属的研究不够深入,学者的论著大多在探讨与西南或西北区域相关问题时才涉及武都郡的区域归属,但均言而未详。①涉及武都郡区域归属的论著主要有: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认为武都郡虽属“西南夷”,但由于各种条件不能成为西南地区的一部分(《西南民族史论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张珂风《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认为学界目前已经把陇南等地排除在西南之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张勇《“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认为武都郡早期属西南区域,后来受行政区划影响才逐渐划入西北地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辑);雍际春《陇右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地域特征》认为武都郡地区在先秦至前汉时期作为梁州一隅而被视为西南地区,后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而与陇右融为一体(《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时期武都郡的区域归属变迁作进一步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言历史时期上迄武都郡置郡下至当今,武都郡地区的疆域以西汉武都郡为蓝本,视论述需要作必要的盈缩。
一、两汉时期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
武都郡置郡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汉书》云:“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1]武都郡置郡之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都视其为“西南夷”地区,《汉书·地理志》(以下称《汉志》)把武都郡纳入益州刺史部,史称“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址,北置朔方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2]益州之地在先秦时期即有西南之意,《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杨慎《山海经补注》认为,“黑水广都,今人成都也。”[3]但先秦时期的“西南”与益州还不能对等起来,仅作为一种方向概念而非区域概念。秦汉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成后,司马迁出于构建“五方之民”格局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作“四夷传”,①黎小龙认为,“《礼记·王制》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人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的理想与展望,而司马迁《史记》所构建的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才是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反映。”见黎小龙、徐难于《“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标志着西南区域概念的正式形成,而武都郡因其地“白马氐”的存在而被视为“西南夷”地区。班固沿袭司马迁关于“西南夷”的认知并以更加正式的《地理志》方式把武都郡划属到益州刺史部,这样武都郡从民族和政区层面上都被纳入西南地区。
马、班二人把武都郡纳入西南地区,其地理位置与民族风俗是重要原因。《汉书》第一次明确记载了武都郡的辖境,《汉志》“武都郡”条云: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县九: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泽在县西。莽曰循虏。上禄,故道,莽曰善治。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平乐道,沮,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莽曰杨德[4]。
西汉武都郡辖九县(道),包括今武都、康县、宕昌、成县、徽县、两当、西和、礼县(部分)、舟曲、迭部(部分)及陕西省略阳县和凤县一部。其辖境东邻陕西省汉中市,西接甘南藏族自治州,北靠甘肃省天水市,南壤四川省广元市。《汉志》引《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西顷因桓是俫。”[5]岷山延绵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嶓冢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境内,桓水即发源于甘肃,流经宕昌、武都最后经文县进入四川的白龙江,可见秦汉时期的梁州是包括武都郡一带的。汉武帝“改梁曰益”之后,益州的地理范围与梁州大致相当,不同之处是益州开始作为“五方之民”格局下之西南一隅出现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内,属于益州刺史部的武都郡自然亦属西南地区。又《华阳国志》记载,“华阳”即华山以南地区的史事,而“华阳”在汉晋时期亦被赋予西南之意,无独有偶,据《阶州直隶州续志》载,武都郡境内亦有“华阳洞”,“金莲洞,在县东三十里旱麓之下。一名华阳洞。”②[清]叶恩沛,《阶州直隶州续志》卷2《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10》,第225页。据王百岁研究,金莲一词源于全真教经典,所以金莲洞之名最早应始于元代之际。(详见王百岁《甘肃省成县金莲洞石窟与全真道》,《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另葛兆光关于“异域?想象”的研究对于金莲洞和华阳洞之名出现的顺序很有启发,“一名华阳洞”可能暗示华阳洞是金莲洞之前身,这也与华阳观念始于魏晋之际相吻合。详见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第73-74页。“华阳洞”与《华阳国志》两者孰早出无考,但“华阳洞”无疑精准地表明了武都郡所处的地理位置。
如果说武都郡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宏观的国家民族格局中属于西南区域,那么武都郡的物产就是其连接与西南区域的黏合剂,武都郡与西南诸郡物产的均质性使其与西南地区融为一体。③徐国利认为,界定区域史研究的区域范围的原则之一是“区域内社会诸要素或某要素应当具有均质(同质性)。”见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辑。《后汉书》称武都郡“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6]而《华阳国志》则云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蜡”、巴西郡“有牛、马、桑、蚕”[7]。武都郡与西南诸郡物产的均质性在历史时期变化甚微,《梁书》称武兴国“种桑麻。出䌷、绢、精布、漆、蜡、椒等。”④武兴国系氐人杨文弘昇明二年建立的地方政权,其境包括武都郡之一部。详见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页。直至清代,《阶州直隶州续志》云,“丙穴鱼,左思《蜀都赋》云:‘嘉鱼出于丙穴。’嘉鱼,蜀郡处处有之……成县金谷水,春分时有鱼涌出,亦即此类。”“蜀椒,出武都山谷。”[8]武都郡与西南区域的均质性还表现在“风物”上,宋治平元年苏轼与章敦等人游览石鼻城有诗云,“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石鼻城位于宝鸡东北的武城镇,对蜀地苏轼而言此地无疑是西北异象,而正是这种西北异象才唤起了苏轼的西南印象:流水和修竹。武都郡境内之“风物”与苏轼的西南印象十分吻合,如《阶州直隶州续志》载,“鸡头山,在县西南十五里。……松竹葱茂,苍翠欲滴。”“香水洞,在县北二十五里。洞水飞下如珠,中有小石,龙蟠其上。外有茂林修竹。”[9]故有(徽县)“山犹为蜀色,人已作秦音”之说。⑤此语见《徽县志》引述“古县志”之语,但出自何种县志,笔者未能查明。详见徽县志编撰委员会编《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页。武都郡的物产和“风物”与西南诸郡的均质性是武都郡被划属在西南区域的微观原因。
班固认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主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0]一方之民所处的“水土”与“主上”很大程度上决定其风俗,而风俗也是区域划属的标准之一。《汉志》曰:“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11]武都郡地处巴蜀与关中两大经济文化中心之间,风俗自然会受到双方的影响,班固用“略与”“颇似”来形容武都郡与巴蜀和天水郡风俗相似的程度,看似矛盾,实则辩证。武都郡北部与关中相邻而南部则与巴蜀接壤,其风俗南北迥异正是双方影响随距离递增而传播递减的表现。如武都郡北部的天水、陇西二郡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关中,所以“天水、陇西、北地于关中同俗。”[12]虽然如此,先秦时期武都郡似乎在风俗上更倾向于巴蜀,《蜀王本纪》云,“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13]“蜀王”虽无法确知,但既曰“蜀王”当为秦灭巴蜀之前,亦可以视为班固所言之“主上”。抛开神话色彩,我们仍可以看到武都郡与巴蜀地区早期模糊的联系,武都女子代表了一种遥远美好的但蜀地稀缺的意象,而蜀王挽留武都女子则反映了蜀地对这种意象的需求和对外交流的渴望,无论如何,这都反映了武都郡与巴蜀地区的早期交流。①武都郡地区尤其是其南部与巴蜀地区的神话传说引人关注,如《凤凰山的传说》讲述瑶池边的金童玉女私自下凡,为逃避玉皇大帝缉拿而趋蜀地峨眉山未果之事。如果民间神话视蜀地之峨眉山是能够躲避危险的大本营,那么民间也可能认为其地属西南地区。见文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文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71页。先秦至西汉数百年间,武都郡与巴蜀风俗相互浸染,所以《汉志》称武都郡与巴蜀风俗相似当无疑义。
东汉武都郡被置于凉州刺史部,标志着两汉之际武都郡在区域划属上发生了变化。武都郡何时由益州刺史部划属到凉州刺史部《后汉书》缺载,②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认为,马援任陇西太守时把武都郡改属凉州刺史部,即建武十一年。详见《中国民族史》(上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但同书《马融传》云,“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14]可知,武都郡最迟在安帝永初二年已划属到了凉州刺史部。
东汉时期武都郡除了被划属在凉州刺史部外,其郡治和郡境也做了调整。郡治和郡境是一个郡区域归属的重要依据,郡境确定了一个郡的地理位置和行政管辖范围,而郡治则代表了一个郡的统治重心所在。《后汉书》载,“武都郡武帝置。……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沔水出东狼谷,羌道。”[15]东汉武都郡首县为下辨,应为郡治所在。《舆地广记》亦载,“同谷县本汉下辨道,属武都郡,东汉及晋为郡治焉。”[16]东汉武都郡省并了郡境南部的嘉陵道、平乐道和循成道,增加了原属于陇西郡的羌道,由西汉的辖九县变为辖七县,但属县的分布格局未变,大多集中于郡境北部的西汉水流域和徽成盆地。东汉武都郡省并的平乐道等三道应为氐羌杂居之地。③“汉制,县有蛮夷曰道”,见欧阳忞《舆地广纪》,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4页。东汉初年参狼羌多次反叛,虽然用兵镇压但控制疲软,于是汉廷撤并武都郡南部的三道,④李晓杰认为,平乐道、嘉陵道和循成道在永和五年前废弃,详见《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郡治也由武都东移至下辨,这样,武都郡的统治重心无疑向北转移了。经此变化,武都郡的郡境虽变化不大,仅多出了西北部的羌道一地之境,但武都郡地理空间的“拼凑性”⑤察前三史关于武都郡置郡的记载,看似略同,实则不然。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曰:“白马氐,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郡。”范晔这里用“合”来描述武都郡地理空间的形成过程,西汉武都郡北部在秦代属陇西郡,南部为汉开“西南夷”所得之地,东汉武都郡则在西汉的基础上加上原属陇西郡的羌道,武都郡地理空间的构成对其区域归属产生了微妙的作用,并且在其后的历史中一再呈现,对武都郡这种地理空间的构成模式暂且称为“拼凑性”模式。显露无遗。追溯武都郡属县的历史沿革,下辨、武都道、和羌道三地原属秦置陇西郡,故道为秦内史之地,上禄、河池和沮三地为汉开西南夷时所置。⑥刘琳认为下辨道为秦所置县属陇西郡,武都和故道也为秦时所置,但未言其所属。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2《汉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61-162页。周振鹤则认为下辨道和武都均属陇西郡,故道属秦内史之地。见《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换言之,东汉武都郡属县之中有四县原属秦置,仅有三县为汉开“西南夷”所置。陇西郡和内史之地在秦代均属雍州之域,而雍州自先秦起就为西北地区。《晋书》云,“雍州,案禹贡黑水、西河之地……亦谓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雍阏也。”[17]对于一个处于南北交界之地的边郡而言,这样的变化足以颠覆其初步定位的区域划属。梳理武都郡属县的历史沿革,与其说东汉时期武都郡由西南划属到西北地区,不如说武都郡由西南回归到西北地区。
西汉武都郡位于益州刺史部的北部边界,依靠巴蜀诸郡维持武都郡的稳定受到距离的限制。西汉氐人多次叛乱,“元凤元年,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18]“昭帝时,武都氐人反,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19]武都郡氐人叛乱不见益州刺史部用兵镇压,而是直接依靠中央力量去平叛动乱,说明武都郡在区域划属上虽在西南,但由于武都郡距离西南地区的统治重心巴蜀诸郡过于遥远,益州刺史部对武都郡鞭长莫及,控制软弱,武都郡长期游离于西南地区,最终在东汉划属到凉州刺史部。凉州虽为西北之地,但就此一点不能完全肯定武都郡的西北区域归属,若从永初二年算起至曹丕称帝,武都郡在东汉一朝划归凉州刺史部仅百余年,元康六年武都郡又划归梁州,①《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载:“至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元康六年,广汉(还)益州,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常據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18页。范晔也视武都郡为“西南夷”之地,所以在两汉时期武都郡属西南地区。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
魏晋南北朝时期,杨氐在武都郡地区先后建立过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五个地方政权,历33主,凡380余年[20]。从杨氐政权疆域的视角来探讨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有以下考虑:第一,这一时期南北政权更迭频繁,疆域多变,杨氐政权虽然前后多次立国,但武都郡地区全部或部分始终都在其疆域内;第二,地理区域是人们依据不同标准而主观设定的区域概念,区域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西南与西北区域的划分也应如此;第三,杨氐政权立国300余年而疆域比较稳定,为我们探讨该地区的区域归属提供了较好的延续性。②鲁西奇认为,“在设定研究区域时,应该注意保持区域的完整性。这里所说的‘区域完整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地理完整性,二是历史完整性。”(详见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视杨氐政权为一个比较固定的区域来研究其区域归属就是保持了区域的历史完整性,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政权林立之际。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都郡地区表现出了中间地带的特征。③关于中中间地带的概念,陈金凤认为,“我们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沿秦岭、淮水一线争夺、对峙,双方势力常有进退而军事控制线相应作南北推移而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的地带,称之为‘南北中间地带’,简称中间地带。”(见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页)据此,杨氐政权处于秦岭西端,亦为中间地带,陈氏也认同杨氐政权为中间地带,但是笔者这里所言中间地带侧重于区域划属,军事控制线只作为中间地带形成的原因。《梁书》称武兴国的疆域,“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汉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东去长安九百里。”[21]武兴国的疆域较武都郡略广,《梁书》将其与宕昌、龟兹、于阗等国归为西北地区。《梁书》称,“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阙庭者,则仇池、宕昌、高昌、邓至、河南、龟兹、于阗、滑诸国焉。今缀其风俗,为《西北戎传》云。”[22]梁天监五年,北魏遣刑峦攻克武兴置武兴镇,后改置东益州,领武兴、仇池、广业、盘头等七郡。置州之后,“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23]显然,北魏视杨氐所据的武都郡地区为西南地区。
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对武都郡地区区位归属的看法恰好相反,北魏视杨氐为西南之忧,而萧梁则认为杨氐是西北诸戎,这在南北政权对杨氐的各种封号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蔚为大观。《梁书》称,“齐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归款,齐世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24]南北政权对峙之时封号虽然有政治意义,但其蕴涵的区位指向的涵义也不容置疑,从“南梁州刺史”和“北梁州刺史”的封号清晰地看出南北政权对杨氐地区的区域归属认识相悖。南北政权之所以对杨氐之地的区位定位大相径庭,主要是由各自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北方政权多定都于关中或中原地区,南方政权则多在江左,而都城是区位定位最重要的参照物之一。④在正史中,《后汉书·郡国志》首次以都城(雒阳)为参照定位地方郡县,后世史书多继承此论。杨氐统治者似乎对自身的区位定位更为准确,《北史·氐传》称,“文德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25]秦州和梁州在古代区位指向向来明显,即秦州为西北而梁州是西南,杨文德自称秦河梁三州之牧,不是其占据了全部三州之地,而是其拥有三州之地的结合部。以南北政权之都城为参照物,杨氐政权的区位归属自然介于西南与西北之间,到是杨氐统治者冠以自身“秦河梁”三州牧等封号更能体现出武都郡地区中间地带的特征,《武阶备志》亦称,“杨氏窃据,地界南北。”[26]
武都郡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个中间地带与杨氐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杨氐政权在南北缓冲地带形成一种中间势力达380余年,比任何一个南北政权都持久,况且这种中间势力为南北统治者所接受,进而影响到了对其区位定位。①这一时期南北双方都视仇池国政权为自己的藩属国,如元嘉十九年刘宋占领仇池国,杨难当逃至北魏,北魏即移书刘宋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藩属国,准备十道伐宋,而刘宋则认为己方有征伐不服藩属国的权利。见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1986年第79页。萧齐建武四年,李崇攻克盘踞在武兴的杨灵珍后,魏高祖拓跋宏嘉奖李崇诏曰:“今仇、陇克清,镇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实允远寄,故敕授梁州,用宁边服。”[27]陇山以南地区,古称陇右或秦陇,②陇右、秦陇之称大约始于东汉,见《后汉书》卷5《孝安帝本纪》、《晋书》卷63《张轨传》。此处“仇陇”分称是一个巨大转变,表明以武都郡地区为主体的杨氐政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陇右之外的中间地带。
三、隋唐时期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
隋唐时期,剑南道、山南道和黔中道均属西南地区。③张勇《“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辑。此外黎英《唐代西南三道物产研究》也认为西南地区包括剑南道、山南道和黔中道,见2002年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武都郡地区涉及山南道的是凤州河池郡、兴州顺政郡和成州同谷郡,但史籍对成州同谷郡的记载并不一致。《新唐书·地理志四》“山南道”条包括成州同谷郡,《元和郡县图志》与其一致认为成州同谷郡属于山南道,然《唐六典》和《旧唐书》则认为成州同谷郡属于陇右道,至于凤州河池郡和兴州顺政郡属山南道则无异议。④成州同谷郡所属之不一致或由改属造成,贞元五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出于抗击吐蕃的需要奏割原属陇右道的成州同谷郡改属山南道。(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3《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2页)但此说只见于《元和郡县图志》,新旧《唐书》之《严震传》均无此说。武都郡地区的两郡之地被纳入山南道,显然认为其属于西南地区,唐人诗文也表现出对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的定位。李华《李夫人传》云,“卢公为宕州司法参军,夫人随之官。西南羌戎,不知长幼之别。”[28]李华称原属汉武都郡之地宕州为西南羌戎之地。⑤宕州在汉代属于武都郡西北部的羌道,贞观元年原属成州的潭水县并入宕州,这样宕州之一部无疑属汉(接上页)代武都郡。《新唐书·地理志四》“宕州”条称其领二县:“怀道,下。贞观三年省和戎县入焉。西百八十三里有苏董戍。有同均山。良恭。下。贞观元年以成州之潭水来属,后省入焉。”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4页。姚合《送殷尧藩侍御游山南》云,“诗境西南好,秋深昼夜蛰。”[29]姚合虽未直言武都郡地区为西南,但山南道包括部分武都郡地区,其西南定位的语意甚为明晰。
与以上认识相左的另一种看法是武都郡地区属于西北地区。《旧唐书·地理志三》“陇右道”条包括了成州同谷郡、阶州武都郡和宕州怀道郡,同书“陇右道”条云,“秦州中都督府隋天水郡。武德二年,平薛举。改置秦州,仍立总管府,管秦、渭、岷、洮、迭、文、武、成、康、兰、宕、扶等十二州。”[30]唐代陇右道被认为属西北地区,《令河西陇右等处防边诏》云,“今年十月,东幸雒京,西北二边,倍宜严警。”[31]可见,陇右道是传统的西北地区,武都郡地区的三州之地划属陇右道,其被视为西北地区,唐人诗词亦可佐证。“安史之乱”后杜甫流寓同谷郡,咏郡境仇池山诗云,“近接西南境,常怀十九泉。”[32]杜甫在同谷郡寄居数载,对其“山川形便”十分熟悉,认为其“近接西南境”,弦外之意是该区还不是西南地区,只是接近而已。后贺铸来此追慕杜甫有诗云,“少陵昔避地,幽栖凤凰川。……鸣呼歌七章,暮节西南迁。”⑥贺诗为“名嘉亭”而作,当年杜甫流寓同谷郡有“栗亭名更嘉”之句,后邑令赵洋建亭而以杜诗命名,见《阶州直隶州续志》卷15《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10》,第317页。贺诗言杜甫晚年从同谷郡向“西南”流徙,其意与杜甫一致,即此地是通往西南的通道而不属于西南地区。
隋唐时期是武都郡地区由西南向西北地区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其标志是汉代武都郡主体部分的成州同谷郡、阶州武都郡和宕州怀道郡划归到属于传统西北地区的陇右道,而武都郡地区向西北地区靠近的深层原因则在于武都郡地区氐羌民族的消亡和行政区划的分割。
武都郡地区自先秦以来就是氐羌民族的聚居地,其区位划属明显受到《礼记·王制》中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的影响,而秦汉时期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为其区位定位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史记》《汉书》《后汉书》均因武都郡氐羌杂居而把其纳入“西南夷”地区,然至隋唐之际,该区的氐羌民族经魏晋南北朝盛极而衰,氐羌人数剧减,①关于羌人消亡的原因有“汉化”“蕃化”“夷化”三种看法,详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第150-165页。尤其是氐人几乎销声匿迹。这在正史的“四夷传”中反映最为明显,《隋书·西域传》包括武都郡地区西北部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尤其是《附国传》之“西南夷”确指武都郡地区以南的“嘉良戎”,可见武都郡已被排除在“西南夷”地区之外;《旧唐书·南蛮西南夷传》亦无武都郡之“白马氐”,《新唐书》之“四夷传”即《东夷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四方之民”完整无缺,而武都郡未列其中,至此支撑武都郡地区“西南夷”身份的“白马氐”几乎消失于官方正史,从而在民族层面上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也由延续了近千年的西南区域归属向西北靠近。
隋唐时期该区行政区划的分割使得维持武都郡地区“山南道”身份的依据也岌岌可危,“山南道”是唐代西南三道之一,亦是武都郡地区区域定位的另一个重要参照。这一时期,在汉代原属一郡之地的武都郡设置了五个州郡,其中只有凤州河池郡和兴州顺政郡稳定保持在山南道内,而作为武都郡地区主体的成州同谷郡、阶州武都郡和宕州怀道郡则属于陇右道。这样,武都郡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也由西南转向西北地区。
四、宋代以来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
两宋时期武都郡地区继续向西北地区靠近,但其已不是大一统国家的西北地区含义,而是作为边疆出现在西北一隅。两宋时期西北地区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其一,西北地区为边防重地;其二,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其三,西北地区是战略资源边疆。武都郡地区作为西北地区之一部也对应了这三点。《宋史》中屡次提及西北地区为用武之地,《宋史》云:“沆为相,王旦参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33]“庚戌,金人破成州,守臣辛□之遁去。吴曦焚河池县,退屯青野原。癸未,金人破阶州。”[34]成州、河池和阶州均属武都郡之地,在宋室南渡之后作为西北边防重地亦一度被金攻破。②史念海认为南宋时期武都、河池为宋金西部防线的重镇。见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在民族层面,武都郡地区也属于西北地区。《宋史·兵志五》云:“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35]宋代武都郡地区因隶属秦凤路而被视为西北地区。宋人论及边防兵备多提及西北马匹,如《宋史·张方平传》云,“举西北壮士健马,弃之炎荒,其患有不可胜言者。”③《宋史》卷318《张方平传》,同上,第10358页。《宋史·李纲传》亦云:“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见《宋史》卷358《李纲传上》,同上,第11256页。武都郡地区自先秦就是良马之产地,《成县新志》称其地“后孝王封非子于秦养马汧渭,即今秦州地。”[36]《宋史》亦载,“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37]阶州和秦州的部分地区属汉武都郡,武都郡地区作为资源边疆亦属西北地区。
元代武都郡地区在区域归属上虽划属西北,但其区位定位不甚明显。元代空前广袤的版图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④胡小鹏认为元代重建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是按照草原内地一体化的格局构建的,岭北、辽阳、甘肃行省虽凸显出东北和西北的边疆性质但其地位未被边缘化,“换句话说,黄金家族及蒙古千户集团的游牧地,是元朝政治结构的重要一极,不论其在东西南北,不管其为蒙古贵族私产或帝国之共产,在政治版图上均处于中心位置。”武都郡地区在元代虽不属甘肃行省而属陕西行省,但胡氏的研究也表明元代大一统国家区域概念之模糊,武都郡地区地处南北之交,其区域归属自然难以明确。见胡小鹏《试论元代边疆民族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元史》云,“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38]元代版图的急剧扩大,对时人的区域边疆观造成了巨大冲击,过去的边远地区在元代都如同内地,正如同书《地理志》所云,“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39]元代西北地区往往指代西北藩王之地。《元史》载,“壬申,以西北诸王察八儿等来朝,告祀太庙。”[40]察八儿为海都之子,其国远在西域。《元史》称海都封地,“阿里麻里。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鹘五城,唐号北庭,置都护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41]元代西北地区的偏远使得武都郡地区很难与其划为一体。武都郡地区只有在特定的地理概念中才能表现出其区域归属,武宗至大四年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云,“本省地方,东南控接荆湖,西北襟连秦陇。”[42]武都郡地区与蜀地相邻,自然属“秦陇”之地,在此语境下,武都郡地区才能体现其西北地区的定位。
明清时期是武都郡地区继唐置陇右道以来区域归属发生重大转折的第二个时期,其区域归属继续倾向西北并且明显加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清时期武都郡地区以南的文州开始向西北地区靠近,鉴于其与武都郡地区在历史时期的隶属关系且与武都郡地区相邻,此后一并视之。①文州与武都郡地区的隶属关系参阅《甘肃通志》卷3《建置》,兹不赘述。
明清时期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继续由西南到西北巩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史书立足全国视野,明确了武都郡地区所在的甘肃省的区位定位。《清史稿》载,“同治二年,议定甲子科始廷试优生,仿顺天乡试例,分南、北、中卷。八旗、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为北卷。”[43]这是正史中首次明确把甘肃省划为北方地区,弥足珍贵的是这种认知肯定了武都郡地区亦属北方,因为在历史时期该区的南北区位定位都十分隐晦。②如唐柳宗元《兴州江运记》称该区为“西鄙”,宋胡世将《宋忠烈公吴公祠祀》以其为“西土”,元陈季《宣王庙碑》称该区之山为“西山”,明张潜《李公生祠记》称其为“西秦”等,这种只言“西”而回避南北称谓的修辞反映出该区南北定位的模糊性。《清史稿》所映射出的清代甘肃省属于北方的这种主流意识对其南部地区即武都郡地区长期以来不能确立其南北定位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清两当县令秦武域在其任上作《罗园梅花》云,“毕竟北人还识得,殷勤索笑不禁狂。”[44]与秦诗“北人”对应的自然是北方。清代还强调地方与省治之间的方位关系,这正是地方与省治之间联系加强和时人对全国区域划分认识加深的体现,这对武都郡地区的区位划属尤为重要。《清史稿·地理志》载,“阶州直隶州……西北距省治千一百五十里。……京师偏西十一度二十三分。”“秦州直隶州……西北距省治七百三十里。……京师偏西十度四十分。”[45]这表明清代武都郡地区是以双重区位定位出现在全国版图之内的,于省治而言武都郡地区位于西南,于国家而言武都郡地区只能位于西北,《甘肃通志》亦云“甘肃西北巨镇”[46]。
与国家宏观层面的认识相一致,地方士人从微观层面亦开始认同武都郡地区的西北区域归属。清光绪辛己年,徽县县令陈鸿章登县境铁山,作《登铁山诗(三)》云,“将才西北知谁伟?蜀国当年有武乡。”[47]又清吴鹏翱《武阶备志·山水》序云,“东南之山,山不敌水,西北之水,水不敌山。”[48]陈、吴均视武都郡地区为西北地区。
民国至今是武都郡地区确立西北区域归属的时期。民国三十一年蒋经国考察西北后写道,“其次是西北的铁矿,大概可以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二是凤残余铁矿,包括有成县、西固、永登和斗虎沟各铁矿。”[49]成县在东汉曾作为武都郡郡治,这里蒋经国视其为西北地区。当然,武都郡地区是一个南北交界之地的小区域,这样微观具体的例子在历史时期甚少,这里蒋直言成县的区域归属完全是因为其铁矿资源,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该区地处边陲而被边缘化,迟至清代仍被视为“西鄙”或“西陲”,武都郡地区长期被中原主流意识所忽略。明万历五年,文县邑令王三锡与阶州守备孟孝臣游览文县天池,王抚临天池胜景而谓孟曰:“古今称奇致者,杭之西湖,岳之洞庭。子瞻有‘淡抹浓妆”之句,希文有‘先忧后乐”之辞,至今与山川增丽,何者?以越、楚当车辙冠盖之冲,众易见而名之无难也。使天池而与二湖并列,吾不知骚人墨客,来往登临,品题而称述者凡几矣!”[50]王之意甚确,天池地处鄙陋之地而不能被人广知。王孟虽为明人,但《游天池记》所揭示的武都郡地区由于地处边远而被主流意识所遗忘和忽略的事实应该是贯穿整个武都郡地区发展历史的。这种事实从很大种程度上解释了武都郡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区域归属需要借助具有特定区位含义的地理概念来判定的必要性,汉晋时期的“凉州”“益州”“梁州”“华阳”概念、隋唐时期的“陇右”“山南”概念都是判定其区域归属的地理概念。这种宏观的地理概念在历史时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对武都郡地区的区位判定作用却是一致的。甘肃省这一行政区划概念最早出现于元代,至清代同以上地理概念一样具有了区位定位的作用,民国时期这种作用仍在延续。如蒋经国认为,“通常人们所讲的西北,大概可以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新疆诸省,乃至西藏的一部分地方。”[51]蒋认为甘肃省属于西北地区,武都郡地区自然也属西北地区,这种认知的前提是武都郡地区属于甘肃省之渭川道。
“三陇”概念与甘肃省在地理空间上的重合标志着武都郡地区西北区域归属的完全确立。“三陇”概念顾名思义指陇山以西、以东、以南地区,所以“三陇”概念从地理范围上看是一个“拼凑式”扩大的过程,从内涵上看则是一个逐步确立的历史过程。“三陇”所指的陇西、陇东和陇南三个地理概念中,以陇西最早,陇东其次,陇南最末。①陇西最早见于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见《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页。陇东最早见于唐代诗人王建的《陇头水》,“陇东陇西多屈田,野麋饮水长簇簇”,见《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315页。另外陇东还见于宋王安石《陇东西》一诗,见《王安石全集》,大东书局,1935年第196页。陇南作为地理概念滥觞于明天启年间,精乐子撰《凤凰仙山补修圣母地师金象碑记》称,“创造伊始,相传起自西汉,德威昭彰,宏恩丕显陇南。……天启岁次乙亥年三月下浣谷旦敬立。”[52]“三陇”概念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黄英《碧口行二首》云,“三陇春光此地先,一江碧野诵富源。”②文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文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8页。叶春生认为三陇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地域文化概念中的‘三陇’一词,具有广、狭二义,狭义的‘三陇’,实为甘肃的代名词。广义的‘三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主要指陇山以东、以南、以西之地,大致包括今甘肃省全境、宁夏和青海的部分地区。”这里所指三陇当取狭义。见叶春生《区域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碧口是文县最南端与四川南坪县接壤的一个贸易码头,“碧口不像甘,南坪不像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甘肃碧口与四川南坪之间风物之相似,黄诗视甘肃省最南部的碧口为“三陇”地区表明该概念已完全成熟,也喻世甘肃与“三陇”的重合。
“三陇”概念的成熟意义在于武都郡地区可以摆脱历史时期依赖“陇蜀”等地理概念判定区域归属的尴尬境地,亦有利于陇蜀边界的明晰。③陇蜀边界明晰的趋势大致始于宋代,《阶州直隶州续志》引述《通志》称“浊水,在县西南。亦谓之白水,又名‘天水’。经旧栗亭县,东南流,过徽州,入蜀,合于嘉陵江。”又《阶州直隶州续志》引述《画漫录》云:“太白山,在州南四十里……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记‘无忧城东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也’。”这些记载说明陇蜀山川虽然在地理上相互毗邻,但各自的归属还是明确的。这种趋势在明清时期延续且更加明显,地方志中关于道里四至的精确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武阶备志》称玉垒关,“在文县所城东南一百二十里,路通四川剑州。”如果说方志所记为陇蜀山川道里的客观归属,那么民间传说就隐喻着一定的感情色彩,今人陈晓翌作《鹰咀崖》云:“奇峰雄鹰踞,博翮巴蜀飞。俯啄天府稻,仰护陇上麦。”其诗原注:“天寿山有一峭崖,山尖向下勾弯,极像鹰咀。民间传其啄食四川,阴护陇上。山嘴已被凿毁。”(见陈晓翌牛民选王登尧编《古咏今咏—成州诗词精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陈诗一反温情,陇蜀分明,联系明清以来陇蜀边界的匪患和罂粟种植给陇蜀边民造成了惨痛苦难,窃疑其时可能导致陇蜀边民对双方产生误会和怨恨,以致相互排斥,陇蜀分界渐趋明晰。这种民间意识可能是促成地方文化精英提出“三陇”概念的原因之一。如明郭从道《徽郡志》称,徽州“明兴置郡,顾山河佳丽,风物宣朗,且介于陇蜀之间。”④[明]郭从道《徽郡志》卷1《舆地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9页。又嘉靖二十二年知州许钊重修的徽县城增置东西南北四门,其中“南曰通蜀,北曰眺陇”,在“陇”“蜀”被赋予特定的区位指向的涵义下,这种修辞对判断武都郡地区的区位归属无疑是模糊的。见《甘肃通志》卷7《城池》,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这种修辞对武都郡地区北部的徽州确定其区位尚属不易,遑论武都郡地区南部的文州了。“三陇”概念成熟之后,“陇蜀”概念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但已不像此前那样模糊不清了,刘宏谋《碧口》一诗就很好地体现了“三陇”和“陇蜀”概念在这一时期对武都郡地区南部区位判定的功用。刘诗云,“石铺街,街心弯,弯月集市闹声喧,情系巴蜀,根固陇原,笑迎九州岛八方客,紫云宫中春满园。”[53]这里“情”与“巴蜀”和“根”与“陇原”既反映历史沿革又立足现实归属,与清吴永谦《重修阴平桥记》有异曲同工之妙。“昔蜀而今秦,昔盛而今颓。……余,蜀人也。文,古蜀地也。”[54]如果说吴记反映的是明清时期文县向西北靠近的开始,那么刘诗体现的就是民国至今文县划属西北的终点。
新中国成立后,武都郡地区主要属陇南地区管辖。据《甘肃省志》所附之《甘肃政区图》,陇南地区的武都、文县、成县、康县、徽县、两当、西和、宕昌和礼县的一部均属武都郡地区。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统一管辖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55]。在单一经济层面,1978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建成西南、西北、中南、华东、华北和东北6个大区的经济体系[56]。新中国之后这些依据不同标准而制定的区域规划不论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武都郡地区都属于西北地区。
然而,即使这一时期武都郡地区的政区范围如此整齐划一、区域归属如此明确清晰,其区域归属本身和区域划属标准也是多元的。1930年梁钊韬绘制的“西南民族分布于分类图”就包括甘肃甘南等地[57]。又1950年董其祥谈及《西南沿革地理研究计划》目的说,“我研究的范围是秦岭汉水以南,衡岳湘江以西,正是我国版图的西南区。……照人文区划说,他包括川康云贵的全部,秦陇湘鄂的一部”[58]。其内容包括自然地理、行政区域、民族活动和交通方面。梁董所言的“甘肃甘南”和“秦陇”均包括武都郡地区在内。依据民族、地理和行政等因素来判定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归属古已有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武都郡地区区域划属已经衍生出新的因素。有学者研究碧口话最后得出结论,“碧口(话)虽属甘肃文县管辖,但碧口话却属地道的四川话。”①“碧口话”或为碧口之误,括注为笔者所加。详见张成材《甘肃碧口话的特点及其归属》,《语文研究》,2005年第4期第65页。②明清时期不论是正史地理志还是地方志都对府县的疆域四至记载更加详实,这反映出这一时期边界意识的增强。以清代直隶州阶州为例,《甘肃通志》载:“东至汉中府略阳府县界三百二十里,西至巩昌府西(接上页)固厅界九十里,南至松平寨四川龙安府平武县界三百里,北至秦州礼县界二百五里。”(见《甘肃通志》卷4《疆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阶州属汉代武都郡而与汉代广汉郡相邻,清代边界意识的强化使得陇蜀边界渐趋明晰,改变了历史时期“陇”“蜀”作为具有区域指向的地理概念而使武都郡地区在西南与西北之间徘徊的境地,陇蜀边界的清晰对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的确立至关重要。白酒板块和方言归属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西南区域划属的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划属本身会随着区域划属标准的多元化而有所不同。
五、结语
武都郡自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至今,其区域归属经历了西南-中间地带-西北这样的历史过程,考察其整个变迁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武都郡地区在两汉时期属于西南地区,魏晋南北朝处于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隋唐时期是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由西南到西北的第一个转折时期,其标志是陇右道的设置;两宋时期武都郡地区则表现出西北边疆之意,蒙元时期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不甚明朗,明清时期是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的第二个转折时期,其标志是甘肃省这一行政区划概念衍化为具有西北含义的地理概念,民国至今这一时期武都郡地区最终确立了其西北区域归属。
第二,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在历史时期的变迁是由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区域观念、民族分布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推动的。地理位置因素贯穿整个变迁始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行政区划因素则更具决定性作用。
第三,具有区位指向的地理概念在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变迁的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汉晋时期的“益州”“凉州”“仇陇”“华阳”概念、隋唐时期的“陇右”“山南”概念、明清时期的“甘肃”概念和民国至今的“三陇”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其固定的区位指向功能。“益州”是武都郡地区西南区域划属的起点,而“三陇”是其西北区域归属的终点。
第四,历史时期全国政局的统一与否对武都郡地区的区域划属有直接影响,这在魏晋南北朝、南宋和元代表现得最为突出。魏晋南北朝之际南北政权对峙,武都郡地区长期为杨氐政权所盘踞,南北双方视其为缓冲地带,至“仇陇”分称取代“秦陇”并称表明该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于陇右之外的中间地带;宋室南渡之后,其版图大为缩减,与金人相持在秦岭—淮河一线,对宋廷而言武都郡地区处于这一政权军事分界线的西北方向,自然被视为西北地区。宋金对峙时期武都郡地区之所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之际那样演变成一个中间地带是因为其时武都郡地区不存在一个中间势力,加之宋金对峙与魏晋时期南北对峙的时间长短不可同日而语。元代全国版图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其西北地区多指西北藩王之地,其与武都郡地区相距甚远,难以划为一体。如果说魏晋南北朝和南宋是因政局分裂而使武都郡地区区位归属凸显的时期,那么元代就是湮没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的大一统国家之极致。
第五,纵观武都郡地区区域划属变迁的全过程,其西南区域归属模糊而西北区域归属清晰。汉晋时期,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的定位主要依赖“益州”“梁州”“华阳”等地理概念的区位指向功用,而这些地理概念本身就是根据“山川形便”设定的,武都郡地区又处于这些地理概念的边缘地带,这样武都郡地区西南区域归属的模糊性就可想而知了。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增强,西北区域范围的明确,都使得武都郡地区西北区域归属愈加明晰。
第六,武都郡地区长期处于西南与西北之间一种尴尬境地,其得不到主流意识的关注而被边缘化,也喻世其在边疆化和内地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中摇摆不定,历史时期中原经略边地的属国制、道制和羁縻州制、土司制等制度都曾在该区施行,迟至雍正年间该区还有土司制的存在。①《明史·土司传》不载甘肃土司,《清史稿》则为甘肃土司立传云:“甘肃,明时属于陕西。西番诸卫、河州、洮州、岷州、番族土官,明史归西域传,不入土司传。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阶州直隶州续志·名宦传》“葛时政”条亦云:“雍正七年,知文县……改土归流,民番感德。”《文县志》亦云:“蕃地,系土司王守印、马起远所辖,雍正八年,知县葛时政奉文改蕃归流,土司裁革。”谭昌吉据今文县中寨发现的《王氏宗谱》和《马氏谱抄》,认为文县土司制始于明洪武六年,结束于雍正七年的改土归流。可见甘肃南部地区的土司制度与其它地区大约相始终。详见谭昌吉《白马人土司制度》,《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调查资料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271页。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的长期徘徊,对该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1][2][4][5][10][11][18][19]班固.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2.1609,2998,1609,1531,1640,1646.225,2972.
[3]袁珂.山海经校注[Z].成都:巴蜀书社,1980.505-514.
[6][14][15]范晔.后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5.2859,1953,3518.
[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1-45.
[8][9][32][50][54]叶恩沛.阶州直隶州续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10 -311,253 -255,17,483,489.
[12]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1959.3262.
[1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1.541.
[16]欧阳忞.舆地广记[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434.
[17]房玄龄.晋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4.430.
[20]马长寿.氐与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61.
[21][22][24]姚思廉.梁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3.816-817,809,816.
[23][27]魏收.魏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4.2232,1466-1467.
[25]李延寿.北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4.3174.
[26][48]吴鹏翱.武阶备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42,6.
[28][31]董诰.全唐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2.3255,328.
[29]彭定求.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5622.
[30]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30.
[33][34][35][37]脱脱.宋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7.9539,742 -743,4750,4932.
[36]黄泳.成县新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 70年.94.
[38][39][40][41][42]宋濂.元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6.1345,1346,525,1569,2548.
[43][45]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3107,2122-2123.
[44]刘瑞,杨永红.两当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831.
[46]查阿郎.甘肃通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7]徽县志编撰委员会.徽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1125.
[49][51]蒋经国.伟大的西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41-42,19.
[52]西和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西和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851.
[53]文县志编撰委员会.文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1051.
[55]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97.
[56]张普一.试论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冲突[J].丝绸之路,2011,(22):62.
[57]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贵州民族研究,2004,(3):62.
[58]重庆三峡博物馆.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