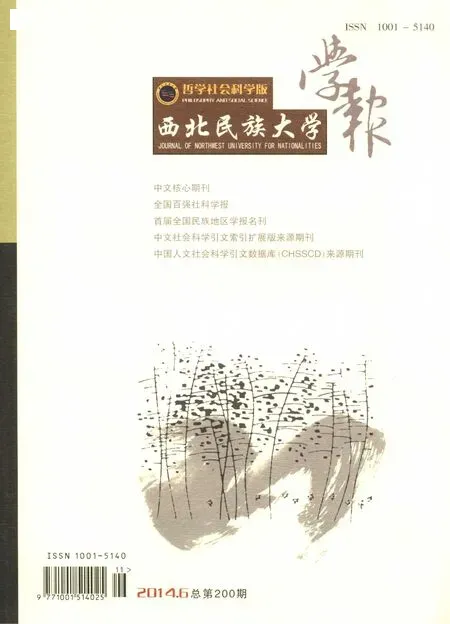碎片化的信仰——论民族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化”建构
肖云泽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200241)
一、民间信仰与传统社会结构
现代社会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以往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1],在这个非延续性和未完成的社会当中,权力、资本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但是在经历权力和文化的强劲祛魅之后,二战以来,作为前现代社会遗物的宗教信仰却在现代社会以普遍的复魅形态出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卷入到这一进程当中,除了三大宗教的复兴之外,民间信仰也重新被激活,近年来尤其显著。在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家那里,宗教是分析传统社会的重要进路。在涂尔干看来,宗教是社会事实的反映。在韦伯眼中,宗教精神催促行动者推动了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不管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宗教和社会是有相互适应的机制的。20世纪末发轫以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囊括了大量的宗教文明遗址和传统宗教信仰,或许“遗产”两字很好地描述了前现代社会的信仰在现代社会的保护、复生和接续情况。但是作为“遗产”又重新焕发新生命的传统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结构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于中国民间信仰来说更是如此。
在杨庆堃那里,中国宗教被区分为制度宗教和扩散宗教,作为扩散宗教的民间信仰与制度宗教有依附关系,他们从儒、释、道中汲取神圣资源,并扩散、依存在儒家权力结构所设置的礼俗体制当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2]。在长期的儒家权力结构下,皇帝统率俗世与阴间的一切事务,驾驭阴阳两套官僚体系[3],中国民间信仰尽管作为儒家信仰的反动,但很难挣脱儒家的价值观和权力体系,往往与皇权、儒家共享一套宇宙观,并在信仰仪式上被皇权、儒家教化,或对之进行刻意模仿,这在汉人民间信仰中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实[4]。
随着中华帝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所依托的礼俗体制逐渐败亡了,以至于20世纪中期余英时把儒学比作“游魂”——儒学所依托的一整套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迁[5]:现代经济的兴起、权力秩序的重新建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延展都在不断地参与到社会的再生产当中。与儒家信仰、礼俗体制共生共荣的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是否也是无处安放的“游魂”也许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是民间信仰复魅是否依然如在传统社会中那般,扩散在现代社会体制当中,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杨庆堃在完成中国民间信仰扩散性的论证后便戛然而止,要讨论清楚民间信仰本身的同时,在“照着讲”之余更要“接着讲”,必须在其所嵌入的现实关系、权力结构和信仰建构中予以梳理。本文将以民族民间信仰为①本文的民族民间信仰是指少数民族信仰,按照宗教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少数民族信仰不是制度宗教,也不是既成的五大宗教之一,应属于民间信仰讨论范畴,所以我们称之为民族民间信仰。中心展开探讨。
二、民族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当代复兴
中华帝国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大致依循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度”展开,尽管期间夹杂战争,但政策强弱随着中央-民族政权力量对比而有不同呈现[6],这也给予大多处于帝国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族裔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汉文化与多文化的夹缝和互动中,民族原生性信仰之间开始互相影响,同时与儒、释、道信仰互相渗透,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民族信仰。比如纳西族的民族原生信仰在与苯教、藏传佛教、民间巫术长期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东巴教;西南民族如白族在受唐文化“以土立德”影响,吸纳道教、佛教等各种文化形成了本主崇拜[7];有些民族则形成了混合型的民族信仰,如壮族的师公教、道公教、么公教,就有道教和原始信仰混合的痕迹。这些信仰都构成少数民族认同的基础。
但是明清两代帝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明显加紧了,这对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变迁乃至当代呈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朱元璋深谙儒家神明对于巩固帝国秩序的益处,下诏加封天下城隍,从高到低分为都、府、州、县四级,皇权所及之地概莫能外,少数民族地区亦是如此。②朱元璋说道:“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明太祖实录·卷八十》),洪武六年三月癸卯;转引自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1版。明朝政权征服云南之后,迁徙大量汉人入滇屯田,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首当其冲。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进,中央政权试图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儒家帝制的统绪当中,普遍在西南地区推行“圣化”政策,即用“孔孟之道”改造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用儒家秩序对民族信仰进行改造,推行儒学、开科取士、移风易俗、改行土葬等,在白族聚居地大理地区和纳西族聚居地丽江地区尤为典型[8]。这些举措都对当地的民族信仰、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多重影响。
尽管历史上民族民间信仰嵌入在中央—国家—域外的权力、文化博弈中,但是金泽认为汉族的原生性氏族——部落宗教向宗法性传统宗教转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宗教主干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直接继承了原生性宗教的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和天地崇拜等基本观念并加以发展,与其他民族所保持的原生性氏族——部落宗教有许多内在的共性因素,从而构成了相互认同基础[9]。而早前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牟钟鉴等学者所倡导的中华宗教文化多元融和也有与此类似的逻辑。可以说,中国各民族在信仰结构上的共通之处,造就了历史上各民族信仰之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这种宗法性宗教或宗法性宗教滥觞构成中国扩散性宗教的内核,对现实社会予以规范。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和汉族民间信仰一样依附在世俗制度当中,他们在信仰结构上的近似和功能的雷同,使得中央政权用儒家对少数民族信仰进行改造有了可能。“神本信仰建构的神圣秩序,通过宗教共同体来表达;人本信仰建构的社会秩序,则通过权力建制来实行”[10]。中央权力对少数民族地区信仰的干预,直接影响其当地的宗教生态和身份认同,①参见云南丽江和先生访谈记录,2012年10月22日。儒家是取得一定程度胜利的。
从晚清、民国到文化大革命,这一长时段的战乱和逐渐加强的反“封建迷信”历程对于民族民间信仰来说是灭顶之灾,有许多经书亡佚、仪式失传。但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宗教复兴当中,民族民间信仰却首当其冲,东巴信仰是个中典型。丽江市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被称为“东巴之乡”,在当地的田野调查中,村民告诉我们,1949年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东巴信仰被认定为“封建迷信”,东巴教经书、法器被收缴,其中大多数以“破四旧”的名义被焚毁,大多数东巴法师被划定为地主和富农,东巴教全面被禁止。但尽管如此,日常生活层面东巴信仰和仪式并未完全消失,他们还在暗地里做一些仪式,只是进行了精简和隐匿。“除非丧葬仪式,白天不敢做,晚上随便地念念经,敲敲鼓,大仪式不做,小仪式还做呢……但是晚上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偷偷摸摸地还干一些呢。瞧日子啊,算命啊,推八字啊,这些还有干的”。②参见云南丽江和先生访谈记录,2012年10月22日。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东巴信仰才渐渐进入缓慢而长期的恢复态势,村民开始请东巴做仪式,但是也仅限于祭祖、婚丧、牵魂等四五个主要仪式,并始终保持小心翼翼的状态,依然是晚上做,白天不做。直到1983年丽江市政府召开东巴座谈会,宣布东巴教为文化,不是迷信,东巴信仰才正式进入了全面恢复的轨道。
与很多民族宗教类似,东巴信仰呈现非常鲜明的日常性和扩散性,神圣与世俗高度合一,其繁复的仪式内容涵盖婚嫁、丧葬、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东巴教一般没有寺庙神殿,也没有专职祭司。东巴平时不脱离生产和民俗生活,只是在应别人邀请之时主持宗教仪式。而正是这种日常性和扩散性的东巴信仰与纳西人的初级社会融为一体,构成了纳西社会本身,惯习化沉淀形成传统。纳西孩童通过东巴教的信仰和仪式完成初级社会化(primarysocialization),成为纳西人。以至于在老东巴老去、经书亡佚、仪式流失的情境中,东巴信仰依然在尝试恢复和传承。而民族信仰已经凝固在他们的记忆中,村中50岁以上的人对东巴法师所念的经文所做的仪式都能听得懂、看得懂,“哪个人做得不好,哪个人做的不对,比以前改进了什么东西,他们会说出来,会提建议”。③参见广西田阳县苏师公访谈,2013年2月6日。这些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东巴法师一旦被指出错误,都必须按照这些老人的意见去更正。民族信仰作为可以识别、非常难忘的实体,作为一种共享经验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
正是基于这样的扩散性和日常性,惯习化所形成的沉淀和传统,使得各民族民间信仰得到普遍恢复,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前以及随后政治权力打击“迷信活动”的几次反复,给予民族民间信仰不少冲击。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师公告诉我们,他的徒弟大多来自偏远山区,也有不少徒弟从业不久便放弃职业外出打工。④Y先后在丽江地区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文化局等文化部门工作过,从1983年第一届东巴座谈会开始,参与了纳西东巴经翻译、纳西族民间歌谣收集、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等大型文化活动,并亲身参与了为丽江地区3个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一位在2004年主持广西田阳县敢壮山祭祀布洛陀大典的黄达佳么公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观念更新与时俱进,将来谁还兴这种旧风俗呢!我已看破红尘,么公不久将被历史自然淘汰。”[11]当然,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大抵也与其神圣资源、社会资本和与权力结构的互动有很大关系,也有很多具有“文化”价值的民间信仰在地方权威和现代经济的裹挟下风生水起。
三、民族民间信仰的“文化化”建构
在许多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和都市精英的眼里,边缘共同体(marginalcommunities)往往体现着民族精华或者国粹[12]。1997年,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并进行数码记录;2006年、2008年纳西东巴画、手工造纸技艺和“热美蹉”舞蹈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指定了一批传承人;2006年,广西布洛陀口传史诗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前现代的少数民族宗教遗产,在当代的民族国家叙事中重新加以建构,这种建构难免进入“民间信仰文化化”[13]的范畴,并呈现与原初的信仰大相径庭的形态,但正如肯尼思·格根所言:吊诡的是,延续传统的方式恰是对其加以改造[14]。
在前现代社会中,精英的聚合形态是单向依赖,社会精英依附于政治精英,乡村精英依赖于城居精英,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为占据弱势地位的精英和普通民众提供庇护,在地方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中保护着社区、群体的利益,承担“保护型精英”的角色[15]。在民族地区的传统社会当中宗教精英有着至高的地位,但是,近代革命和现代化的过程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民族宗教的地位大大下降,而从权力结构中让位,乡村精英迅速退出宗教活动而集中精力于新的举措(从事革命、阶级斗争),继而产生新的政治精英。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改革,乡村被卷入城市化进程,规则、资源和权威格局进入新的调整,新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纷纷被生产出来,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和世俗制度正处在孕育当中,当民间信仰褪去信仰色彩穿上“文化”的外衣,“文化”一旦与精英的权力和资本运作逻辑相结合,便处在一个新的建构当中,这就是“民间信仰文化化”。比如丽江市东巴信仰的建构就是这样一个个案。
Y副市长是丽江市东巴文化复兴的全程见证者,她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纳西族学生教官,也是丽江地区中共建党、建军、建政的主要领导人[16]。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她结识一些纳西文化的泰斗级人物,开始长期从事民族文化工作。①徐霞客在《滇游日记——六》中说丽江纳西族是:“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尽管明朝之后由于屯田、迁移的影响,丽江姓氏大大增加,但是和姓仍然是纳西族普通民众的传统姓氏。参见杨瑞芬,《纳西族姓氏浅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四期。这些在民族文化领域的长期工作和任职经历为她积累了从政的社会资本,Y于2001年通过省厅级干部公开招考担任丽江地区行政署副专员,2003年丽江撤地改市,Y成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成功实现由文化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型,也实现了家族中政治精英的再生产。显然,作为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她的政绩都跟民族文化有关,而民族文化则是当地旅游继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把手中的权力资源转换成可配置资源是她的重要任务。作为全国第十届、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她连续10年提案建议保护纳西东巴文化[17]。2009年,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纳西族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属“吃饭财政”,面对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重任,我们深感需要由国家层面建立有效的保护传承机制,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财政支持,才能保证东巴文化的传承工作循序渐进,使东巴文化的活水源远流长[18]。
为什么声名显赫的丽江还是向国家伸手的“吃饭财政”呢?不管如何,这其中大概有微妙之处。丽江自1994年正式确立旅游为先的城市发展策略,伴随着1999年“黄金周”政策的出台,20年来,丽江从一个年财政收入不到3000万的边陲小城,生长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旅游市场之一:2012年游客数量达到1600万人次,带来了两百多亿元旅游总收入。但政府能从中获得的收入却极其有限,这一年丽江的全部财政收入不过55亿[19]。由于丽江财政的拮据和1992年“南方谈话”后全国的市场经济导向,丽江的旅游开发,走的是民营经济模式。直到今天,除了知名度和市场份额最高的四大景点——古城、玉龙雪山、泸沽湖和老君山掌控在四大管委会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手中外,丽江旅游产业的其余,几乎全部放开给社会资本[20]。
坐落在玉龙雪山底下的民营景区“东巴教圣地”——“玉水寨”就是社会资本运作的受益者。“玉水寨”成立于1997年,2005年被评为国家级AAAA级旅游风景区,其总经理和长红②参见云南丽江和先生访谈记录,2012年10月22日。是纳西人。其母族是丽江知名的东巴世家,已传承16代。如今,和长红已经成为云南省知名民族企业家,是丽江旅游市场催生的经济精英[21]。以“东巴教圣地”自诩的玉水寨拥有一系列颇具颠覆意味的东巴信仰景观:人首蛇身的自然神塑像广场、供奉有东巴什罗和纳西族祖先的和合院、世界记忆文化遗产纪念碑。这些塑像、寺庙与传统的东巴信仰是存有出入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玉水寨的亮点在于一系列的东巴信仰展演和信仰传承活动,在玉水寨网页的景区介绍上写着:一是按纳西族传统,定期举行祭天、祭风、祭自然神等东巴活动;二是每年农历三月五日在和合院举行盛大的东巴法会,各地东巴云集,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相互切磋、相互交流;三是培养年轻东巴,设立原生态东巴文化保护区,资助民间东巴文化传承活动[22]。和长红以商业开发进行信仰传承的方式,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被和长红请去做顾问的当地学者和力民自称“我们常常争论”[23]。
和长红还有一大创举是成立东巴文化传承基地、玉水寨东巴文化传承学校,购买经书,聘请老东巴,专职培养职业东巴,学校培养的东巴还曾代表丽江市政府的各项旅游推广活动。2003年和长红还发起成立丽江市东巴文化传承协会,出任会长,2012年他还获得玉龙县政府批复进行东巴学位评定,这些在东巴信仰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2013年5月和长红还走马上任白沙镇新善村村委会主任,那是和长红的家乡,他的东巴文化传承学校就设立在村中,成为风景区的人才培养基地,而这座村落实际上就是玉水寨风景区的所在地。
近年来,丽江市政府为了加大对旅游市场的控制,以国家实际控股的“大玉龙”景点为中心推动联盟的形成:把玉龙雪山周边大大小小7个景区整合在一起,专门成立一个门票销售公司,一票通行。这其中便包括了民营景区玉水寨。据介绍,2012年,大玉龙景区的门票收入在2.8亿到3亿之间,其他景点分去了4600万。但是显然,未能囊括在这个阵营内的经营者是有不同意见要抒发:“无论大玉龙还是其他景点,收入都增加了,比如玉水寨以前年收入也就五六百万,去年分了三千多万。”[24]
而在新主村的访谈中,和桂生东巴说丽江地区“文革”后的第一场祭天仪式就在新主村举行,当时Y副市长亲临,文化局也到位了。丽江市博物馆里陈列的东巴经有60%是“文革”期间从新主村收去的,H东巴在访谈104次提到文化,俨然以东巴文化的传承者自居。和桂生东巴说东巴信仰有很多仪式,连吃饭的程序都有讲究,目前恢复的仪式只是原有信仰的凤毛麟角。2004年和桂生东巴向丽江政府各个部门集资在村中成立一所东巴学校,但如今政府部门看到他都怕他伸手要钱。①参见云南丽江村民访谈,2012年10月30日。当我们前去访问新主村东巴学校的时候,被访谈人告诉我们村里的东巴学校实际上是玉水寨东巴学校的分校,村民说:“你们还没有到过呢,那座山,还有大树啊,瀑布啊,以后可能开发旅游,就为了这一点。还有主要还是为了文化传承,新主村是发源地嘛。”②丽江旅游三大资源和品牌:看文化遗产到古城,看自然风光到玉龙雪山,看纳西传统文化到玉水寨。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特别是1996年分税制改革完成之后,随着近年社会保障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推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压力形成倒逼,地方政府的“营利型政府”角色逐渐加重,丽江当地政府也难免要拖入到这一转型当中。旅游是丽江的经济命脉,掌握地方权力的政治精英和掌握配置性资源的经济精英关系便会出现微妙变化,于是产生了大卫·文克(DavidWank)在研究私营企业与地方权力的关系时所提出的“共生庇护主义”现象,即从“单向依赖”变为“共存依赖关系”,干部仍然拥有分配资源和机会的权力,但私营企业主对干部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了,而干部对私营企业主则产生了新的依赖关系[25]。所以,丽江旅游模式便是这样的典型,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权力与私营企业主便处在这样的“共存依赖关系”当中。以文化形态出现的东巴信仰便嵌入在这样的社会体制当中,而玉水寨在东巴信仰和文化传承中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不但增进了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为企业主对东巴信仰的营销增添了合法性。
四、民族民间信仰的现代建构
我们的田野调查点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远离丽江古城区,远离丽江的旅游资源中心,其虽然以“东巴之乡”自居,但却不是纳西东巴信仰的发源地。“东巴教圣地”玉水寨在长年经营下虽然被列入丽江旅游“三大资源和品牌”,但传统上认为东巴教圣地却是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的白水台,白水台相传为东巴教创始人东巴什罗道场。2007年,被文化部命名为第一批国家级“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和志本大东巴就居住在三坝乡白地村。
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圣化”政策对东巴文化冲击非常大,逐渐改变了纳西人对东巴文化的认同。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丽江古城的民众大多推崇汉文化,认同于汉文化,将汉文化视为本地“精英文化”“雅文化”的一种标志;而对东巴文化则普遍缺乏认同,除个别与乡村有亲缘关系的家庭之外,东巴教在丽江大研镇城区是不被认同的。而在乡村里,本土文化习俗保留得还比较多,形成了多元的文化认同。民众既认同东巴文化,也认同汉文化、佛道文化,形成了有区域性和社会阶层差异的东巴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的认同局面[26]。
全球化和现代性对他者的追寻使得丽江①丽江从来不是与世隔绝之地,相反在近代,丽江作为进藏的入口,一直是各路外国人,包括军人、间谍、淘金者、传教士出没的地方。18世纪以来,作为英国陆上帝国的跳板,丽江更成为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地区。1990年,英国BBC4台纪录片导演PhilAgland来到丽江,拍摄了7集电视纪录片《云之南》,这部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英国本土的收视率超过了同期播出的电视剧,并获得多个国际大奖。这使得丽江在海外声明鹊起,最早到丽江的游客,也多是零星的外国人。参见刘薇.如何既不乱,又不死丽江:让活的城活着[N].南方周末,2013年7月11日。的独特魅力重新被挖掘了出来,伴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名和“黄金周”所催发的旅游热潮,确实促成了丽江“墙内香”的旅游格局。藏匿在乡村渐趋消亡的“东巴文化”又在丽江古城获得复生,大放异彩,同时又重新获得纳西社会的认同。
在前现代社会,民族民间信仰通过信仰精英操办的仪式、惯习化力量扩散至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层、分工使得群体间异质性拉大,原先同质性较高的初级社会迅速向次级社会演进,每个群体都必须实现次级社会化(secondarysocialization)。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民间信仰运动是恢复到初级社会的话,那么当前在现代性场域下发生的,与旅游经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相伴随的民族民间信仰复兴则是一个次级社会化的进程,而这一切都建基在信仰“文化化”的基础上。
辛允星在研究我国乡村治理术时提出,各种类型的农村社会精英几乎全部成为了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经济精英主要借助于市场手段来扩大自我利益,政治精英则通过扮演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纪人”角色来谋取更大的个人利益,他们之间具有了自发“合谋”的潜力与契机,这就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精英联合”现象在农村地区蔓延开来,并迅速主导了整个乡村治理运动的全过程[27]。而神圣资源的原初拥有者,宗教精英要么进入精英的联合体一同挖掘“文化化”信仰的富矿,要么固守着原初的信仰,进而被遗忘。“中国的宗教和信仰往往不是单纯的宗教和信仰,它们常常被镶嵌在权力与秩序之中而难以得到一种纯粹的呈现形式”[28]。而嵌入在这一进程中的民族民间信仰也必须与现代社会的权力与秩序发生嵌入关系,直至扩散到新的社会结构当中才能真正在现代社会扎下根来,但是现代社会是否有为前现代遗产提供对应的社会结构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宗教是信仰、器物和仪式的统一体,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还往往依托在教会意义上的制度组织当中。玉水寨对于东巴信仰的现代建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品出现的,但在丽江古城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的东巴信仰遗珠,已经被肢解为仪式、法器、音乐、形象等各样的碎片,在市场上贩卖。消费者在市场上只需要消费商品,却不是东巴信仰,甚至也不是东巴文化。
2006年东巴手工造纸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巴纸在市场上受到游客追捧。传统的东巴纸制作工序十分复杂,一天一人仅能制造十几张,由于原材料略带毒性,被誉为“造纸活化石”,能够按照传统工序制作东巴纸的东巴已经十分罕见。和志本曾和儿子在丽江开店,一边贩卖少量东巴纸,一边传承东巴造纸传统技艺。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劣币驱逐良币”:由机器批量生产的东巴纸很快充斥丽江市场,真纸销量锐减,店铺难以为继,多处投诉无门,真正的民间技艺传承人只能撤返回乡[29]。如今丽江随处可见以“东巴”打头的行当:东巴银器、东巴烤鱼、东巴T恤、东巴香烟、东巴裹裙……林林总总,其实很多商贩们根本不知东巴为何物。
五、结论
彼得·伯格在谈到世俗化问题时曾指出,与现代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信仰私人化导致宗教的多元化,多元化则造成市场化,而市场化最终导致神职人员以更理性的方式来经营宗教,以在市场上有竞争力[30]。中国民间信仰的经营方式却不一定由神职人员来完成。在现代经济体制下,在缺乏监管或蓄意而为的市场中,中国宗教的扩散特征使得各种资源拥有者都可以进入宗教市场的领域,推出“灵力”商品。而宗教的扩散性特征使得人人都可以支取神圣资源,也为“文化化”存留了可能。民族民间信仰可以在“文化化”的包装下以旅游项目、文化活动的形式嵌入地方社会,也可以肢解成物化的形式脱域,乃至成为全国性、全球性的文化产品;社群性的民族民间信仰则努力寻求寄生组织,可以是传统的“洞经会”“妈妈会”,也可以是“老人会”“庙委会”,也可以是“传承学校”。它们以各自的途径发挥着这些民族信仰在各自生存环境中的制度资本。但是在这样的经营中,神人关系却被悬空,信仰的内核变得无足轻重,渐次庸俗化、私人化,甚至信仰是什么,大概是没人关心的。
在现代社会,神圣与世俗的界限越发模糊,“文化化”的神圣资源是镶嵌在现实社会网络中的。如果现代社会是娱乐的社会,那么信仰便难逃世俗的娱乐;如果现代社会是利益交往的社会,那么信仰便难逃世俗的功利;如果现代社会是权力交往的社会,那么信仰便难逃世俗的权力;如果现代社会是碎片化的社会,那么信仰便难逃世俗的碎片。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4.
[2]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15]杜赞齐.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4]王斯福.帝国的隐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余英时.现代儒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张声作.宗教与民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张泽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J].中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
[8]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金泽.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关系[N].中国民族报:2005-12-06.
[10]李向平.信仰社会学研究要义——兼论信仰如何成为中国问题[J].江海学刊,2013,(5).
[11]时国轻.广西壮族民族民间信仰的恢复和重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6).
[12]范可.信任、认同与“他者”:族群和民族省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3]陈纬华.灵力经济:一个分析民间信仰活动的新视角[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8,(3):66.
[14]肯尼思·格根.社会建构的邀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
[16]中共丽江县委党校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史志征编办公室.丽江革命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215.
[17]石宏毅.杨一奔:旅游地产开发应着力打造特色文化[EB/OL].http://house.focus.cn/news/2012-03-05/1820663.html.
[18]昆明日报.丽江副市长建议抢救性翻译《东巴经》[EB/OL].http://news.kunming.cn/yn-news/content/2009-03/10/content_1792510.htm.
[19][20][24]刘薇.如何既不乱,又不死丽江:让活的城活着[N].南方周末:2013-07-11.
[21]石玉麟,李倩云.一位民营企业家保护纳西文化的无私奉献——专访玉水寨文化旅游公司总经理和长红(纳西族)[J].云南民族,2012,(12).
[22]丽江玉水寨景区简介[EB/OL].http://www.yushuizhai.com/about/?8.html.
[23]卢斌.丽江古城文化遗产面临生死考验[EB/OL].1.http://news.sina.com.cn/c/p/2008-01-28/030214840352.shtml.
[25]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J].社会学研究,1999,(4).
[26]杨福泉.东巴教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655.
[27]辛允星.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92.
[28]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29]申剑丽.东巴纸贵.21 世纪经济报道[EB/OL].http://money.163.com/11/0216/08/6T0HGJ9K00253B0H.html.
[30]彼得·伯格.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