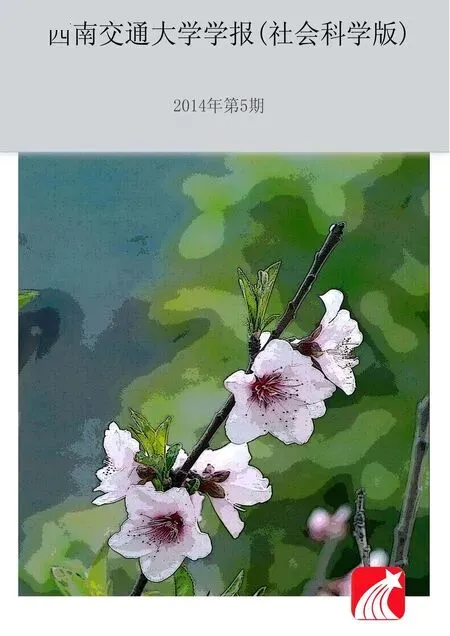黄文旸生平行实考述
相晓燕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戏剧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13)
一
清代乾嘉时期正值升平盛世,社会富庶安定,学术文化高度繁荣,朴学思潮蔚然大兴。不少学者以“博综”著称,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文学、艺术等领域广泛涉猎,并有卓越建树。他们大多幼习辞章,然而囿于“以艺为末,以道为本”的传统习见,成年后往往鄙弃辞章,潜心研治学术。因经史成就太过突出,无形中湮没了他们在文学、艺术等其他领域的成就。同样,亦有部分学者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凸显,从而令后人忽视了其学者身份。戏曲目录学家黄文旸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多才多艺,涉猎广泛,诗、古文、词曲诸文体皆擅长,还穷研六经,融贯诸史,又好审辨金石文字,是一位著述繁富的考据学家,其《曲海目》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综合性戏剧目录。
在灿若星辰的乾嘉学者群体中,黄文旸显然并不是光芒璀璨的一位。他一生未中举,终以贡生,但在清中叶的扬州诗名、文名卓著,颇为当道所重。《清史列传》、《(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和《(光绪)增修甘泉县志》等皆收有关于他的个人小传。笔者曾结合其诸小传,并从黄氏《扫垢山房诗钞》(以下简称《诗钞》)、同时代作家诗文集中钩稽史料,作《清代戏曲目录学家黄文旸生平事迹考》一文加以考辨。现拟撰文对其生平行实作进一步考述。
二
黄文旸的人生历程,经笔者梳理后,大致可分为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期、科考失意的壮岁里居时期和晚年游历齐鲁吴越时期等三个阶段。
(一)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五年(1736 ~1760)——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期
乾隆元年正月十六日,黄文旸出生于扬州甘泉一个破落的盐商家庭。其祖、父名号已不可考,只知其父业鹾,家境一度颇为殷实。至黄文旸时家道已中落,境况大不如前。乾隆二十五年即黄文旸25岁以前,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黄文旸少负才名,师从甘泉名儒、“二王”之一的王世锦,精通制义为文之道,颇受当道赏识,“每学使按试,则首拔”①,因此他踌躇满志,胸怀利济天下之心,以为功名唾手可得。其《哭戴母》诗云:“其时方年少,意气各自喜。缕心事词章,唾手视金紫。”〔1〕乾隆二十四年(1759),黄文旸与何仁山、彭晋函等人在南京结秦晋大会。是年参加乡试,不第②。次年,黄文旸与好友戴润分咏松竹梅,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并订岁寒之盟。其《宝廉堂诗钞序》云:“始予与雨峰缔交,互以制义相劘切,意气壮盛,视金紫如俯拾地芥,谓诗特余事耳。”③其心迹可窥一斑。按,戴润,字雨峰,仪征生员,擅诗。据《扬州画舫录》卷十记载,戴润作有多首平山堂游宴诗,当时传为绝唱。
黄文旸与甘泉公道桥北湖儒生张坚之女张因联姻,其事因和《柳絮》诗促成。张因出身词曲世家,其母系清初戏曲家徐石麒之孙女。因此家学渊源,张因知音审律,诗画皆擅,尤工花卉,在当时颇有声誉,索画者时常盈门。据黄氏《柳絮和韵序》云:一日,好友张丹崖以《柳絮》一诗遍请塾中同学和诗,黄文旸和诗云:“梅实青黄春意微,吹来柳絮拂人衣。鸳鸯宿处多芳草,化作浮萍不肯飞。”张丹崖大为赞赏,因恳请座师王世锦主盟。王师索诗观后,欣然允诺,云:“此诚佳话,吾当力成之”〔1〕。于是作书告知时在淮右的黄父,索币聘请。乾隆二十五年,黄文旸和张因完婚,时黄文旸25 岁,夫人张因20 岁。按阮元《净因道人传》云张因“年二十五归于黄”,其言不确。其实黄氏在《诗钞》中多次言及此事,如卷三《净因四十初度赠四律索和》:“影逐形依二十年,看看黑发变华巅。”〔1〕可知张因40岁时,两人已联姻20 载,则张因于归时为20 岁。卷九《寄寿净因》云:“影逐形依四十年,弟兄师友乐相兼。”〔1〕《灯》云:“贮油燃草明尔室,犹是山妻嫁时物。一卷联吟坐比肩,纸阁芦帘四十年。”〔1〕两诗皆作于张因60 岁时,两人已有相依四十年之说,则知张因结缡时为20 岁,黄张联姻时间应为乾隆二十五年。成婚日,业师王世锦作《双美行》,吴并山作《柳絮篇》和书一册相赠。黄、张联姻这段佳话,在友朋中颇为传颂。《诗钞》中亦多次提及。
乾隆年间扬州地处南北要冲,盐商麇集,往往挟雄财巨贽炫富耀奇,追求奢靡享乐,引领着当时的社会风尚。乾隆六度南巡,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供奉,天下名伶纷纷被征召至此,戏曲演出活动空前繁盛。评话艺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扬州声色之胜,一时甲于天下。置身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黄文旸对戏曲、小说这种不为士大夫所重的俗文学样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微波榭借书歌》中,他曾自述早年读书情形云:“浮沉忆昔寄穷乡,无书可借心茫茫。老巫村妪相慰悦,盲词野史来盈箱。胭脂灵怪银字儿,狡童佚女写迴肠。提刀赶棒铁骑儿,士马发迹数兴亡。我亦孜孜看不厌,爱其结构超庸常。”〔1〕早年僻居乡野的生活给了他广泛涉猎戏曲、小说等各种俗文学样式的机缘,此后黄文旸对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甚为爱好。在此期间,他洞悉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当时扬州著名的说书艺人叶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他还把笔触伸向下层艺人,为名不见经传的杂耍老人作传。
(二)乾隆二十六年至嘉庆三年(1761 ~1798)——科考失意的壮岁里居时期
这一时期,黄文旸忙于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往返于扬州与南京两地。据笔者考证,他至少参加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十七年(1792),嘉庆三年的三次考试④。事实上黄文旸乡试赴考次数应不止此数。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参加乡试,却因病未入考场。其《妻兄张石洲远游十载,归不数月复之粤东军门,作八律寄之》诗下小注云:“石洲约予会于金陵,及予抵秦淮,已留书径去矣。予亦大病几死,不能入棘围而归。”〔1〕此诗创作时间虽未明言,但可考知。《诗钞》按年代分卷,其后《上巳后二日同人雨中登红桥用渔洋山人冶春原韵》诗有“三十过头百不成”之句,则知此诗作于黄文旸25岁至30 岁之间,其时已远游十载的妻兄张石洲约他在南京晤面,结果等不及而径赴粤东军门。黄文旸大病一场,未能入考场而归。从科考时间上推算,该年应为乾隆二十七年。
黄文旸虽精通制义之道,然而造化弄人,科考屡屡失利。时好友戴润所居不远,与之往来密切。互相切磋诗艺之际,黄氏心中郁结发诸诗端,存诗日多。其《宝廉堂诗钞序》云:“及屡试不得志,歌哭不能得已,诗遂日多。时雨峰所居去予不数十武,矮屋一灯,搜罗汉魏迄前明名人专集,寻源竟委,吟讽讨论,往往至午夜不能休。”③他对于汉魏至明代的诗集多有揣摩,用力甚殷,因此其诗文声誉日隆,赢得了主持风雅的扬州长官们的赏识。
乾隆四十二年(1777),黄文旸奉两淮盐运使朱孝纯之命前往桐城敦请姚鼐任梅花书院主讲。朱孝纯风雅好文,师事桐城派古文大家刘大櫆,与姚鼐交情深厚。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出任两淮盐运使后,曾招致名贤为文酒之会。次年即接手官办梅花书院,延姚鼐为山长。乾隆年间扬州梅花书院与安定书院齐名,共同培养了任大椿、段玉裁、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孙星衍等一批能文通艺之士。姚鼐掌教梅花书院期间,“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2〕。黄文旸即为其高足,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诗钞》中存诗《朱思堂都转命往桐城敦请姚梦谷夫子再主梅花书院讲席,吕江花见送,口占一绝》,所咏即是此事。黄文旸对姚鼐执弟子礼甚恭,曾作《呈梦谷夫子》表明心迹,其诗云:“命驾遽云远,登堂宿愿酬。心香焚一瓣,吾道足千秋。盛德休歌凤,离怀自梦鸥。渊源看逝者,日夜水东流。”〔1〕其妻张因作有《祝姚姬传先生尊堂陈太夫人七十寿》,可知两家关系非常亲密。黄文旸执贽姚鼐这位古文大家门下,其古文造诣无疑进益不少,因此得到督学江苏的学政们的赏识:“尝以古文见知于彭芸楣尚书,时尚书督学江苏,后仁和胡豫堂总宪督学时亦倾倒”①。日后扬州学派重镇阮元谓其“雄于文”,自然不纯为溢美之词。姚鼐对黄文旸也颇为器重,有知己之遇(《诗钞》卷五《黄河舟中料理诗文旧稿,奉怀姚姬传、曾宾谷两先生》有诗句云:“蜀岗较文心先折,宾谷先生都转两淮,与予有国士之知,时入觐京师。钟阜谈经鬓早斑。姬传先生为予授业师,时主钟山书院讲席。天南地北两知己,感深老泪落潸潸”),但两人治学主张却迥异:姚鼐尊奉宋学,崇信程朱之学,力倡义理、考据、词章兼容并蓄;黄文旸淹通六经、史学,却厌恶程朱理学,这从其后来撰写的《通史发凡》中可见一斑。
黄文旸曲学造诣颇深,在当时颇有声誉。乾隆四十五年(1780)冬,两淮巡盐御使伊龄阿奉旨删改古今杂剧传奇之违碍者,在扬州设立了临时性的词曲删改局,聘请黄文旸为总校,襄理其事。参加校曲活动者为一批精通曲律的白衣书生,此外还有乐工伶人,场上、案头校曲交相进行。修改戏曲涉及内容、文辞、曲牌及曲词的音律规范等系列问题,校曲人员因此得以观摩大量演出,曲学修养大为提高。这段校曲生涯的历练对黄文旸来说,可谓受益匪浅,其《曲海》即是这次校曲活动的重要成果。乾隆四十七年(1782)秋,扬州词曲删改局撤去。通过一年半的诗文唱酬、曲艺切磋、交流提高,他与校曲局中不少同仁成为知交曲友,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如分校凌廷堪、程枚,戏曲家金兆燕、李斗、方竹楼,“扬州八怪”之一罗聘,著名说书艺人叶英等。
黄文旸虽科考屡屡失意,但身为“邑名诸生”,关心乡邦事宜。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间,他应甘泉令陈太初之聘,参与了修纂《甘泉县志》事。时总校删改戏曲事刚完毕,因此两事在《余伯符重过扬州,感赋四律,并哭令弟少云》诗中都有反映:“方志何堪分史席,时予与邵二云先生有邑乘之役。吴歈只合供歌筵。予年来受鹾使者之聘,校改元明及国朝各杂剧传奇进呈。”〔1〕这次修志事后因故中辍不果,《扬州画舫录》卷十“邵晋涵”条下曾记载之。嘉庆十四年(1809),《甘泉县志》再修时,所录尽散佚。
乾嘉之际,黄文旸为两淮盐运使曾燠招入题襟馆中,与当时名流迭相唱酬。乾隆五十八年(1793),曾燠由员外郎超授两淮盐运使,驻扬长达14 年之久。曾燠擅骈文,以文采风流名世,公事之暇于榷署中专辟题襟馆,昼接宾友,夜染篇翰,四方文人闻风而至,幕府中云集了乾嘉之际著名诗人王芑孙、郭麐等47 人。在其倡导下,宾主间文学活动十分频繁,传世诗集有《邗江题襟集》。时人以为较北宋西昆酬唱有过之而无不及。曾燠爱好戏曲,幕府中延致的戏曲家除黄文旸外,尚有清代红楼戏谱曲第一家仲振奎、传奇《渔家傲》作者吴锡麒、“乾隆时期曲家第一”蒋士铨之三子蒋知让等。梨园名班时常应召入其幕府中演出,在时人诗文集中不乏演出活动记载。黄文旸之入曾幕,当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四年(1793 ~1799)之间④。曾燠对他甚为礼遇,黄文旸称与其“有国士之知”。唱和诗作现已不存。
里居期间,黄文旸与扬州学派诸子阮元、江藩、焦循、黄承吉、李钟泗、凌曙、汪冬巢等交往频繁。论年辈、声望,黄文旸自为里中老宿。他与阮元、黄承吉为闾巷忘年交,彼此声气相通,来往密切。甘泉焦、黄两家联姻,焦循长妹嫁与黄文旸长子黄金为妻,因此黄文旸与焦循存姻亲之谊。江藩与他有通家叔侄之谊。居里时,诸子时相过从,或研讨曲学,或辑录诗文。在阮元主持编纂《淮海英灵集》时,黄文旸和焦循、阮鸿、李斗、江藩等扬州学派诸子一起参与了征诗和编辑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和这些同乡后学多次赴南京参加了三年一度的乡试。
嘉庆三年秋,63 岁的黄文旸在南京参加完最后一次乡试后,与友人王豫、焦循等雅集于快园小西湖。这时距离他首次参加秦晋大会已近40 年,与他同科赴考的后学黄承吉高中江南省乡试解元。多年的名落孙山令他心力交瘁,在目睹阮元、凌廷堪、黄承吉等后学纷纷步入仕途之后,黄文旸这位“雄于文”的里中老宿彻底断了科举之念。
(三)嘉庆四年至嘉庆十四年(1799 ~1809)——晚年游历齐鲁吴越时期
黄文旸既科场失意,又治生乏术,家境窘迫。《诗钞》中多有叹贫嗟怀之作,如卷一《水南村墅梅花盛开,时雪盛,绝粮,戏作长歌》、《敝葛行》、《秋寒戏作无衣歌示净因》,卷二《客有于岁暮馈金者,作诗却之》等。早年的他显然以高人雅士自许,作诗自矜怀抱,如“最爱冰清与玉洁,萧然终日绝逢迎”、“闭门且试疗饥方,细嚼梅花与雪和”〔1〕等,夫妇安贫乐道,诗词唱和。张因常典当簪珥以为炊资,或以画易米,或赌记书籍、策数、典故以为乐,犹不失风雅之举。晚年其妻张因则“心劳家屡空,肺病药频倾”〔1〕,生活穷困愁苦。伴随科考的多次失利,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黄文旸日益清醒,更失意颓丧,在诗中发出了类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哀叹:“我涉世路太蹇踬,袖手愧无生业作。亦知闭户非长策,无奈出门多困挫。”〔1〕卷十二《自述》诗云:“古今较穷境,我穷实无敌……我以贱得贫,无田更无宅。举家系生死,岂能讳谋食。所嗟谋太愚,碌碌事笔墨。文境与穷境,其苦无不历……丈夫身既废,性情聊自适。白日照箪瓢,歌声出金石。俛仰苟随人,富贵早可得。若以诗悦世,枉直愧今昔。分咐妻与子,饿死共努力。”〔1〕此诗诚为乾隆盛世的虚光幻影下,士人生计维艰、穷愁困顿的真实写照。
乾嘉时期扬州盐业经济畸形发展,在浓郁的商业化、世俗化气息熏染下,在生计存亡的现实面前,要保持高洁的文人品格实属不易。黄文旸无奈之下,作出了趋利避害的选择。父子一度投靠盐商林松,沦为门下食客,又因“助纣为虐,几陷绝境”⑤。焦循《上阮中丞第二书》云:“且此黄秋平者,实为无赖之小人,以刀笔佐讼之才为其才,贾虚名以惑众。始认王虞载之弃妾为女,假此以靠汪斗张为衣食父母,斗张穷则反噬之。既则投身为商奴林松之门下客,怂恿其捐官。已而蒙捐狱起,伊则助林奴与缙绅诸公抗,及合城绅士起而攻之,伊则舍松而去。又腆颜与士大夫为伍,反覆无耻,实士林所不容,貌为乡愿而心则蛇蝎。”《上阮中丞第三书》云:“父子同投身为商奴林松之门下客,且使其子效奔走买办之役……因念文旸助商奴林松与缙绅为难,谢太常、秦太史率合城绅士攻之,若非阁下荐之于圣府,则文旸既得罪于士大夫,又无以谢商奴,不为饿莩,必流入讼棍。不自敛抑,公然放肆,又得罪于圣公,亦无颜面见大人矣。”虽然焦循之言辞未免过激,但从中可知黄文旸已完全沦为盐商之门下食客,充当清客蔑片之流,此与其《诗钞》中自抒高洁志趣之隐士形象判若两人。
为谋生计,晚年他一度奔走齐鲁吴越间。嘉庆四年端午,在阮元的荐举下,64 岁的黄文旸北上阙里,教授阮元妻舅、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经文。在阙里,黄文旸参谒至圣林庙、颜子庙等,登舞雩台,观览御赐姬周礼器、吴道子画鲁司寇像、端木子手植楷、阙里所藏先世衣冠及明太祖御容并所颁铁冠图,一一形诸歌咏,往往是“语不惊人聊自适,稿才脱手已争传”〔1〕,诗名盛播山左。他与孔府诗人孔宪圭、孔小荭、孔季衡、孔季镇等诗酒唱和,衡文麈艺,结下了深厚友谊。帷帐授经之余,他尽览阙里藏书,探奇采异,日不暇接。在孔府诗人们眼中,黄文旸这位儒家正统人士用世之心甚殷,自觉地以辅民化俗为己任,“谈忠孝则可歌可泣,谈奸佞则宜雷宜霆,即偶谈稗官野史、神鬼怪录,顷刻变幻千态万状,令人目眩神摇,几不自主。一言一语诙谐嘲笑,无不动人如此”(孔宪圭《〈扫垢山房诗钞〉序》)⑥。
嘉庆五年(1800)张因六十寿辰之际,黄文旸在阙里作《寄寿净因》诗四首寄归。张因和长子黄金皆有和诗,姻亲焦循爱而刻之,一时传播四方,友朋纷纷投赠佳篇,得诗近三百首,次原韵者35 人,形成一时盛事。按,黄文旸诗礼传家,张因工诗画,“花卉翎毛称逸品”。黄氏夫妇题咏联吟,琴瑟和鸣,时人传为美谈。其长子黄金亦擅诗,“得唐人绝句法”。因此黄家在当时扬州一带颇有声誉,《扬州画舫录》卷九云:“江北一家能诗者,黄氏其一焉”〔2〕。冬至日,黄文旸返回甘泉家中,开始着手删改《诗钞》,并嘱二子收藏。
次年春,黄文旸再次动身前往阙里。这次可能是短期游历,阙里诗友孔宪增、孔宪堃、孔宪圭及阮元等纷纷为其《诗钞》作序,高度评价其文学成就。嘉庆八年(1803),黄文旸将自己的诗歌删定成《诗钞》十二卷,并在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之父孔宪增资助下付梓。
这年十月十日,应浙江巡抚阮元之邀,黄文旸携妻张因作西湖之游。黄文旸比阮元年长27 岁,阮元称其“自幼里巷间为忘年交”,黄、阮两家声息相通,来往密切。因此阮元对黄氏夫妇礼遇有加,于节署中特辟客馆居之,并赠诗云:“特因梁孟启高席,纸阁芦簾绝尘埃。相近白圭诗馆外,两家书卷一齐开。”⑦一时传颂,堪称盛事。两年客游中,黄文旸夫妇怡然自得,形迹洒脱,“每二老出游,竹舆小舫,秋衫白发,潇洒于湖光山色间”〔3〕。张因与阮元之妻孔经楼相得甚欢,后者以师事之,诗词唱酬,多有吟咏。嘉庆九年(1804),张因的《绿秋书屋诗钞》在阮元夫妇资助下刊刻。
嘉庆十年(1805)正月十六日,黄文旸在阮元节署中度过了七十寿辰。阮元招饮于积古斋,并以所藏古铜爵酹为他祝寿。早春二月,黄文旸与阮亨等人修皋亭之禊,阮亨首倡一律,黄氏有和作《同人皋亭看桃花作》。
这年家遭变故,黄文旸弟黄三诬陷长媳焦氏将黄家钱财透入其母家买置田地。黄文旸在杭州知悉后诘问焦氏母女,信中有“家用一百九十六两七钱三分之多,仅十四月,何以不足用而典当一空”④的疑问,遂使“管理家事”的焦氏媳有口难辩,焦母“愤结而成疾”,数月后病故。事实上长子黄金夫妇体弱多病,所耗银两皆用于问诊买药。因此,焦循多次请求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主持公道,《里堂札记》中关于此事就有三封信函。在《上阮中丞第三书》中,焦循多述黄文旸为人之“虚”与“妒”,并言“文旸之人谊所当绝”。按,黄焦两家联姻,关系原本亲密,其后竟因此构爨而断交。十月,黄文旸夫妇从杭州返回甘泉,当与此事有关。其后黄氏夫妇居天心墩扫垢山下,张因画《扫垢山房联吟图》,阮元、李斗、李周南等皆有题咏。嘉庆十二年(1807),长媳焦氏因此“意外之谗,突来虺易”〔4〕而逝。季冬,张因卒,年六十有七。
嘉庆十四年二月,74 岁高龄的黄文旸与好友凌廷堪相会于浙江学政阮元节署。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诗酒唱和,颇极友朋之乐。此后他返回甘泉,不再外出。时与同里孝子吴涣论诗,相互唱酬,并为之作《枕流阁诗钞序》。其后事迹不详。
注释:
①孔宪增《〈扫垢山房诗钞〉序》,见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卷首,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59,第1 页。
②这是目前可考知的黄文旸参加乡试的最早年份。具体考证参见笔者《清代戏曲目录学家黄文旸生平事迹考》(刊发于《文化艺术研究》2011 年第4 期)一文的“乡试考”。
③黄文旸《宝廉堂诗钞序》,汪廷儒辑《广陵思古编》卷十一,清刻本。
④具体考证参见笔者《清代戏曲目录学家黄文旸生平事迹考》一文中的“游历齐鲁吴越考”。
⑤焦循《上阮中丞第二书》,见《里堂文稿》(未分卷),上海图书馆藏。
⑥孔宪圭《〈扫垢山房诗钞〉序》,《扫垢山房诗钞》卷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59,第5 页。
⑦阮亨《瀛舟笔谈》卷八,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1〕黄文旸. 扫垢山房诗钞〔C〕∥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2,8,28,107,103,117,13,26,37,9,75,38,135,112.
〔2〕李 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63,214.
〔3〕阮 元.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531.
〔4〕焦 循.雕菰楼集〔C〕∥丛书集成初编(集部2196).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