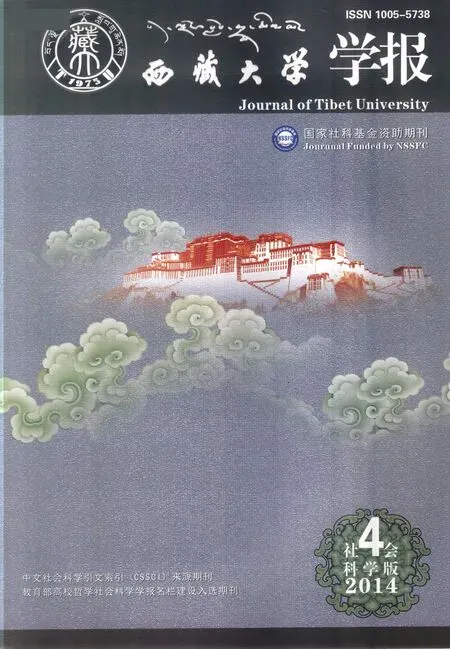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叶拉太,《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拉卜楞属寺在安多藏区的地域扩展研究
属寺的确立是藏传佛教各派别地域扩展的标志。1710年格鲁派拉卜楞寺建立,它以夏河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将政教势力先后伸向大夏河、洮河、白龙江等流域以及青海、四川地区,逐渐成为安多藏区最大的政教集团之一。至清末民初基本定型,拉卜楞属寺在安多藏区的空间分布基本维持在甘、青、川交界一带。其地域扩展经历早期在卓尼、大夏河等地区扩展势力的艰辛,后期在安多藏区的全面开拓,以及民国时期缓慢发展三大历史阶段。(梁姗姗,《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藏族传统生态观的体系架构
青藏高原是一个自然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然而,藏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生态观,基本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藏族传统的生态观大致包括∶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朴素观念;禁止杀生、爱生护生的生命伦理;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的平衡法则。同时,原始信仰、藏传佛教以及历代法规都对藏族的生态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构成了一个包括朴素观念、核心思想以及制度保障的藏族传统生态观的体系架构,并通过风俗习惯形式得以传承。当然,藏族的传统生态观的体系架构也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切排,陈海燕,《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百年语文教科书中的西藏书写
百年语文教科书中,西藏题材课文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课文对西藏的书写经历了从描述西藏地理风物到展现西藏特色文化,从提醒国家边防安全到关注边疆经济文化发展的演变历程。语文教科书是青少年学生的重要读物,西藏题材课文成为他们了解西藏、熟悉边疆的重要媒介,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素材。西藏题材课文生动形象地让全国的中小学生认识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安全稳定,关心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赵新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第一,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强化了寺院作为藏族精神圣地的影响力,而城市中的重要寺院也往往成为城市的经济重心,特别是寺院周围地区成为重要的商贸之地;第二,寺院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寺院经济的发展对西藏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多种不利影响。西藏寺院经济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群体经济,这种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种排外封闭的经济类型。一方面,西藏寺院大量占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其生产、消费和管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进行,较少参与社会的再生产,因而影响了社会再生产能力的提高,对城市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西藏寺院所占有的耕地、牧场、牲畜以及各种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僧侣消费、各种宗教活动,以及寺院的建造、装饰和修缮等方面,较少用于社会再生产,因而严重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了西藏城市化进程。(何一民,邓真,《兰州学刊》2014年第3期)
驻藏大臣统辖西藏驻军研究
清代用兵西藏,健全驻军制度,行使维护地方和保卫边疆之职责,有力地推进了清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纵观清代在西藏的驻军和驻藏大臣统领军务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到,第一,清代在西藏的军队,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绿营兵、乾隆年间整编后正式建立的常备藏军及清末的新军。第二,驻藏大臣统领清代在西藏的驻军,包括统领中央政府驻藏清军、达木蒙古军、整编后的西藏地方常备军。第三,清代前期,西藏地方内讧不断,战乱频仍,以致出现了驻藏大臣被杀震动朝野的事件。第四,清朝中后期西藏地方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特别是面对英、俄对西藏的入侵,中国藏军以防御反击战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维护了国家统一,并为安定西藏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在西藏的驻军和驻藏大臣统领军乡的制度,对于清代中央政府行使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保卫中国西南边疆安全、抵御外来侵略、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和国家领土完整,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冯智,《西藏研究》2014年第4期)
敦煌等地在吐蕃时期的藏汉音乐文化交流研究
古代民族间的战争与侵略形成了民族迁移,并促进了民族间的音乐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形成大规模的相互交流与融介。这些交流影响不仅在敦煌壁画中、石窟古文献中、民间保存的乐器中、寺院的佛经中留下痕迹。以敦煌等地为中心的河陇地区,在吐蕃时期的汉藏音乐文化交流中达到“繁荣”的状态,在这一片地区的各个阶层中流行起吐蕃民间舞;在吐蕃时期的壁画中还能找到藏族传统舞—鼓舞的前身;当时汉族流行的乐器被用于吐蕃军乐队中在户外、行进之时表演。因为吐蕃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而唐朝的僧人伴以音乐进行佛教传播,故僧人们在唐朝与吐蕃两地传播佛教的同时也传播了音乐,同时促成了藏戏的发展繁荣。吐蕃政权崩溃后,有相当部分的吐蕃后裔留在了河陇一带,构成了今天甘青一带藏族的最早先民,吐蕃东向发展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林裕春,《民族音乐》2014年第5期)
试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
《宋史·吐蕃传》记载唃厮啰政权的宗教是“尊释氏”。由于史料的缺乏,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唃厮啰政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属于藏传佛教的范畴,或者认为受到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分析,比较了吐蕃佛教和汉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影响,认为宋代河湟流域的佛教发展有两种不同的方式,首先是汉传佛教继续传播,而另一传播方式是在藏族中用藏语传播的深受汉传佛教禅宗影响但不同于藏传佛教的佛教,即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河湟流域在藏族中传播的佛教融入藏传佛教序列自元代开始,特别是明末清初时期,随着藏传佛教教派在河湟流域的传播,河湟流域藏族中传播的藏语系佛教也就逐渐融入藏传佛教体系了,可将河湟地区的佛教归为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张虽旺,王启龙,《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论因明学对根敦群培学术思想的影响
根敦群培是20世纪藏族文化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在藏族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的研究成果涉猎近十个学科领域,且独领风骚、自成一体,他是一位学术功底深厚、特立独行、最具现代感的学者。文章通过因明学的视角,探讨了根敦群培在宗教、历史和文学学科领域中所受因明思想对他治学方法及思维的深刻影响,提出了推理论辩、判别考证、澄清事实的因明思维方式是根敦群培学术思想的根基,也是他富有特质的叙事依据和逻辑起点。(万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
藏文的创制与早期典籍的装帧设计
藏文的创制年代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吐蕃时期的吞弥·桑布扎创制的藏文无疑比早期的文字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普及和推广,惠及了整个藏民族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文字的价值体现的更为充分,而这个时期恰逢佛教开始驻足西藏,佛经的传入引发了译经事业的蓬勃兴起,藏文字体和佛教典籍的装帧设计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文章通过梳理典籍文献以及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吐蕃时期藏文字体及其典籍的装帧设计的基本特征。(格桑多吉,《西藏艺术研究》2014年第3期)
白马藏语与周边其他藏语方言的层次关系研究
根据安多藏语方言诸土语群的不同语音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语音层。在这三个语音层中,辅音由繁到简或彻底消失,复合元音由少变多,声调从不区别词义到区别词义,是白马藏语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白马藏语语音特点的综合分析,得知其已基本失去第一语音层的特征而接近康藏方言,说明白马藏语是安多和康藏方言之间的一种藏语次方言。除了语言自身发展的原因外,经济、宗教、历史等社会因素对语言演变具有重要影响。(杨士宏,第五淳,班旭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汉语词“吐蕃”的起源和本真音读考
汉语词“吐蕃”的注音历来有分歧。文章探讨吐蕃一词的起源,认为“吐蕃”并非吐蕃政权或族群的自称,而是他称;吐蕃作为他称应先产生于突厥并后传于吐谷浑,吐谷浑人引导吐蕃使者通使唐朝的话,其所介绍的吐蕃名称应是“音自于突厥”。结合“吐蕃”一词在唐代的音韵表现和敦煌出土吐蕃时期汉藏文对音材料,分析“吐蕃”一词起源时“蕃”的本真音读为重唇音声母和-n韵尾韵母,不可能读为bō,主张按“追史从古”原则给“吐蕃”注音。(南晓民,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