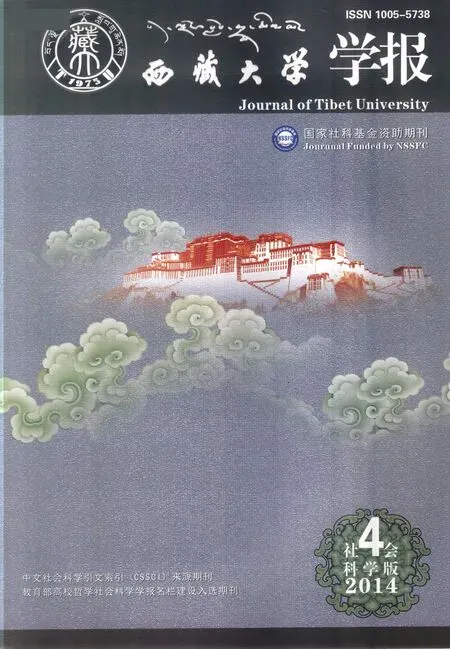略述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基本经验
次旦扎西顿 拉
(①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②西藏社会主义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略述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基本经验
次旦扎西①顿 拉②
(①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②西藏社会主义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元朝统一全国后,为全面管理西藏政教事务,采取了诸多施政措施,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文章概述了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基本经验,认为元中央政府通过推行帝师制度、设立中央机构宣政院和地方行政组织万户,稳固建立对西藏地方的统辖,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中央;西藏地方;宗教事务;经验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地方,其杰出首领铁木真(成吉思汗)通过长年的兼并战争,于公元1206年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蒙古汗国通过西进南征的几次军事行动,统一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结束了全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历史,使全国各民族地区统一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也顺应了各族人民的愿望,带给祖国各族人民以深远的影响,揭开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新的一页,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入确立阶段奠定了基础。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1229年窝阔台继位,他将原来西夏的辖区以及甘青部分藏区划归其次子阔端作为封地。阔端一方面致力于经营西夏地区和甘青藏区,另一方面下决心将西藏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阔端派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入藏。蒙古军队从青海进入藏北,焚毁了噶当派主寺热振寺,一些作过抵抗的噶当派寺院遭到惨重的失败,蒙古军队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然后返回。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有二:一是阔端所统辖的西夏王室崇信佛教,曾经聘请西藏佛教僧人担任国师,因此阔端要物色一个佛教领袖人物来协助他管理西夏地区;二是为了将西藏统一于蒙古汗国之下,要在西藏各地方势力中寻找一个代表人物,与其商讨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大事。多达那波回到凉州后向阔端呈递了《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其中说道:“此边徼藏区,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法者,唯萨迦班智达。当迎致何人,请传王命。”[1]
多达那波的《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表明,其奉命带军深入卫藏不辱使命,反映的卫藏政教势力现状符合实情,为阔端准确物色代言人提供了有效情报,应该说,多达那波为西藏的归附和后来元中央政府对藏区有效行使主权功不可没。鉴于萨迦派在后藏的雄厚势力和其教派领袖萨班·贡噶坚参在卫藏各地享有的崇高声望,阔端决定选择萨班作为商讨西藏归附事宜的代表人物,于1244年再次派遣多达那波等人带着召请萨班的旨令和赏赐物品来到后藏萨迦地方,请萨班赴凉州会见。当萨班接到阔端召请旨令时,已经是63岁高龄,他审时度势,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应召。“贡噶坚赞于63岁的阳木龙年(指1244年),伯侄三人(指萨班携其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侄子)前去,路上走了三年,于马年(指1246年)到达凉州。”[2]一路上萨班与各地方势力磋商归顺事宜,争取大家的支持,并承诺代表西藏政教和各地方势力的利益进行妥善的会谈。
公元1247年,萨班与阔端在甘肃凉州(今武威)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晤”。会晤的重要意义在于详细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附蒙古汗国的条件,并达成了共识,这为后来元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
归附事宜议定后,萨班为传达商定结果向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纳里速各地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信中宣告,自“凉州会晤”西藏诸地皆并为蒙古汗国,藏族百官和众僧俗百姓已为蒙古大汗臣民。信中同时传达了两件事:归附的西藏各地首领的原有地位蒙古大汗皆予以承认;萨迦派已受命代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
萨班的凉州之行,促使了蒙古汗国以和平方式在西藏地方建制,避免了军事征伐引起的涂炭,因此西藏地方的正常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未遭到大的破坏、干扰,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这些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当时西藏各地僧俗首领所完全接受。同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西藏400年的割据征战,使西藏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和平生活。萨班不愧为祖国统一、民族兴旺、西藏社会长足发展做出卓越功勋的杰出历史人物。
1251年蒙哥汗即位。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统管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藏族地区。忽必烈沿着阔端、萨班开创的蒙古汗国统辖西藏地方的历史轨迹,积极推进了与萨迦派的关系。1251年11月14日,萨班·贡噶坚赞圆寂于幻化寺,八思巴遂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继承萨班遗愿,发展萨班开创的依托蒙古汗王确立萨迦派对西藏各地方势力领导地位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这位新一代领袖的肩上。
随着蒙古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进程,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1253年忽必烈再次召请八思巴,同时还召见噶玛噶举派的首领噶玛拔希。因为八思巴学识渊博,忽必烈留八思巴在营帐中,为八思巴尊“上师”名号,接受八思巴的灌顶。
1259年7月,蒙哥汗病死在攻打南宋的四川战场上,翌年,忽必烈继汗位。鉴于八思巴自1253年多年追随忽必烈左右,忠心可鉴,忽必烈封“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3]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忽必烈于1262年派遣使臣进藏,向各教派的寺院发放布施,并颁布法令,宣布新即位的大汗对西藏的德惠。八思巴作为国师积极配合忽必烈的行动,写了一封致乌思藏大德的信,这是继萨班公开信后萨迦派首领致西藏地方各派僧人的又一封重要通告信。
1265年,八思巴奉命返回西藏,着手进行划分十三万户、建立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工作。为有效管理西藏地方事务,1267年忽必烈任命释迦桑布为第一任萨迦本钦,成为萨迦地方政权的实际首领,从此确立了“萨迦本钦”代行帝师掌管西藏政教事务的地方管理模式。历任“萨迦本钦”即为帝师的属员,由帝师举荐,皇帝任命产生,因此必须为帝师负责,代替帝师处理西藏一切事务,因而形成了萨迦政权特有的一种体制,即“帝师——本钦”体制。
一、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基本经验
(一)推行帝师制度
1269年八思巴从西藏返回大都,完成并进献了由他创制的“蒙古新字”,通常被叫作“八思巴文”。由于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对维系新王朝的威望有功,更由于八思巴竭力推行中央政权管理西藏事务的各项举措,使西藏纳入元朝中央的稳固统辖之下,1270年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又加封为“大宝法王”,并且将原西夏王玉印改制成六棱玉印,其封文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4]1280(中统十六)年,八思巴逝世于萨迦,鉴于其卓越功勋,忽必烈为其“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5]并建真身舍利塔以示怀念。
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一百年中元朝共有8个皇帝,每个皇帝都封有帝师,元代先后有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帝师是“(元朝)帝国政府中一个常设的职位,他在总制院以及后来的宣政院中享有非凡的荣誉,”[6]其办事机构为都功德司。帝师的主要职责有:第一,给皇帝讲经说法,授戒灌顶,带领僧众做佛事,为皇帝及其家族禳灾祛难、祈福延寿;第二,统领天下僧尼,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第三,管理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
元朝历代皇帝均笃信佛教。元朝统一全国后,利用宗教教义和宗教势力管理全国成了重要国策。而抬高帝师地位,授予帝师重要职责,令其协助治理全国是必要手段,所以,终元一代帝师的地位极其崇高。据史料记载,皇帝听法,帝师要坐上座;朝廷朝会,帝师位居诸王、百官之上;帝师嗣立,皇帝赐以玉印,并下诏宣谕天下;帝师将临京都,一品以下官员皆需出城迎接,并以皇帝出行的一半仪仗作为前导,如此种种尽显帝师受到的殊胜礼遇。
元朝推行帝师制度,优崇西藏佛教领袖,稳固地建立对西藏地方的统辖,由此形成了中央王朝通过西藏佛教领袖人物加强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格局。这种格局在明清时代得以延续和发展,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宣政院的设立
宣政院的前身是总制院,于1264年设立。按照中原的仪文制度是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大机构,而总制院是元朝特设的一个机构,它与前面所述之三大机构成为元朝中央的四大政权机构。总制院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整个藏族地区行政事务,以国师八思巴领院事。总制院的设立,是元朝的新创,是史无前例的,它的设立充分体现了蒙古人的聪明与智慧,是忽必烈强化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推进全国大一统的一项重要举措。后来在桑哥任总制院院使期间,认为总制院所统管藏区事务繁重,为加强对西藏和整个藏族地区的管理,须提高总制院的官阶和地位,乃奏请改名升格。桑哥向忽必烈提出:“总制院所统西番诸宣慰司,军事财谷事体甚重,宜有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7]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下令将总制院改名为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8]地位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平等。“由于都功德司和总制院都由帝师统领,后来,在总制院改为宣政院后,元政府便把都功德使司合并到宣政院机构中去。”[9]宣政院“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四员、管沟一员、照磨一员”[10]等各级官员,其官员建制遵行“僧俗并用”的原则,而第二位院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产生。其历任院使为桑哥、暗普、脱虎脱、铁木迭儿、月鲁帖木儿八剌、八思吉思、钦察台、丑驴、旭迈杰、锁秃、囊加台、答儿麻失里、回回、马札儿台、沙剌班、伯颜、末吉、汪家奴、脱脱、亦怜真班、韩家讷、笃怜帖木儿、哈麻、搠思监、橐驩。[11]宣政院的编制问题,仁庆扎西先生认为终元一代其编制增减常有变动,直到“天历二年,罢功德使司归宣政院,定置置院使十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佥院二员,同佥三员,院判三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三员,照磨一员,管沟一员,掾使十五人,蒙古必阇赤二人,回回掾使二人,怯里马赤四人,知引二人,宣使十五人,典史有才差。”[12]宣政院作为元朝中央管理西藏事务的常设机构,它“军民通摄”,不仅管理藏区的行政、宗教事务,而且有权管理藏区的军事。
(三)万户的设立
万户是元朝在西藏地方设立的次于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行政机构。万户在西藏地方的设置早在蒙哥汗时期就已经开始,但那时万户的机构和职权不明确。忽必烈时期命令八思巴按照元朝的制度,在西藏划分万户,调整和确定各万户的辖地和属民,从而使各万户成为地域性的行政组织。
忽必烈时期,依据西藏各教派和地方政教集团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属民分布情况,在西藏划分了十三个万户。十三万户实际上就是卫藏地区的十三个势力集团。其建立也是“通过联合各地教派和世俗势力的办法,首先划分了米德和拉德,然后划分十三万户,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萨迦政权。”[13]万户长官为万户长,一般而言,万户长一定是当地政教两方面的领袖或具有左右当地政教势力的地方代表人物。
二、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主要教训与启示
关于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的主要教训,王启龙教授在《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中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在该文中藏传佛教对元代政治的消极作用归纳为三:权势过大,中央难以掌控;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影响朝廷政治,导致国家衰败。[14]《释老传》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15]表明元廷礼佛敬僧程度之最。就因朝廷过度佞佛,导致社会的不满和萨迦地方政权的迅速衰落。对于此问题有不少学者已撰文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今从两方面稍作阐述。
(一)元中央政府对萨迦的偏袒与“止贡林洛”事件
元朝在西藏划分了十三万户,萨迦政权的行政建制是以十三万户为基础的,而其划分的依据为原有各教派和其他地方势力的传统属地范围。所以说,十三万户的建制既尊重沿袭了西藏传统的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政治格局,又以赐予萨迦本钦为“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的头衔,将原来的仅仅作为卫藏十三万户之一的萨迦派立为十三万户之首。如此做法,在元中央政府利用萨迦派在西藏行使主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其不可避免的弊端。因为十三万户原来并没有高下尊卑之分,各万户在各自辖区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分别管理自己的庄园属民。而萨迦作为十三万户之首的地位并非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而是元朝强加于其他万户之上的。由于元朝极力扶植萨迦派,硬使其成为十三万户之首,其他万户是迫于元朝的压力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的,一旦元朝对萨迦派的支持稍微松驰或是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变得十分尖锐时,其他万户对萨迦就不那么顺从了,萨迦政权的地位就必然受到来自西藏内部其他教派势力强有力的挑战。公元1290年发生的“止贡林洛”事件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
对于“止贡林洛”事件,东嘎·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论述:“他(指恰那多吉之子达玛巴拉)执政一年后,止贡派的京俄居尼巴仁钦多吉去世,由仁波且扎西益西接任,他把自己的外甥那察扎列巴送到萨迦派喇嘛益西仁钦那里。正当萨迦派要任命他为止贡寺的座主时,被京俄居尼巴仁钦多吉的弟弟甲吾扎巴仁钦杀死。萨迦派为此责问止贡派时,止贡派全都起来支持甲吾扎巴仁钦,萨迦派和止贡派由此开始发生纠纷。达玛巴拉执政的第五年、藏历饶迥木鸡年(公元1285),止贡派的根多仁钦领来西路蒙古之王旭烈兀的军队九万余人进藏,向萨迦派进攻。此后,由不是萨迦家族的绛漾仁钦坚赞从藏历第五饶迥火猪年(公元1287年)起执政八年。在他执政的第四年,萨迦本钦旺琏引来由忽必烈的儿子铁穆别克(铁穆别克,应为铁木儿不花,是忽必烈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之子,他本人受封为“镇西武靖王”)率领的军队,与后藏军队一起进攻止贡派,放火烧毁止贡梯寺的大殿,杀死止贡僧俗平民一万余人。止贡派的属地甲尔、达波、工布、唉、列、洛若、山南、扎噶、雅觉、门等地方被萨迦派夺去。这一事件在藏文典籍中称为‘止贡林洛’”。[16]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记载可见,“止贡林洛”缘起于萨迦派对止贡派内部事务的干预。实际上,萨迦派完全有处理西藏各地政教事务的权力,早在1247年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纳里速各地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中萨班已向当时的西藏各僧俗官员宣告——萨迦派已受命代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但问题是在实际的权力行使过程中,不少地方势力并不买账,尤其在涉及重大利益之时,其结果是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以兵戎相见。从“止贡林洛”事件的结局看,没有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介入,萨迦政权无力收拾其残局。所以说,萨迦政权能否在西藏行使其施政权力,主要取决于元朝中央政府在各阶段对它的支持程度。
(二)对萨迦派僧侣集团的过度纵容与萨迦统治集团的腐败衰微
终元一代,对藏传佛教僧侣集团,尤其是萨迦派上层僧侣过度崇信,对社会和藏传佛教本身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百年之间,朝廷所以崇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继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17]在元朝中央的支持下,萨迦派上层僧侣集团处于养尊处优、权势显赫的地位,他们仗着朝廷的支持,生活腐化、唯利是图,迅速堕落,使萨迦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据一些汉文史籍记载:萨迦派有恃无恐,僧衣罩住了武装,地上的乐土就是幻想里的天国。他们或者结婚生了子女后,再剃度出家,或者出家后又还俗娶妻。居山村而列钟鼎,入仕途又兼修行,僧俗界限已经没有了。他们下有农奴服侍,上有朝廷优待。醉心利禄,纵情声色,周旋卿相,出入权门,穿着蒙古官服,说着蒙古话,仆仆风尘,驰驱大都与萨迦之间。在上都擅殴职官,在外省则骚扰驿户。由于元朝皇室对萨迦的尊崇,帝师的法旨和皇帝的诏敕并行西土,皇上皇妃受戒向帝师弟子膜拜。帝师弟子佩金玉印章,仗势跋扈,气焰万丈。他们在北京与王妃争道,殴打王妃,皇帝不问。《元史·释老传》中记载:“为其徒弟者,怙势瓷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壁。壁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椊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房,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坠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时仁宗居东宫,闻之,亟奏寝其今。”[18]犯罪的官吏,一经帝师说情,便可赦免。曾经被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番僧杨琏真加,“怙思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帅徒顿役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肢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赀,弃骨草莽间。”[19]所有这一切均说明萨迦派上层仗着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仗势跋扈,政治腐败的情形,正因如此,使萨迦派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与八思巴在世时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1324年(藏历第五饶迥木鼠年),萨迦分为四个喇章,使萨迦上层集团内部走向了分裂的道路。他们在政治上日益腐败,对百姓索取过重,各级官员往往不遵循元朝法令,“严弛随意”,甚至任意胡为,因此日益引起广大僧俗群众不满,其它教派和贵族集团处此情况下,自然不甘心再受其束缚,起而反抗,乌斯藏地方一时纷争不已,十三万户各自为政,扩张自己的势力,或争权夺利,或挟私复仇,萨迦统治者已无力重显昔日的威风。
萨迦政权作为元朝中央政府扶植起来的地方政权,其荣辱兴衰随元朝中央政权的强盛抑或衰微沉浮摇摆。元中央强则萨迦政权的统治稳固,一旦元朝对它的支持力减弱,萨迦政权则趋于瓦解。随着元末的统治危机,萨迦政权随之衰败,加之萨迦政权内部的分裂和政治上的腐化堕落,终于导致了被新兴势力帕竹政权所取而代之。
三、结语
元朝统一全国后,为全面管理西藏事务,采取了诸多施政措施,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就西藏宗教事务管理而言,元中央推行了帝师制度,在中央设置了权力机构宣政院,在地方设置了行政组织万户,而这些施政皆为元朝的创举,对管理西藏宗教事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帝师是元朝中央政府的常设职位,其职责是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宣政院是元朝中央政府的常设机构,其院使通过帝师的荐举由皇帝任命,具体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整个藏族地区的行政、军事、宗教等诸事务;万户是元朝在西藏地方设立的中层行政机构,十三万户以当时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占地范围和属民分布为依据划分,以政教结合形式对当地属民和寺院集团进行了有效管理。
元朝通过推行帝师制度,设立中央机构宣政院和地方行政组织万户,优崇西藏佛教领袖,稳固建立对西藏地方的统辖,由此形成了中央王朝通过西藏重要宗教人士加强管理西藏地方的格局,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由于元朝极力扶植萨迦派,对萨迦派上层僧侣集团的过度尊崇和纵容,加速导致了萨迦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使萨迦政权的统治随着元朝中央的式微而瓦解。
[1]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60.
[2]蔡巴·贡噶多吉.红史[M].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40.
[3]《元史》卷4《世祖本纪》[M].
[4]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147.
[5][15][17]《元史》卷202《释老传》[M].
[6](意)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M].张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9.
[7]《元史》卷205《列传》12[M].
[8]《元史》卷87《百官志·三》[M].
[9]赵玉田.中国治边机构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177.
[10]《元史》卷87《百官志·三》[M].
[11][12]仁庆扎西.元代管理吐蕃的中央机构宣政院[G]//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10-113,110.
[13]王启龙.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G]//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北京: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6:349,352-360.
[16]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M].陈庆英,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40-41.
[18]《元史》卷202《列传》89[M].
[19]陶宗仪.辍耕录(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80.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Tibe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siden Tashi①Tunla②
(①China Tibetan Studies Institute,Tibet University②Tibet Institute of Socialism,Lhasa,Tibet 850000)
After China was reunified in the Yuan dynasty,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for the overall administration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ffairs in Tibet so as to maintain it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Tibe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and discusses that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 by mea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perial Master System,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institution named Xuanzheng Yuan and a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Ten Thousand Famil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governance of Tibe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Yuan dynasty;Tibet;religious affairs;experience
D922.15
A
1005-5738(2014)04-061-06
[责任编辑:蔡秀清]
2014-06-04
2014年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项目“从历史视角探析依法加强与创新寺庙管理”阶段性成果,项目号:sk2011xtcx-01qy03
次旦扎西,男,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