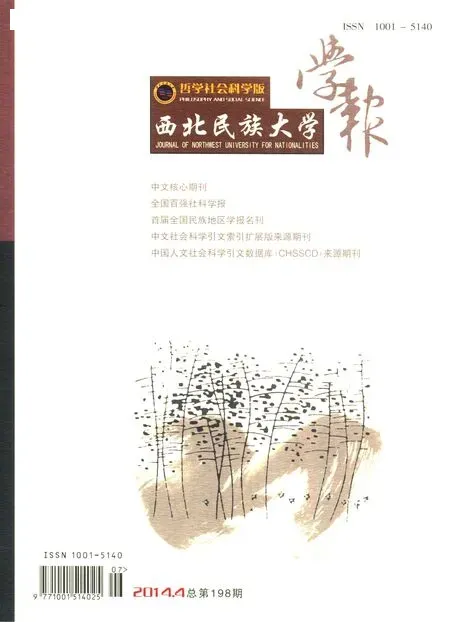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的伦理问题
范俊军,马海布吉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632)
一、语言田野伦理的概念
田野调查是针对特定地域、社区、群体或个人,通过实时观察、咨询、访问、交流、参与、驻地生活等途径,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的活动。从科学研究角度看,田野调查调查是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践检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台湾人类学者谢世忠指出,人类学家对四组不同的人即研究对象、田野调查地的学术合作人、自己所属的学术群体以及所在大学的人文学科,有着相互冲突的义务[1],由此产生了三种具体伦理问题,即妥协、利用和互惠[2]。英国学者奥斯丁认为,田野伦理应用的重要方面就是确认利益相关者,如调研的社区和群众、项目合作参与人、资助人和有关机构,在田野工作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立场[3]。美国人类学者肖斯塔克则指出,田野伦理在应用上表现为超越金钱的施受,强调双方平等合作,强调受访人的知情同意,重点关注双方在情感乃至社会贡献方面的双赢[4]。由此可见,田野调查涉及合作关系、道德义务、权益和责任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构成了田野工作的伦理内容。
语言田野调查记录有没有伦理问题?可能有人认为,语言田野调查主要是了解语言使用状况,记录和收集一些字、词、句发音和故事叙述材料,用于语言学研究,工作单纯,材料也无关大事,不存在什么伦理问题。
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当代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不但要记录语言,而且要了解语言族群和社区的生活、历史和文化;不但要记录字词句的读音,而且要记录生活言谈话语和言语实践;不但有文字记录,而且有录音和录像。语言田野工作者不只是跟某几个发音人打交道,还要直接参加语言社区的言语生活和其他活动。可见,当代语言田野工作已经不再“单纯”。在语言社区访问、咨询、交谈、驻扎、记音、录音、摄像、测试、实验等等,可能触及个人隐私、族群敏感、公共禁忌、身心健康,涉及人际关系、合作关系和利益关系。调查记录材料的加工、处理、使用、发布和传播,还可能对相关个人和群体带来显性或潜在的影响。在新媒体时代,音频、视频、网络数据库比纸质文献更容易传播和接受,造成影响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什么是语言田野伦理?简言之,语言田野伦理就是语言田野工作者在田野调查记录中以及调研成果加工、存储、发布和传播等过程中的行为理性、权益关系、道德义务和服务责任。任何语言田野调研活动,都必须考虑调研项目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考虑语料采集录制行为和结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如,尊重语言族群对记录活动的知情权和许可权,保护合作人和当事人免受身心侵害,保守调研对象个人和集体的隐私和秘密,正确处理知识产权和其他相关权益等等。
二、少数民族语言田野工作中的伦理缺失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语言田野调查,但语言田野调查领域还没有普遍形成伦理意识,伦理缺失现象时有所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触犯族群文化敏感和社区行为禁忌
研究者对语言族群社区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和学习诚意,田野调查期间的某些日常习惯行为,触犯语言族群社区的公共行为禁忌。例如,有的女同志着装颜色艳丽或袒露,男同志光天化日在村边井头赤膊洗澡,或者将内衣内裤晾晒在街旁巷边等等,都是有伤风俗的行为。村寨里出生婴儿,祝贺时说长得胖、很重、漂亮之类的赞美词,对有些族群来说是不吉利之词,将新生婴儿抱出门外观看,更是犯大忌。
已故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当年在彝族地区调查时,有个随行的年轻人为取暖而双腿跨过锅庄,林先生当即对其严加训斥。彝族人认为锅庄附有神灵,双腿跨过是对神灵不敬。林先生尊重彝族习俗,深得彝族同胞的尊重[5]。语言田野工作者不应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带到语言社区,不能一律把民间行为和乡土习惯看成是落后的或封建迷信的东西而不加尊重,否则有可能给语言族群和个人造成尴尬或伤害,产生矛盾冲突。
2.对语言社区资源缺乏珍惜意识
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常常要驻扎到偏远的村寨。这些地方往往条件差、资源匮乏,如缺水、缺电、缺少食品和药品,无卫生设施,甚至冬季取暖都困难。调研人员看来很常见、不值钱和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在这些地方显得弥足珍贵。有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经意间随意使用、损坏、丢弃这些东西,给村民或集体造成损失。生活在高山上的少数民族,旱季时节往往要花三四个小时才能背回一桶水,不说洗脸洗脚,煮饭做菜都要节省,有人只顾自己个人卫生,却不注意节约用水。这些“细小”的行为习惯,不仅会给语言族群造成坏印象,而且也给语言族群造成损失和伤害。
民族学者詹承绪等人当年在凉山进行田野调查时因为缺水,不洗脸,不刷牙,牙龈发炎溃烂,一直坚持到最后,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3.忽视发音人和说话人的知识产权
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的成果核心是语料。有人缺乏知识产权意识,认为自己给发音人和相关参与人支付了报酬,就等于买了语言材料,当然属于个人资源,因而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我们注意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的少数民族语言调研成果作品有上百种,政府也资助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调研的西部计划项目。据我们所知,不少参加过本民族语言调研项目的少数民族发音合作人,只知道有几拨人找过他们做了几天录音和调查,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调研项目,不知道记录材料编成了什么书,录音录像材料制成了什么产品,也不知道调查成果的去向,更不知道调研人员对材料内容作了什么处理,看不到任何回赠的调查录音材料。有的调研者把发音合作人和参与人看成雇工,把调查材料当作自己的创作,采录的语言材料只供自己独享,或按自己意愿指定享有者,漠视发音人和相关当事人的知情权、署名权和支配权。这种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领域并非个别现象。
与文学创作作品不同,语言田野记录的成果作品属于合作作品,著作权由记录人员和发音人、说话人共同享有。语言田野记录者和研究者对语言分析、描述享有创作权,而发音人和说话人对真实语料文本和声像享有著作权和支配权。
4.泄露和传播语言族群个人信息和内部情况
我们发现,不少公开出版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报告和研究著述,详细列出了发音人和相关参与人和家庭成员信息,甚至事无巨细地把语言族群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生活状况、详细人口、性别年龄、人伦制度和内部情况也照实详加描述。这种做法,不经意间严重侵犯了语言族群的个人隐私,向外散布了语言族群不愿外界所知的敏感事务或秘密情况。在著作中对语言族群的情况详加陈述,在研究者看来是尊重事实的学术研究行为,殊不知它给当事人和族群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对当地环境和资源的叙述,可能给资源窃取者提供信息。对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的分布、家庭人口情况和日常生活状况的描述,可能给外来敌特和犯罪分子提供藏匿和渗透机会,还可能成为军事情报被敌方利用。这样说绝不是小题大做、神经过敏。20世纪早期,法国人类学者孔多米纳斯在越南山地的恩龙卡族(Mnong Gar)做过田野调查,在发表的作品中详细记录了恩龙卡族人的人伦制度、价值观、族群状况和个人家庭情况,结果这些情况在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军利用。美军根据著作的描述找到了该族群居住地,逼迫他们刺探情报并参加军事行动,结果许多村民被敌军抓捕,遭受逼迫、折磨而死,村寨也被毁灭[6]。这是作者万万未曾料想到的。
5.暗访、暗记、偷录、偷拍
有人为了获得“真实”材料,事先不跟相关当事人打招呼、不征得许可,就独自对少数民族村寨的某些家庭或个人暗访,甚至在被访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言谈话语,内容可能涉及本人和他人隐私或秘密。访问少数民族村寨的老人或未成年人,也不征得监护人许可。有的老人看起来有精神,实际有病在身,暗访调查可能给老人造成身体伤害。例如,某地一位年轻教师私自访问独居的少数民族老人,老人亲戚发现后,愤怒地将其赶走。
还有人采用偷录偷拍来获得某些有特殊价值的语言材料,而不顾语言族群的伦理禁忌和文化敏感。例如,偷录和偷拍少数民族的巫师、法师在丧葬、婚庆、生育、驱邪等民族民间道场仪式中的行话、秘密语,甚至转录成文本,作为研究成果发表。这不仅犯了有的少数民族的大忌,而且严重侵犯了隐私权,给个人和族群带来不可预知的伤害。偷录材料中的当事人可能因族群秘密的泄露而招致族群成员的孤立和仇恨,或因隐私泄露导致名声受损,并遭受心理痛苦或承受情绪抑郁。偷拍偷录行为会使语言族群对外来人员产生恐惧和不信任,导致语言族群对所有田野调研和政府的帮扶工作一律抗拒。对族群禁止拍摄的仪式活动偷录和偷拍,还会引起村民的公愤。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早年就有过教训。他在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时因一时头脑发热拍摄火葬场面而被追杀,最后躲在一个寡妇家逃命[7]。
6.酬金支付不合理,扰乱地方薪金惯例
不同省区、高校的学者在学术地位、财力物力方面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不同语言族群的生活水平也存在差距。酬谢在田野工作中付出劳动的人是必要的,但近年来有学者获得了大量资助,显得财大气粗,不顾语言社区普遍薪金水平,为了获取资源,用钱开路,给有关参与人支付很高酬金。个别港澳学者以及与国外有合作项目的内地学者,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时,也背着当地的语言学同行给发音人支付很高报酬。这样一来,造成有的族群村民将此视为挣钱方式,争做发音人,导致邻里关系恶化,或使拿到高酬金的参与人招人嫉妒或被人误解为敲诈而遭到村民的唾弃,同时也扰乱了当地薪金支付惯例,让当地低工资、经费少的语言调查者陷入尴尬,无法开展工作。还有的人在调研过程中承诺给予发音人和参与人酬金,但调查一结束,获得了所要的材料以后,就与语言族群断绝联系,不兑现承诺,或降低、拖欠酬金,对发音人的困难不闻不问。这些行为都是违反语言田野调查伦理的不良行为,伤害了语言族群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权益,也败坏了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的形象。
国外有些学者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英国学者苏珊·伯莱克在肯尼亚少数民族部落做田野调查时,考虑当地村民有人暗中吸海洛因,因而她决定支付给发音人的现金少于一小袋海洛因的价钱,而用其他酬金为发音人购买食品、支付医疗费,对于坚持要拿现金买毒品的人只好放弃研究[8]。这样做既避免了发音人用酬金再购买毒品而造成的进一步身心伤害,也不会使自己落得帮助村里人吸毒的坏名声。我国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村寨也有不少吸毒现象,语言田野工作者应坚守对语言族群的伦理责任。
7.调研手段存在损害发音人和说话人健康的潜在风险
根据教科文组织《世界濒危语言图谱》统计,我国130多种语言中已经濒危的有20多种。对于那些仅有少数老人使用的濒危语言,有的研究者为了“抢录”,忽视了发音人的意愿和身体状况。每天记录发音时间达七八个小时,有的甚至晚上加班,发音工作量过大,造成发音人过度劳累和身体不适。有些老年人无意参加发音,而有的研究者则通过当地干部“做工作”促其参与。
有些少数民族村寨的老人害怕面对录音机和摄像机,录音摄像会给其造成心理压力。本文另一作者马海布吉有一次假期采录自己外婆讲的彝语故事,但老人见到录音机后坐立不安,神经紧张,竟然怎么也说不出来。后来进行“偷录”,但老人声音小,反复提高声音,结果第二天就声音嘶哑。这种做法招致了其母的斥责。笔者希望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者引以为戒。
还有一种现象也不容忽视。近10多年来许多大学的硬件建设资金充足,购买了各种语言研究仪器设备,如电子腭位仪、气流测量仪、喉头仪、X光发音摄像仪、声门高速成像仪、言语活动脉冲仪等等。有人为了自己的研究,擅自对发音人随意使用这类仪器进行实验和测试,而不考虑这类仪器可能对发音人造成的潜在身体损害。
伦敦大学Peter K Austin教授指出,语言田野调查的基本伦理是“不要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不要做参与人后悔做的事情”[9]。不顾老年人意愿和身体承受力的语言记录行为,不考虑参与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反伦理行为。
三、建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的伦理准则
在国外,语言田野调查研究项目都要经过伦理审查和评估。许多国家的语言学会和语言研究机构,都有明确的伦理规则约束会员的田野调研行为。美国语言学会通过了《美国语言学会伦理声明》[10],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制定了《田野调查研究伦理的基本准则》[11],澳大利亚语言学会发布了《语言学研究的伦理声明》[12],欧洲马普研究院也有明确的《伦理指南》[13],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针对语言田野调查研究者制定了相关伦理守则。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目前还没有语言田野调查研究的伦理规范①我国整个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都没有伦理审查制度。。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有人类学者开始呼吁,我国应建立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和评估制度。少数民族语言学界应率先建立基本的田野伦理准则,以规范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者的调研行为,进而推动我国语言学领域建立伦理评估制度。鉴于此,我们参照国外语言研究机构的伦理声明和条例,提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的基本伦理准则:
(1)遵守国家法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地方法规和公共管理规范,遵守当地乡规民约。
(2)尊重语言社区和语言族群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遵守语言族群的文化禁忌和公共言行禁忌。
(3)尊重语言族群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政治倾向,入乡随俗;不展示和宣传自己的习惯、信仰和政治倾向。
(4)对语言族群个人和群众清晰讲解语言田野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族群和语言社区对所有调查和研究本民族语言的行为活动的知情权和支配权,使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研工作不欺民、不扰民。
(5)明确和尊重少数民族发音合作人在语言田野工作中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权益,不造成发音人、参与人以及语言族群所有成员的利益冲突。
(6)不泄露语言族群和社区的个人隐私和族群内部秘密,不传播语言族群的内部事务,包括在发布的作品中不泄露个人和家庭成员信息。
(7)考虑自身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田野工作者的财富和地位差异,不展示自身优势,客随主便。
(8)不擅自使用语言族群个人和公共财物;给予语言田野调查的贡献者以适当感谢和合理酬谢,不拖欠和随意拔高或降低酬金。
(9)未征得语言族群的当事人许可,不得对语言社区的日常言谈和会话事件进行录音或录像;不对语言族群视为禁忌的宗教仪式、特殊民俗事件、民族内部仪式话语活动进行摄录。不以偷录、偷拍或其他不人道和不合法方式在语言社区获取语料,不留存涉嫌侵犯说话人隐私或对说话人构成精神或名誉潜在侵害的录音录像语料,即使说话人没有发现和意识到这种侵害。
(10)语言族群成员参加语言田野调查工作应当是自愿的,不通过行政手段要求语言族群成员充当发音人、说话人或演唱人,尊重个人拒绝合作和中途退出的权利。
(11)语言族群的发音合作人、参与人和其他调研对象免受生理、心理和名誉损害,不延长工作时间,不增大发音说话工作量;不因田野调查工作使其遭受困苦。未征得监护人同意,不将未成年人和老人作为合作人和参与人。
(12)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研者对语言田野调查、研究和实验行为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以及潜在后果,必须有充分的预想和估计;不得对发音人、参与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使用有损身心健康和伤害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语言田野调查的成果和作品,不能对语言调查研究的合作人、参与人造成身体、心理和名誉的不良影响。
(13)对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活动负责,研究成果科学和真实。不得因自己研究需要而编造不真实成果误导他人。未征得明确许可,不公布和扩散他人的研究和发现。尊重发音人、说话人和相关当事人对语言材料访问、使用和传播的支配权。
以上是我们提出的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的基本伦理准则。我们希望少数民族语言学界对此引起重视、达成共识,建立适合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伦理原则。
四、结 语
樊浩在其《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指出:“现代中国社会,断言伦理濒临死亡也许过于武断,或者会影响人们对于生活和未来的信心,但伦理确实已经成为十分稀有的‘文化熊猫’,无论如何,伦理在经济生活中退场了。”[14]当代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伦理缺失,固然有传统、历史和文化根源,但更多的则是现实生活剧变使然。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一方面,追求学术研究的高增长和快产出的功利主义思想,使得我国优秀学术伦理传统有所退却;另一方面,沉重的学科和学术传统包袱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我国当代人文学科的封闭和滞后,国际科学研究普适的学术伦理尚未得到有效认知、引进和融入本土。建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和语言学科研究的伦理体系,在学术研究思想上予以肯定,贯穿于语言田野调查和语言研究的实践之中,这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
[1]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2.
[2]Stevan Harrell.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J].张海洋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3]Peter K Austin.Communities,ethics and rights in language documentation.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Volume 7,p35
[4]张丽梅,胡鸿保.作为民族志的个人叙述——从一位昆人妇女的生活史谈起[J].广西民族研究,2009,(1).
[5]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6.
[6]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2.
[7]朱文旭.彝文古籍及其研究价值[J].兰州学刊.2012,(5).
[8]苏珊.伯莱克,吉莉安.洪特.对肯尼亚海洛因吸食者的田野工作反思[A].龙菲,徐大尉译.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60,174-176.
[9]Peter K Austin communities,ethics and rights in language documentation.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ume7,P35-36.
[10]美国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会伦理声明[EB/OL].http://www.linguisticsociety.org/files/Ethics_Statement.pdf.
[11]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田野调查研究伦理的基本准则[EB/OL].http://www-01.sil.org/sil/research_ethics.htm.
[12]澳大利亚语言学会.语言学研究的伦理声明[EB/OL].http://www.als.asn.au/activities.html.
[13]欧洲马普研究院.伦理指南[EB/OL].http://www.eva.mpg.de/linguistics/resources/ethics-guidelines.html
[14]樊浩.中国伦理道德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