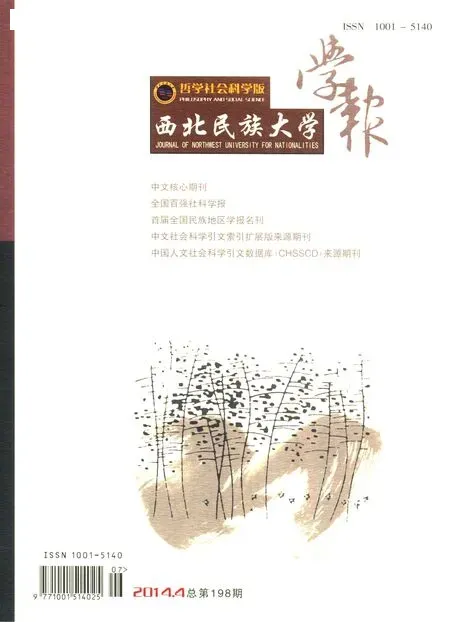明清时期西方人载记中的中国清真寺院
马建春,徐 虹
(暨南大学 中外关系研究所,广东 广州510632)
为探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人颇为重视相关汉文史籍的收集,从正史、地方志到文集、笔记和行纪,他们都有仔细的查阅、考证与分析,且除了史籍外,他们还深入各地的穆斯林社区,探访清真寺和各种碑铭遗迹,同阿訇和穆斯林进行零距离接触,对中国清真寺的建筑与职能有了较为真实、直观的认识。这些记载也为我们探究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西方人笔下的中国清真寺
明清两代中国各地穆斯林聚居区均建有清真寺。在西方人的记载中,中国的清真寺承载了穆斯林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不仅是宗教礼拜、经典学习的场所,还是穆斯林节日庆典聚会、婚丧礼仪举行的主要地方。这些清真寺既有别于中国的佛寺、道观、文庙等庙宇,亦与国外清真寺建筑有较大差异,因此,引起西方人的注意。利玛窦曾讲道:“穆斯林想来中国,几乎随时都可以进来,还在中国建造起清真寺,而且生活极为自由。”[1]
尽管各地清真寺的创建年代或早或晚,规模也有大有小,但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清真寺建筑大体一致,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又具备了伊斯兰建筑的某些特征。卫三畏就谈道:“中国各地的清真寺在格局上都是相似的,在许多方面也与佛教的寺院相似。大拱门和墙上的阿拉伯文题字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特色。”[2]但由于各地穆斯林所处人文环境不同,乃使得各地清真寺既具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
1849年来华的巴拉第,曾访问北京的清真寺。他言道:“汉语中把清真寺叫‘礼拜寺’,指做礼拜的地方。它东西走向,朝向麦加。没有宣礼楼,代之以加高的小亭,叫月亭,用于观赏新月,清真寺顶一般插上镀金球,而不是土耳其月亮。清真寺附近设有专门的地方作宗教学校,节日期间因无其他场所,学校也作洗礼之地,所以到处摆满了装有水的铜壶。清真寺一般也是阿訇和伊玛目的住所。”[3]显然,巴拉第看到的北京的清真寺建筑有着鲜明的中国化特点,寺里没有阿拉伯尖塔式的宣礼楼,代替的是中国传统木结构楼阁式的望月亭。而且,寺顶装饰的并不是最具伊斯兰标志的月亮,而是一个镀金球。此外,中国清真寺里专门建有宿舍以供阿訇和毛拉住宿和办公,这是中国清真寺的一大特点,国外的清真寺一般不设住宅。
巴拉第还详细记载了北京一所清真寺建筑:“阿訇领我走进中式建筑的清真寺。寺内有横隔板,隔板内是木制的半露的长方柱,寺庙中央悬挂着欧洲吊灯,西北部有个讲坛。往西,庙宇深处是半圆形圣堂,用低矮的栏杆隔着……圣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墙上遍布阿拉伯文(古兰经文)。这些文字是用镀金纸刻出后贴上去的。顺便说,这样的题词在清真寺的其他墙上也有……古兰经中的话大量用于装饰穆斯林住所并刻在石头上。我在阿訇的住所见到麦加和麦地那的地图,上面标着中国到阿拉伯的路线和臆想中的神圣国度的纪念碑……在穆斯林住所的墙上,我还看到类似于通告的印刷文字,它用阿拉伯语描写了穆罕默德英俊的外貌,并附有汉语译文。上面说,谁要是根据描述经常想象神义代言人的面容,谁就会避免许多灾难。这显然是模仿了佛教和道教迷信的、欺骗性的招牌。”[4]巴拉第记述大殿的墙上贴着刻有阿拉伯文的镀金纸,这种以美化的古兰经文做装饰的手段,其实是中国清真寺建筑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既利用了中国传统的装饰手法,又突出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巴拉第提到阿訇住所的墙上挂着描述穆罕默德面容的通告文字,这是我们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所没有看到过的。巴拉第认为这是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应是有道理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渗透清真寺建筑细节的同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巴拉第还曾记述自己1858年由北京前往天津的路上所看到的一所清真寺:“4月23日,……到了一个大镇,河西务。这条路上经过一个很美的清真寺,寺顶上不是月亮而是被这里的穆斯林所接受的苹果。”[5]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季理斐,记录了他在山东临清所看到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的外观,从远处看并不是读者想象的那样。读者可能会想到摩利亚山上的奥玛清真寺,或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些建筑物与这些清真寺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这里圆顶被替换为一个铺着绿色瓷砖的四方屋顶,并远远超越下方的墙壁,以此来增加它的斜率,直到到达顶端……这些清真寺被许多不同高度的建筑物环绕,屋顶有着装饰非常漂亮的屋檐,清真寺的大门与中国、实际上与东方的习俗一致,非常的壮丽。主门只会在重大场合打开。”[6]季理斐参观了临清洪家寺的正殿、沐浴房和阿訇的客房。根据季理斐的记述可以看出,临清清真寺布局精巧,舒展大方,是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佳作。
西方人拉尔森记述,一些建设较好的清真寺都有着圆拱顶,上面偶尔还会有漂亮的阿拉伯式花纹。山西大同的一所清真寺被分行排列的拱门分为三或四个部分,“大殿最里面的部分有一个供阿訇下跪的凹座,地面铺着地板还有彩绘。这个清真寺与山西部分地区的相比十分奢华。内部的屋顶是圆的,类似北京的清真寺。”[7]拉尔森描述的这种圆拱顶的清真寺,明显是受到阿拉伯建筑风格的影响。
常驻南京的传教士裴德士注意到,南京的清真寺“表面上他们和其他寺庙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入口外‘清真寺’或‘礼拜寺’的标志,陌生人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进去以后是一连串的院子,接待室和各种小建筑与中国其他的寺庙、衙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在里面能找到很多阿拉伯文的卷轴。清真寺大殿和沐浴室这两个具有伊斯兰教特点的地方最引人注目。清真寺大殿令人印象深刻,通常宽度大于深度。主要入口在东侧,圣龛或后面的假门则朝向麦加。不做礼拜时,大殿内不放任何家具,如要做礼拜,则会放一张大椅子供阿訇跪着宣教,旁边还有燃烧的香瓮。楼梯在房间的一边,地上铺着地毯或长条状的席子,感觉是让穆斯林跪着祈祷之用。殿内的很多吊灯可能是穆斯林祈求还愿的供品。穆斯林面向的西面墙上,特别是在圣龛内,有很多用镀金和彩色刻写的阿拉伯人名。在不止一处地方,我看到圣龛上悬挂着克尔白的图案,克尔白对中国穆斯林来说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8]从裴德士的描述可以看出,南京的清真寺与其他寺庙、民居无甚差别,建筑本身也无多少特异之处。裴德士提到殿内的很多吊灯,其是供穆斯林晚间礼拜照明之用,并非他猜测的是祈求还愿的供品。
西方人通过考察发现,同其他地方的清真寺相比,广州怀圣寺呈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光塔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与西方相似的宣礼塔。此外,它似乎与钖兰的长钟形的、顶端为管状的古佛塔并非没有渊源。光塔的建造者从锡兰古塔如箭一般尖细的阿拉伯顶塔中得到过更多的启发。看到这一点,或将有助于人们确定这座古塔的建造者来自何方。”[9]海恩波在《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中也谈到:“光塔建于公元900年左右,实际上它是原建筑唯一遗存下来的部分。光塔高约160尺,而且完全不像中国国内任何其他的塔……塔内有螺旋形楼梯直达建在顶上的尖塔。”[10]由于建设年代较早,怀圣寺的建筑形式主要是阿拉伯式,在外观造型上呈现出明显的阿拉伯伊斯兰风格。
中国清真寺有不少都与墓地相连,有的是寺中有墓,有的是陵园中建寺。海恩波详细记述了广州著名的清真先贤古寺、古墓。“寺院附有一片约四分之一英亩的小墓地,墓地四周围有坚实的、建筑得很好的围墙,院内有高大的木棉树,一派乡村景象,于净、整齐,优雅宜人。这里葬着一些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墓地尽头坐落着所谓先知的舅父之著名圆顶墓,该墓是摩尔式风格的建筑”,“墓地由砖墙与庭院隔开,其中心是主墓,墓基占地20平方尺,用砖砌成,十分坚固,覆以圆顶。墓地右边有两墓,盖有顶棚,以蔽风雨。庭院和墓地间的隔墙有三扇中国风格的木框门,分中门和两边门。每个门楣上刻着一段阿拉伯文《古兰经》经文及一句中文题词。中门题词为‘高风仰止’;边门框上刻着‘善者之门’和‘诚者之境’……”[11]
法国传教士安邺记载了他在云南漾濞所见的一座清真寺,其装饰以木雕和彩色图案,显示出非常典型的阿拉伯艺术:鹅卵石的马赛克、瓦与方砖以鳞状覆盖。那些带有几何图案的壁画出自一种很粗糙和很原始的艺术,但却与中国中原的艺术完全不同[12]。同是在云南,下关的清真寺建筑在风格上与漾濞完全不同。传教士记载,下关有两座庞大宏伟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都是具有中国艺术特征的漂亮建筑,有雕刻大门,建筑用材为很坚硬的石灰石和雪松木,院子地面用大石块铺成[13]。
传教士特里记述沈阳的一个清真寺,没有宣礼塔,但有一个正方形的屋顶塔,非常的匀称和别致。他称赞这个清真寺“被建设的又好又稳固,有着别具特色的美,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清真寺的大殿宽敞又通风,而且冬暖夏凉。里面没有凳子或座椅,只有阿訇的宣教台和信众聚集的地板。”[14]西方人尼尔记述,在满洲的法库门有一所中式风格的清真寺,寺内有个高高的宝塔,是当时那个城市里最高最漂亮的建筑[15]。而法国学者杜隆记载四川松潘的清真寺“只是一普通厅堂式建筑,在外表上并无明显的特征,有如一座私人住宅。”[16]
虽然“中国的清真寺通常符合本地的建筑风格,很少有例外,除了名字,我们很难把清真寺建筑同普通的民居区分开来”,但是海恩波看到,新疆地区的清真寺,其建筑形式却有别于内地,一般来说都有一个尖塔式的建筑。“在哈密,几乎每一个房子的前面或侧面都有尖塔的缩影,而清真寺则有一个大大的尖塔。”[17]
总的来说,西方人对中国清真寺建筑的记录较为丰富。既有临清洪家寺那样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的,也有松潘清真寺那种样式普通如民居的;既有北京清真寺那样采取中国传统庭院式布局的,也有广州怀圣寺那种颇具阿拉伯建筑特点的。对中国清真寺的礼拜大殿、宣教台、邦克楼或望月楼、沐浴室、阿訇的住所等主要建筑设置,西方人都有记述。对清真寺里的壁画、吊灯等装饰细节,西方人也有注意。但由于西方人的著述基本限于自己对某地或某所清真寺的所见所闻,大多属于游记式的记录,故对中国清真寺建筑未能予以全面认识。
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晚清到中国的西方人,他们都惊奇地发现中国各地的清真寺里均摆放有一个“皇帝牌”,这令他们十分不理解。卫三畏谈到,“在清真寺里,他们立着一个牌位,上面写着赞颂皇上的常用话语,穆罕默德的名字则写在后面。清真寺里没有偶像或其他的牌位,但是挂着标示其教义的卷轴”[18];巴拉第亦云:“清真寺的门廊东面拜着供桌,有一个小板上刻着祝当今皇帝万寿无疆的常见题词,小板前则是插有熄灭的香烛的炭火盆”[19];传教士裴德士注意到南京的每个清真寺也都有“万岁牌”,“牌子摆在靠近入门的一张桌子上,看上去不是很尊贵的位置”[20]。
西方人之所以如此关注此牌,是因为他们知道伊斯兰教严禁偶像崇拜。而在清真寺里摆放皇帝的牌位有违伊斯兰教义,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穆斯林在中国为生存和发展,需不断调整自身来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乃不得不在一些方面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调适”,以符合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需要。在清真寺里供放皇帝的牌位,实为伊斯兰教在传统专制社会中中国化的表现。正如阿訇向西方传教士坚决声明的那样:“他从来没有、也绝不能礼拜这个牌位。他指出牌位所处的低下位置,以此来证明他说的话。他补充说,之所以容许把它放在这里,仅仅是为了方便。因为,如果反对他们的信仰的人控告他们不忠于皇上,他们就可以依此抗辩。”[21]
有的西方人在访问过清真寺之后表示,相对于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堂,中国清真寺建地更好,不仅更符合中国风格,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色。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应该效仿中国穆斯林的做法[22]。
二、西方人载记中的中国清真寺职能
海恩波对清真寺邦克楼作用的记述颇为到位,即为宣礼员登楼高念“邦克”,以召唤教众按时礼拜的处所。“大多数人也称邦克楼为‘望月楼’,有些地方也称之为‘叫拜楼’。还有些汉人因为无法理解穆斯林在塔上念邦克的意义,误解了穆斯林的行为,因此将这种建筑命名为‘喊天楼’”[23]。季理斐在山东临清时曾应邀去参加当地穆斯林的礼拜,他谈到,礼拜者在仪式开始之前,都会在浴室里洗浴干净,并戴上他们的礼拜帽。“阿訇首先进入,我可以听见他念颂辞而升高的嗓音。然后礼拜者们依次进入,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我被引至礼拜者的后面。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跪坐成三行礼拜,所有人都穿着应季的白色衣服。阿訇和他的十二个辅助者念赞圣词时面朝着东方,其余的十八或二十个人面朝着西方。所有礼拜者则是面朝着麦加。”[24]季理斐观看完礼拜后感叹道:“圆帽,头巾,没有辫子,外国话,都处处显示这是中国之外的一块领地,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想到这是在中国,礼拜者普遍使用的扇子。”[25]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也曾参观过北京清真寺的礼拜:“在每个清真寺都有一个沐浴室,那里有热水提供,还有淋浴房。在星期五,信徒们首先在沐浴室将自己洗净,然后进入清真寺,仪式在下午2点举行。地板是木头铺成,并保持得非常干净,所有的地方都能用来下跪。进入时,鞋子脱在门口。阿訇登上西北部的宣教台,用阿拉伯语念颂辞,并用中文对人们的道德和宗教义务发表演说。”[26]
“清真寺一般也是阿訇和伊玛目的住所。伊玛目称号的获得者是本堂的教民,聚礼时站在最前面,他负责协助警察维持清真寺的秩序。有些阿訇即毛拉从有些学问的穆斯林中选举和授封,但常常是由社团从远方请来的。”[27]故清真寺内为其建有宿舍供他们居住和办公,以便于主持清真寺里的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而通过拜访与交流,西方人发现,中国阿訇的宗教教育程度很高,他们不但有汉文图书,而且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图书,“遍布于中国的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个人藏书中保存有许多从13世纪即元朝起带入中国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真本。”[28]不少西方人对中国阿訇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表示惊讶,如卫三畏记述一位阿訇:“他能轻松地朗读阿拉伯经文,也能熟练地运用这种语言交谈,却不能读、写汉语。这多少有点令人吃惊,因为他出生在中国,汉语说得很好,而且在中国人中间作宗教导师。”[29]
清真寺也是穆斯林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主要场所。巴拉第记载:“我首次拜访一所清真寺时,被领进一个不大而整洁的房间,炕上一个年青的阿訇盘腿坐在虎皮上,他相貌俊秀,缠着不大的白色包头,身边有个小男孩跟他学阿拉伯文……阿訇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清真寺里同时教授这两种语言,但他们的发音走样了。穆斯林因长期生活在中国已不习惯发阿拉伯的ρ音和喉音,代之以л音和х音。”[30]
西方人看到,除了教授基本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和读写算知识,有些清真寺还设有讲经堂,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向他们教授伊斯兰教经典,培养宗教继承人。“遍及中国的清真寺大多数都和学校相联系。这些学校根据所在位置和穆斯林社区而有所差别。在那些穆斯林较少的省份,这些学校单纯是教会学校,仅限于培养宗教神职人员。在像甘肃这样穆斯林较多的省份,那些附属于小镇清真寺的学校,则会教授孩子一些信仰的教条和一知半解的阿拉伯语,间或有少量的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然而,对于准备担任教职的人来说,这些知识太过浅显。即使是在伊斯兰教最兴盛的地区,也只有一定比例的人能够认识和阅览阿拉伯文,不超过一至两成的人能够理解他们所读的内容。有些传教士证实,一些大学校中立志成为阿訇的年轻毛拉,也很少有人能阅读和理解阿拉伯语的《新约圣经》”[31]。
季理斐注意到,清真寺里的阿訇还负责为本地穆斯林宰杀清真牲畜,他们宰杀每一个家禽,信众们会给他们一笔钱[32]。在古尔邦节,教民把羊拿到清真寺去请阿訇下刀,在清真寺将宰杀的牛羊洗剥干净,削成小块后,再分给全体教胞。
明清时期,中国清真寺之所以会成为大量来华西方人的关注对象,其原因自然与清真寺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性相关联。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社会职能,中国清真寺都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自然而然吸引外来西方人的目光,并使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汉文史籍不载的珍贵记录。
[1][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18][21][29]周宁.第二人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3][4][5][19][27][28][30]曹天生,张琨.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C].北京:中华书局,2004.
[6][7][14][15][17][22][23][24][25][31][32]Marshall Broomhall.Islam in China:a Neglected Problem[M].London:Darf Publishers Limited,1910.
[8][20]William Bacon Pettus.Observations and Conversations among the Moslems[J].The Chinese Recorder,Vol.39,1908.
[9][10][11]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12][13]耿昇.法国政界与商界对云南茶马古道南北两道的考察[A].马明达,纪宗安.暨南史学(第八辑)[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6]房建昌.国外研究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概况[J].固原师专学报,1988,(4).
[26]Rev.J.Edkins.Note on Mohamm edanism in Peking[J].The Chinese Recorder,Vol.1,1869: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