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烫的档案
◇ 李新立
滚烫的档案
◇ 李新立
铁
一堆形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档案里,我最先翻出了铁。
秉性冰冷,硬度实足的铁,因它的形成过程特殊,骨子里仍然有着烈火般燃烧的激情。这种激情是物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
那些请示、汇报、批复,使用了许多繁体字,用蜡纸刻成印制,字迹工整,功力不凡,看得出身着中山装的他,履行职务时庄重严肃的程度。除了文头纸,内页用纸轻而薄,三十多年过去了,油墨仍然泛着深蓝色的光芒,纸张上指头触摸过的痕迹清晰可见,加上龙飞凤舞般的签阅,觉得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温热。
这是物质极度匮乏,生产技术极其落后而又大办工业的年代。地方工交局印有最高指示的文件,报送到了革命委员会,称计划利用地方资源建设国有铁厂。这个计划在同样印有最高指示的文件上很快得到批复,接下来,成立指挥部,组建人员,筹备建厂事宜。工程并不浩大,但工作十分繁复,选址、平地、通水、通路,反复上报文件,申请百元、千元建设资金和建设用钢材、木料、燃煤。从春暖花开时节起,一直拖磨到九月,筹建指挥部上报工交局,在小城东北边的烽台山下的几十亩空地上,“战斗一号”炼铁炉建成。建设者们很少显摆自己的劳动艰辛,那几张情况汇报,除了必要的语录和时代口号,建设过程的描述字数不多,但不难看出,场地是他们一锨一锨铲平并一夯一夯砸实的,设备是他们反复琢磨后加工出的非标件,土建设施是他们一砖一瓦砌就的。
两辆老式汽车从运输队调派到了铁厂,承运矿山开采的铁矿石。两处矿点均位于北部,距县城四十多公里,全部用人工掘进,小炮爆破,每颗石头,由人工用背篓背出巷道。每天能开采四五吨原石,业绩已经相当可观。这些石头,要经过破碎、粉碎、研磨,才能进入熔炉。一张圆珠笔绘制的表格告诉我,这些石头解决不了生产所需,于是,废铁收购工作全面展开,那些废弃不用的铧尖、破锅、镢头等物件,开始涌入生产场地。我记得清楚,曾经有收购废铁的人,推着架子车进入村庄,我没有关心过他的长相,对杆秤一窍不通,却死死盯着秤星,看我家的破铁锨、烂脸盆能卖几分钱。
一九七○年的国庆一定繁华热闹。“战斗”一号炼铁炉流出的第一炉铁水,经过冷却后,被小心地运送到宽阔场地。这块沉重的物件,上面布着一些坑窝,甚至有些不规则,但她的名字叫产品。生产总指挥部派人对这块铁进行处理,类似于现在的包装。细砂纸在她身上慢慢抛光后,打眼看上去,不再像当初一样丑陋,扭捏的姿态,像朴素的姑娘,天然得笨拙,笨拙得可爱。十月一日早晨,一辆汽车的车箱前一天就做好了支架,现在,大家在支架上铺好了红布,几个男工,将铁块抬到了支架上,虽然吃力,却很兴奋。然后,量身定制的大红花扎在了她的顶部,有红色衬托,她的脸膛泛着黝黑色的光芒,端庄而又不失喜庆。她是节日的献礼。上午十时,敲锣打鼓、扯着彩旗的队伍在前面走着,载着她的汽车跟在后面,此时的城区,也是一片欢呼声,锣鼓声。我揣测,广播站的大喇叭,反复播送着同一个消息:在战无不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工人阶级为伟大的祖国献上了一份节日厚礼。
衰减是繁华过后的必然。不久,印有最高指示的请示转到上级,因资源短缺,需要转产。多年以后,我走过位于华家岭之下的高峡,看到了昔日的矿山,低矮狭小的洞口塌陷、封堵,曾经的畅通的小道荒草覆盖。据说,这里的铁矿石储量十分有限,并且以蜂窝状分成布,根本不宜开采。那些铁质产品,也因杂质太多,达不到使用标准。
时光远我而去,有限的文字不能让我看到蹉跎岁月留下的更多秘密。但是,翻阅这些于我十分陌生的文字记载时,内心仍会感到一个时代的滚烫。
爱情或者偷情
十分惊异,这类文字怎么会装入档案,并且还会归在永久类中呢?看完之后,平静了下来,毕竟,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者,对时代背景有些了解。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少数者的需要。
铁厂于一九七二年转产水泥后,用工量明显增加,女工也在用工范围,主要从事备料工种。她们从农村来,在战天斗地的年代,她们衣着朴素,大多身体强壮,不怕脏不怕累,长辫子朝后一甩,潇洒帅气,一点儿不亚于男人。厂区的地势由北向南渐渐沉了下去,在西北角,约有五六亩地空地,平坦瓷实,这里是女工们的主要劳动场所。拖拉机运进来的粘土,堆在这里,她们用铁锨摊开,然后用枹子仔细打碎,将晒干的粘土过筛后,再把筛子下面的细土转运到大棚里去。她们的手上长了茧子,擦子一样粗糙,一些人手上还裂开了口子。名字叫秀秀的她,这年二十刚过,脸上尽管留下了风吹日晒的印痕,但这不影响她眉眼的好看。那天,她显得有气无力,拄着锨休息时,备料组杨组长走了过来,没有骂,只是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的脸上泛起了羞涩,杨组长是过来人,明白她来例假了,就让她回宿舍休息。她多么感激他!
杨组长是新来的干部,年过三十,眉清目秀,戴着副眼镜,书生气十足。他是招人喜欢的,倘若不是他已经结婚生子,肯定有不少女工向他示爱。三五天里,杨组长经常安排秀秀休息一两个小时,还去她的宿舍,给她送来十分紧缺的红糖。在宿舍里,他们没有发生什么,只是一种友好和关心。有天,她却去了他的宿舍,他的宿舍里充盈着五月槐花的香味,显然,他经常用香皂洗脸。她进去时,他正趴在桌子上在写字,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她不由自主地伏在了他的背上。很快,他们不正常的举动引起女工们的警觉,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用匿名信的方式举报了他们。

书法 管布坤
问询类似于审讯。一间小房子里,一名支部委员站在政治的高度,批评了一顿杨组长,可谓语重心长。杨组长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觉得自己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影响了正常工作。支部委员不这一切样认为,批评他对事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说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从问询记录里我完全能够感觉得到现场的紧张气氛,支部委员的目光紧紧盯着杨组长,杨组长低着头,不时扶着滑下来的眼镜,躲避着领导的眼光,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曾经担任过公社政工干部的女人,正在对秀秀进行问询是。从记录里看出,女政工不时对从在她对面的面色通红的秀秀进行讽刺挖苦,尽管她表面正直,却掩饰不了内心的淫邪。女政工问:几次?在啥地方?谁先主动的?啥动机?秀秀泪流满面,将头深深埋了下去,但她不得不回答这些探究隐私的提问。她说,她喜欢他,感激他。
他们的检讨书反复写了三四次,一次比一次详尽,一次比一次深刻。这长达数十页的文字,读来更像纪实散文,更像一篇言情小说。洒在纸张上面的泪痕,更能证明他们的痛苦和无奈。结局是肯定的,为保护干部,杨组长停职察看,而拉拢腐蚀干部的秀秀被辞退回家。
事情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我看到了另一份杨组长写下检讨书,时间在他们被处分后的半年之后,我揣测,是厂里发现他的行踪后,责令他写下的。这份检讨,其实是一篇民情笔记。秀秀辞退回家后,杨组长看望过两三次,有次因天阴下雨,还住在了她家。秀秀家在北部某公社,偏远闭塞。她家的院落破败不堪,多处土墙塌坍,三间瓦房风雨飘摇,生活十分艰辛。他去了她家后,她和她的母亲都显得十分热情,秀秀更是高兴愉快,为他烙了油饼吃。他每次去,都给她留下了几元钱和几斤粮票,最多的一次留下了七元钱。最后一次去时,她一再叮咛今后别来看她,好好工作。她已经找到了婆家,会好好儿过日子的。他在检讨中说,他的行径荒唐的不可饶恕,他为自己再次犯了资产阶级意识而后悔,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
二○○七年,我编工厂发展简史时,将旧档案重新翻阅了一遍。特别留意了一下职工花名册,在一九七四年后的名册中,再没有找到杨组长的名字。曾经询问过老同事,说他这个人曾经出过事,被调走了。可是,我在他姓名中断的时间段里,也没有找到他调离的文件。这些都不重要了,眼下,我想,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应该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事件
一九七三年,如果没有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铁厂就处于半停产状态。从一些资料上看,半停产的原因还有一条,那就是资源的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了生产指标,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原料供应,也无法完成任务。
矿山开采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位于距厂区四十多公里的高峡,是当时的主矿区。国道的柏油路沿城北穿过,过了狗娃河,迎面便是一座大山。山上的路,仍然是柏油铺成,但狭窄盘旋,坡度较大,一辆老式汽车翻越它,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下山,半个多小时后,更高更大的华家岭挡在眼前。运输石头的汽车不必上山,朝左一拐,驶入一条满是砂石、坑坑洼洼的道路,摇摇晃晃的,就进入了高峡。东边峡壁上,人工挖掘出了两条高不过两米的洞口。每次实施小爆破作业时,长长的导火索延伸到洞外,地面轻轻晃动一下,气流夹裹着尘土涌出洞口。这意味着爆破成功。但人不能进去,待二十多小时后,才能有人进去探察情况。确认安全后,开采者们把炸下来的石头,用竹子编的背篓背出来。我实在不敢想像采掘的进度和安全系数有多高,只是佩服劳动者们的过人胆量和勇气。
翻看这些工作总结和数据汇总时,紧揪着的心,终于舒展了开来。或许是上天的怜悯,短短的三四年间,竟然没有出现塌方掉顶的事故。我为他们庆幸。
但不等于平安无事。高峡矿建设得相当简陋,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地理条件,也不可能修建得像个企业。峡谷靠西稍微平坦的地方,修了七八间土木结构的瓦房,每间可供两人容身,大约非本地村民晚上不能回家时,居住在这里。有两间大的房子,没有住人,是矿山的仓库,存放生产性工具和材料。峡区的二月,草木枯萎,峡水封冻,石头散发着寒气,如果一场雪落下,道路结冰,一些裸露的石头泛着青光,别说车辆,就是行人也寸步难行。加上矿山距村庄太远,眼下已经十分荒凉了。这个时节,矿山应该放假了,只留下了两三位值班人员。他们是附近的村民,白天可以在家呆着,晚上必须返回矿山值班。二十日的晚上他们觉得平安无事,熄灭煤油灯后,昏然睡去,早晨起来巡察矿区时,大吃一惊,甚至吓得要死:库房门口发现纸火灰迹,当时,库房里存放着土制炸药2498公斤,制作炸药的原料麦麸1500公斤。
值班者不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个人看守现场,一个人滚爬着朝公社的邮电所跑去。情况很快通过手摇电话,传送到厂里。此后,厂里的民兵紧急集合起来,去保护和控制现场。接着,情况被迅速反映到工交局、公安局和革委会。事态和后果并不大,但政治斗争的弦似乎一直没有松弛,是谁干的?动机是什么?最初的判断是,不甘死心的敌人在搞破坏。调查多头展开,值班人员当然被多次询问,然后是附近村庄的反右富。那些盖着红色指印的笔录,不知是否还在某个上级部门的卷宗里,我不得而知,但整个事件的复杂性,足以让人咂舌。
事件的真相很快明了。我没有找到后续事件的处理结果,但从性质上看,值班人员肯定被辞退,想必他们卷着铺盖回家时,没有什么怨言,心里长舒了口气。从资料里能够看到,矿山负责人和铁厂领导自上而下都写了检讨,高度认识姑且不说,只是,假若炸药爆炸,将是什么后果。领导们书写检讨时,或许心脏加速,精神萎靡,许多设想的后怕,包括责任承担,都让他们浑身流汗。
还好,事情最后确认是流浪汉夜间烤火时所为。
好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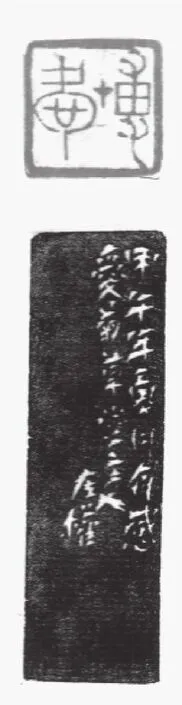
治印 左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