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那些久远却新鲜依旧的歌声
王可田
杨争光:那些久远却新鲜依旧的歌声
王可田

作为小说家和编剧的杨争光,凭借《老旦是一棵树》《黑风景》《棺材铺》《从两个蛋开始》等小说和《双旗镇刀客》《水浒传》等剧本,蜚声国内文坛。声名鹊起的背后,他的诗人身份却不容忽视。他曾是陕西诗坛一位重要诗人,富有时代气息和乡土情味的长诗《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今,回望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时,他却不无调侃地说:“我只是一个做过诗人梦的家伙。”
对于杨争光来说,诗神并没有走远,熠熠闪亮的诗性作为一种首选品质,已经进入他的写作和生命内部。
“启蒙”年代的青春生命
王可田:1970年代末,也就是在大学时代,你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了。那时,中国社会刚刚“解冻”,振奋,迷茫,焦虑,阵痛,成为一种社会的情绪和思潮。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作为一个亲历者,你能描述一下你心目中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和写作环境吗?
杨争光:
先说“启蒙”。百年间,中国有过两次“启蒙”。一次是五四,一次就是你提到的1980年代。两次“启蒙”都夭折了,都是灵光一现式的,很可惜的。五四的那一次是因为“救亡”,1980年代的这一次是因为“经济建设”。理由都很现实,也符合“现实优先”的自然生存律。所谓“启蒙”,要的是民族、国家和人的“现代化”,要的是“自由”和“进步”。比之“救亡图存”和“要温饱”,不但遥远飘渺,也很不实惠。当然要闪开要让路了。但我实在就是不服气。我总是以为,现实的“救亡图存”、“要温饱”和看似遥远的“启蒙”并不必然相悖,在一个极其讲究统筹兼顾的民族和国家里,怎么就一定相悖了呢?不能统筹兼顾了呢?我还以为,放弃“启蒙”,只顾“救亡”的“图存”,“存”下来的我们,其所以是这样的我们,正和放弃“启蒙”是有关的。放弃“启蒙”,只“要温饱”,“温饱”之后的我们,其所以是这样的我们,也和放弃“启蒙”有关。缺了的课是一定要补上的,不在这时候,就是在另一个时候。以什么样的现实理由拒绝补课,造出来的现实都是畸形的。两次“启蒙”,我更看重的五四的那一次。它虽然因“救亡图存”而夭折,却有着潜在的延续性,一直延续到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历史时代的开始。也正是那一次“启蒙”,不仅给我们这个民族造就了一批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精品人物,也使我们这个民族终于有了珍贵的“现代意识”,并成为精神遗产,可以承接的精神遗产。1980年代的“启蒙”,就是对这一精神遗产的一次承接。我相信,这样的承接,以后还会有的。除非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拒绝进入“现代化”。
1980年代,可以看成是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节点。以国家名义发动的,七亿人民参与的“文化革命”,演变成了一场悲剧性的社会动乱和残暴的历史浩劫。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伤害,都需要疗伤,需要改变,需要发展,也就需要反思。“反思”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启蒙”的起始。蜂拥而来的各种“主义”和“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都能得到呼应。仅就文学领域,不到十年的时间,先后就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等等,让人眼花缭乱,又不觉其烦。这就有乱象了。而乱象是会影响秩序的,这就出现了“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记忆中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写作环境。
诗和诗的写作,与其它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在同一个处境里。一会儿鼓满风帆,破浪前行,一会儿在翻卷的浪涛中挣扎哭喊。各种社团,油印的、铅印的民间诗刊很多,互相应和。我们在大学的诗社叫“云帆诗社”,有油印的《云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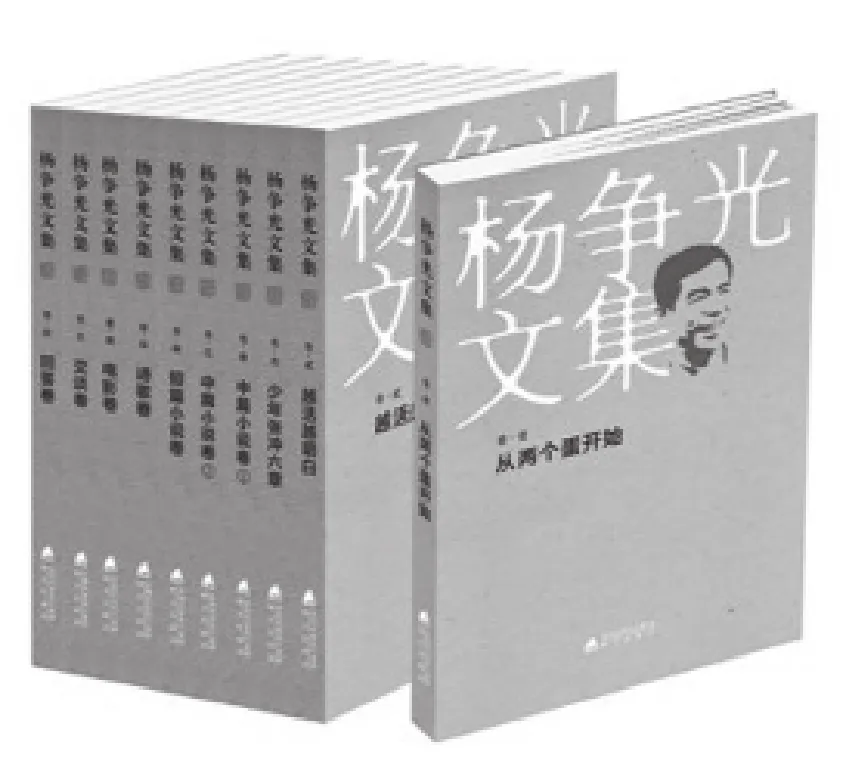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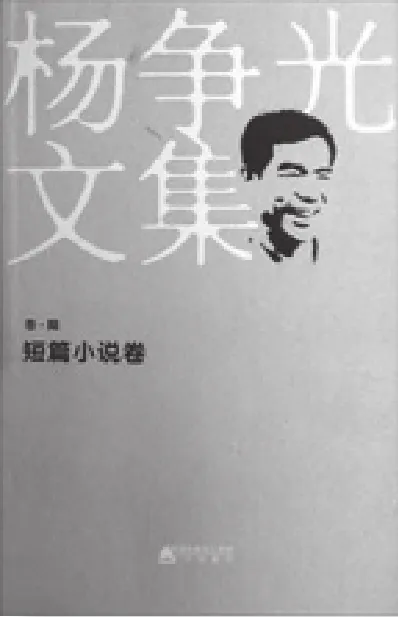
王可田:
在你早期的诗歌中,大海、太阳、星星、海岸、血等意象,很引人注目,象征派、意象派的写作技法已在娴熟地运用。其中交织着对理想的追寻,痛苦的思辨,焦灼和热望,甚至挣扎。这与我阅读“朦胧诗”群体的那些作品有类似的感觉,而你的写作时间和他们基本相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是整整一代人的思考,你通过个人命运的反思参与了整个时代的话语构成?你当时的诗歌思考和意象元素的设置,也请谈谈。杨争光:
被愚弄后的愤怒,愤怒中的反叛、控诉,很容易情绪化。情绪化的反思、反叛、控诉,激情大于理性,意象多于内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写作。不仅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共同参与。是青春的,激情的,狂热的,既合着“启蒙”的脚步,又乱着“启蒙”的节律——“启蒙”的过程有反叛和激情,但“启蒙”要的是庄严的理性。这也是你所说的“大海、太阳、星星、海岸、血”等意象在我的诗中出现的来由。象征派、意象派在诗的领域,也是外来的思潮,我运用得并不娴熟,也不可能娴熟。但这种不成熟,却是我在那个时代青春生命的真实记录。王可田:
写于1981年的《沙滩奏鸣曲》不得不提。这首诗通过对自我的审视与确认,表达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整首诗奔放舒展,开阔浑然,洋溢着乐观豁达的精神,这也是生命意识的自觉与张扬。对于这首诗,你能具体谈谈吗?杨争光:
这首诗是对惠特曼的模仿和致敬。就诗来说,是青涩的,但致敬是由衷的,真诚的。在我的心目中,惠特曼是几百年来人类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是一个“新大陆”的发现者,也是这“新大陆”的毫无保留的歌者。他的“新大陆”不仅是自然地理的,更是精神的、情感的、意志的;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是一个象征,甚至,在我看来,具有某种新的精神原型的意义。
在他那里,自由、平等、博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有的存在。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林木、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的器官,都在呈现着人类最为珍贵,最具美感的存在之境。是当下的,也是将来的。
驳杂、饱满、丰富、奔放、自信、舒展……用不着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脱口而出,随笔流泻——正适合他要呈现的对象。
也是惠特曼,修正了我对赞歌的偏见。赞歌和谀诗的本质区别也许在于:真赞歌,是给有真价值的东西的。它不会放错地方,给错对象。
《沙滩奏鸣曲》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青涩的生命,用青涩的笔,对惠特曼的那个“新大陆”表达的一种向往。
从淳朴诗情到诗性的延续
王可田:
但很快,你就把目光转向故乡乾州,抒写大平原上的人和事。叙事成为诗写方式的主体,语言简约洗炼,更加注重节奏和语感。比如《外祖父》《母亲》《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的朴素动人,《流浪汉小调》的民谣风格,《黄河》《黄土高原》《大西北》《鼓阵》的厚重大气,这一时期的诗就像一张张风味独具的年画,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从最初的注重隐喻,以凝重的意象传达思想和情感,到这一时期的贴近生活和土地,彰显地域风情,这种转变你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杨争光:看样子,你好像真把我当成诗人了。我只是一个做过诗人梦的家伙。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和诗一起行走的。我走到哪儿,我的“诗”就会在哪儿生长。你提到的那些诗,大都和我的生活履历有关。从大学校园,走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到渭河平原,身体和精神都在游走。不同时期的生命,对世界的感应是不同的。兴奋点也会转移。手里的笔就会显出不同的“个性”。还有,表达和呈现的东西也需要不同的笔法。
我不相信刻意出来的“风格”。如果想有自己的“风格”,也应该让它自然成形。我以为,创作者是无须为所谓的“风格”劳心费神的。
王可田:
写于1988年的《交谈:自言自语》就有些不同,明晰节制但更趋理性的语言,举重若轻地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境遇;时隔20年写的《给我的蟑螂兄弟》,经过提炼的口语化的表达,以鲜明的幽默反讽意味,带给人出乎意料的阅读快感。关于这两首诗,你想说的一定很多吧?杨争光:
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交谈:自言自语》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是写一种境遇。那时候,快到世纪末了,都在说“世纪末情绪”。可能也有一种“世纪末的情绪”在里边吧。《给我的蟑螂兄弟》是蟑螂兄弟要我给他写的。他说你不是写过诗吗?给我写一首吧。就写了那一首。我有很多诗是写给朋友的。我感到很庆幸,因为这些诗不是为写诗而写的。
王可田:
从写诗改写小说,你是不是感觉诗歌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因为,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体。可不可以说,你的小说是你诗歌的叙事特质的延续和深化?杨争光:
事实上,还在写诗的时候,我就客串过小说写作。写小说并不是因为感到诗的局限性,是因为想写了,想写的东西,更适合小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的局限性。极端一点说,它的局限性也证明着它的不可替代性。没错,小说比诗更具包容性,但小说并不能代替诗。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都是有诗性的。如果说我的小说有诗的延续性,延续的就是我说的那种“诗性”。我喜欢描述性的诗,这可能对我转写小说带来了某种好处。诗性,还是诗性
王可田:
如今,你的小说创作已是蜚声文坛,改编的影视剧也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些声誉掩盖了你的诗人身份,或许诗人从来就不是一种身份。回望诗歌陪伴你走过的那些岁月,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诗歌对你的小说和剧本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在你的一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杨争光:
诗不但陪伴我走过了我的青春岁月,更让我感到了“诗性”的珍贵。发现诗性,保持诗性,不仅在后来的写作中,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生命中都显示了它的贵重。“诗性”并不抽象,它很具体,只要你有诗心,并能留心,就能和它相遇。缺失“诗性”的生命是没有弹力的。王可田:
你的诗歌写作集中在1980年代,持续了近10年时间。如今,我们回过头来阅读这些作品,依然能感受到你的那份真诚,感受到那有些久远却新鲜依旧的歌声带来的感动。离开诗歌的日子你依然关注诗歌吗?你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发展持怎样的态度?对于诗坛上涌现的种种潮流和现象,作何评论?杨争光
:对我来说,对诗的关注可能是永远的。对诗的阅读,虽然少了,但没有和它完全隔绝。我在即将出版的诗集后记中,对几十年来中国诗的行走路径曾说到过我的看法。摘几句话放在这儿吧:无话可说的诗人堆积来的语言是与诗无关的,无论你摆成多么崇高的姿势,扮成多么神圣的面孔。
“拒绝崇高”是一个误会。中国的诗从来就没有涉及过这一领域,自己也并不拥有这种东西。本就没有,何来拒绝?
就诗而言,中国没有真正的民间写作,也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如果有,诗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怪相了。
汉诗的纯正不纯正,不是洋人破坏的,汉语写作的尊严,也不是洋人扭曲的,更不是汉语译文。汉诗的纯正和汉语写作的尊严,要靠实实在在的作品维护和捍卫。我们有吗?我们的汉诗更需要的是丰富,甚至庞杂,还远谈不到纯正。
写什么和怎么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只有在初级写作教程的意义上,它才是两个问题。
诗不是行为艺术。
世俗的写作与诗无关。
诗,一种无法与叙事艺术争夺世俗眼球的文体,只能无奈而尴尬地退到边缘。诗人们在马桶上沉思,还是在床上跳舞,几乎已无人关注。也许,经济动物在物质文明化和精神世俗化的进程中是不战而胜的。诗不属于经济动物。
生活资源的贫乏和情感失血,大面积的精神萎缩和思想枯竭,是诗颓败的症结。也包括其他艺术。也包括艺术批评。曾经的诗人们大多换了面目,也许新换的才是真面目。
但诗还在。它不仅见于真诗人的笔端,也跳跃在小说、随笔、甚至回忆录等作家作品的字里行间。这足以证明诗心未死。
行了,摘过来的已经太多了,我自己都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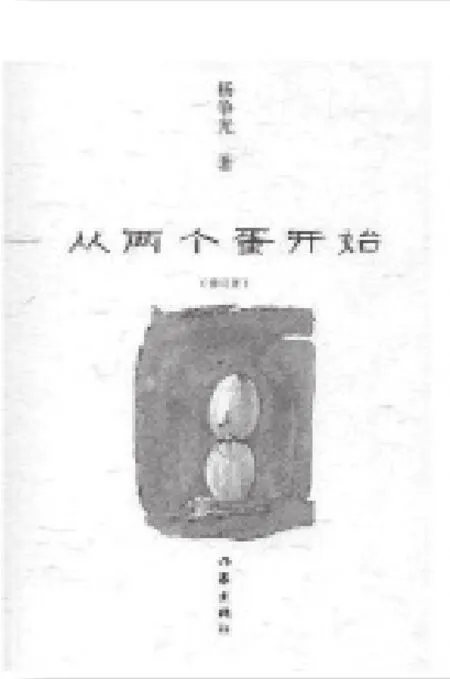

王可田:
你曾说过:“富有诗意的生命才是有美感、有价值的。”离开诗歌,再看诗歌,就会有一种全新的视角,或许就能看得更清,也就更加珍视诗性在个体生命和当下社会中的存在意义。是这样吗?杨争光:
应该是的。诗性,还是诗性。它比诗重要。我们看重诗,看重的也正是这个东西。王可田:
在一篇文章中你也写道:“这个时代可以是世俗的汪洋,可以没有诗,但不可以没有诗心。诗心在,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就不会在物欲和肉欲中腐烂,甚至相反,还要在物与肉的拥堵中冲动。”写诗或不写诗都不重要,关键要有一颗诗心。在结束这个访谈的同时,也愿你诗心常在,更期待有新的诗作问世。杨争光:
谢谢。杨争光早期的诗歌有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和狂热,痛苦与焦灼。在稍后的乡土书写中,同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一种原汁原味的淳朴魅力,已是这个时代丧失殆尽的东西。读杨争光写老家乾州的诗篇,冰封的记忆开启了,童年乃至比童年更久远的时光向我走来,山原、土梁出现了,村庄出现了,劳动的场面出现了,唢呐吹起来了,秦腔吼起来了……
感谢诗歌,它为我们亡逝的岁月构筑了一片家园。一切都在那里,原封未动,只等我们轻轻走近,推开那扇虚掩的门……
责任编辑:阎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