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中沈从文的“梦”和“摘星”“看虹”
何宝民
沈从文的《摘星录》和《看虹录》一直是沈从文研究中的疑案。
几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看到据说收录这两篇作品的《看虹摘星录》,最后连是否真有这本书也众说纷纭。20 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沈从文文集》收录了《摘星录》和《看虹录》,事情似乎有个结果。但读者和研究者又心生疑惑:两文在1944年已受到左翼的批评,被指为有色情倾向,1948 年郭沫若判为“桃红色”文艺的代表作。但就读到的文本(尤其是《摘星录》)而言,却感到与郭的定性距离不小,指斥作者“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也未免言之过甚。
这一扑朔迷离的“摘星”“看虹”之谜,直到2009 年才有了谜底。学者裴春芳检索《大风》杂志,发现了沈从文的3篇作品,从而证明:《沈从文全集》所收的《摘星录》,是沈从文移花接木用另一作品《梦与现实》替代;所收的《看虹录》也非原刊,且有较大的修改。真正的《摘星录》另有其文,但被沈从文长期有意遮蔽,《沈从文全集》及各种作品集均未收入。( 《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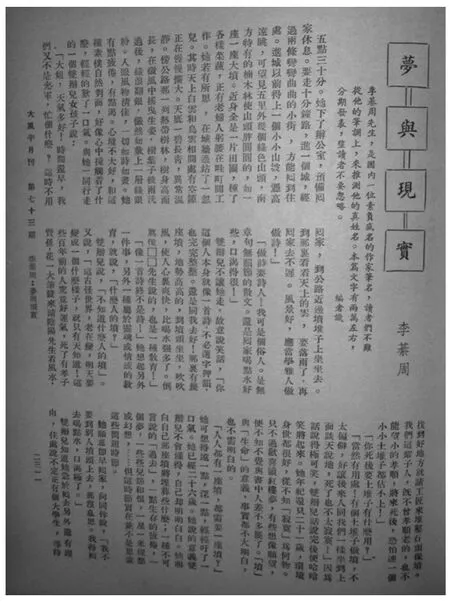
《大风》刊《梦与现实》首页
《大风》是抗战时期在香港出版的一个以文史为主要内容的刊物。1938 年3月5 日创刊,16 开本。初为旬刊,1940年1 月5 日第五十九期后改为半月刊。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事爆发停刊,出版至102 期。办刊初期署“社长林语堂、简又文,编辑陶亢德、陆丹林”,后署“社长简又文,主编陆丹林”。简又文(1896—1978),广东新会人。常用笔名为大华烈士。岭南学堂毕业,留学美国。曾任燕京大学教授。1949 年去香港,任香港大学研究员等职。陆丹林(1896—1972),广东三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入南社。曾任上海中国艺专、重庆国立艺专教授。两人先后创办并编辑《逸经》《大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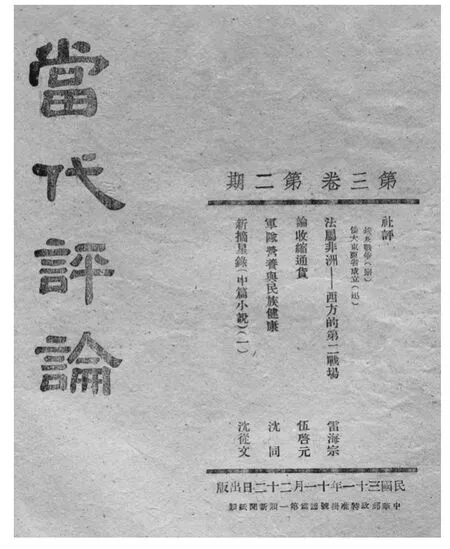
《当代评论》第三卷第二期刊影
沈从文在《大风》发表的作品均署名“李綦周”,这是他极少使用的一个笔名。
第一篇《梦与现实》,文前有编者加的一段按语:
李綦周先生,是国内一位素负盛名的作家笔名,读者们不难从他的笔调上,来推测他的真姓名。本篇文字有两万左右,分期发表。望读者不要忽略。

《当代评论》刊《新摘星录》首页
篇末作者记录的写作日期是“廿九年七月十八四川峨眉山”。 《梦与现实》连载于当年(1940 年) 《大风》第七十三期、七十四期、七十五期、七十六期,出版时间分别为8 月20 日、9 月5 日、20 日、10 月5 日。1942 年,沈从文改题《新摘星录》,发表在11 月22 日、29 日、12 月6 日、13 日、20 日昆明出版的《当代评论》第三卷第二至六期,署名沈从文。文后的写作日期分两行书写:“廿九年七月十八写卅一年十月末改写”。 《当代评论》为一个综合类周刊。1941 年2月在昆明创刊,1944 年3 月停刊。1944年,沈从文又改《新摘星录》为《摘星录》,在1 月1 日桂林出版的《新文学》第一卷第二期刊出。署名沈从文。文后的写作日期又加了一行:“三十二年五月重写”。1943 年7 月15 日创刊的《新文学》月刊,只出四期,1944 年5 月15 日终刊。 《沈从文全集》编者编入第十卷的《摘星录》,就是依据《新文学》文本。

《新文学》1944 新年号刊影
第二篇《摘星录》,1941 年,《大风》分三次在第九十二期、九十三期、九十四期连载,出版时间为6 月20 日、7 月5日、20 日。文后《后记》注出: “时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五黄昏,李綦周记于云南”。
《摘星录》刊出不久,11 月5 日出版的《大风》百期纪念号上一次刊出了《看虹录》,这是第三篇。篇末有“三十年七月昆明”的写作时间。1943 年,沈从文以“上官碧”的笔名,又在7 月15日出版的《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刊出《看虹录》,篇名未变。后依据《新文学》文本,编入《沈从文全集》第十卷。
三篇作品都是以“一种融合了梦想与真实因而亦小说亦散文亦戏剧独白等相杂糅的文体”,写“难忘的爱欲记忆和无忌的爱欲想象”, “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确实程度不同地注入了相当私密的情感和想象,而写法也异乎寻常的越轨和大胆”。 ( 解志熙: 《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

《新文学》刊《摘星录》首页
《看虹录》一般认为是沈从文写30年代末与高韵秀(笔名青子)的婚外恋情。沈去西山熊希龄的别墅,见到当时在熊家任家庭教师的高青子,两人遂有密切的交往。“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画,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 刘洪涛: 《沈从文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原型考证》) 论者称《看虹录》 “笔致较为隐晦,写实的色彩淡化,典喻的色彩更浓,叙述的方式亦更为唯美化、象征化”。( 裴春芳: 《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 桂林《新文学》刊出时,沈从文对《大风》的初刊本做了修改,一个最重要的变动是第一节“我谨谨慎慎翻开那本书的一页,有个题词写得明明白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这里“神在我们生命里”一句题词,初刊本中则是一段文字:

《大风》百期纪念号刊影
这是一个生物对于另外一个生物所具有的一种幻象,情感荒唐而夸饰,文字艳佚而不庄。然而这就是“生命”。是生命最真挚的燃烧一种形式。尽管所写到的,如何与习惯所许可相远相违,不碍事的, “道德”与“艺术”常常不能并存,尤其是庸俗道德与纯粹艺术不容易混在和( 似应是“混合在”——引者) 一个作品里恰到好处。这个记录不足供多数人的取乐,却足给少数人的深思。少数中的少数,应当从这个猥琐记录中,见到一般经典所不常见到的一点说明,即“神”原本在我们生命里。

《大风》刊《看虹录》首页
沈从文的作品常带有相当强烈的自传性,作者、叙述者与作品中某些角色几乎合一,因之论者认为:看虹、摘星,各有所喻。沈与高的情事在30 年代的文化圈中并不是秘密, 《看虹录》写的是旧情;而《梦与现实》和《摘星录》则是写的新爱了。
《梦与现实》中的女主角“她”,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独身的美丽女性。她长期寄居在“老同学”家里,与“老同学”的丈夫(情人?) “老朋友”日益亲密,引起“老同学”的嫉妒以至离家出走。三人都为此痛苦。研究者认为,“她”很可能指的是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老朋友”隐指沈从文,而“老同学”则是张充和的姐姐、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化身。因为不是一般的风流韵事,作者有意写得深微隐曲,难以捉摸。与香港《大风》的初刊本比较,昆明《当代评论》刊出时的修改,除了一般的词语修饰和语义补充之外,有两点值得玩味:一是文中叙述者对“大学生”的描述。如,初刊本写大学生“站在门边笑着”, “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昆明本在“笑着”前加“谄媚的”,“手”前加“只知玩扑克牌的”,轻视和嘲弄的语气明显加重。文中当大学生从“她”手中抢去了一小朵白兰花后,接下来写大学生的神态,初刊本是“偏着个大蒜头,谄而娇的笑着,好像一秒钟以前打了一次极大胜仗”,昆明本改为“偏着个扁葫芦头,谄而娇的笑着,好像一秒钟以前打了一次胜仗,又光荣又勇敢”。 (桂林本又改成“偏着个梨子头,谄而娇的笑着,好像一秒钟以前和日本人打了一次胜仗,争夺了一个堡垒,又光荣又勇敢”。)比喻的内容逐步细化,但“大蒜头”“扁葫芦头”和“梨子头”一改再改,似乎区别不大,无非极言其丑,说明此乃“典型的俗物”罢了。文中说,“她觉得这是一种妒忌的回声”。二是时间和数字的改变。如初刊本“一首小诗是上一月临向百里外旅行时留下的”,昆明本则改为“是上三个月临离开她时留下的”;初刊本中“她”给老朋友的信里一句“快有二十天不见你了”,昆明本改为“快有三个月不见你了。”特别是有关“她”阅读的三封旧信的交代。第一封,初刊本说:“是那个习英国文学的留学生写的。编号三十一,日子一九三三年七月。”昆明本却改为“是那个和她拌嘴走开的大学生写的。编号三十一,日子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二封稍长的信初刊本这样写:“编号第七,日子为四月十九日。”昆明本则是“编号第七十一,三年前那个老朋友写给她的。日子为四月十九”。第三封,初刊本的记述是“编号二十九,五年前三月十六的日子”,昆明本改成“编号四十九,五年前三月十六的日子。那个大学二年级学生,因为发现她和那两兄弟中一个小的情感时写的”。这类修改,是为了与“真实”有意趋近,或是故意拉远?缺少资料,不好悬揣。桂林《新文学》本保留了昆明本的修改,变动很少,但有所增补。如,“她”读了大学生的信之后,初刊本和昆明本只是写“信中不温柔处,她实在受不了”。而桂林本在这两句之后,加了一段:“尤其是她需要那个为忌讳与误会沉默不声离开了她的老朋友,她以为最能理解她,原谅她,真正还会挽救她,唯有这个对她不太苛刻的老朋友。”突出和强化了对老朋友的怀恋。
《摘星录》写男女肌肤之亲、肉体之爱。暑热天气,夜静以后,女主人在客厅里等待客人的来临。开篇极力刻画女主角色相之美: “主人是个长眉弱肩的女子,年龄从灯光下看来,似乎在二十五六岁左右。”“镜中人影秀雅而温柔,艳美而媚,眉毛长,眼睛光,一切都天生布置得那么合式,那么妥帖”。“手白而柔,骨节长。伸齐时关节处便现出有若干微妙之小小窝漩,轻盈而流动。指甲上不涂油,却淡红而有真珠光泽,如一列小小贝壳。腕白略瘦,青筋潜伏于皮下,隐约可见。天气热,房中窗口背风,空气不大流畅觉微有汗湿。因此将纱衣掀扣解去,将颈部所系的小小白金练缀有个小小翠玉坠子轻轻拉出,再将贴胸纱背心小扣子解去,用小毛巾拭擦着胸部,轻轻的拭擦,好像在某种憧憬中,开了一串白(百)合花,她想笑笑。瞻顾镜中身影,颈白而长,肩部微凹,两个乳房坟起,如削玉刻脂而成,上面两粒小红点子,如两粒香美果子。记起圣经中说的葡萄园,不禁失笑。”小说继而写男女的性挑逗和性行为,尺度放大,笔触刻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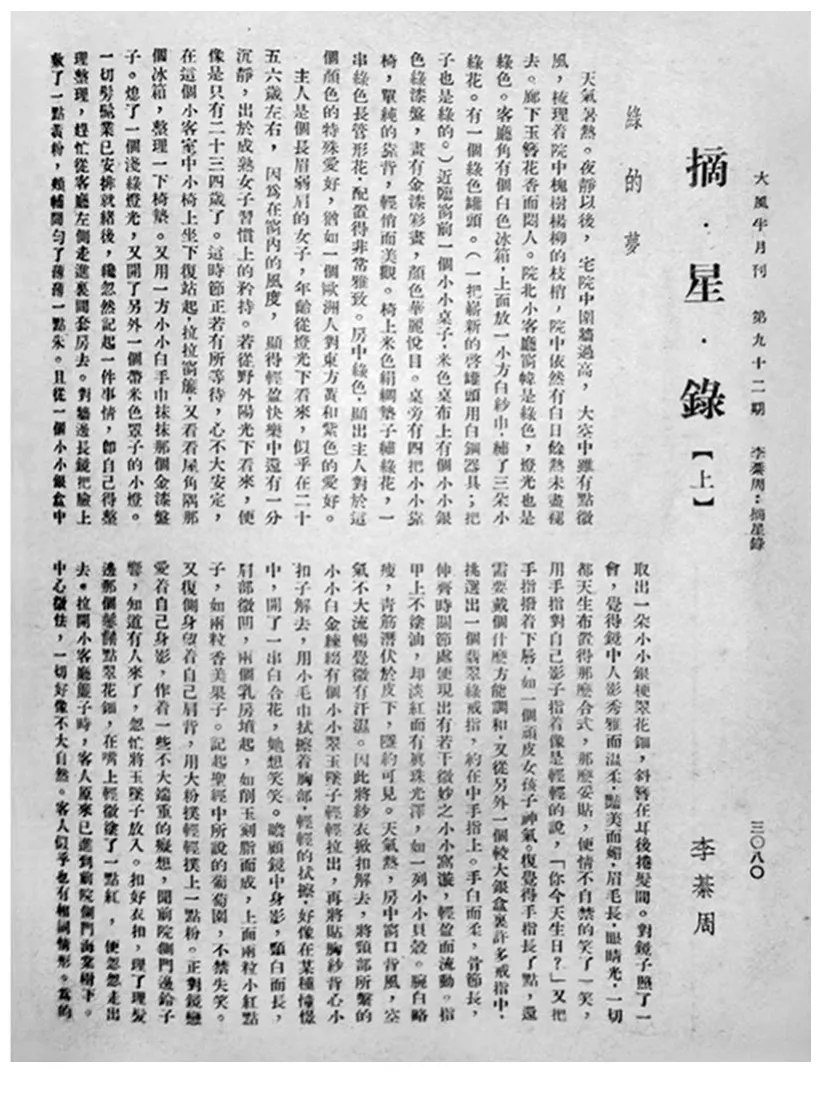
《大风》刊《摘星录》首页
因为新爱的非同寻常,作家铭心刻骨;也正因为非同寻常,作家讳莫如深。解志熙论及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行为,说:“大概也只有两种解释:一、他的反复用《梦与现实》代替《摘星录》,标明他特别钟爱《梦与现实》,并试图以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复发表的姿态来加强读者的印象;二、他的反复用《梦与现实》代替《摘星录》,乃是移花接木之策,表明他后来对《摘星录》心有忌讳,因而怕人知道和记住《摘星录》。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倒可能共存且并行不悖的。” ( 《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