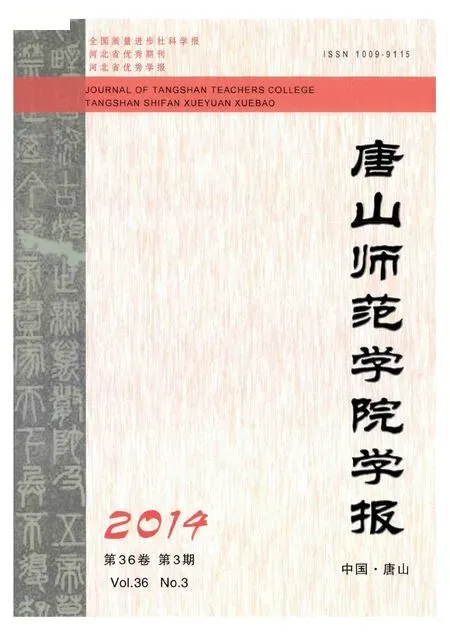论胡风与《希望》的主体人格建构思想
张玲丽
(湖北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论胡风与《希望》的主体人格建构思想
张玲丽
(湖北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现代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轫、发展及成熟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胡风集诗人、理论家、编辑家三重角色于一身,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编辑的《七月》与《希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胡风思想与两份刊物以相互促生的关系激发与提升了现代文学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理念——主体人格建构。
胡风;《希望》;主体人格
鲁迅在20年代初的《摩罗诗力说》中初步确立了其后文学思想的核心,呼唤摩罗诗人,为中国文学及文化注入了刚健的主体力量。在其后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又为中国文学寻找到向内挖掘的创作方向。深受鲁迅影响的胡风,在确立自己的文学之路之初就找准了其后创作与思考的重心。“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对鲁迅“主观”与《苦闷的象征》“主体”思想的拓展与深化。这种深化不仅成就了胡风的思想精髓,也引领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份文学奇葩——《七月》与《希望》。尤其是《希望》,它不仅是“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文学思想演化与成熟的主要媒介,同时,更成为与左翼文学界以及文化界争夺话语权以及文化人格的重要阵地。
胡风对作家主体的思考始于1934年的《张天翼论》,直到1943年的《现实主义在今天》,“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理论术语已经基本成熟,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其内涵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胡风认为,就文艺家一方面说,只有提高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展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的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以此为出发点,胡风在其后创办与坚守《希望》的过程中,逐渐扩展与深化“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使它成为一种文化人格的标识。
1944年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无疑是一份宣言,不仅是对单一、被动、惰性的左翼文学界以及文化界的质疑与宣战,同时也是其后《希望》精神实质的宣告。“主观战斗精神”若影随行地贯穿在《希望》的始终。
《希望》时期恰逢左翼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运动——由延安铺展开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场运动直接
涉及到作家自身价值与角色定位的问题。在《希望》前后,国统区的作家在创作层面、自我定位方面已经开始以《讲话》作为标准。《新华日报》在1943年之后,登载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反思自我价值的文章,对于其小资产阶级出身表示不满,力图肃清其出身带来的负向影响。舒群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的《作家的自我批评》中,提到“不管我们来自城市还是乡村,曾经是学生还是流浪汉,却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这个思想,贯串着每一篇,每一个字。不管我们曾经生活得简单还是复杂,大体都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语言。”[1]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的颠覆。但是,许多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颠覆性定位似乎是顺理成章,无需置疑的。
胡风强烈地感受到了当时倾向于左翼思想的作家的人格萎顿,因此,在他独立创办的《希望》上不遗余力的倡导“主观战斗精神”就成为其首要的目标。在《希望》的创刊号的首页登载鲁迅20年代初的《摩罗诗力说》,同时把舒芜的《论主观》置为刊物的首篇,尽管在后者遭到质疑甚至围攻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转换措辞以希冀改变胡风本人以及刊物的当时的紧迫境遇,但是,不足以扭转《论主观》本身对于左翼思想界带来的冲击力量。
胡风在《希望》时期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丰富复杂性的充分自觉:“知识分子是加在锤与砧之间的最先见最尖锐的说出人生的真谛,而且是最勇敢的最坚决的保卫了人生真理的最敏感的触须,最易的火种。”[2,p264]胡风对知识分子作家的先锋性定位显示出对“五四”精神内质的承继,同时又显示了特殊的历史阶段——“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的风暴”时期,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历史的创造意识。这无疑影响着《希望》的精英气质的呈现。胡风对于知识分子的先锋位置的体认对于《希望》的作者是一种潜在的鼓励与支持。“最近读了《约翰·克利斯多夫》,多么想给你和门兄读一读呵。这是理想主义,甚至带有宗教的气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觉得受了洗礼似的幸福。是,这是理想主义,但现实主义如果不经过这一历程而来,那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屁现实主义呢!”[3,p208]这是胡风在创办刊物两年前给路翎书信中的一段话。此时,胡风对文学以及文学家的理解透露着理想主义的气息。
胡风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把批评矛头指向左翼阵营内部的作家?就是因为这些作家、这些作品的“枯干”,对于神圣的文学而言是戕害与破坏:
因而更奇怪文坛为什么这样枯干,因而也就想,能弄起来还是弄起来罢。如能变成‘过街老鼠’,这次信顶倒也比装死好一些的。[3,p225]使我高兴的,是读了关于欧洲的书。生命,能够扩张才能够成长。有些人,成天文学文学,因而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好像一个人干子。悲惨得很。但当然,要扩张,首先须得他自己是一个活的人。[3,p212]
“枯干的文坛”是因为“人干子”作家的存在,因此,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开辟了书评专栏,并且矛头直指左翼阵营的那些“人干子”作家。
胡风的良苦用意得到了道友的理解与支持。路翎在给胡风的书信中写到:“觉得目前情况昏沉,出版社及刊物非坚持不可。固然‘书生之见’无大作用,总可以借新生者竖一面旗帜。而且我们自信在应该的时候,拿起‘枪’来,是不会比别人差的。读前信,觉得你的心情似乎非常沉重。你走得甚远,觉得孤零罢。在目前,举起鲜明的目标来,是最要紧的,否则,少许的努力,落入大海洋中。这目标要明快,而且煽动。使混蛋们不能出头。”[4,p117]“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但现在却连幼苗都被摧残了。你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因而也比什么都困难罢。”[4,p131]感知到中国文学文化的传统思维习惯,路翎意识到了胡风的工作的神圣与重要,也意识到了胡风走得很远而产生的孤独感,鲁迅在世纪初所倡扬的“精神界战士”实现得步履维艰。胡风对于诗人的界定是精神战士:“生活道路上的荆棘和罪恶里面有时闪击、有时突围、有时迂回、有时游击地不断地前进,抱着为历史真理献身的心愿再接再厉地向前突进的精神战士。这样的精神战士。即使不免有时被敌对力量所侵蚀所压溃,不,正因为它必然地有时被敌对力量所侵蚀所压溃,但在这里面更能显示他的作为诗人的光辉的生命。”[2,p76]在《希望》时期,“精神战士”的定位明确并且有力坚定。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及《希望》作家群对外批评的衡量尺度,在他们看来,观照与冷静透视是创作态度的错位,有违于作家主动性品格,偏离了承担意识的定位。《希望》进行的书评运动,对于客观主义、市侩主义、庸俗甚至色情主义进行的批判,都能在这里找到根源。
1945年《希望》创刊。从第二期开始发表路翎、石怀池等人指向左翼进步阵营的作家作品的批评文字,主要涉及的作家作品是沙汀、严文井、碧野、姚雪垠等在当时左翼文学界享有盛名的作家。其实,这些书评文字不仅仅是单个作家的心血来潮,不是各个批评者的不谋而合,而是与刊物编辑的思想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胡风有意识的发动的“清肃”运动。这在胡风书信中得到有力的张显:“书评,好的。应该这样,也非这样不可。但我在踌躇,至少第二期暂不能出现。”[3,p209]“所以,暂找别的典型罢。《戎马恋》、《幼年》。”[3,p256]这些作品在当时是得到认可的比较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沙汀、姚雪垠等在当时是影响颇大的左翼作家,书评把矛头指向他们,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创作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歧途,因其影响颇大,必须大力对其批驳,以期得到校正。
对客观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石怀池和路翎的书评文字之中。路翎对客观主义的批评,指向了另一个文学维度,他从作品所产生的读者效果出发认为:“人们走进一件艺术作品去,却总是怀着某种斗争的热情的兴奋,希望着一场恶战,希望着提高人生,希望艺术的幸福和人生的勇敢的”,而《淘金记》则“表现着对于生活(特定的时代的热情的内容)的麻痹,和对于生活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客观的态度。”[5,p179]路翎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作家的主体创作意识。路翎以尖锐的语气批评碧野的《肥沃的土地》:“碧野先生的‘肥沃的土地’,是表征着目前的新文学创作上的一种恶劣的倾向的作品”,“色情主义加上政治的文学的公式主义,一面向今天的苦闷的中层社会博取观众,一面又宣告说‘看吧,人民大众!’这是把自己当做妓女的色情文学!这是把作者自己及其观众们当作嫖客,把人民大众当作妓女的色情文学,这样的卖笑者,这样的色情文学,是目前的文学创作上的一个显明的倾向。”[5,p116]批评语言极为激烈,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表明对这种创作倾向的无法容受。在路翎而言,这种倾向的描写,在文学创作中应该被抑制,因为它显示出文学的软性力量,背后隐含的是作家自身的非严肃的创作态度。
对于《希望》的主要作者,诸如路翎、阿垅、绿原、吕荧们而言,《希望》成就了他们,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但他们无悔,不仅在初期据理力争,在厄运结束之后,又聚集为同道,投入到文学事业中。这群作家为一种精神力量所凝聚,为一种理想光源所接引,即使面对种种批判的武器,也始终没有从内心崩溃。
其中,阿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典型。阿垅在建国后的创作包括《人和诗》、《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论倾向性》、《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建国后,他在《七月》时期对于“真”的阐述以及《希望》时期诗论中对于刚健人格的追求凝结成一股力量,喷发而出。1965年的申诉材料《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是集中的体现。阿垅在当时发出了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一个政党,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6]阿垅掷地有声地反驳对于他们这群作者的诬蔑,同时,对“政党”的纯正的理解喷射出振聋发聩的力量。
阿垅在遭受误解、批判的情势之下,在与青年的书信中流露出逆境之下对于时代的敏锐感知以及对于自己定位的深度思考:
我要说到做人。因为做人是第一义的,而做诗,到底是第二义的。好的人才有好的诗,健康的人才有健康的诗。
我们服膺鲁迅先生。那么,他就说过:傻子,闯将,和沉默的工作者——就是说,一切,首先让我们自己沉默地工作吧!
表态是无用的,无效的。进一步说,态度,是什么?还不是人底斗争和行动么?”[8,p166]
不要寂寞,不要沉在那里面,冲出来,多看人,少自我怜惜。绿原就要多看人。要使悲惨成为我们底力量,而我们不可以被悲惨所屈服。绿原就不屈服,而悲惨,也就成为他底激战和奋战的力量。[7]
与此相反,舒芜则成为“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思想“精神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在《希望》时期,除却胡风之外,在理论层面对于“主观战斗精神”理解与阐述得最系统的就是舒芜,他通过一系列文章向左翼文学以及文化界阐明左翼思想的发展是具有多种可能的,在“五四”的道路上是可以贯穿起一种更成熟的左翼思想之路的。但是,舒芜其后却又以切身的被称为“犹大式”的行动再次验证了“主观战斗精神”化作人格精神的艰难。
由此可见,“五四”开启的启蒙之路任重而道远。
[1] 舒群.作家的自我批评[N].新华日报副刊,1944-09-04(8).
[2] 胡风.胡风全集(第3卷)[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64.
[3] 胡风.胡风全集(第9卷)[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5] 路翎.谈“色情文学”[J].希望,1946(2):116-118.
[6] 阿垅.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J].新文学史料,2001(2): 65-67.
[7] 阿垅.阿垅书信[J].新文学史料,2003(4):164-169.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The Comment on Subject Personality’s Construction of Hu Feng and His Periodical Hope
ZHANG Ling-li
(School of Humanities, Hube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
Modern literature periodica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process of modern literature. Hu Feng is considered as the poet, literature theorist and edito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July and Hope founded by him show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e boosting of ideology of Hu Feng and these two literature periodicals had arous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concept —— constructing subject personality.
Hu Feng; Hope; constructing subject personality
I206
A
1009-9115(2014)03-0011-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3.003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b190)
2013-09-22
张玲丽(1979-),女,山东东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