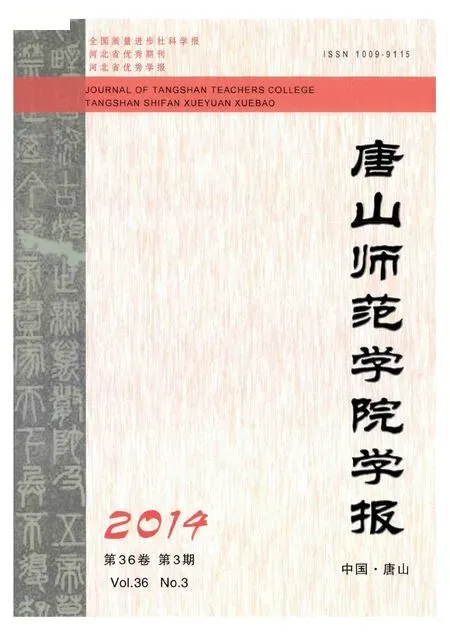“百花文学”中离婚叙事的政治化
王百伶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百花文学”中离婚叙事的政治化
王百伶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百花文学”出现了一些描写离婚叙事的“突破题材禁区”的作品: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丰村的《一个离婚案件》、秦兆阳的《归来》、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布文的《离婚》,但由于“百花文学”是处于“十七年文学”特殊时期,是“国家体制文学”“共和国文学”,是呈现“一体化”趋势的,因此这些作品必然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并从婚姻的缔造与维持、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员的对立关系、未离成的离婚叙事来探讨离婚叙事中的政治化以及将“儿女情、家务事”通过政治因素的干预,提升为“宏大叙事”的文本。
百花文学;离婚叙事;政治化;《在悬崖上》;《归来》
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部《婚姻法》颁布,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描写离婚叙事的文学作品,其主流模式为:乡村女青年摆脱封建包办式婚姻,实现自主离婚。但由于“最初的异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因“小资产阶级情调”“低级趣味”受到批判,致使离婚题材在当代文学中被作家视为禁地而暂时搁置。1954年《宪法》的颁布,以及“双百方针”的实施为文学界带来了暂时的松动,侯金镜指出:在(1956年)思路打开了,创作上的清规戒律被排除掉一些了,这不能不是这一年的短篇小说产生了新气象的重要原因……关于爱情和家庭生活的题材,也曾经有过不少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为内容的作品,但是描写社会主义路途上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作品就很少,这一年在“百花文学”中出现的“突破题材禁区”的描写家庭生活的离婚小说,即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1956)、邓友梅的《在悬崖上》(1956)、布文的《离婚》(1956)、秦兆阳的《归来》(1956)、丰村的《一个离婚案件》(1957),这些作品是作家由于“双百方针”而“喜形于色”的表现,是“从黑暗与血污中升起的星光”。
但是“百花文学”又是处于“十七年文学”总的体制之下,是“国家体制文学”“共和国文学”,是呈现“一体化”趋势的。1956年5月,《文艺报》刊发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出:作家、艺术家对题材、主题和艺术形式的选择,有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必须是在为工农兵和劳动知识分子服务的共同目标下[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更为“双百方针”规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2]。
因此,在特定时期贯彻推行的“双百方针”,虽然为文学界带来了“自由”的曙光,但仍是在符合政治的标准的前提下缓步前行的。
基于上述原因,作家们在相对宽松的自由的百花时代也不能走得太远,害怕一放、二收、三整,不得不把自己的思考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因此这些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说有着政治化的“隐喻”,正如文学评论家茅盾对20世纪普罗文学的评价一样,即“政治宣传大纲加公式主义的结构和脸谱主义的人物”[3]。对于这些文本的解读,也就需要放在政治的层面上来展开。
一、婚姻的缔造和维持:以政治为主导
(一)有条件的婚姻
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是爱情的结果,因为有了爱情才有了婚姻。恩格斯曾经说过:爱情是人们彼此间以相互仰慕为基础的关系。但是在唯政治论、唯阶级论的年代,那时人们所信仰的“爱情,只有建筑在对共同事业的关心、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劳动的热爱的基础上,才是有价值的、美丽的、值得歌颂。”[4]人们考虑婚姻的对象首先是其身上所彰显的政治光环,正如《老二黑离婚》中因为父亲被打为右派,小虎不得不和相恋之人分手,小梅甚至想以死来殉情。因此婚姻的结合也就都有着政治因素的渗透。
丰村的《一个离婚案件》中,首先点明婚姻的本质——婚姻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
婚姻双方的当事人在结婚前四个月还互相不认识,似乎也没有见过面,而且他们之间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一个热情温柔,另一个死板严肃;一个使人感到可亲,一个使人感到可怕,他们认识的“中介”是工作,谈到工作,两个青年人是接近的,是一致的。组织上(以王处长为首)也在极力地撮合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观念中,两个优秀的青年团员,工作上互相扶持,“政治上一致”,还有什么能够阻止男女双方在一起呢?他们认为两个努力工作的男女在一起,就是爱情,而凡是好的青年男女都是可以结婚的,社会群众会批准的,众人的舆论会批准的,因此小刘和小马的婚姻就完全受政治的支配了,他们不得不顺大家的意愿而结合,小马想“既然大家觉得应该结婚那就结婚吧”,而小刘也认为“相爱也好啊”。在此婚姻被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甚的“政治之命”所包办。
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男主人公“我”不知怎的就“爱”上女主人公了,不妨说是爱上她的“政治外衣”——团支书的职务,青年人的领导人,因而能在思想上督促我的进步。在结婚后,两人回家后就一起学习,一个读俄文,一个读技术书,妻子在晚上还要不断要求丈夫念政治书给她听,而男主人公“我”什么也不需要了,唯有好好的工作,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唯恐变成一个“二流子”,和妻子拉开差距。二人的日常生活完全被工作、改造思想所代替,但因为妻子是党的、政治的化身,所以这寂寞枯燥的生活“我”仍然感觉我们的感情很好。
以上男女主人公的婚姻爱情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认为“真挚的爱情是一种深刻的,持久的,有着明确方向的感情,因此它不但不会妨碍双方从事的社会事业,而且会更加鼓舞自己和对方前进的勇气”[5]。在此,人的正常需求被认为是一种庸俗的、会妨碍双方事业的行为。他们超然于世外,追求一种近乎于圣人的爱情,“奖章恋爱”“英雄配模范”的婚姻。其所谓的爱情“是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6]。
布文的《离婚》中林杏春在政治上也是先进的,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她是村里的乡人民代表,植树模范,青年突击手,生产互助组的模范。但是林方三年未回家,不知道儿子的出生,夫妻双方从未有过感情的交流,而维系这场婚姻的是政治,因为林方当时正处于“三反”时期,自己有些问题受到审查,如果婚姻再出现问题,自身恐怕难以自保。
秦兆阳的《归来》、孙谦的《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表层叙事为自由恋爱,可深层的都是政治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婚姻都是依附于政治的,是有条件的。
(二)女性形象的政治化
在这些文本中,女性形象大都是如同革命样板戏中的所塑造的阿庆嫂、李铁梅等女性形象,是被政治定性的脸谱主义人物,是政治的化身,在成长过程中,女性的自身特性、意识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私人话语”“私人空间”逐渐消解。“女性再度成为经典解码和一种意识形态代码被导入叙事之中。”[7]她们标榜自己,要求享有和男人平等的地位,而实质上能力与男人也差不多。
这些女性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拯救型”与“殉道(社)型”两类。“拯救型”女性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马缨花等,但不同的是她们主要是在思想上拯救男主人公,以政治为武器改造着男主人公的思想,她们用政治的乳汁哺育着思想上处于危险边缘的丈夫,改造着一个个心灵卑下扭曲的人物。她们“是维纳斯,是传统美德的对应物和象征体”[8]。最明显的是《在悬崖上》中“我”的妻,妻评价人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并且要求“我”在政治上注意别人,晚上念政治书,改变“我”的言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脚踏实地的学习、工作、生活,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及思想境界,争取做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而且在“我”要求离婚时,妻子关注的不是双方感情的破裂,而是丈夫思想境界的下滑,并因为过去自己没有严格地提醒丈夫、没有注意到丈夫思想意识的变化而自责。
“殉道型”的女性也可以说是“殉社型”的:《离婚》中的林杏春是乡人民代表、植树模范、青年突击手、生产互助组的模范,甚至在见到三年未归家的丈夫时仍在忙着合作化问题、村民丁有荣的离婚问题;《奇异的离婚故事》中杨春梅是共产党员,早晚忙着入社;《归来》中童慧云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深得邻里乡亲的赞赏……作者对这些女性形象是赞美的,不是因为她们的外表美(她们此时在男主人公的眼里已是“黄脸婆”,显得土气、呆板),而因为她们在政治上的信仰所彰显出来的美,似乎只有政治才能体现美、创造美。然而这样的婚姻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不禁要问离开了政治,这样的婚姻关系还能维持多久?
二、在悬崖上
(一)以男、女性为主导的离婚叙事
依附于政治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必然是不牢固的,《婚姻法》的颁布,为想离婚的男女提供了一种契机,离婚趋势开始逐渐抬头。以男女二元对立关系为依据,离婚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男性为主导。俗话说“女人的宗教是爱情,男人的宗教是事业”,但在五六十年代的离婚叙事文本中,两者却正好颠倒了位置——爱情成了男人的宗教,如《奇异的离婚故事》《离婚》《在悬崖上》《归来》,男主人公都要求寻找真正的“恋爱”。这种叙事大多是进城的男主人公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要抛弃“糟糠之妻”,是典型的“福易妻”“负心汉”的文本再现,如王彪弃童慧云、于树德弃杨春梅、技术员弃妻、林方弃林杏春。而丈夫“士贰其行”的原因是“婚外恋”,进城后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腐蚀”、染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而贪恋“奇株异草”:林方喜欢一个19岁的漂亮姑娘;王彪爱上上司的女儿——一位城里姑娘;于树德贪恋城里的漂亮女大学生;技术员痴迷于来自异域国度的艺术学院毕业的、做雕塑师的有着青春气息的姑娘加丽亚……最为严重的是男主人公在婚姻观念上抱着一种“牵着绵羊找骆驼”的心态,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于树德“喜欢”陈佐琴是事实,但他并没有打定主意就要和她结婚,他对陈佐琴还不够十分了解,他还想再做一些选择;王彪与城里的姑娘恋爱,却隐瞒了家里有妻室的事实,他希望回来与妻子离婚后实现他的贪欲;《在悬崖上》技术员在与妻子离婚后,他只是觉得假如没有新的爱情来补偿,他马上会疯的……
而“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的妻子们在面对丈夫的背弃时,仍显示出传统的东方美德,以男性、家庭为本位的传统道德在她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技术员的“挺端庄”“长得挺秀气”的妻子在丈夫出现移情别恋时,反而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没有严格地提醒丈夫注意思想意识的变化,在痛苦地等待丈夫的“回家”的希望破灭之后,想到丈夫要离婚但又担心政治问题而不敢提出来,仍全心全意地为负心丈夫的政治前途考虑,主动提出由自己向组织申请离婚;《归来》中的童慧云在得知丈夫归来的目的只是想要和自己离婚时,表现出了传统女性的善良美德,压抑着痛苦,并没有大声地吵闹,只是以不争之争等待着下文;《奇异的离婚故事》中杨春梅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虽然觉得痛楚得窒息起来,仍没有吵闹,而是用力咬紧嘴唇,跑到大核桃树下,哭了一后晌。
另一种以女性为先导。中国妇女的“结婚的家长决定权”和“离婚的丈夫决定权”这一由来已久的“法则”一直被人们尊崇,并衍化为中华民族儿女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但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重新规定了婚姻制度的核心即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它使得女性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和追求“人之为人”的信念得到唤醒并强化,婚姻中的女性无权现象得到改变,自主权开始真正被她们所掌握的。
其实在《奇异的离婚故事》中女性的这种意识已经开始萌芽,杨春梅不愿再向“睡在外屋的那个人示弱”,觉得不能一次次地受骗,于是“决心要离”。最明显的是《一个离婚案件》中的小刘,到小刘那里这种意识已经完全觉醒。当小马恼怒地对她说“你去离婚好了”,小刘想婚姻不是哀求来的,既然无法培养则大可不必苦心经营,因此踏上了寻找自由的离婚之路,虽然这条路是异常的艰难,有无数的羁绊,甚至没有结果,但小刘仍然坚持,甚至不顾党组织和社会众人对于“女离夫”的舆论谴责,不服初审而上诉。
(二)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
在离婚过程中,提出离婚的一方,都会被谴责为思想路线有问题,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从而歌颂社会主义路途上的婚姻。在这种离婚叙事中也隐含着一种隐蔽的关系模式,即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二元对立模式,坚持离婚的都是知识分子,甚至是诱导人离婚的罪魁祸首,如《在悬崖上》老科长进城后想离婚就是因为接触到了知识分子。而共产党员则在极力地挽救出现裂痕的婚姻,作品中都通过歌颂共产党员来鞭笞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面前的动摇性、软弱性。在这一叙事结构中,工农大众成为历史的主体,而知识分子则被置为边缘的甚至是尴尬的境遇之中。
为什么知识分子在“百花文学”中受到如此的冷遇,这不得不从政治上来理解。
毛泽东坚持“武装夺取革命”,因此,对于处在革命时期的中国来说工农兵才是主体,是历史的推动者。作为领导者,他虽然没有排斥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加入革命队伍里来,但是“对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所持的是这样一种看法:他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9]。最典型的就是他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毛理论。从关于“鲁迅问题”的“罗毛对话”中更能看出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悲凉境遇。
李新宇更为精辟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让知识分子迁就和适应大众,而不是互相之间的迁就和适应?为什么让知识分子无条件地接受工农大众的教育和改造,……唯一的解释是政治斗争的现实要求。”[10]
因此当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出现矛盾纷争时,知识分子就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遇中,他们通常被要求无条件地接受工农大众对其进行的教育和改造。以便使其做到“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11]。
三、归来——未离成的离婚叙事
百花时代的离婚叙事,总体说是一种未离成的离婚叙事的作品,文章往往被作家处理为中国式的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具体地说,主人公由寻求一种新的感情关系开始,使旧的平衡关系遭受破坏,但‘尝试’过后,经过自助或他助,自律或他律的修复过程,重新回到旧的感情状态。”[12]迷失的羔羊大都归来,而未离成的原因大多仍是以政治为主导。
从道德的角度来说离婚是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即源于原始的性爱要求与源于封建主义礼教规范的婚姻道德的冲突,而最后的解决方式大多是情感为理智所战胜,原始的性爱要求屈服于封建主义礼教规范的婚姻道德。《离婚》中处于孤寂生活的、想恋爱的林方,内心需要一个真正的爱情,但是当回家后看到杏春孩子气的脸,那种对他完全信任的眼光,看到她那件老蓝色的衫子,看到她那小巧的可怜的身材,回家“离婚”的目的也忘记了。《在悬崖上》技术员也不断地受到良心上的叩问,看到妻子由于受离婚的折磨而平添的委屈的、痛心的神色时,他也很自责、内疚;想到马上要办理与妻子的离婚,妻子的许多好又涌到了他眼前:男女双方第一次见面,妻子给他留下的美好的端庄的印象;吵架中妻子对自己的忍让态度;生活中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些生活中的温馨场面让男主人公心理一度处于矛盾的状态中,并产生了自责心理。在听了老科长的话后,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与妻离婚后,妻子的悲惨处境。甚至在《奇异的离婚故事》中,万恶的于树德也把自己尽情地咒骂了一通,想象到:杨春梅一定会为丈夫的“荣归”高兴地眉开眼笑,想象到当他和她谈到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她会惊得发呆。然而必然要爆发一阵可以掀起屋顶的哭叫——孩子们也会吓得哭成泪人。他不愿看见这种场面,也不忍看见这种场面,他忽然可怜杨春梅,——她以后怎么办呢,不行得替她找一条出路。
还有一种未离成的是因为政治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与政权话语的冲突。“成也政治,败也政治”,婚姻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在那个政治性敏感的特殊时期,“离婚率的高低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低离婚率被政府,被媒体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13]。《婚姻法》同意离婚自由,但是又规定“男女双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得有区人民政府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应即转报县或市人民法院处理”,“区人民政府并不阻止或妨碍男女任何一方向县或市人民法院申诉,但县或市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也应首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即行判决”[14]。而这种以调解为先行的离婚必然又会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如《归来》中的婆母和村里代表的调解,《在悬崖上》的老科长的劝告,《奇异的离婚故事》中的农业社长周立本的嘲讽,尤其是《一个离婚案件》中的组织(以王处长为首)的干涉:组织是“不提倡离婚的”,而对于小刘的坚持离婚,不服初审而上诉的行为,直接将其定性为是小刘的思想问题愈来愈严重了,因为在王处长看来爱情无论怎样现实,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在《一个离婚案件》中,作者在结尾安排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这只是作者的一种梦想而已,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需要这样的经验叙述。“对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在政治挂帅的历史现实面前,撇开组织化的安排,从其主观选择来说,一种最直观、朴素的选择同样是以当下的政治任务、政治政策、政治运动、政治思潮或者相应的政治路线,以及有影响的时代事件等为主题进行相应的生活选材,直接为认识、宣传诸如任务、政策、运动、路线等服务。”[15]
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道德原因,其处于支配地位的都是政治。
在这些文本中作者又有时穿插潜在的副线对离婚当事人来进行规训。如《在悬崖上》老科长就以自身的经历对“我”进行了道德规劝:抗战前他在农村家里结的婚,夫妻两人的感情很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进了城,接触了新的环境、新的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妻子和自身的差距,于是一时冲动,便想和自己的“糟糠之妻”离婚。但是老科长只是一闪念,并没有付诸于实践。他用共产主义所追求的道德精神——关心别人、关心集体、对别人负责、对集体负责的信条遏制住了离婚的念头,因为他觉得离婚不仅给苦心等待自己回家的妻子造成精神上不堪承受的伤害,而且也否定了自己的精神品质,减少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含金量。
《离婚》中小保的爸爸进城升迁,在工会里当了个职员,虽然官位比林方小很多,但是早已抛弃了同甘共苦的文盲老婆,不仅成为村里人唾骂的对象,也使得林杏春通过小保爸爸的行为更加觉得林方的“好”,不时用“暗带责备”而实则“欣喜”的口吻夸赞丈夫“老实”,是个“傻子”。而村民丁有荣要离婚,林杏春也说“怎么能让他离呢?”
《归来》中童慧云的妹妹与志同道合的恋人相亲相爱。
《奇异的离婚故事》中农业社长周立本以林方的父亲娶小老婆的原因对想要离婚的男主人嘲讽了一番。
可以说这些离婚故事,作者是将“儿女情、家务事”的小题材,通过政治因素的干预,提升为一种表现大主题的“宏大叙事”,涉及到了历史问题(阶级/政党)。“那些看起来好像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主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16]
这些鲜花只绽放了很短的时间,在其后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政治声讨式的批判。姚文元称其为“小市民的庸俗趣味”“把自私自利的感情暴露的极为深刻”,是想用“资产阶级恋爱观点推翻爱情中的政治基础”[17]。
“这样一来,作家们就在两个层面上丧失了主体能动性,面对火热丰富的现实生活,他们丧失了透视的自由,而被强迫到按照某种政治理论去理解,重构;面对文学,他们丧失了自由创作的权力,而被规定必须以某种模式和程序进行探讨。”[18]
总之,处于百花时期的离婚叙事,一方面它不断反“政治渗透”而向艺术回归,挣扎着向“艺术的独立性”方面靠拢;另一方面这股“创作上的逆流”并未清理掉“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它虽然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但仍摆脱不了“主题先行论”的潜在规则,它们是一批以政治角度来阐述婚姻的内涵的文本。“努力在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与维护个体精神独立之间寻求协调的可能性”[19],是一种离婚书写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合作,在简单的表层叙述下潜藏着一种复杂的政治化。
[1] 张光年.张光年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86.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毛泽东选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92-393.
[3] 茅盾.关于“创作”[J].北斗(创刊号),1931(1):75-89.
[4] 了之.爱情有没有条件?[J].文艺月报,1957(3):54-55.
[5] 谢云.苏联文艺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J].文艺报,1953 (6):29-30.
[6] 黄秋耘.“谈爱情”[J].人民文学,1956(7):59-61.
[7] 杨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200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6.
[8]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8.
[9] 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3.
[10] 李新宇.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1998(3):45-53.
[11] 中共中央党史党校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7.
[12] 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于“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J].文学理论研究, 2004(1):29-37.
[13] 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213.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81:175.
[15] 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1.
[16]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张京媛,译.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J].当代电影,1989(6):47-59.
[17]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J].人民文学,1957(11):109-126.
[18] 丁帆,王世诚.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86.
[19]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7.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The Politicalizaiton of Divorce Narrative in Baihua Literature
WANG Bai-ling
(School of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In the relatively relax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Baihua Literature produced some works which make a breakthrough in divorce narrative subject such as Sun Qian’s Strange Stories of Divorce , Fengcun A Divorce Case, Qin Zhao-yang’s Return, Deng You-mei ’s On the Cliff, BuWen ‘s Divorce. But Baihua Literature was during the peculiar period of "seventeen years", so the political ideology inevitably affected these works. The texts a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riage’s crea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oppos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unsuccessful divorce to discuss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divorce narrative and to explore these grand narrative text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factors.
Baihua Literature; divorce narrative; politics; On the Cliff; return
I206.7
A
1009-9115(2014)03-0017-05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3.005
2013-10-19
王百伶(1987-),女,满族,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