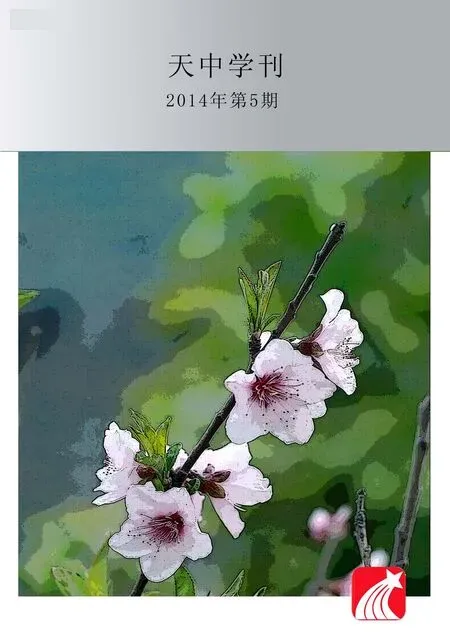20世纪以来汉唐间道巫关系研究述评
韩书晓
20世纪以来汉唐间道巫关系研究述评
韩书晓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汉唐间道巫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东汉时期道巫关系的研究,包括建立在考古资料基础上对道教与巫者信仰对象关系的探讨,对道教斋醮符咒科仪与巫仪关系的分析及对道、巫区域特征的阐述;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巫关系的研究,涉及道巫的相依性、道巫的对立性、兼顾道巫的对立性和相依性等三个方面;三是隋唐时期道巫关系及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涵盖道教转型过程中对巫者的信仰对象、巫术和巫俗的吸纳,道教科仪对巫术活动的影响,百年来汉唐间巫术与巫者方面的研究进程,以及道教研究重要文献史料。当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研究内容不够系统和深入,研究视角不均衡,研究方法缺乏互鉴等。
道教;巫者;巫术;汉唐;述评
道巫之间关系密切,研究道巫关系既是推进道教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石,也是全面深刻认知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的重要环节。不少研究者对此予以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有鉴于此,下面笔者将对20世纪以来汉唐间道巫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望有助于日后进一步探究。
一、东汉时期道巫关系的研究
在20世纪30年代,即道教研究的发轫时期,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道巫关系的问题。1934年许地山著述的《道教史》问世,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道教历史的著作。在第七章,作者探讨了道巫关系,指出中国古代巫觋道是道教的重要源头,秦汉时期巫觋的信仰对象和巫术或被道教直接借用,或经改造后使用[1]。不过,许地山着墨的中心在于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并非道巫问题。
继许地山的《道教史》之后,国内又先后出版了多部道教史专著,如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著述的《道教史》。这些著作立意高远,内容丰盈,体例多样。在道巫关系问题上所表述的观点与许地山相一致,即早期道教吸收了巫术及巫的信仰对象等。不仅中国学者对此问题有所关注,一些日本学者也早有所论及,如酒井忠夫、福井文雅的《道教是什么》、秋月观暎的《道教史》、松本浩一的《道教和宗教仪礼》。他们主要研究六朝道教,在追溯道教起源时,阐述了道术与巫术、道士与巫祝之间的联系。以上论著在道教研究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内容皆涉及道巫关系,但皆停留在“顺带性地叙述”层面,并未全面展开、深入探究。这固然与论著研究的核心内容不在于此有莫大关系,然而从侧面也反映了全面系统地论述道巫关系是深化、拓展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批镇墓文、解注符、巫祷券书等考古文物资料的出土,使道巫关系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突破。研究者开始试图划分道巫之间的界线。1981年,吴荣曾在《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中,通过剖析东汉墓中出土的镇墓文材料,指出东汉时期诸如泰山治鬼、黄神乐章等与巫术有关的内容被道教吸收[2]。与吴荣曾的观点一致,方诗铭在《曹操·袁绍·黄巾》中,也指出民间的巫术和巫的信仰对象如黄神乐章被原始道教吸收[3]。
另一些研究者关注道教和巫觋所使用工具的异同。王育成在《东汉道符释例》中,提出东汉户县曹氏符和洛阳解注符都是道符,并对其进行破译和意释[4]。刘仲宇赞成王育成对符的结构的解析,又初步辨析了早期道符与巫符的不同之处,指出这些符是巫符而非道符[5]。之后,连劭名在《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与古代的册祝》中,依托简牍文物,解读了东汉建初四年巫师祝祷的内容,认为这是巫师为人除病的券书,其性质同于后世道教进行禳解时使用的“章”[6]。与单篇论文相比,刘昭瑞的《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涉及面更广泛,内容更厚重。该著作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近20年研究成果的集锦,共10章43节,涵盖道教观念、道教典籍、道教法器、道教科仪、道教传播、道教史等多个方面。其中,作者从道巫的仪式出发,分析了禹与巫道发生联系的原因、禹步的起源等问题,认为道教的“禹步”与巫同源[7]。
以上除了道教通史类著作和吴荣曾、方诗铭的论著稍略论述了道教对巫者信仰对象的吸收,其他皆从道教斋醮符咒科仪的某一方面切入,探究道巫关系。1999年张泽洪《道教斋醮符咒仪式》和2002年刘仲宇《道教法术》的问世,打破了先前道教斋醮符咒仪式研究单一性、零碎化的状况,开始转向整体化、系统化。《道教斋醮符咒仪式》展现了东汉至明清时期道教斋醮科仪的发展轨迹,并阐释了道教斋醮科仪的宗教功能及其蕴含的思想[8]。但该著作对汉唐间的道教斋醮科仪着墨较少,且在追溯道教斋醮科仪源流时,对先秦民巫的作法方式和巫术如何被道教斋醮符咒吸收的论述仍停留在宏观把握的层面,并未细化。《道教法术》以道教法术这一专题为中心进行剖析,梳理了由巫术至方仙术再到早期道教法术形成的几个变迁阶段,进而探讨了道教法术对巫术观念和内容、巫术施法手段和方法的继承,以及两者的区别。此外,作者还对道法理论和巫术原理进行比较,指出道法理论与巫术原理有相似之处,但道法还取得了整个道教道炁论、宇宙论和形神观的支撑[9]。这种从理论层面理解道巫关系的观点颇为新颖。以上两位学者从道教的立场出发思考道巫关系,而张紫晨的《中国巫术》和高国藩的《中国巫术史》则是从巫术的角度出发阐释道巫关系。《中国巫术》提出道教与巫术是相互影响的[10],而《中国巫术史》更强调巫术对道教的影响,拟定了“道教巫术”的称谓[11]。这些著作虽谈及道教、巫术相互影响的观点,但都浅尝辄止,没有翔实的论证。
此外,还有研究者着眼于道巫的区域特色,如王丽英、阮荣华、赵芃和刘燕妮分别探究了岭南地区、荆楚地区、山东地区的道巫关系。王丽英在《道教法术与岭南巫俗初探》中,认为道教在岭南传播过程中,一些重要法术深受岭南民俗巫风的影响,道教法术中的三种具体形式——步罡踏斗、气禁、道啸分别源于岭南巫舞、禁咒、巫啸[12]。阮荣华《论荆楚之“巫”与道教——“荆楚文化与道家、道教研究”系列之二》指出该地的“巫”所崇尚的鬼神及擅长的巫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前者为道教的多神崇拜,包括张道陵所奉“太上老君”等楚地神祇,为各种世俗神的缔造提供了借鉴,而后者极大丰富了道教的阴阳道术[13]。赵芃、刘燕妮在《先秦时期山东地区的巫文化与山东道教的产生》中,提出山东是中国道教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该地区的巫文化催生了道教的产生[14]。与以上研究思路相似,刘仲宇在《中国道教文化透视》中,也指出道教是燕、齐、楚、蜀地域巫文化的产儿,但偏于区域间共性的叙述,疏于区域间差异性的阐释[15]。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巫关系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分化、整顿、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道巫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道巫的相依性、道巫的对立性、兼顾道巫的对立性和相依性。所谓“道巫的相依性”,指道教对巫术的吸收、影响和道教对巫的信仰对象、巫乐、巫觋的吸纳。“道巫的对立性”指道教与巫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兼顾道巫的对立性和相依性”指既辨析了道教对巫的吸收,又指明了道教对巫的排斥打击,既强调两者间的区别,又承认两者间的联系。
关于道教吸收巫术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将按照期刊著作发表出版时间先后一一缕析。1991年王育成在《武昌南齐刘觊地券刻符初释》中,解读了1956年武汉东郊何家湾发掘出土的地券刻符所蕴含的意义,指出从1991年之前已发表和见于著录的资料看,南齐刘觊地券刻符是我国华中地区首次发现的纪年明确、时间最早的道教刻符,对辨析道符对巫符的借鉴和改造大有裨益[16]。2001年唐长孺的《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也论述了道巫关系。他指出,孙恩起义失败后,天师道在上层信徒中发生了变化,本来各行其是的天师道逐渐与神仙道结合,陆修静和顾欢在这一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陆修静尊重神仙道而贬抑巫鬼道之意十分明显,但从此神仙道与巫鬼道合为一炉。这一演变表明汉代以来神仙家与民间巫术的结合[17]。唐长孺的看法颇具启发意义,神仙家是如何将神仙道与民间巫术糅合在一起?神仙道与民间巫术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联系?神仙家在思想上排斥民间巫术,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对待民间巫术呢?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证。2003年金霞在《魏晋时期的尚巫之风》中,提出魏晋时期的巫术出现了巫术民俗化、礼仪化和宗教化的趋势,巫术成为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术宗教化”指魏晋时期道教的兴起,继承和发展了很多巫术技法,如斋醮、咒语、符咒等。至于各种作法、厌胜的工具如镜、印、剑等的使用,也发源于巫术[18]。2005年,胥洪泉《道教的法术——啸》追溯了魏晋时期道教常常使用的一种法术——啸的渊源,指出该法术是道教对巫术的直接借用[19]。以上研究者着重探讨了道教对巫术的吸收,而没有阐述道教对巫术产生的影响。2012年李世武的《从神仙信仰看道教对工匠建房巫术的影响》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作者指出,一方面道教神仙直接或间接地对工匠建房巫术系统的形成产生增益作用,另一方面在道教的影响下,建房工匠鲁班最终演变为道教散仙,并成为建房巫术仪式中祭祀的主神。这体现了道教的民间化、世俗化倾向和巫术、道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20]。
道教对巫的信仰对象、巫觋、巫乐的吸纳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魏晋神仙道教》《道乐通论》《道教音乐》等。胡孚琛在《魏晋神仙道教》中,以早期道教在魏晋时期分化为下层民间道教和上层神仙道教为大前提,围绕《抱朴子·内篇》,着重剖析了魏晋时期葛洪的神仙道教。在第一章,作者考察了魏晋前后巫祝的活动,社会上的淫祀和方士的活动,指出方士将巫祝的俗神信仰发展为神仙说,而巫祝、方士成为道士的主要来源[21]。蒲亨强的《道乐通论》提出早期民间道教音乐主要源于古代巫觋乐舞,但对整个道教音乐历史的发展影响甚微。至东晋南北朝时期,才形成了道乐传统模式[22]。史新民编著的《道教音乐》对道乐与巫乐关系的探讨更为深入,不仅梳理出了道乐的发展脉络,还分析了不同时期道教音乐受巫乐影响的程度。作者指出,东汉时期道教音乐直接承袭巴蜀巫祝歌舞,南北朝时期开始模仿、借鉴佛教音乐。道教斋醮科仪音乐经过改革、修订后,逐渐摆脱了巫教祭祀音乐的影响,东汉有“巫俗解奏之曲”“歌讴击鼓”音乐,两晋有“仙歌道曲”“步虚”音乐,南北朝有“直诵”“音诵”和“梵咏”,初步形成了道乐的声乐与乐器两大形式[23]。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巫关系第二类研究内容为道巫之间的差异和对抗。林富士在《试论六朝时期的道巫之别》中分别从信仰对象、仪式特征、通神方式三个方面比较六朝时期的道教与巫教,进而指出巫觋和道士的信仰是两种互有差异的宗教传统[24]371−386。孙长初在《六朝青瓷中的宗教信仰》中,通过对六朝青瓷造型和装饰题材的分析,揭示了六朝青瓷所隐含的史前原始宗教、巫术、道教和佛教信仰等四项内容,从侧面展现了这一时期巫术信仰与道教的不同之处[25]。《试论六朝时期的道巫之别》和《六朝青瓷中的宗教信仰》探讨的是道巫静态的差异,而羊华荣的《道教与巫教之争》、王承文的《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则论述了道巫动态的对抗。羊华荣将道巫之争分为东汉时期和东晋南北朝时期两个阶段,指出前阶段偏重于实力的较量,后阶段偏重于理论的论争[26]。王承文以东晋南朝之际在江南产生的天师道经典和古灵宝经为中心,阐述了道教对民间鬼神祭祀和巫术的激烈批判,认为这是道教从汉魏民间道团向上层化的教会道教发展的重要表现[27]。羊华荣与王承文在论述道教与巫教之争时,皆偏于道教对巫教单向性的批判,几乎没有论及巫教对道教的回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巫关系的第三类研究内容兼顾了道巫的对立性和相依性。林富士的《中国六朝时期(公元3―6世纪)江南地区的巫觋与巫觋文化》第六章阐释了巫觋的主要竞争者——道教对民间信仰(或巫俗)采取的策略:一方面把某些因素吸收、转化,整合部分无可替代或消灭的因素于其本身的系统中,另一方面则采取鄙视、拒斥和攻击的态度,企图完全取代巫觋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宗教角色和功能[28]。此外,林富士在《中国六朝时期的巫觋与医疗》中爬梳文献资料,以六朝巫觋疗病的23个事例,分析了巫觋与道士对疾病看法和疗病方法的异同,指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林富士还指出,道教在医疗上仍时时鼓动其信徒不可寻求巫者(甚至医者)的救助,并频频强调信奉道法、“悔过”“首过”和“善行”的重要性[29]。这一观点早在日本学者小林正美著述的《六朝道教史研究》中,便有所体现。
三、隋唐时期道巫关系及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
葛兆光的《道教与中国文化》第二编,着重论述唐宋文化的嬗变与道教的三种趋势,指出盛唐时期道教仍全数搜罗巫觋的信仰对象和巫术,道教中的巫觋成分一度膨胀,中唐至北宋时期,道教内部逐渐摒弃粗俗鄙陋的巫仪方术,理论建构向老庄归复,与禅宗融合[30]。葛兆光对唐宋时期道教发展趋势的见解,重于文化层面大而化之的叙述,而疏于详尽细化的考据论证。卢国龙、汪桂平的《道教科仪研究》上篇着眼于道教科仪的历史沿革。可贵的是,作者不仅描述了道教科仪的嬗变轨迹,而且通过重点梳理《道藏》,阐释了道教科仪是如何一步步规范的,指出道教科仪一方面因应民间礼俗而出现各种滋生蔓延,另一方面又对固有的巫俗信仰及活动进行规范化清整[31]。然而,作者没有清晰地界定巫俗的范畴,将道教科仪发展过程所清整的不合时宜的内容都划入了巫俗范畴。马新、贾艳红、李浩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中,论述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信仰的转型,认为作为民间信仰组成部分的巫术活动,在当时因道教科仪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直接取而用之,以提升自身在民众中的信服力[32]。但作者的研究视野在于整个民间信仰,并未聚焦于巫术进行详尽阐述。
道巫关系的研究主要牵扯两个核心点,即“道教范畴”和“巫范畴”。以上笔者重点评述了道教研究范畴中的道巫关系,其实道巫关系研究也存在于巫研究范畴。为了使道巫关系研究的历史坐标更为明晰,笔者以为有必要概述百年来学界在汉唐间巫术与巫者方面的研究进程。
中国巫术引起学者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开始活动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192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他们把巫术作为民俗现象进行调查,这成为近现代民俗学、历史学关注研究巫术的肇始。后来,知名历史学家如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等的研究,使得巫术问题进入近代中国民俗学、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但这一时期,巫术研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1931年至1937年,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的李安宅首次将英国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理论研究著作《金枝》(李安宅译书名为《交感巫术的心理学》)和《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翻译介绍到国内。随后,国内学者多以他们的巫术理论为依据,通过分析古文献资料,展现中国巫术的面貌。1940年,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便是采取这种方法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巫术的代表性成果。然而,全书着墨中心在汉代之前,极少涉及汉以后的巫术史。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如许地山、吕思勉采取文献史料考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开启了道巫关系研究的大门。总之,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古代巫术研究仍是一块未被全面开发的处女地。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术界受“左”的思潮影响,中国巫术研究被冷落了几十年,直到1980年以后才逐渐好转。中国巫术通史类、断代史类以及巫术理论类的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通史类的著作以高国藩的《中国巫术史》为代表。作者将巫术分为“交感巫术”“模仿巫术”“反抗巫术”“蛊道巫术”四类,按照朝代顺序,展现了原始时代至现代社会中国巫术的发展历程,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巫术通史[33]。汉唐间断代史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吴成国的《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等。作者主要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探寻了六朝时期巫术的存在状态及产生的影响,研究方法新颖,视野开阔[34]。其实,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较早关注六朝巫术。1948年,宫川尚志在《六朝宗教史》中便有所论述。相比之下,以汉代、隋唐时期的巫术为中心的专门性研究极其薄弱。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论述,主要有赵宏勃的《〈太平广记〉中的语言巫术及唐代民间信仰》、赵荣俊的《隋唐宋时代的巫术特征考察》等。在巫术理论研究方面,詹鄞鑫的《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和钟国发的《神圣的突破——从世界文明视野看儒道三元一体格局的由来》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汲取西方巫术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日后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巫术与巫者有天然的联系,但巫术与巫者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实体,前者指“术”,后者指“人”。一些学者着重研究巫术,还有一些学者则以巫者为中心展开论述。但整体而言,对汉唐间巫者开始进行系统研究的时间要晚于巫术,挖掘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及巫术研究。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着重探究了汉代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评估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分析了他们在各个领域及各种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勾勒出他们活动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35]。在此研究基础上,林富士在《中国六朝时期(公元3―6世纪)江南地区的巫觋与巫觋文化》,又探讨了江南地区六朝的巫者与巫觋信仰。1999年,文镛盛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在继承《汉代的巫者》的研究方法、体例的基础上,论述了秦汉时期巫觋的存在状态及其与道教、佛教的关系[36]。目前,笔者未发现研究隋唐时期巫觋研究的专著。期刊论文方面,赵宏勃的《隋代的民间信仰——以巫觋的活动为中心》《唐人小说所记载之巫觋及其求雨研究》、廖春水的《浅说我国古代巫觋及其影响》、王天玉的《巫术与性别政治——历史镜像中的女性巫术从业者》有所涉及。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几部著作,即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续考》、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朱越利的《道藏分类解题》、李零的《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这6部著作并非探究汉唐道巫关系问题的专著,但却是深入研究道巫关系的基础性史料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著。《道藏》是一部汇合一千多种书的大丛书,语言艰涩难懂,时代混杂,是道教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因此,一些研究者试图厘清这部丛书,为道教研究铺平道路。陈国符是《道藏》研究的开创者,他将重心放在与道教炼丹术有关的文献上,先后出版了《道藏源流考》和《道藏源流续考》。1991年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问世,葛兆光称其为“汉语世界最完整的道教文献提要目录”。《道藏提要》介绍了《道藏》每一部书的时代、作者、内容,并附有目录索引、道书撰人编者的简介等[37]。朱越利著述的《道藏分类解题》在很多方面匡正了《道藏提要》的缺失,当然其中也有不足之处。李零在《中国方术考》中,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古代的各种占卜和神秘法术,还有许多实用技术和科学思想,从而窥探古人怎样思考宇宙、生命等问题。李零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考证了“巫”字的释义、商代、两周时期、秦汉时期的“巫”,将各个时期的巫术归纳为16种。最后,作者提出“礼仪”和“方术”脱胎于“巫术”,但反过来又凌驾于“巫术”之上,限制压迫“巫术”。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梳理了原始巫术、礼仪和方术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划定在各自的归属体系中,为区分之后道教中的“术”与巫术奠定了基础。
四、当前道巫关系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20世纪以来汉唐道巫关系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道巫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仍需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内容不深入、不系统;研究视角多元,但每种视角之下的研究仍有很大挖掘和拓展空间;研究方法多样,但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互鉴。
第一,研究内容不深入、不系统。在纵深挖掘方面,大多数论著对道巫关系的研究属于“顺带性”探讨,专门剖析道巫关系的论著稀少。国内道教研究伊始,宗教史类著作已经涉及道巫关系问题,但一直停留在点出道教产生过程中汲取了巫术这一观点或对其进行较为笼统的阐述这一层次。“顺带性”地探讨不仅出现在宗教史类著作中,还潜藏于其他道教、巫术研究著作中,如《道教法术》《中国巫术史》《道教斋醮符咒仪式》等。整体观之,道巫关系研究偏于一概而论,而疏于具体剖析。在横向拓展方面,以笔者所见,至今国内还没有学者将道巫关系的研究时间拓展至汉唐间,仅有个别论文探究了东汉时期和六朝时期。这表明汉唐间道巫关系的研究呈现断裂状态,有待后来者进一步细致入微、纵深挖掘,打开视野,横向拓展,以实现研究纵横交织、敦实厚重。
第二,研究视角多元,但每种视角下的研究仍有很大拓展空间。总的来说,对道巫关系的研究视角为:道教对巫术的借鉴、吸收、利用及影响;道教对巫的信仰对象、巫乐、巫觋的吸纳;道教与巫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兼论道教对巫的吸收利用与道教对巫的排斥打击,分析道巫区别的同时探究二者的相通之处。相比之下,东汉、隋唐时期道巫关系的研究角度较窄,只包括道教对巫术、巫的信仰对象的借鉴、吸收、利用,未旁及其他。虽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巫关系的研究角度更为宽泛,但每个角度的研究深度仍不平衡。一般而言,从第一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者居多,其他则寥若晨星。
第三,研究方法多样,但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互鉴。研究者在论述道巫关系过程中采用的理论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大都被单一地运用。如考古学者大都采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很少兼采其他理论方法。若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博采众长、同时吸纳多种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或许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收获“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再者,《道藏》既是道教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道巫关系研究的基本史料,对于《道藏》这一重要文献资料,研究者并未细致挖掘,充分利用。
[1] 许地山.道教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J].文物,1981(3).
[3] 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4] 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J].考古学报,1991(1).
[5] 刘仲宇.道符溯源[J].道教研究,1994(1).
[6] 连劭名.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与古代的册祝[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6).
[7] 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 张泽洪.道教斋醮符咒仪式[M].成都:巴蜀书社,1999.
[9] 刘仲宇.道教法术[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10] 张紫晨.中国巫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11] 高国藩.中国巫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2] 王丽英.道教法术与岭南巫俗初探[J].宗教学研究,2005(2).
[13] 阮荣华.论荆楚之“巫”与道教——“荆楚文化与道家、道教研究”系列之二[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5).
[14] 赵芃,刘燕妮.先秦时期山东地区的巫文化与山东道教的产生[J].世界宗教研究,2012(2).
[15] 刘仲宇.中国道教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6] 王育成.武昌南齐刘觊地券刻符初释[J].江汉考古,1991(2).
[17]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18] 金霞.魏晋时期的尚巫之风[J].许昌学院学报,2003(6).
[19] 胥洪泉.道教的法术——啸[J].文史杂志,2005(5).
[20] 李世武.从神仙信仰看道教对工匠建房巫术的影响[J].宗教学研究,2012(2).
[21] 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2] 蒲亨强.道乐通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23] 史新民.道教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24] 林富士.试论六朝时期的道巫之别[C]//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台北:联经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
[25] 孙长初.六朝青瓷中的宗教信仰[J].东南文化,2004(1).
[26] 羊华荣.道教与巫教之争[J].宗教学研究,1985(1).
[27] 王承文.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2001(4).
[28] Fu-shih Lin.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3rd-6th Century) A. D. [D].Princeton University,1994.
[29] 林富士.中国六朝时期的巫觋与医疗[J].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9.
[30]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1] 卢国龙,汪桂平.道教科仪研究[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
[32] 马新,贾艳红,李浩.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3] 高国藩.中国巫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4] 吴成国.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
[35]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M].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
[36] [韩]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37] 任继愈.道藏提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刘小兵〕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Tao- Witch Relations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ince the 1900s
HAN Shu-xia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Since the 1900s, many scholars devoted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ao-Witch relationship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221BC-907AD)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the study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25AD-220), including the researches establish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aoism and witchcraft belief object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ir features; 2) the stud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AD220-589) including the analysis of the dependency and opposition of Tao and witch; 3) the study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D 589-907)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other relevant aspects of Tao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witch belief object, magic and Shamanism and Taoist influence on witchcraft activities. All these researches are now important documents. Of course, the research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the content is not systematic and in-depth,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not balanced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simple.
Taoism; witch; witchcraft; Han-Tang; review
B95
A
1006−5261(2014)05−0093−06
2014-04-01
韩书晓(1990―),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