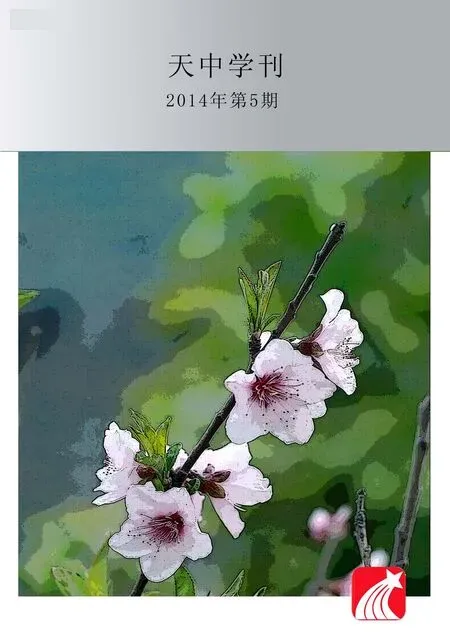论孙觉《春秋》学思想对胡瑗的继承与发展
崔广洲
论孙觉《春秋》学思想对胡瑗的继承与发展
崔广洲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胡瑗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其《春秋》学思想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影响巨大。孙觉作为其门人,同时也是北宋著名的《春秋》学学者。孙觉主要从尊王和伦理道德两个大的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胡瑗的《春秋》学。探讨二者之间的学术继承,有助于把握宋代《春秋》学的师承关系和整体脉络。
春秋;胡瑗;孙觉;尊王;道德伦理
《春秋》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早在中唐时期,啖助、赵匡和陆淳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和汉儒治经方法完全不同的路子,他们有关《春秋》的著作很多,从这些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们抛弃了以往汉学家研治《春秋》的思想和方法,另辟蹊径,开创了一条尊经贬传、尊王、疑经疑传、汇通三传、遍采群经和直训大意的新途径。北宋初期,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纷乱,致使儒学凋零,儒生政治地位下降的现象仍让士大夫心有余悸,他们对国家四分五裂,百姓流离失所所造成的灾祸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加之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的威胁,虽然北宋通过割地、纳币等一系列屈辱政策求得了暂时的相安无事,但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使北宋君臣如鲠在喉,建立相较于汉、唐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就显得更为迫切。《春秋》在满足宋儒的复杂的心理方面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对中唐啖助、赵匡、陆淳解释《春秋》的方法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宋代《春秋》学独有的特点。
胡瑗,北宋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学者称之为“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后胡瑗经范仲淹保举,以推官的身份在湖州授学。庆历年间,国家兴太学,胡瑗的教育方法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得以在太学推广。皇佑中,胡瑗又被提升为国子监直讲,为整个大宋王朝培养人才。从胡瑗游学者甚众,据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其门人有程颐、范纯祐、范纯仁、吕希哲、吕希纯、孙觉、钱公辅等。胡瑗研治儒家经典,尤擅《易学》。《四库全书》中有由其弟子倪天隐记录下来的胡瑗《周易口义》,可见其学问对整个北宋儒学影响甚大,为宋学先驱。据《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书籍记载,胡瑗的《春秋》学有相当造诣,著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春秋辨要》,今已亡佚。《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存胡瑗“春秋说”7条,可大致窥其《春秋》学思想。胡瑗门人孙觉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春秋》学者,著有《春秋经解》,其在《自序》中说:
《左氏》多说事迹,《公羊》亦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榖梁》最为精深,且以《榖梁》为本。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则以安定先生之解说之。[1]1
可见孙觉的《春秋》学思想深受胡瑗的影响。孙觉主要从尊王和伦理道德两个大的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胡瑗的《春秋》学。
一、尊王
《春秋》桓公元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条,《左传》详细地叙述了周王伐郑的过程,《公羊》则以“从王正也”肯定了整个事件的正义性,《穀梁》从“讳自伐郑”的角度解释了书三国“从王伐郑”原因,胡瑗则曰:
不书“王师败绩于郑”,王者无敌于天下。书“战”则王者可敌,书“败”则诸侯得御,故言“伐”而不言败。[2]27
《左传》记史事多数可信,按《左传》的记载,周王在这次公开的与诸侯交战中是打了败仗的,但是为何孔子在这里不书“王师败绩于郑”呢?胡瑗认为天王无敌于天下,书“败”则诸侯得御。其实此时的周王和普通的诸侯国无异,但是为何孔子在这里不书“战”呢?胡瑗还是从天王无敌的角度考虑,书“战”则王者可敌。胡瑗从书“战”、书“败”正反两个角度加以解释,最后归结到“尊王”这条大义上来。孙觉对此条的阐述就显得与其师胡瑗有些不同,他说:
盖天子者,至尊至贵,至高至大者也。四方有一弗率,则天子退讬不明,盖修德教,而方伯连帅,问罪专征。其义以谓天子至尊至贵,则不可敌;至高至大,则不可拟。有罪,则驱除之而已;为恶者,则灭绝之而已。焉得天子之尊,而下伐于诸侯乎?春秋之时,天王衰,令不能行于天下,诸侯人人自专征伐,有罪者不罚,而无罪者见侵,干戈妄动,盖无虚月也,虽天王之尊,亦亲伐于诸侯。圣人欲见上下之交失道也,则书之曰:“王伐郑”。夫以天王之尊,而诸侯不服,至帅诸侯以伐之,而蔡、卫、陈三国之君又不自行,而但遣微者,则天王之衰、诸侯之强,义可知矣。圣人恶天下之无王也,则变其文而书之,曰“从王”,以谓王者之尊,天下之民、天下之土皆所自有,一令之出,则天下莫敢不从焉,然诸侯有罪,天王不能号令方伯讨之,而至于亲行,三国从王,不自行而使微者,盖有罪矣。[1]69−70
孙觉把“尊王”思想更加强化了。“天子至尊至贵,则不可敌;至高至大,则不可拟”,也就是说天子无敌于天下。作为至尊至贵、至高至大的天子,是不应该自己亲自讨伐诸侯的,一诸侯有罪,他诸侯应该不待天子号令出而自觉替天子讨伐,为何孔子书“王伐郑”呢?孙觉认为“圣人欲见上下之交失道也”。孙觉从“罪臣”的角度强化“尊王”大义,认为一诸侯有罪,他诸侯应该主动讨伐之,但实际上只有蔡、卫、陈三个小诸侯国“从王伐郑”,且三国君主不自行,“而使微者”,三国是有罪的。
胡瑗在此条经文下还有解说,他说:“茅戎书‘败’者,王师非王亲兵致讨取败,而书之。”[2]27王师败绩于茅戎此事,见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与茅戎”条,胡瑗认为书“败”是因为不是周王亲自率兵讨伐,胡瑗这样解释虽然显得有些牵强,但是能更好地弥补前文解经之疏漏,“尊王”大义凛然。孙觉继承了胡瑗的“尊王”大义,但他在孔子于此为何书“败”的原因上,与胡瑗意见不一,他说:“天王之尊,天下莫之有敌,王师败绩于茅戎,非茅戎能败王师也,王师自败尔。”[1]301何为“王师自败尔”?孙觉此说比胡瑗显得更加牵强了,但是尊王的意味也更加浓厚:王师无敌于天下,茅戎是不能败王师的,这和是不是周天王亲自率兵已经无关了,不论率兵人的身份如何,只要是王师,天下就不能与之相敌。
《春秋》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条,《左传》于此无解说,《公羊》《穀梁》都认为此事应该褒奖王人救卫的行为。胡瑗则曰:
诸侯伐卫以纳朔,天子不先救,朔卒为诸侯所纳,天子威命尽矣。先师谓:犹愈乎不救。书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于此也。势既已去,焉能必胜哉![2]27
胡瑗认为天子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了,然而仍书“王人子突”,则是“王法尚行于此”,反映出他希望王道之兴的愿望,也是一种“尊王”的表现。孙觉在此条经说下则高谈阔论,洋洋洒洒五六百字,大谈“救”的义例和天王无褒亦无贬的原因。他说:
于是之时,周衰如此,而天王能征朔之不义,而助黔牟之当国,使子突者将兵救之,益善矣。然经不褒之,盖春秋之法,有褒则有贬,有善则有恶,褒一善所以使善者劝,贬一恶所以使恶者畏,无空言也。天王者,天下之至尊,而道德之所从出,其善者众,不可以一善褒,盖褒者有贬之辞也。天王可褒,则亦可贬矣,故春秋之义,天王无褒非无善也,其善者,一褒不足以该之也;天王无贬非无恶也,天王之位,非为恶者居之,虽有恶不加贬焉。所以责天王备而预为之嫌也。王人子突救卫,子突之善,非天王之善也……[1]353
孙觉认为天王是天下的至尊,道德标准由天王来制定,天王即使做了可褒奖之善事,也不能褒奖,反之,也不能贬斥。
尊王的另一个表现便是责臣。《春秋》庄公十二年“宋万出奔陈”条,《左传》曰“宋人皆醢之”[3]157,认为弑君之人宋万被宋人正法了,《公羊》曰:“一大夫也,亦书月者,使与大国君出奔同,明强御之甚是也。”[4]134《穀梁》曰:“宋久不讨贼,致令得奔,故谨而月之。”[5]141《公羊》与《穀梁》都把重点放在为何书“月”上,而胡瑗则曰:“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见讨贼可知也。”[2]27胡瑗明显是在责备臣子不能尽忠而讨贼,致令贼人出奔。孙觉在这方面完全赞同胡瑗的说法,他说:
宋万已弑其君,杀其大夫,其国之臣子,不即讨贼,使之出奔,则是其臣与子无恩于君父,而纵之使奔也。宋万之罪,已不容诛,书其“出奔”,所以深罪宋之臣子也……[1]147
此观点孙觉在《春秋解》多次表达过,如“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条,“宋人弑其君杵臼”条,“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条等,强烈谴责了臣不臣的现象。
以上反映了孙觉的“尊王”思想,与其师胡瑗是相一致的,只不过孙觉的“尊王”思想显得更加强烈。
二、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的一个表现即是突出妇道。《春秋》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妇觌,用币”条,《左传》曰:“非礼也。”[3]189《公羊》曰:“见用币,非礼也。”[4]154《穀梁》曰:“觌,见也。礼:大夫不见夫人。”[5]167三传都从“礼”的角度解释此条经文,胡瑗则说:
妇人,从夫者也。公亲迎于齐,妇人不从公而至,失妇道也。大夫宗妇者,同宗大夫之妇,非谓大夫宗妇也。觌者,见夫人也;用币者,为贽不过榛、栗、枣、佾。今妇人用男子之贽,庄公以夸多失礼也。[2]28
胡瑗显然对三传从“礼”的角度解释不满,且认为《穀梁》对大夫与妇人相见的解说是错误的。他重点指责哀姜不守妇道,孙觉此条赞同胡瑗的解说,他在此条经文下说:
大夫宗妇,则大夫之家宗妇尔……庄公欲侈大之,故令大夫之宗妇觌夫人者,用币为贽。币者,男子之贽,非妇人之事,妇人之执,榛、栗、枣、脩而已。圣人罪庄公娶仇人女而又侈之,至于失礼也,故特书曰:“大夫宗妇觌,用币。”所以见币非妇之贽用者,不宜用也……不正,失妇道也……[1]170
孙觉也认为《穀梁》对大夫与妇人相见的解说有误,他亦从恪守妇道的角度对此条经文做出解说,贬斥哀姜不守妇道的行为。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伯姬卒”条,《左传》曰:“妇义事也。”[3]1139《公羊》曰:“伯姬守礼,含悲极思之所生。”[4]501《穀梁》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传母不在,宵不下堂。’”[5]595三传对伯宋姬卒之事皆持褒奖之义。胡瑗对伯姬亦有褒奖:“伯姬乃妇人之中伯夷也。”[2]28胡瑗把伯姬比作“妇人之中伯夷”,可谓给予了很大的褒奖。孙觉亦采取褒奖的态度:
伯姬之行,盖妇人之伯夷也。方春秋之际,人伦大乱,而妇德扫地矣。伯姬立淫乱无礼之世,而为高洁难行之行,宁杀其身于火以死,不苟其生于有过之地。虽其身不幸于一时,而万世无礼不洁之人,小闻其风,则知所愧矣。孔子贤之,于纳币、致女、归媵、卒、葬,虽法所当略者,一切书之,所以乐道人之善,而使不洁之人惧也。[1]337
孙觉直接引用了胡瑗的解说,来突出伯姬的“妇道”。
伦理道德的另一个表现即是兄弟伦理,在这一层面上孙觉比其师显得更进一步,不仅倡导兄弟之道,并且从这种兄弟之道当中探寻出了尊王大义。《春秋》桓公十七年“蔡季自陈归于蔡”条,《左传》曰:“蔡人嘉之也。”[3]124《公羊》曰:“故贤而字之。”[4]98《穀梁》曰:“蔡季,蔡之贵者也。”[5]100三传皆认为蔡季贤者,应该嘉之,而胡瑗则从兄弟伦理层面上对书字做出了解释:
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季当立,“归”者,善辞也。时多弑夺,明季无恶。字者,诸侯之弟例书字。[2]27
春秋之时弑君夺权之事常有,而蔡季并没有想着为政权之争而归,所以嘉之,且胡瑗认为蔡季书字是春秋的例,“字者,诸侯之弟例书字”,从书字不书字上并不能看出春秋大义。孙觉首先考《史记·蔡世家》和《史记·诸侯年表》,驳斥了《左传》、何休和杜预认为弟季当立的说法,紧接着他说:
季之所以得字,著于《春秋》,当如《左氏》、何休之说。蔡季去其国以避如位,入其国以终其丧,一国之尊,社稷之重,则径去以逊于人。吾君之丧,吾兄之丧,则必归焉以服其服。然则为蔡季之行,亦足以取于孔子,而书字于《春秋》也。[1]101
孙觉显然也不同意其师胡瑗的“字者,诸侯之弟例书字”的理论,他赞同的是《公羊》的“故贤而字之”。另外,孙觉认为蔡季之所以归,不单单是为了恪守兄弟之道,为其兄奔丧,“则必归焉以服其服”,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既然孙觉不认为蔡季当立为蔡国的国君,那么蔡季就是臣子,臣子回国为其国君奔丧则再合情合理不过了,但是在春秋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弟不弟的年代,能做到这样也是应该褒奖的,于是“取于孔子,而书字于《春秋》也”。显然孙觉从其师胡瑗所提到的兄弟伦理中又探寻出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尊王大义。
以上,我们从尊王、伦理道德两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孙觉的《春秋》学对胡瑗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包含的尊王、责臣、妇道、兄弟伦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孙觉的《春秋》学的确在很多方面受到了胡瑗的影响,他们在尊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孙觉的尊王思想显得比其师胡瑗更加深厚;二人在道德伦理的评价上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孙觉更能把伦理道德上升到春秋大义的层面上来,显得比其师胡瑗更进一步。胡瑗作为宋学之先导,虽然他在《春秋》学上的学说并不是很多,但是其从《春秋》中探寻的“义”实开后世宋学的先河,其弟子孙觉继承了并发展了胡瑗的“春秋”之义,使宋代的《春秋》学在整个宋学之中异常闪耀。
[1] 孙觉.春秋经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 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承载.春秋穀梁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刘小兵〕
B244
A
1006−5261(2014)05−0090−03
2014-03-24
崔广洲(1988―),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