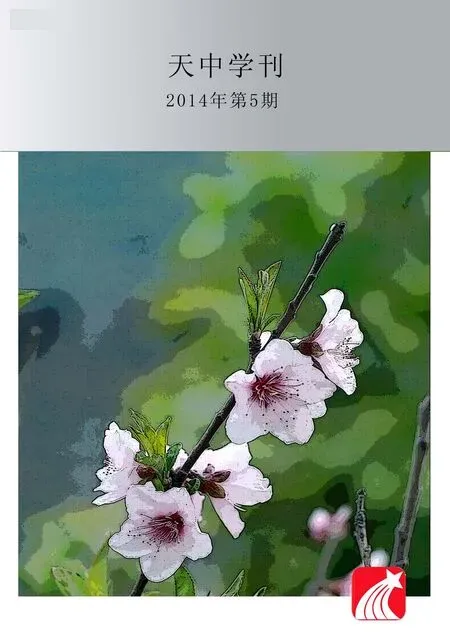论王国维《人间词》与《人间词话》
蒋亚男
论王国维《人间词》与《人间词话》
蒋亚男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词学方面拥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词学思想渗透在他的词学创作《人间词》及词学理论创作《人间词话》中。《人间词话》可以说是《人间词》实践创作经验的总结,它们共同见证了王国维在清末词学领域的成就。
王国维;《人间词》;《人间词话》
生于清朝末年的王国维深受时代影响,将资产阶级新思想及康德、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相互渗透并吸收,走出了清末常州词派“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的传统词学功利性追求道路,把握词体审美品格方面的认识,正视词的美感特征,最终以《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编织出清词的结篇。
一、“人间”之由来
王国维《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分别于1906和1908年刊行,“《人间词话》最初发表在《国粹学报》上,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到宣统元年(1909年),分三期(第四十七期、四十九期、五十期)登完,共六十四条”[1]11。从《人间词》与《人间词话》的刊登时间便可判断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人间词》是此阶段诗人心灵之思、情感之动的真实痕迹,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对《人间词》创作经验的总结和理性把握。《人间词》和《人间词话》正是王国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的精粹,两者是相互交融、相互关联的”[2]4。这两部作品名都包含“人间”二字,为何以“人间”为名?“人间”有何含义?
赵万里先生曾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陈鸿祥在《人间词话三考》中认为《人间词话》冠以“人间”之名“不仅承袭了他填词而来的一个名称;实际上也是他此时哲学、文学思想之直接的反映和表现”,是“表现‘人生之问题’的直接尝试”。近年,日本学者木夏一雄从《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跋语中考证出“人间”乃是王国维的号,得到了学者普遍认可。此说法后又遭质疑,学者考证出王国维以“人间”为号最早也应在1908年,而这之前《人间词》《人间词话》已完成。由此可见“《人间词》不是‘人间’先生所写之词,而是写‘人间’之词”、“《人间词话》不是‘人间’先生之‘词话’,可能是‘人间词’之话,或者‘话’‘人间词’,更可能是关于‘人间’的词话,与历代诗话词话如《沧浪诗话》、《白雨斋词话》等一样用作者之号、书斋名等来命名不同”[3]。据统计,《人间词甲稿》61首词有22首含“人间”句,《人间词乙稿》43首词有14首含“人间”句,所以笔者认为赵万里“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的结论最为直接。
“人间”有何含义?严迪昌所著《清词史》提到王国维的词“以抒述‘人间苦’为多”,并列举23例“人间”句,认为这些“充分集中地表现出王国维词贯串始终的那种‘一生难得是春间’(《浣溪沙》)、‘侧身望,天地窄’(《贺新郎》)的厌世消沉的心绪,其名为《人间词》之意似也可探知及了”[4]560。黄霖、周兴陆在《王国维〈人间词话〉导读》中写道:“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人间’、‘人生’。‘人间’、‘人生’作为诗人体验思索的对象进入诗人的视野。王国维将他的词集称为‘人间词’,将他的词话称为‘人间词话’,其中似乎暗含着一种人生扣问的哲学况味。”[2]5学者李庆认为王国维受日语影响,指出“‘人间’这个由汉字组成的词,在日语中比在汉语中包含更多的表示个人、个体以及个性这样的含义”[5],并通过考证指出受日语影响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严迪昌、李庆等人的见解都有可取之处,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对“人间”进行的思考。
二、《人间词》开阔的意境
王国维的《人间词》可以说是对《人间词话》理论的实践,他对自己的词很自负,在托名为樊志厚的《人间词甲稿序》中说:“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而他的词也确实造诣很深,为其词学理论《人间词话》提供许多实践经验,例如《人间词话》关于境界论的阐述在《人间词》中就得到很好的表现。《人间词》很注意意境方面的塑造,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写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人间词甲稿》与《人间词乙稿》共104首词,题材广泛,感情基调复杂,意境深远。在题材方面,《人间词》既有咏物词、思妇词,又有悼亡词、伤春词、记梦词,还有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词。王氏最引以为豪的三篇分别是《甲稿》中《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及《乙稿》中《蝶恋花》之“百尺朱楼”,《乙稿序》中曾夸口这几阙词“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浣溪沙》之“天末同云”叙述了一只孤雁于阴冷的环境中被人射落,继而被烹煮的悲惨故事,由小见大,揭示了弱肉强食的客观现实。《蝶恋花》之“昨夜梦中”是一首记梦词,记述了词人在梦中与情人一见钟情,醒来后发现不过是美梦一场,其惆怅之情溢于言表。在这里,词人对人间真情的渴求通过一小梦得以抒发。《蝶恋花》之“百尺楼头”是一首游子思妇词,楼外大道车来车往,车轮隆隆作响,楼头思妇望穿秋水却始终等不到远行的游子归来,双方只能“都向尘中老”,读来感人至深,这首词同样以小见大,由“一霎”的相思、期盼,衍生出一生的相见无望,由一人之遭遇衍生出人世众生之宿命,意境渐趋宏大开阔。除了这三首,其他的“人间词”,无论是咏梅、咏柳、咏春、伤春,其境界开阔深远,词人以一己之遭遇引发对人世的悲悯或深思,包含了无尽的哲理。例如《水龙吟》咏杨花进而引出思妇“日长无绪,回廊小立”的“迷离情思”,但整首词却并不局限于某一思妇,而是上升、拓展到整个“人间哀乐”,写的是人间的“离人泪”,意境得到升华。
再看《人间词》的感情基调,整个《人间词》弥漫着忧伤的气息,究其原因,“‘苦情’人生观的形成既与他对家族多灾难、时代多变故和个性多矛盾的生命体验有关,又与叔本华悲观人生哲学的影响息息相关”[6]。王国维4岁时母亲凌氏去世,1906年7月父亲去世,1907年夏妻子莫氏病逝,1908年继母叶氏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必然影响到他的词学创作。“悼亡词”作为《人间词》中最直接表达词人痛苦之情的作品,催人泪下,如《蝶恋花》之“落日千山”,上阙回顾妻子莫氏病榻上“无多语”的光景,下阙纵观今生来世,发出“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的绝望呼声,各种无奈、伤感、悲伤、绝望交杂其中。除了悼亡词,他的咏物词也有典型的伤感之作,如《摸鱼儿》之“问断肠”,借秋柳萧条之景抒发离愁别绪,由伤秋之情上升至对整个人世的悲悯,“金城路,多少人间行役”,又一次在词中嵌入“人间”二字,感时伤世之情自然流露出来。当然,《人间词》的感情是复杂、矛盾的,虽然悲伤之情溢于其中,其呈现欢快之情的作品仍很醒目,如《蝶恋花》之“谁道人间秋已尽”“衰柳毵毵,尚弄鹅黄影”“潋滟金波”等流露出词人秋日闲暇之余享受生活的雅致。这也是多数学者所说的王国维性格的矛盾之处,然而不可否认,正是这些复杂的情绪开阔了他的词境。
三、《人间词话》对《人间词》意境的实践及升华
王国维托名樊志厚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可见,王氏颇为看重意境的塑造。这里所谓的意境与他在别处所说的境界实为同义语,“境界”是他创造的一个专用理论术语。他的词学理论《人间词话》便是《人间词》创作经验的总结。《人间词话》第一则提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论成了《人间词话》最重要的词论之一。对此,王氏提出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境界有大小以及三种境界的说法。
王国维认为造境与写境实为“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随之又认为二者实难区分,指出造境必须合乎自然,写境必须“邻于理想”,二者有相通之处,因为理想缘于现实,脱离实际的理想是不合理的。但同时他又认为二者是有差别的,写境更偏重于客观上的描述,而造境更需要融入想象成分,带有理想色彩。正因为“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所以作品的理想境界应是融造境和写境于一体,正如《人间词》之“谁道人间秋已尽”中既有写境也有造境,其中“衰柳”“落日”“疏林”“青松”等自然意象便是写实,属于写境,“衰柳”“尚弄鹅黄影”“落日疏林”“光炯炯”以及词末“何处江南无此景,只愁没个闲人领”便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抒发了词人面对此秋景无限闲暇快意之感,这便是造境。
王氏在《人间词话》中认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比较而言,王氏更推崇无我之境,认为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但其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说历来为学人所诟病,多数学者认为真正的无我之境是不存在的,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纯纪实的语句不具备优美性,并抨击王氏所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这句诗仍可看出陶渊明隐居南山的悠闲自得,并不是完全的“无我”。笔者认为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说,表达的应该是含蓄与直露的问题。有的词表现情感比较直接,如王氏看作是有我之境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明显带有伤春之感,而有的词比较含蓄,需要读者敏锐的体悟,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闲暇自得的字眼出现,但仍可揣摩出诗人的心境,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王国维的词也以有我之境为多,前面提到的他自己最欣赏的三首“人间词”也是处处可见有我之境,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词中写到“云”“天”“孤雁”等意象,却并不是完全是客观写境,“寥落”一词的出现正透露出本首词的感情基调,带上了主观感情色彩,明显的是有我之境。
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有小,但词的优劣并不以境界的大小来区分,认为杜甫《水槛遣心》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境界并不比《后出塞》中“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弱,在王国维看来,后一句诗虽然写的是出塞的大场景,但前一句诗的意境也是很好的。虽如此说,但王氏对于大境界还是尤为赞赏的,他说“太白纯以气象胜”,并以李白《忆秦娥》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为例,夸赞其“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他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说明他推崇的还是大境界、大气象,其《人间词》中“人间”二字屡屡出现,不断将词境扩大到人间层面也因如此。这样看来王氏的词学观点是不是自我矛盾呢?其实他所谓不以词意境大小划分优劣,还应该结合后面几则词话来看,如第十五则“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可见,境界优劣不止看的是境界大小,还得看词有没有很深的“感慨”。这样一来,他所举杜甫的境界大小不同的两句诗却优劣相当就合情合理了,因为杜甫《水槛遣心》和《后出塞》一样都有着诗人颇深的感慨。
《人间词话》第二十六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王国维划分的这三种境界,也是艺术境界形成过程中必经的三个阶段。在意境形成的初始阶段,“诗人运用艺术的联想与想象,上下求索,追求意与境的交融,好比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当意境初步形成以后,继续挖掘开辟,熔铸锻炼,这是构思过程中最艰苦的一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恰好形容此中的苦况。当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达到一定程度,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便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此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按:此句《人间词话》作‘回头蓦然’,系王氏笔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二字恰好说明意境的完成是不期然而然的一次飞跃。”[7]415
综上所述,王国维博览群书,广泛汲取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文学功底深厚。他自幼丧母,30岁以后亲人陆续离世,《人间词》见证了他悲观的人生态度。《人间词话》是对《人间词》创作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其境界论或许还不够成熟,仍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但我们不可否认其境界论的成就,尤其不能否认其关于“造境”“写境”等说法的新颖别致。王国维的词学理论远不止境界论这一方面,他还有许多别的见解,如“隔”与“不隔”等观点。当代学者应该辩证地对待王氏词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也是我们对待一切前人作品应有的态度。
[1] 王国维.谁道人间秋已尽·人间词·人间词话: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 李晓华.转型期文论经典《人间词话》的写作——《人间词》、《人间词》甲乙稿序与《人间词话》[J].电影评介,2006(13).
[4] 严迪昌.清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 李庆.《人间词话》的“人间考”[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
[6] 李春芳.从《人间词》看王国维“苦情”人生哲学[J].名作欣赏,2009(17).
[7] 丁放.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杨宁〕
I206.5
A
1006−5261(2014)05−0052−03
2014-02-19
蒋亚男(1989―),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