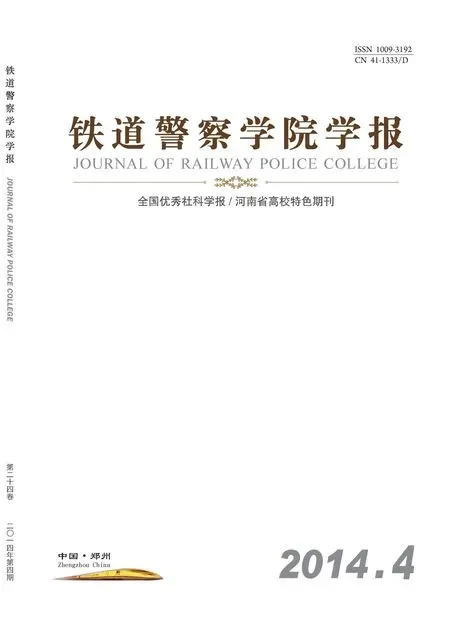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改造
随庆军
(河南警察学院 法律系,河南 郑州450002)
一、毒品犯罪不应当配置死刑条款
(一)配置死刑条款不符合我国的死刑政策
“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19字方针,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1979年刑法对这一死刑政策贯彻是比较好的,总共设置了28个死刑罪名。死刑罪名仅仅涉及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贪污罪,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外,多是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但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不断恶化,我国逐渐出现了重刑化的倾向。其一,在刑事立法上,死刑罪名不断增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了一些罪名的法定刑,把原来法定最高刑不是死刑的提高到死刑,如故意伤害、盗窃、流氓罪等;二是增设了一些罪名,法定最高刑直接规定为死刑,如传授犯罪方法罪。截止到1997年刑法修订前,死刑罪名高达71个。其二,在司法上,量刑普遍加重,具体案件中实际判处的死刑数量也在逐步攀升,很多罪行没有达到“极其严重”程度的犯罪分子也被顶格判处了死刑,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实际执行的死刑数量大幅度提高。1997年刑法虽然试图对死刑条款在立法上进行限制,但雷声大雨点小,仍有47项条文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此后的15年,我国的死刑罪名相对比较稳定,既没增加也没减少。2011年5月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标志着我国的死刑制度在经历了膨胀式的发展之后,正逐步向我国死刑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55个死刑罪名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的紧缩的死刑政策而言,数量仍然过多,仍需进一步压缩。
(二)配置死刑条款达不到刑罚目的
关于刑罚的目的,存在不同的观点。比较中西学者对于刑罚目的的论述,本文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对犯罪分子施以报应和预防犯罪,并由此来维护和恢复社会关系。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刑罚的目的不应是一元的,而应该是二元的,这就是报应与预防的辩证统一。”[1]因为“犯罪具有双重属性:作为已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未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再犯可能与初犯可能相统一的人身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这就是犯罪本质的二元论。立足于此,刑罚的功能应当是具有相应的二元性: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从刑罚功能推论出刑罚目的,当然也具有二元性:惩罚之功能表现为报应,教育之功能表现为预防”[2]。但是,对毒品犯罪的死刑而言,过量的刑罚夸大了对犯罪的报应,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貌似严厉的教育难敌暴利的诱惑,无法改变贪财图利犯罪唯利是图的本性。毕竟,毒品犯罪属于典型的非暴力犯罪,犯罪行为本身也不会造成直接的严重后果,以死刑作为报应有失罪刑均衡。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4]毒品犯罪也是一样,只要不消除毒品犯罪存在的条件,单靠死刑的威慑,是难以遏制毒品犯罪的。
据统计,破获的毒品违法犯罪案件数量,1991年至1998年增长20.7倍,平均年增长率达55.2%,而在2005年至2011年的7年间,我国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增长1.2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7.7%;抓获的毒品(违法)犯罪人数,1991年至1998年间增长11.5倍,平均年增长率近43.4%,而2005年至2011年间,被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数量增长0.94倍,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3.4%[5]。上述统计数据表明,自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率大幅下降,非但没有导致毒品犯罪的急剧泛滥,而且毒品犯罪的平均年增长率反呈下降趋势。因此,死刑对毒品犯罪的遏制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取消毒品犯罪的死刑,不会对毒品犯罪的发生率产生显著影响。
事实上,1979年刑法规定毒品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1987年《海关法》规定走私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也只有10年有期徒刑。只是到了1982年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1988年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才分别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和走私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至死刑。而出现在1991年至1998年间的毒品犯罪高峰,恰恰是出现在毒品犯罪法定最高刑上升为死刑以后,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配置死刑条款不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条件
毒品犯罪不仅危及吸毒者的身心健康,危害吸毒者的家庭,而且还诱发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的威胁,甚至导致社会的颓废。但不可否认,毒品犯罪属于典型的非暴力犯罪,没有直接的受害人,而且其行为本身不会直接引发严重后果,与侵害生命的严重暴力犯罪相比,还没有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况且,对毒品犯罪规定死刑,也不符合我国1998年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的规定。因为对其中“最严重的罪行”的含义,国际社会已形成如下共识:一是应尽可能以最受限制、最例外之方式来解释所谓“最严重的罪行”,二是死刑只应适用于故意且造成致命或极其严重后果的案件,三是国家立法上应当废除对经济犯罪、非暴力犯罪或无被害人犯罪之死刑[6]。据此理解,毒品犯罪显然属于国际公约中“最严重的罪行”之外的犯罪,配置死刑条款,不仅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条件不符,导致了总则与分则在死刑规定上的脱节,而且也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背离,与国际上废除死刑的潮流背道而驰。
二、某些毒品犯罪选择性罪名设置不合理
(一)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设置成选择性罪名不合理
我国刑法把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一起,设置于同一条文并具有完全相同的法定刑与量刑标准。在立法者看来,运输毒品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唯有如此才会对这四种行为作出等量齐观的法律评价。但运输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其他三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非完全相当。在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的行为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况:(1)行为人将自己走私、贩卖、制造的毒品予以运输;(2)行为人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接受他人委托、雇佣或者被胁迫帮助他人运输;(3)行为人被人利用,不知是毒品而运输的。对于第一种情况,运输毒品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牵连行为,对其作出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相同的法律评价,设置相同的法定刑,具有合理性,符合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只是在罪名上将其并列起来,没有加重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处罚。对于第三种情况,由于行为人欠缺主观罪过而不构成犯罪。但在第二种情况中,行为人帮助或被胁迫运输毒品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性显然比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小得多,将其与后三者并列于同一条文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将导致罪刑失衡和司法不公。
(二)欺骗他人吸毒罪与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设置成选择性罪名不合理
所谓欺骗他人吸毒,是指故意虚构事实,隐瞒毒品的真相或制造假相,使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例如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毒品掺入食品、饮料中提供给他人食用。引诱、教唆他人吸毒,则是指在他人无吸食、注射毒品意愿的情况下,通过向他人渲染吸毒的感受,传授吸毒的方法、技巧,以及利用金钱、物质等方法进行诱惑,使他人产生吸毒意愿或欲望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欺骗他人吸毒与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的最大区别是由此造成的吸毒行为是否体现了吸毒者的意愿。在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的情况下,没有强迫,没有欺骗,被引诱、教唆的对象是否吸食、注射毒品,还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自由。他既可以选择吸,也可以选择不吸,体现了一种主动的选择。若其选择了吸食、注射毒品,导致最终陷入毒魔不可自拔,除了引诱、教唆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吸食者或其监护人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负一定的责任。而在欺骗他人吸毒行为中,被欺骗者对吸食、注射毒品是不知情的,被欺骗者吸食、注射毒品体现的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事先知道事情真相,就很有可能拒绝吸毒。因此,欺骗他人吸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比引诱、教唆他人吸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将三种行为规定成一个选择性罪名,规定相同的法定刑,也是有欠妥当的。
三、某些毒品犯罪法定刑配置失衡
(一)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窝藏毒品罪法定刑失衡
从法律规定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窝藏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两罪在法定刑配置上是失衡的。因为“窝藏”是一种特殊的“持有”,与一般地持有毒品罪相比,其不仅是明知毒品而持有,还多了明知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毒品而予以藏匿,试图使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或法律严惩的犯罪意图。显然,窝藏毒品罪是比非法持有毒品罪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但由于法定刑配置上的失衡,使得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窝藏毒品罪罪刑轻重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以下法律上的困惑。
1.当行为人持有毒品时,司法机关若没有证据证明其持有的毒品是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毒品,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是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窝藏的毒品,按照法律规定就要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导致了一种不合理的法律后果:一行为如果无法证实其构成一种轻罪(窝藏毒品罪),就将其归于一种重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是否有悖于“疑罪从无”原则呢?
2.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窝藏毒品罪是指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的行为。如果司法实践中窝藏毒品仅限于法律规定的上述情形,此种规定并无不妥。但在现实中,行为人不仅可能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窝藏毒品,还可能为非法持有毒品的犯罪分子窝藏毒品。如某吸毒者拥有达到刑法规定数量的毒品,为了逃避刑事追究而将毒品委托朋友保存,该朋友便将毒品藏匿家中,该朋友应如何担责?由于刑法未将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的行为规定为窝藏毒品罪,司法实践中对此只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责任。这样就出现了问题: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的构成处罚较轻的窝藏毒品罪;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的,则构成处罚较重的非法持有毒品罪。毫无疑问,前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大于后种行为的,这样就会造成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行为处以轻刑,而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则处以重刑的不公正现象。
(二)运输毒品罪和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法定刑相对过高
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的行为人往往是一些社会底层贫困人员,为生活所迫受人利用铤而走险。如被告人唐某为赚取1000元钱,帮助毒贩杜某携带420克海洛因从昆明坐火车前往上海,在列车上被抓获,上海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347条运输毒品达到数量大的要求,依法判处被告人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才改判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7]。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本案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类似的案件主观恶性不大,对他们适用死刑,既达不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也震慑不了幕后操纵的毒枭毒贩。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其区别对待合情合理,于法有据。当然,本案中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并非不符合法律规定,主要是刑法将运输毒品罪的法定刑规定过高,从而导致了运输毒品罪罪刑的失衡,单靠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治标不治本,应将运输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降至无期徒刑。
如前所述,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与欺骗他人吸毒罪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造成的吸毒行为体现了吸毒者的意愿,是吸毒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后者造成的吸毒行为则排除了吸毒者的意愿,是吸毒者不得不接受的结果。两者虽然可能造成同样的危害结果,但由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使得两者的社会危害性存在差异。在吸毒行为尚不为罪的情况下,将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与欺骗他人吸毒罪规定相同的法定刑,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导致了罪刑的失衡。应减轻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或适当增加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将其与强迫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相持平,以求罪责刑的一致性。
四、建议增加吸食毒品罪
吸毒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损害吸毒者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及生命,而且会引起犯罪率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多国家(或地区)对吸毒行为作了犯罪化的处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我国2008年《禁毒法》第62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并且针对吸毒者的不同情况规定了相应措施:“对吸毒成瘾人员,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同时通知吸毒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的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戒毒的期限为3年。”“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一)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二)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三)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吸毒行为完全纳入了行政处罚的范畴。本文认为,无论从吸毒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还是从刑法目的的实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等方面考量,都应当将吸毒行为纳入刑法规制。
(一)吸食毒品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由社会危害性的抽象性和隐含性所决定,其危害程度并不太容易被证明,因此,是否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通常是立法者综合考量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吸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因为吸食毒品不仅直接损害吸毒者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给吸毒者的家庭带来灾难,还极易引发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加剧社会治安恶化。其一,吸毒行为是其他一切毒品犯罪的根源。我国刑法规定了12种毒品犯罪,暂且称为吸毒的上游犯罪,都是围绕吸毒展开的。正是有了毒品消费的市场需求,才激发了其他的毒品犯罪,并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严厉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其他的毒品犯罪,而对吸毒行为网开一面的话,可以说治标不治本,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把贩毒和吸毒两手抓,并且两手都要硬,才会取得好的效果。其二,由于毒品价格昂贵,并具有上瘾性和耐药性的特征,吸毒者为了达到最初的吸食效果,就要不断加大毒品的使用量。当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消耗殆尽以后,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进行贩毒、卖淫、抢劫、杀人、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由此可见,吸毒行为不仅为其他毒品犯罪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也必然导致卖淫、抢劫、杀人、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可见,吸食毒品并不是吸毒者个人的事,该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社会秩序,达到了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用刑罚的手段予以禁止。
(二)吸食毒品入罪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由于吸毒违法而不犯罪,对吸毒者只能给予行政处罚,特别是劳动教养废除以后,即使吸食毒品被抓,大不了关几天,接受轻微的行政处罚,容易导致吸毒人员无视法律的规定,不利于对吸毒行为的自我控制。尽管许多吸毒成瘾者被送进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但由于时间不长,心瘾难除,不少人从戒毒所出去不久后难以以坚强的意志抗拒毒品的诱惑,很快又走上复吸的道路。如此形成吸了戒、戒了吸的恶性循环。从犯罪特殊预防的角度看,如果对吸毒者处以刑罚,较长时间与社会隔离,不仅可以让吸毒者充分体会失去自由的痛苦,也可以消除复吸的环境,使戒毒取得较好的效果,有利于彻底戒掉毒瘾。从犯罪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将吸毒行为入罪,会对没有尝试过毒品的人产生震慑,对社会上意志薄弱的人起到警戒和预防作用。通过两方面的结合,就可以将吸毒行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防止毒品犯罪的泛滥和由吸毒引起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吸食毒品入罪体现了法的公平正义
在吸毒行为尚未入罪的情况下,我国刑法将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首先,我国《刑法》第354条明确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事实上,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只是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有利条件的行为,至多属于帮助行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其从属于吸毒行为,并通过吸毒行为表现出来。怎么会出现帮助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的人构成犯罪,而行为人却不构成犯罪这种非正常的情况呢?正如窝藏、包庇罪中被窝藏、包庇的人一定是构成犯罪的人一样,容留性犯罪的成立必须是以被容留的行为人实施的是犯罪行为为前提,否则容留性行为也就丧失了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
其次,我国《刑法》第348条规定,非法持有鸦片1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可见,非法持有毒品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可谓是重罪。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成立条件却值得研究,它是在排除其他毒品犯罪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的犯罪:该行为如果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前提或结果,就不再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而应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承担刑事责任;该行为如果是为了帮助毒品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也不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而应以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承担刑事责任。所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成立空间其实非常小,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合法取得后的非法持有,如捡到数量较大的毒品该上交而没有上交;二是为了吸毒而购买毒品后的持有。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逃避打击,许多吸毒者包括以贩养吸者,往往采取多次少量买卖,即多次进货,而每次进货量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为10克以下来逃避法律的严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发现查获,如果只承认供自己吸食,公安机关就只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而不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存在空间就进一步压缩,只剩下合法取得后的非法持有,从而使得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存在失却了应有的意义。
另外,刑法典既然将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规定为犯罪,甚至将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规定为犯罪,那么对社会危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非法制造制毒物品行为却未规定为犯罪,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遗憾。
总之,毒品犯罪的产生、泛滥、危害,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吸毒展开的,吸食毒品是一切毒品犯罪的根源。如果不将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无疑相当于“杀了卖刀的,放了杀人的”,不仅会失去法律规范内部的协调统一,有悖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使法律失去其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
[1][2]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36,437.
[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29.
[4][英]托马斯·约瑟夫·登宁.工联和罢工[M].1860(伦敦版):35-36.
[5]何荣功.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8.
[6]Rick Lines,The death penalty for drug offences: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The International Harm Reduction Association, London,2007,p.18.
[7]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第 2辑)[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