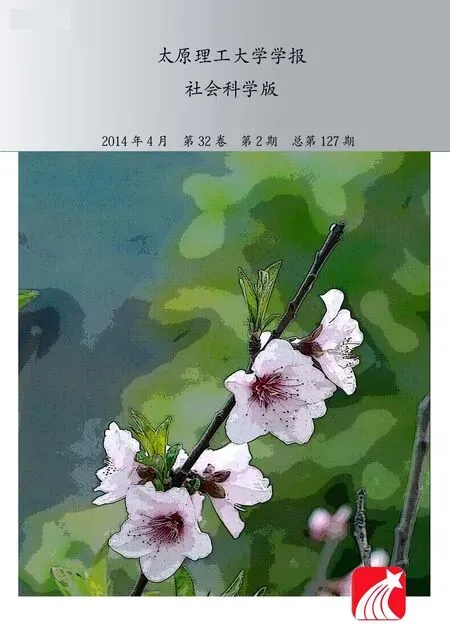* 激活宋代志怪小说的三大因素
袁文春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思政与通识教育部,广东 广州 510970)
基于现代小说观念上的偏见,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宋代志怪小说是“贫乏”的。若能真正对古人“了解之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宋代志怪小说其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宋代志怪小说的兴盛迹象
宋代志怪小说首先在作品数量上表现出了其兴盛迹象。笔者通过对李剑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所收录的志怪小说作品进行统计对比,发现宋代志怪小说作品一百零八种,唐代志怪小说作品七十种左右,再加五代二十多种,总数有九十多种,先唐时期的志怪小说作品四十三种。由于所据文献由李剑国先生搜集编著,统计标准是比较客观的。若从作品卷帙方面比较,则宋代志怪小说的优势更突出,仅洪迈《夷坚志》皇皇四百二十卷之巨,就已经逼近整个唐代志怪小说数量。洪迈对这种成就也颇为得意:“予毕《夷坚》十志,又支而广之,通三百篇,不能满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1]
此外,在宋代志怪小说编撰者(为方便叙述,下文皆称作者)特点方面,其作者基本来自上层社会,甚至是帝王,如《列异传》作者魏文帝曹丕。《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云:“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又如《金楼子》作者是南朝梁元帝,此书乃是他还是湘东王时所撰。其他如张华、干宝、曹毗、祖台之、王嘉、刘义庆、祖冲之、陶弘景、任昉、殷芸等人皆为朝中官宦。一些宗教身份的作者,如郭璞、葛洪等人,也都有做官的经历。唐代志怪小说作者则多数为科场得意者,如《冥报拾遗》作者郎余令、《梦书》作者庐重玄、《洽闻记》作者郑常、《龙城录》作者柳宗元、《广异记》作者戴孚、《妖录》作者牛僧孺、《乾巽子》作者温庭筠、《宣室志》作者张读、《杜阳杂编》作者苏鹗、《剧谈灵》作者康軿等人,皆科举而仕者。一些作者即使没在科场顺达,却或以荫入官,或由幕僚入仕,总之来自下层的文人甚少。而宋代志怪小说作者则显得成分复杂:有朝廷大臣,如文彦博、陈彭年、曹勋、洪迈等,《宋史》有其本传;有下层官吏,如金翊、马纯、王明清、李泳、刘名世、王辅等;有科场失意者,如聂田、吕南公、武允蹈、鲁应龙等;有江湖俗士,如刘斧、李献民、皇都风月主人等;有佛道中人,如景焕、黄休复、勾台符、归虚子、梁嗣真、僧惠汾、王日休、蒋宝者亦厕身其间;名氏身份无考者更难以胜数。
宋代志怪小说作者成分复杂性与作者阶层整体下移密切相关,从《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北宋与南宋作者的统计情况看,北宋作者多当朝大臣,南宋则多地方小官;北宋多科考得志之士,南宋作者则多不入场屋之人。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其实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据笔者的统计,竟有五百多位志怪小说作者或爱好者参与《夷坚志》成书,其中大部分都是下层民众,《夷坚丁志序》记述:“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1]。此外,大量无名氏志怪作品的存在也是宋代志怪小说作者身份层次下移趋势的佐证。宋代志怪小说题材内容也随着作者身份整体下移出现世俗化倾向。《夷坚志》中不少内容便直接记录了当时的市场生活情形。据统计,《夷坚志》反映宋代城乡各阶层人们经济活动的条目近全书内容的30%,这些记录大多出自于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雇工、穷酸士人、乞丐、巫师、娼妓等,这是前代志怪小说中很少出现的。
总之,无论从作品种类、卷帙数量、作者身份或志怪故事条目来源看,都表明了宋代志怪小说的蓬勃生机。李剑国先生在文学价值上虽不看好宋代志怪小说实绩,却很客观地肯定其优势:“平心而论,如果从数量上说,宋人志怪传奇不算少,现存和可考的多达二百余种,与唐人旗鼓相当(不包括五代的二十多种),一点也不落后;而且因有四百二十卷的超级小说集《夷坚志》的存在——全书故事多达五六千个,现存仍有二千八百多个,因而从简(条)数上说更是超过唐人。数量上的繁盛是因为小说在宋代文人中有着极好的生长土壤,喜欢读小说的人多”[2]。
二、宋代志怪小说的“源头活水”
宋代处于儒学复兴、理性昌明时期,对于鬼神的怀疑比前代强烈,所以,以鬼神为主体的志怪小说在此时期更难有生机,可事实却正好相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笔者尝试从新的角度探寻宋代志怪小说的“源头活水”。
(一)南方巫觋文化的滋养
由于地理与历史原因,中国南方文化在唐朝以前明显落后于北方,在北方兴起儒家礼教文化时,南方仍盛行上古所遗存的巫觋文化。王逸《楚辞章句》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3]朱熹也言“昔楚南鄂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4]。南方虽然不断受北方儒家文化影响,但“巫”性不改。而“巫”性正是志怪小说的重要命脉,李剑国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指出,巫教与原始宗教是志怪小说产生的两大重要源头。上古文明开蒙时期,南北皆盛行巫风,只是后来北方迫于生存需要,选择了关注现实人生的儒家思想,从而逐渐疏离巫觋文化。因此,北方对于南方总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这在韩愈的贬谪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可以体会到。穷乡僻壤本是滋生志怪小说的地方,当儒家文化渗入这些穷乡僻壤,自然会将这些地方所流传或发生的各种事情纳入其文化体系,而对于许多没有经过儒家文化改造或无法改造的宗教现象或民间巫风,就归之为“怪”“异”。儒家文化对穷乡僻壤种种怪异之事有相对的包容性,使许多奇奇怪怪之事有了一定的存在空间。
长期远离文化中心的南方是滋生鬼神怪异之事的“沃土”。先唐时期志怪小说繁荣的一个原因是民智低下,鬼怪之说皆可作为实有之事记录与传播;加上六朝时期又受佛教激荡,因而先唐志怪小说繁盛。然而,随着民智水平不断提高,志怪小说逐渐失去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而衰落。唐代志怪小说以辑抄前代书籍事迹为主要成书方式,这正说明志怪小说逐渐丧失文化上的“源头活水”。宋代随着建都位置两次南移,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志怪小说在南方巫觋文化中再次找到“源头活水”。全国文化中心从长安移至宋都开封,再伴随北宋“靖康之难”,宋代宗室南渡,文化重心再次南移至临安,文化重心不断南移,南北文化互相影响与交融。但在这一过程中,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强势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相对而言,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渗透则相对隐蔽。北方文化传播礼教文化,南方文化则渗透巫觋文化。因此,最适宜滋生鬼神怪异故事的南方巫觋文化进入儒家正统文化的领域,无数志怪故事开始显露,这就无异给逐渐失去活力的志怪小说及时引入一股新的“源头活水”。
宋代史料文献所载的巫觋文化有个显著特点,即绝大部分记载都来自南方,这充分说明南方巫风浓厚,同时也表明宋代史家对于南方巫觋文化的关注。江浙一带在北宋时经济文化已相当繁荣,南宋时又地处统治中心区域,可直至南宋,此地巫觋活动仍然兴盛,南宋初年有官员上奏:“近来淫祠稍行,江、浙之间此风尤甚,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听”[5]。与两浙毗邻的江西巫鬼之说更浓,北宋官员周邦式在奏疏中指出,“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之风,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弃医官,惟巫觋之信”[6]。福建的巫觋文化并不亚于江浙、江西地区,北宋蔡襄谓:“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7]。据《宋史》卷八十九《地理五》云:“福建路……其俗信鬼尚祀……与江南、二浙略同。”宋代巫觋文化浓厚的地区除上述几个省份之外,南方其他省份也都巫觋文化活跃。
宋代统治者对巫觋活动颇有顾忌,频频下诏禁巫,研究者李小红对宋代朝廷与地方政府的禁巫政令与事例做了统计,指出宋代禁巫政令与事例有一百零四则材料,其中九十多条材料所涉地区皆在南方,这说明宋代统治阶层对于南方巫觋活动的关注,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南方巫觋文化之兴盛。昌盛的巫鬼之风为宋代志怪小说的兴盛繁荣提供了一方文化“沃土”。宋代巫觋为了生存,想尽办法争取信徒,编造并传播鬼神事迹,高翥在其《松溪庙》诗中云:“庙自何年立,门深画不扃。寒藤扶坏壁,秋草带疏棂。溪接东西碧,山分远近青。老巫逢客至,谩说有神灵”[8]。由此看来,他们对鬼神有灵的宣传是从不懈怠的,当这些巫觋“谩说有神灵”的声音传到信奉鬼神的文人耳中,就成为了志怪小说的素材。
(二) 统治者“神道设教”的培植
儒家重实务而少玄想,对鬼神敬而远之,但在礼教体系却保留“神道设教”思想。《易·大观·彖传》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关于“神道设教”本质和原因,孔子在回答学生宰我的问题时精辟说明:“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9]。这种思想其实是儒学初创时对殷商巫鬼之风的接纳与改造,利用鬼神威慑力服务于教化实践。汉代王充深谙此意:“圣人举事,先定于义,义已定立,决以卜筮,示不专己,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小疑。”宋代立国者鉴于唐代灭亡的历史教训,特别重视文人统治与文教事业,在宋太宗时便确立“文德致治”统治方略,希望恢复上古三代的圣王事业,他们在重视“文德”的同时,也接纳了上古圣王“神道设教”思想,想借助鬼神力量来推行“文德致治”统治方略。正是在这种统治思想指导下,佛道两教得到了统治者的积极扶持。
宋太祖即位之初便下令恢复被周世宗废除的佛教,诏曰:“诸路寺院,经显德二年当废未毁者,听存;其已毁寺,所有佛像许移置存留”[10]。对于道教,宋太祖则先是选拔道官,后又禁私度道冠,并考核道士。宋太宗对佛教也积极扶持,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三月,“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并赐紫方袍”[10]。太宗在政治上崇尚黄老,谢灏《混元圣纪》卷八载:(太宗尝对侍臣说)“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朕当力行之”[10]。宋初两位统治者对宗教的种种“善举”若出于宗教热情,尚可理解,可事实上他们并无宗教信仰。太宗曰:“日行好事,利益于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饭一僧、诵一经,人何功德?”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太宗下诏建道场为百姓消灾,曰:“朕恐百姓或有灾患,故令设此,未必便能获佑,且表朕勤祷之意云”[11]。可见宗教在其心目中不过是“神道设教”的工具。
宋初统治者“神道设教”其实还有深层原因,即为新建的赵氏王朝寻求统治的合法性。宋太祖原为后周将领,深受周世宗柴荣器重,可在世宗死后却上演“陈桥兵变”,从世宗的遗孀幼子手中谋取政权,另立新朝。因此,在儒家文化语境之下,赵宋政权的合法性方面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所以,宋初的统治者需要一种为其合法统治辩护的文化语境。佛道两教因此极力迎合帝王心思,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进行神秘性的论证。《佛祖统记》卷四三云:“周世宗之废佛像也——世宗自持凿破镇州大悲像胸,疽发于胸而殂。时太祖、太宗目见之。尝访神僧麻衣和尚曰:‘今毁佛法,大非社稷之福。’麻衣曰:‘岂不闻三武之祸乎!’又问:‘天下何时定乎?’曰:‘赤气已兆,辰申间当有真主出兴,佛法亦大兴矣。’其后太祖受禅于庚申年正月甲辰,其应在于此也。”[10]此外,还有“定光佛出世”之说,《曲洧旧闻》卷一云:“五代割据,干戈相寻,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12]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以上谶言正中宋太祖下怀,为宋太祖兵变夺权的合法性进行神秘性辩护。
“神道设教”并没有帮助宋代统治者实现“文德致治”,甚至还加快了王朝的衰败。但对于以鬼神为血脉的志怪小说来说却是一大幸事。许多志怪小说直接受到宋代统治者“神道设教”诱导与激励而产生,尤其是宋代初期的志怪小说,有许多内容即是为神化宋代初君主或赵氏政权而产生的。与前代王朝的“神教设教”不同的是,宋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志怪小说对于“神教设教”的工具价值,宋太宗所诏编的“小说之渊海”——《太平广记》,其实就是一种志怪性的实用类书。《太平广记》所收录的九十二大类中,道教与佛教类作品所占比例极大,再加上民间鬼神内容的作品,志怪小说性质的作品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二以上。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泛释无义论》谓:“且《太平广记》者,乃《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13]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支持使志怪小说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存在合法性,为其大量出现提供了最适宜的宗教文化环境,为宋代志怪小说的繁荣作了铺垫。
(三) 新兴印刷出版业的刺激
宋代大量志怪小说作品的涌现与当时印刷出版业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在宋代,印刷术得到快速发展,《梦溪笔谈·技艺》记载了毕昇改进的印刷术:“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正是先进印刷技术的推动,宋代出版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叶德辉《书林清话叙》指出:“书籍自唐时镂板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14]。出版业的兴盛使书籍快速产生与广泛流布,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五月,宋真宗询问朝廷藏书板数量,祭酒邢昺应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15]。由此可见,先进印刷术的推动之功。据张秀民先生统计[16],南宋时杭州书坊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等共二十家。在离南宋首府较远、中央控制力量较弱的福建建宁地区,其书坊发展似乎比临安更快,仅建宁地区在南宋时期明确存在的书坊就有三十多家。
巫风浓厚地区正好是出版业最兴盛区域,这造就了宋代志怪小说兴盛的独特条件。袁同礼《两宋私家藏书概略》称:“印书之地,以蜀、赣、越、闽为最盛”,这些地区正是南方巫觋文化极浓厚的区域。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其中具有商业性的坊刻最兴盛。官刻基本以儒家经典、历代文史名著和医书等为主;家刻基本与官刻相似,只是增加家族、亲友和乡贤的文集;而坊刻以谋利为目的,更多地涉及经典作品之外的书籍,因此,作为九流之外的志怪小说便成了坊刻对象。苏轼尝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7]“市人转相摹刻”的“诸子百家之书”必定含有志怪之类的书籍。据宋周辉《清波别志》记载:临安城中太庙前的书坊“尹代书经铺”主要刻印小说和文集,其中就有黄休复的志怪小说《茅亭客话》[18]。坊刻在雕镂与校勘方面虽不及官刻与家刻细致精审,而且坊主出于成本考虑,采用较为低廉的纸张,如福建的建阳、麻沙刻坊即采用当地易得的竹纸,但是坊刻却有速成优势,故坊刻书籍在宋代流播天下,“至宋则建阳、麻沙之书林、书堂,南宋临安之书棚、书铺,风行一时”[18]。洪迈《夷坚志》之所以能够随写随刊,正是得助于坊刻的速成优势。
宋代兴盛的印刷出版业使志怪小说的传播能够突破各种限制,在社会各阶层传播,这不仅极大激发文人士大夫编撰志怪小说的热情,还培养出众多志怪小说读者,有些读者最后还转变为作者,进一步促进志怪小说的兴盛,这在《夷坚志》成书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洪迈之所以能倾心于《夷坚志》六十载,一方面是其猎奇兴趣所致,另一方面也跟读者的反馈激励不无关系。据《夷坚乙志序》称,甲志完成后不久即在闽、蜀、婺、临安刊刻传播:“《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1]。李剑国先生认为:“甲志问世后取得极大成功,各地竞相印行,短短五年间一刻再刻,以致‘家有其书’,这种始料未及的‘轰动效应’对洪迈无疑是一种极大鼓舞。”[19]
一些《夷坚志》的读者还主动地参与《夷坚志》成书。洪迈对此也有交待,《夷坚乙志序》曰:“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1]。据笔者统计,有五百多人参与《夷坚志》成书,其中大部分参与者是下层民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即一些参与者在向洪迈提供志怪故事过程中,也逐渐产生自主成书意识,如南宋刘名世的志怪小说《梦兆录》。据李剑国先生《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乾道中刘名世为洪迈述异,尙未有撰书之事,大约受洪迈影响,遂又自撰之,不赖洪书以传其事,而竟亦又被洪迈所采。”李剑国先生将《夷坚志》的成书现象称为“洪迈现象”,认为“在洪迈带动下,造成孝、光、宁三朝的小说繁荣,郭象《睽车志》、王质《夷坚别志》等更是直接影响下的产物,而其影响流风还及于理宗以后,及于金元”。洪迈在当时的崇高声望对于《夷坚志》成书及它对其他志怪小说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宋代印刷出版力量的刺激与推动。李剑国先生认为,宋代印刷出版业的发达,以及由此而造成宋人喜著书的风气是宋代文人小说(以志怪小说为主)兴盛的重要因素[2]。
参考文献:
[1] (宋)洪 迈.夷坚志[M].何 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1820,531,185,185.
[2] 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2,3.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5.
[4] (宋)朱 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9.
[5] (清)徐 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 (清)徐 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 (宋)蔡 襄.端明集·圣惠方后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583-584.
[8] (宋)高 翥.菊磵小集[M].汲古阁景宋鈔本.
[9] (魏)王 弼,注.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9:36.
[10] (宋)志 磬.佛祖统纪·卷四三[M]//大正藏第49册.日本东京大藏经刊行会,2001:394,396,397,394.
[11] (宋)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596.
[12] (宋)朱 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85-86.
[13] (宋)郑 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18.
[14]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M].李庆西,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
[15] (元)脱 脱.宋史·邢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798.
[16]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70.
[17] (宋)苏 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74.
[18] (宋)周 煇.清波别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5,33.
[19] 李剑国.《夷坚志》成书考——附论洪迈现象[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5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