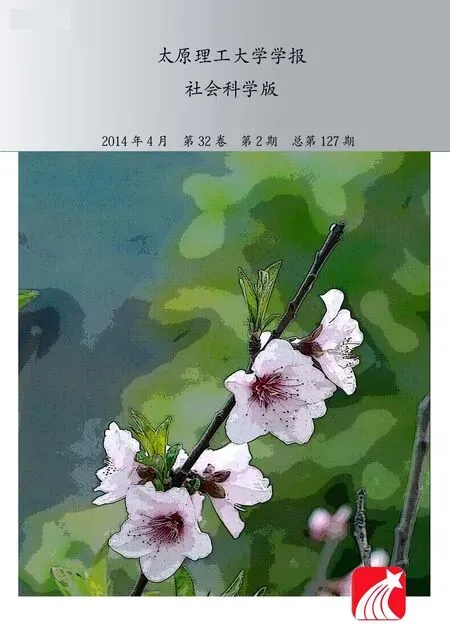* 论立约建国所依赖的“约”的本性
王军伟
(昆明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和平,但由于所诉诸的手段是人的自我保存,而自然状态中人的竞争、猜疑和爱慕荣誉的本性决定了这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一切法在战争中都沉默无语,所以自然法也不例外,它不能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因此,要想实现自我保存,摆在自然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立约建国的道路。
(一)建国缘起
假如世界上仅剩下的一个人也同样具有霍布斯所认定的各种激情,那么无论这些激情多么容易引起战争,也都无害于这个人对自我保存的追求,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他的困境,原因就是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然而人“不可能孤零零一个人存在。他的同类不止一人存在着,这一事实他必须认识到。我们必须从对人的自然(或本性)的考察转向对人的自然状况的考察,人的困境正是在这一时刻才变得明显起来,因为孤单的人除了其必死性以外,呈现不出任何可被正确地称之为困境的特征”[1]。一切麻烦都源自他人的存在,他人的存在注定个人必须生活在群体当中,他人是人的天命。他人的存在成了人追求自我保存的障碍,因为为了获取自我保存所需的资源,人必须与他人展开竞争,于是人与人之间便没有了互信而只有猜疑。可是,他人虽是自己的敌人,自己却又离不开他人,因为“没有他人,就不会有对自己的优越性、从而对引人瞩目的幸福感的认同,构成一个人的幸福的许多、甚或大多数满足,都在于他可能从他人那里强取到的认同”[1]。由于荣誉是带给人满足的幸福之一,因而人人都会求取荣誉。竞争、猜疑和荣誉是作为群体的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本性,是人类群居生活所展现出来的特征,这三种本性再加上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依赖自己的私己之判断(private judgment),便使自然状态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为了使群居的人类能够逃离自然状态,霍布斯先是设计了自然法的出逃路线,但是由于自然法在不安全的状态下只对人的良心起作用并不能约束人的行为,所以人不能摆脱自然状态。霍布斯不得不另寻他途,这个被霍布斯认为是最终有效的“他途”,就是赫赫有名的立约建国的出逃路线。霍布斯建立国家的目的,一是为人们遵循自然法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二是为人们履行契约提供制度保证,这两者合起来就实现了霍布斯梦寐以求的人类和平,有了和平,人的自我保存便有了保证。
(二)契约(contract)和信约(covenant or pact)
在霍布斯那里,国家的建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力取得国家(Commonwealth by Acquisition),一种是按约建立国家(Commonwealth by Institution)。前者是靠自然之力或武力获得的,例如一个人由于对其子孙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因而迫使其子孙服从其统治,这样形成的国家叫做父权制或宗法(Paternall)国家;还有一种以力取得的国家是靠战争中的征服,通过赦免敌人的生命而换来他们对自己的服从,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国家是专制(Despotical)国家[2]。由于这两种建国形式都要用到契约或信约,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霍布斯说:“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2]如果立约双方或多方都立即履行了契约所规定的义务,那么这种契约在每一方来说就都是契约;如果一方先行履行了契约规定的义务,而另一方尚处于先行履约一方对他的期待或信托(be trusted)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先行履约者是立了契约,受人信托而尚未履约的一方是立了信约。如果契约签订之后,双方都没有立即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双方都承诺以后履行他们,那么双方就都处于期待之中,彼此信托着对方,这种契约在双方来说就都是信约,霍布斯称其为“相互信托的信约(Covenants of Mutual trust)”。因此,信约的定义是,“当一方或双方都受到信托时,亦即受信托者承诺以后履约,这样一种承诺(promise)就叫做信约”[3]。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所说的信约实际就是一种承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约实际就是契约的一部分,但不是必然的部分,即契约不一定必然包含信约。例如,在现金交易中,就只存在契约而不存在信约,因为,商品本身已随着所有权的转让而同时交付给了对方,钱货已经两清,按照霍布斯的话说就是谁也不用信托谁,“契约由于履约而终止”[3]。但是,如果一方随着权利的转让交付了东西,而另一方承诺将来再行交付,那么前者立的就是契约,后者立的则是信约。
(三)两种立国形式分别依赖的 “约”
以力取得的国家,其国家的统治者由于靠着征服而做了主权者,他赦免的被征服者则将要成为其臣民,即他的先行赦免换来的是被征服者随后服从的承诺。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契约关系中,由于征服者不杀在先,被征服者服从的承诺在后,征服者就是先行履约者,被征服者则是受信托者;征服者立的是契约,被征服者立的则是信约。但是,因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双方并没有以明确的言词宣布他们之间为契约关系,我们何以知道他们是契约关系?霍布斯的回答是“契约的表示有些是明确的言词,有些则要靠推测”,“推测的表示有时是语言的结果”,“有时是沉默的结果;有时是行为的结果,有时是不行为的结果。一般说来,任何契约的推测表示法就是足以充分说明立约者的意愿的任何事物”[2]。因此,对霍布斯来说,从被征服者愿意接受征服者的保护来推测,足以充分说明被征服者愿意服从征服者的意愿,因此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
而在立约建国的情形中,自然状态中的个体人相互承诺放弃他们各自的“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并承诺把这种权利让渡给第三者,由于这还只是承诺,都还没有实际放弃和让渡这种权利,也就是说,他们都还没有履约,他们还都处在互相信托之中,因此,这种契约只不过是一种信约,是一种“互相信托的信约”,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信约(covenant of every man with every man)”[2]。因此,通过拥立主权者来建立国家的协议(agreement)并不仅仅是契约,因为它含有个体人未来履约的承诺,而所有含有承诺的契约都可称之为信约。
(四)建国的政治信约的殊异特性
但是立约建国的政治信约又不同于任何其他类型的信约,因为就个体人和主权者的关系而言,这种政治信约是单方面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主权者本身并非是这个政治信约的立约一方。而个体人在互相“签署”这个信约以后却背负上“双重的义务”,即“公民同胞相互间的义务和对统治者的义务”[4]。主权者不可能是立约方,这既有逻辑上的理由,也有实践上的根据。
从纯粹逻辑的观点来看,谈论主权者和人民之间的信约很荒谬,因为后者在没有成为“人民”之前只是一群人(a multitude),还不是法人(Person或译“人格”),因此这一大群人便不具有作为立约一方的资格。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即使假定有这种存在于人民和主权者之间的信约,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立约双方在如何执行这个信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信约。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裁断者来解决争执,于是大家便又会重新诉诸武力”,因此,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又重新回到自然状态,“这就和原先按约建国的宗旨相违背了”[2]。
(五)从建立联盟到做到协调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人为什么非得需要一个政治信约或联合体的信约呢?像蜜蜂和蚂蚁这样的政治动物没有联合体的信约不照样生活得很惬意吗?霍布斯经常挂在嘴边的西塞罗的名言是“法在武力中间沉默无语”[4],为了使法“开口说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武力,寻求和平。亦即,只有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法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为了维持和平,人人都得奉行自然法;为了奉行自然法,必须有一个安全的环境。”[4]在人人为战的自然状态中如何获得这种安全?最容易的办法是寻求相互的协助,三两个人联合起来必然会使得其他人不敢侵犯。但是三两个人的联合毕竟不足以获取和平,因为你能联合人,敌人也会联合人,而且敌人联合的人数稍有增加就会对你进行侵犯,因为人数少的联盟只要人数稍有增加就会使这个联盟获得胜利。“因此在人们的相互协助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安全之前,他们的人数必须大到即使敌人人数稍有增加也不会使他们占到明显的便宜。”[5]
联盟除了人数足够多,还要求所有人员的行为必须协调一致,否则防御也不能带来安全。即使联盟已具备人数多和协调一致这两个条件,也会由于人害怕眼前敌人的侵犯而暂时取得协调一致,但是这种协调一致不会持续到侵犯或征服结束以后,因为在人数众多的为利益和荣誉而纷争不已的人们当中,他们各自的判断和激情也必定千差万别,因此,若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力使他们畏服,他们不但不能协调一致地相互协助共同对敌,他们中间的和平也将难以维持。
为什么人看到了协调一致的好处,却不能像蜜蜂和蚂蚁一样不需要强制权力就能保持协调一致呢?霍布斯举出了六个理由。首先,这些动物不像人那样追求荣誉和地位,人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会互相产生仇恨和嫉妒,最后发生战争。其次,这些动物的争斗目标是全体的食品和公共和平,而人奋斗的目标却是为了支配人、胜过人和获得各自的财富。其三,蜜蜂等动物没有理性、没有学识,因而便看不见政治的缺陷,而人却总是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总想着去矫正他们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其四,这些动物没有言语能力,因此便也不能相互煽动叛乱。其五,这些动物没有善恶观,只有痛感和快感,因此他们不会相互指责,不会发号施令。其六,这些动物之间的和谐一致由于是上帝借助自然而成就的业绩,因而它们之间的和谐是自然的和谐一致,而人之间的和谐由于必须借助于信约,因而是人为的和谐。
(六)建立联合体所需要的政治信约是一种服从信约
既然协调一致未能给人带来安全,那么最后的策略便是组建联合体。协调一致与联合体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把“众多人的意志结合在同一个目标当中”;而后者则是把“众多人的意志涵括在一个人或一个议会的意志当中”,“在公共和平所必需的一切问题上,无论这个人或这个议会的意志是什么,这种意志都应当被看作是大家每个人的意志”。这种把所有人的意志涵括在一个人或一个议会的意志当中去,说白了就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来约束每个人自身,不违抗他们已经向之表示服从了的那个人或那个议会的意志,亦即不吝惜那个人或那个议会在反对敌人时对自己的财富和力量的使用”。这里所说的协议实际就是信约,即联合体的信约或政治信约,霍布斯说“以这种方式组建的联合体就被称作国家、或公民社会或公民法人”[3]。
该联合体的信约规定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们将要建立的主权者的意志,把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也让渡给了它,在有关公共和平与防卫的一切问题上也都听命于它,因此他们便由于这个联合体的信约而使自己背负上了一个基本的义务,即他们有义务服从握有主权权力者的一切命令。因此,联合体的信约由于这个基本的义务成了“服从信约”,该信约是这样表述的,“我授权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与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授权他的一切行为”[2]。
(七)霍布斯对传统意义上的服从信约所作的重要改变
虽说霍布斯的联合体的信约是一种“服从信约”,但是它却不同于传统的“服从信约”。在传统的服从信约中,参加立约的一方为作为整体的平民,另一方则是主权者。霍布斯之所以作出这种变化,是为了避免传统的服从信约经常被废除的危险。因为按照传统的服从信约,立约双方就好比是委托人(人民)和受托人(主权者)的关系,主权者的统治权是由人民基于一定条件和期限而寄托在他那里的信托,如果主权者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或者他的统治期满以后,这个信约将会被废止。为了不使联合体的契约轻易地遭人废除,霍布斯作出这种变化是有意增加了废除它的“事实上的难度和法律上的不可能性”[6]。按照传统的服从信约,参约一方是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即人民而非一群人,那么只要团体中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废止信约。但是如果参约一方不是人民而是全体公民社会的成员,即作为个体人的人群,那么,信约只有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可以废除,也就是说,全体一致同意而非大多数人同意才是废除信约的必要条件。而要让所有的公民都同时同意推翻主权者,这显然不合情理,因此,“根本不存在主权者可能被夺去权力的危险”[4]。
霍布斯设计的联合体的信约是一个支持第三方的契约,要想废除这个信约的法律上的不可能性即源于此。因为在这种契约当中,立约各方不但彼此负有义务,而且他们对他们立约支持的第三方也负有义务。因此要想废止信约,他们不但要征得立约各方彼此的同意,他们还须征得这第三方的同意。这就是说,一旦个体人赞同联合体的信约,他们自身的同意(就连这一点也已经不可能,因为这需要全体一致同意)已不足以废止信约,他们还必须征得主权者的同意。
(八)结论
霍布斯赋予他的联合体的信约的功能是,通过拥立一个主权权力,从而引领人类逃出自然状态而进入到国家状态。霍布斯设计的这种联合体信约有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实际也代表着霍布斯的国家观,同时也决定了主权权力的性质。首先,这个信约是一个服从的信约,是由个体人相互之间订立而来,而非由人民和主权者订立而来,这个特征决定了主权权力是不能废除的;第二,自然状态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有的力量贡献给了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这特征决定主权权力的绝对性;第三,这种主权权力所归属的第三方是一个人格或法人,这个特征决定主权权力及信约的不可分割性。
参考文献:
[1] Oakeshott Michael.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M].indianapolis:Liberty fund,inc.,1975:36,38.
[2] [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2,100,101,131,134-135,134-135.
[3] Thomas Hobbes.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vol.II) [M].London:Rouledge/Thoemmes Press,1839:45,20,73.
[4] Thomas Hobbes.On the citize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90,69,70,89.
[5] Thomas Hobbes.The elements of law [M].New York:Barnes & Noble,1969:101.
[6] Norberto Bobbio.Thomas hobbes and the natural law tradi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