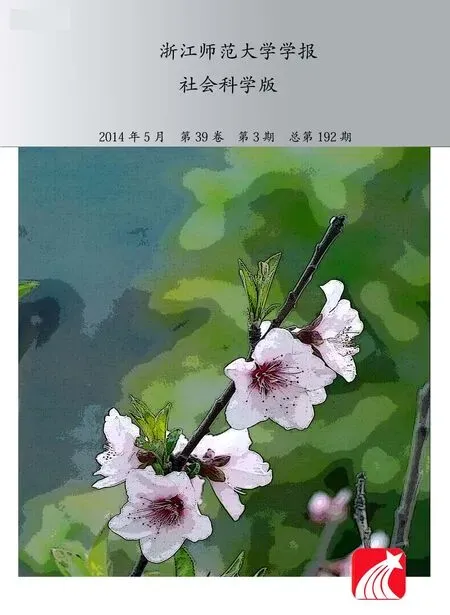桑塔格延展式身份写作*
唐 蕾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387;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苏珊·桑塔格作为美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有很多光彩炫目的荣誉头衔——坎普王后、“批评界的帕格尼尼”、曼哈顿的女预言家、后现代主义先锋作家、“文坛非正式女盟主”、“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等等。而“美国公众的良心”这一称号则是美国人给予她最崇高和最完整的评价。桑塔格在其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更多扮演的是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带给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众的深刻影响。从几十年与病魔斗争、十赴波黑战场、揭露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关押政治犯的非人道行为、对艾滋病人及所有身心受折磨的弱势群体之关注,再到其对同时代所有大事件的关注和评论,所有这些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让这位低调而勤奋的作家收获了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欣赏。一位作家之所以能够在公众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不单要看他是否有天才的创作才华、激情澎湃的奇思妙想,还要看他有多少文字是为这个社会和公众群体承担起观察、提醒和鞭策的责任。因此,在这一点上,桑塔格被美国公众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当之无愧的。
一、从自我到他人:非个人化的自由书写者
桑塔格从不把写作当作私人的行为,在其与南非获诺贝尔文学奖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对话中,她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从未觉得作家所从事的是私人活动。”“我认为,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非作为一个作家,我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说,我当时认为,成为作家是一种特权,我在社会上处于一种有特权的位置,我要公开发出声音,当时情况紧急,我认为自己能够以声音来影响人们,让他们去关注我热切关注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拥有——或许我们大都认为自己拥有——一种道德职责;我认为这是现代生活中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一部分。但我并不认为它决定我们作为作家的价值。”这种非个人化书写的态度和戈迪默达成了内在的默契,戈迪默在《关于作家职责的对谈》中讲道:“要当作家, 就必定要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社会里有什么, 并且明白社会是如何塑造我、影响我的思维的。作为一个人类成员, 我就会自动地为它担当起某种责任(因为作家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要求他去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1]两位作家在关于作家职责的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说到底都源自于作家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公共意识及创作使命感。桑塔格反感某类作家在文本中不厌其烦地书写自己、表现自己,她认为这样的创作不可能成为最一流的作品。无论从服务意识还是从公众效应而言,这样的作品只是为表现而表现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桑塔格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是有限的、逼仄的,如果作家仅把眼光盯在自我的身上,作品则显得非常浅薄和苍白。她认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既创造”、“也回应一个世界”,[2]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桑塔格在其作品中表现出较为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回应当代大事件的积极态度。《疾病的隐喻》由两个部分组成:《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其中讨论了结核、癌症、霍乱、梅毒、鼠疫等让公众尤为恐慌的疾病。桑塔格认为所有疾病都是可以被控制的,而人类对于疾病进行了无限制地放大和错解。人们对于疾病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癌症患者一定是长期精神苦闷者、结核病人都和贫困有关、性病患者均为道德感缺失之人、鼠疫是最可怕而不可自救的人类灾星等等。桑塔格认为,大部分的疾病已经超越了病理学上的范畴,而变幻为某种和人格、道德以及身份有关的社会话题。疾病变成某种身份和符号,被公众贴上指认的标签以便进行分类和划界。公众缺乏对于病人足够的认知和理解,把他们生理上所患的疾病扩展至心理上、身份上的“问题”。桑塔格认为这是可怕的误解,而作家有责任告诉公众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看待疾病和病者。《关于他人的痛苦》由三个部分构成:《关于他人的痛苦》、《致谢》和《附录:关于对他人的酷刑》。桑塔格在其间讨论了伍尔夫有争议之作《三几尼》、无终结的战争、摄影与真相、英雄史诗《伊利亚特》、酷刑等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作家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对于很多问题做出冷静和理性的分析。在书中,她这样写道:“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桑塔格认为“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3]而这往往成为人们选择和平或战争的两难处境。这一段话中对于战争的评论理性且客观,对于一个不介入战争的评论家而言,桑塔格更能够看到问题的最关键点,她清楚战争的根结在哪里,而介入战争的人们也很清楚,但是记忆和对往昔亲友的怀念让人们继续为复仇和暴行寻找理由。她认为这正是战争永远无法终结的原因所在。《疾病的隐喻》和《关于他人的痛苦》是两本主题不一致的作品,有一点是相似的,这是作家总结出来的结论——一切疾病和痛苦的根源都来自人类对自身认知的不完善和理性意识的缺失。
《疾病的隐喻》、《关于他人的痛苦》等作品是面向美国知识界的读本,因此,作家在其中传递了某种想法,而问题是:美国知识界对其作品接纳了多少?又排斥了多少?桑塔格的作品是否如她自己预计一样达到了目的?这一系列问题在作品出版后一一有所回应。如果说桑塔格的作品是带来了新想法,还不如说是带来了大讨论。她习惯给人们抛去一个个有争议的话题,然后镇定、沉着地迎接质问和挑战。当然,辩论总归有正方和反方,总有支持她的人群在背后摇旗呐喊。作为知识分子,桑塔格的勇气和游离状态一直是人们最为欣赏的地方。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一次谈话中对塞纳特这样说道:“因为自己没有走自由知识分子之路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内疚感。”[4]241人们对桑塔格不附属任何机构的勇气和胆识感到钦佩。当然,美国评论界对桑塔格超越科学范畴之上否定疾病存在论的言谈感到不满,有人认为桑塔格的作品是“乌托邦思想的产物”。[4]233在美国前沿文化阵地上,各种思想在碰撞、摩擦、对话,而桑塔格则一直是其中最独立也是最有前瞻性的思想者之一。她的勇敢、执着、勤奋和思辨的个性使之成为美国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位非个人化的自由书写者。西格丽德·努涅斯对桑塔格严肃的创作态度极为欣赏,作为桑塔格身边的助手之一,她在传记《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中记录下桑塔格对于严肃创作态度的一段评价,桑塔格这样对她说:“你做这件不是为了自己开心(这与阅读不一样),不是为了宣泄,不是为了自我的表白,也不是为了取悦某些特定的读者。你是为了文学而为之。”[5]62桑塔格认为所有的写作都应当是许多想法迫不及待的一种表达诉求,她认为在没有任何创作意图和创作动力之下被迫的写作是毫无意义的。任何理由和借口都不能成为作家为现实妥协的原因,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让任何人威逼你”。1947年11月23日,桑塔格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行字:“(b)世上最令人向往的是忠实于自己的自由,即诚实。”[6]11958年1月7日的日记里写着这样一段话:“在我看来,严肃是一种真正的德行,这是[我]在生存论的层面上接受,同时情感上也接受的少数几种德行之一。我爱高高兴兴的,凡事不往心里去,但是,这只有以严肃要求为前提才有意义。”[6]231
二、从美国到欧洲:先锋文化的媒介者
在现代美国文坛上,文学有时也像流行音乐,有其背后的文化策划者、风尚指标以及偶像设计方案。在这一点上,桑塔格可以算得上为美国出版界最为关注的一颗璀璨明星。她既是精英文化的一分子,也是先锋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很好地融合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者的特点,既保持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主流舆论导向一定的距离,又能很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新讯息和重要变化。在与欧洲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桑塔格积极地扮演着媒介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构建起美国和其他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她将德国的法兰克福派、法国的罗兰·巴特、罗巴尼亚的萧沆、英国的王尔德、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等思想者作了详细而别致的介绍,引入到美国思想界,进而推动了美国现代文化与各国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先锋文化追求特立独行的表达方式、不强调传承旧有的文化传统、追求艺术化变形、认为艺术不应当承担任何附加的义务和职责、以梦境表达人的内心世界、表现荒诞和陌生化的现实世界。1963年,桑塔格的第一部作品《恩主》问世,从这部作品开始,作家的创作文风和思想构架初步确定。小说以无数个梦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难以捉摸。桑塔格以变换的主人公、主题和故事背景跳跃性地讲述故事内容,不强调清楚陈述过去发生过的一切,而是借用后现代的艺术手法全面涉及从男人到女人、从正常人到疯子、从西方社会到第三世界的全景化生活,以怪诞和变形的艺术技巧表现了现实世界的荒诞和不确定性,强调了人作为主体存在的不确定性和被异化的现状。批评界对于这部小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是拙劣的,有人则认为它极具前瞻性。美国享有盛名的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对该书充满信心,于1963年正式出版此书。小说收获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评价。约翰·巴思认为该书是“来自伏尔泰影响下的荣格”。[4]88汉娜·阿伦特认为桑塔格“已经学会运用其与法国文学相一致的创新风格”,她十分佩服桑塔格“能做到前后严丝合缝”。其中最为中肯的评价来自于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她说:“她聪慧,相当严肃,长于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的题材。”甚至有评价认为桑塔格很快会成为伟大的作家,“会与玛丽·麦卡锡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样的作家、评论家齐名的。”[4]89《恩主》的出版发行让桑塔格开始走向职业作家的行列。从小说到剧本、从文本创作到影视创作、从文学到文论,每个重要的文化领域都能听到桑塔格响亮的发声。
桑塔格对于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体现出均匀的兴趣度和关注度,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两者之间,这也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美国文学风尚。美国人既可以在《党派评论》中听到她的言论,也可以在《时尚》杂志看到她的身影,这种活跃和伸展度和美国文化是合拍的。桑塔格既很无畏,也很时尚,能够代表美国最有活力、最前沿的女性思想者形象,也顺应了美国大众对于现代女性的某种期待。“苏珊·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诉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4]127《论摄影》不仅被看作一部经典的文论集,也被摄影界视作经典的参考文本。在这部作品中收录了六篇评论和一篇简集,包括《柏拉图的洞穴》、《由朦胧的摄影看美国》、《令人抑郁的对象》、《幻象英雄主义》、《摄影的福音》、《形象的世界》和《引文简集》七个部分。桑塔格用了一种看似夸张的表达形容影像对于人类社会的改变,她这样说道:“十九世纪美学家马拉美(Mallarme)最具逻辑性地说,世上存在的万物是为了终结于书本。如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照片。”[7]这段带有预见性的话在之后的现代生活中不断被证实,而现代人对于影像的信任和依赖程度的确远远超过文字之上。本雅明在《电影拍摄》中感叹到绘画的衰败和电影的崛起之不可避免性,他这样说道:“现在,绘画已经无法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共时接受对象了,尽管它先前可以适用于建筑艺术以及叙事诗,它已经被电影所取代。”[8]安吉拉·默克罗比在《苏珊·桑塔格的现代主义风格》一文中高度评价桑塔格的《论摄影》:“《论摄影》(1978b)是迄今为止对摄影的文化意义的最全面、透彻、明达的介绍。”美国《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对于这部文集都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另一位美国作家约翰·贝尔格认为:“未来,就各种大众媒介中指明对社会作用的探讨,必将以桑塔格的《论摄影》为关键著作而加以引证。”[9]王予霞认为:“桑塔格对摄影的论述集中传达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知识界的声音。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大众文化的‘自由危机’、激进的不确定方面。”[10]桑塔格对于影像的关注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新文化风向的敏锐觉察力,同时对美国后现代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文化转型的70年代,她始终保持着文化风向标的姿势,既不一味向大众文化妥协,也会同意见相左的后现代主义评论家展开激烈地争论。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如同她的作品一样,带给读者的永远不会是方向统一的观点,充斥着矛盾与晦涩,永远不会把最清楚的意思交待清楚,保持谜一般的神秘感。美国现代文化和桑塔格的时尚、自相矛盾、简洁有力、晦涩、折衷主义说到底是统一的,因此,她的作品慢慢为美国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读者所接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五味杂陈的桑塔格文本中找到想要寻找的东西,而这种影响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三、越界的独特性:非典型的女性作家身份
在美国现代文坛上,许多女性作家展现出其过人的才学和卓越的见解,诸如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其中也包括桑塔格。然而,桑塔格从未在女性身份上大做文章,既不纠缠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颇有争议的话题讨论,也不过度凸显女性作家身份,当然为此也引来不少人对她的不满和批评。英国批评家安吉拉·默克罗比在文中犀利地点评桑塔格对女性身份和女性问题忽略不谈。也有批评认为桑塔格实质上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他们甚至认为女性作家过度张显女性身份只会让作家失去一部分支持她的读者,因此,他们认为桑塔格是聪明而狡猾的。这些批评有些不无道理,但是,批评指责的背后体现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桑塔格作为非典型化的女性作家身份该如何被正确理解。确切地说,桑塔格不是忽略女性身份,而是在陈述观点和表达想法时并非一味从女性视阈出发,其阐述问题的视角是多维的、中立的、鲜有性别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视角。从这一点而言,桑塔格不是一位波夫娃式的女权主义者,而是一位颇为中性的知识分子。
女性的社会问题和生存处境一直是西方批评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尽管如此,女性主义作家和女权主义作家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带有歧义和贬义的词汇。客观而言,许多西方作家都不愿被轻率地冠之以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作家头衔,因为这种称呼意味着表达情绪化和有可能被边缘化。桑塔格对西方文明有十分深入的了解,她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未视而不见,而是以一种较为客观和中立的视角对某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和阐述,因此,她既是聪明的,也是冷静的。桑塔格一直认为女性的社会问题和自由问题、艾滋病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问题一样,并不一定得量出孰轻孰重,她认为人们应该就情形和处境的变化而对不同的问题投入相应的热情和关注。人们往往奇怪于她是如何完成了男性主人公在《恩主》中的艺术化表演,而对《床上的爱丽斯》等作品却视而不见。事实上,桑塔格并未彻底抹煞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在《床上的爱丽斯》、《在美国》等一系列作品中讨论了女性的生存现状以及女性发展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桑塔格可以胜任于以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同时发声的创作活动,这一点体现出一位职业作家所具备的专业性和驾驭力。
女性作家是应该以愤怒的控诉者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还是应该以平静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是一个问题。女性作家是应该以女性的身份发声还是应该以中性的身份发声,这也是一个问题。在大众的多重选择中,更多的选票会投给那些平静的、中性的发声者,因为,大众似乎认为后者的表达看起来更为客观和容易让人接受。玛格丽特·福勒、弗吉尼娅·伍尔夫、西蒙娜·德·波夫娃、茨维塔耶娃等人都曾以愤怒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她们被人们接受了,但是这种接受并非全面的、开阔的。桑塔格显然需要找到另一种更为广阔的发声平台,一种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多群体的代言人和传声筒的开放式舞台。现代文明的构成是多维度的,既有性别的问题也有种族的问题,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民族文化差异的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对此,桑塔格没有特别地将性别问题当作最急迫的问题来强调,甚至低调地处理了身为女性作家身份和视阈等问题。桑塔格所关注的林林总总问题就如同她所阅读的浩如烟海的书籍,庞杂而丰富,敏锐而独到,每一个细小的主题都会快速地跃进她的视线之中,而看似重要的主题可能因为说得过多而更无新意便被她匆匆掠过。美国在经历近现代一百年的变革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是所有美国知识分子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对于桑塔格而言尤为重要。桑塔格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而非纯粹的女性作家,她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有包容天下的胸怀,而不应该幽居于女性作家的身份之中,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并未刻意彰显女性身份而低调地回避女性身份这一问题。
美国大众对于作家有一定的期待和要求,他们希望能从作家的文字中得到最大化的信息量和最前沿的知识,希望他既能深入地阐述一些问题、也可以不断地从这一领域跳跃到另一领域。在这一点上,桑塔格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她既很权威,也很时尚,既很专注,也很辽阔,自然而然成为知识界的“明星”——一种美国式的知识界明星。在日趋多元化的美国社会里,各种群体对于讯息和知识的感知方向是不一致的,这就从内在要求美国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要确立自己的认同群体,即搞清楚为谁而写的问题。作家的知识结构、专业训练过程以及专注对象决定了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写作倾向,因此,这就决定了桑塔格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女性作家,而是更为全面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伍尔夫曾经感慨过女人因为缺少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一年几百英镑的收入而无法心平气和而不带任何怨言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而过了半个多世纪,桑塔格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伍尔夫式的女性问题了,她雄心勃勃地准备着每一个新问题并像男人们一样准备去解答和回应,在这一点上,桑塔格的确算是一位非典型的女性作家。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桑塔格较为欣赏的两位女性作家。但尽管桑塔格极其推崇哈德威克的作品,她对于哈德威克的女性气质却颇有微辞。哈德威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直在,一辈子都在,寻找来自男人的帮助。”而这正是桑塔格对其不满的原因所在。哈德威克在和西格丽德·努涅斯谈到桑塔格时,她这样评价桑塔格:“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5]31伍尔夫在桑塔格的眼中的确是个天才的女作家,但是她在个人书信中常常表现出来的不合时宜的“孩子气的语言”和“少女般的闲扯”让桑塔格感觉极为平庸和幼稚。严肃是桑塔格最喜欢的词汇之一,她常常对别人谈起作家严肃的创作态度,她这样说道:“你只要看他们的书就能知道这些人到底有多严肃。”[5]25她认为贝克特是严肃作家的代表,因为他能始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和行为准则,桑塔格认为贝克特真正做到了创作和日常生活的完美统一,并且他从不为物质层面的东西违心地做自己不乐意的事情。纯真是作家对生活和创作体现出来的痴迷和专注。桑塔格认为痴迷的人最纯真、最可能成为艺术家,因为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热爱的事业和生活投入孩子般纯粹的热情和无功利性的付出,才能真正成就一番事业,她认为严肃和纯真是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家可以在其作品中丢弃女性柔弱和依附的第二性特征,其写出来的每一句话应该是完全中性的,不带性别色彩的。她从不相信文学中存在“女人的句子”。[5]61她更难以理解的是文学作品中还会有女性视角和女性叙述这样一种说法,她所理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严肃和纯真相结合的完美体现。严肃的创作态度可以让一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创作投入最饱满的热情,并可以让阅读者从中感知到作家客观而理性的个人立场,而纯真可以让作家远离日常事务的干扰和污染,在游离于权利中心之外可以为自己所表述的每一句话做到问心无愧。
桑塔格是美国和欧洲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她对前沿讯息的敏感度和把握使得她成为美国先锋文化的一位重要领军型人物;她不囿于女性作家的身份,视野辽阔、纵横捭阖,担当起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并以严谨而专注的学术态度影响着美国知识界。美国文化期待出现桑塔格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她全面、客观而不动声色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和判断,这种表达是更为理性的书写方式。
参考文献:
[1]纳丁·戈迪默,苏珊·桑塔格.关于作家职责的对谈[J].姚君伟,译.译林,2006(3):200-203.
[2]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16.
[3]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M].黄灿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6.
[4]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 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西格丽德·努涅斯.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M]. 阿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戴维·里夫.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M]. 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7]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 艾红华,毛雄建,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35.
[8]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M].李伟,郭东,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0.
[9]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 田晓菲,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23.
[10]王予霞.苏珊·桑塔格纵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