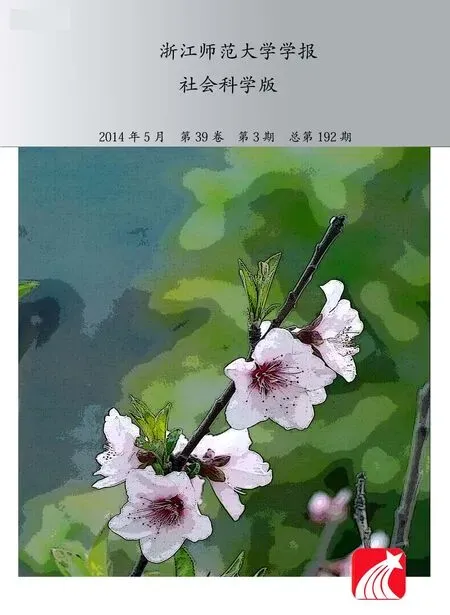论乔纳森·韦纳《雀鸟之喙》的生态意蕴*
张建国
(郑州大学 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1995年,美国图书最高奖普利策奖的普通散文(general non-fiction)奖,授给了乔纳森·韦纳(Jonathan Weiner,1946-)的《雀鸟之喙》(TheBeakoftheFinch, 1994)。乔纳森·韦纳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散文作家,曾任美国《科学》杂志的编辑。《雀鸟之喙》获得许多赞誉。《科学》杂志的评语是:“明智,渊博……韦纳的作品极具魅力,恰切地揭示了达尔文大大低估了的进化理念的力量。”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的评语是:“一流作品……它是我多年来读到的最佳科学散文作品之一。”[1]1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自然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比尔·麦克齐本指出:“这部卓越的作品将彻底改变你对自然节奏的感受——你一旦读了韦纳雅致、迷人的描述,就会觉得世界变动不居、流丽多彩、生机勃勃。”[1]Ⅱ
《雀鸟之喙》的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进化故事”;该作品由三部分组成,共20章,外加尾声。它以“既像侦探小说又像探险故事”的“神奇”、“迷人”结构,以“清晰易懂”、“抒情诗般”的语言,[1]Ⅰ-Ⅱ描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教授彼得·格兰特与罗斯玛丽·格兰特夫妇的雀鸟研究团队20年的科研历程。为了佐证进化生态观,作者韦纳还插叙其他生物学家相关研究的过程及成果。同时,作者还不时加入自己对进化生态理念的评说。本文拟探讨该部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意识。
一
生态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进化论结下了不解之缘。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正式提出生物进化论,这一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在自然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其他生物)发生变化或产生压力的情况下,能够适应的生物得以生存,生存下来的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的特征,通过一代代的遗传逐渐强化,使种群发生显著的进化,最终导致新物种产生。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达尔文的影响下,创制“生态学”一词,并提出相关理念。他1866年给生态学下的定义是:“生态学研究达尔文所说的生存斗争条件之类的所有相互关系。”[2]生态学家皮特鲁塞韦茨(Petrusewicz)1959年“曾写过《达尔文进化论是一种生态理论》一书,强调进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过程”。[3]著名进化生态学家欧利安(Orian)认为:“进化生态学就是研究生态适应的原因,进化看起来是目前生态学唯一的真正理论。”[4]可见,达尔文进化论与生态理念是一致的,它实际上是进化生态学的先声和进化生态理念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在西方思想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具有重要的生态哲学意义。进化论意味着,各种生物并不像西方人长期信仰的那样,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经过自然环境的长期作用,逐渐进化来的;人类不是上帝特创的高高在上的万物主宰,而是像其他物种一样,从最基本的生命体进化而来的,是生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可以说,达尔文揭穿了人类中心主义者所宣扬的人类独特性的论调,首次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
然而,达尔文对进化论的阐述存在着明显乃至严重的缺陷。其进化论的核心,是强调“自然选择”对生物进化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正如《雀鸟之喙》所指出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没有描述任何特定物种的起源,或任何特定物种的自然选择,也没有讲述任何特定物种的优选种群如何在竞争中生存”,“达尔文从没亲眼见过物种的进化过程”。[1]6达尔文对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论证,主要基于养殖动物饲养员在育种过程中对动物进行人工选择的类比,以及现存动物与出土的类似动物化石的进化关系的推断。因此,生物进化论自从提出以来,不仅饱受生物“神创论者”及保守思想家的嘲弄和攻击,而且也频遭崇尚实证主义的科学界的质疑和非难;他们的致命武器是:请拿出进化的证据来!在这种严峻情况下,从1973年开始,富有使命感的格兰特夫妇不畏艰辛,年复一年地带领学生,来到达尔文最初获得进化论灵感的地方——加拉帕格斯群岛,在达芬·梅杰岛上进行观察、测量,然后带着收集的数据回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分析研究。经过20年的持续观察和分析研究,格兰特夫妇的雀鸟研究团队终于拿到了活生生的进化证据,证明了达尔文进化论是正确的。韦纳的《雀鸟之喙》就是对此漫长科研历程的详细描述。这一描述形象地展演了进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捍卫了达尔文进化论,从独特的角度重新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
格兰特夫妇主要研究达芬·梅杰岛上的大、中、小三种地雀。自然环境对三种地雀的生存和形态变异的影响,在极端的气象条件下表现得最为明显。1977年是达芬·梅杰岛最为干旱的年份,全年滴雨未下。格兰特夫妇观察到,各种植物都不能开花结出新种子,三种地雀不得不寻觅1976年产出、被吃剩下的大而硬的种子——蒺藜。饥饿致死对岛上只能吃软小种子的地雀打击最大,对喙较大的地雀的打击最温和:中地雀的数量下降了85%,小地雀的数量下降了90%以上。生存下来的中地雀种群的喙的平均大小,比1976年的中地雀种群的喙的平均大小,大出5.6%。然后,通过遗传,下代地雀的喙有增大的趋势。
但比较干旱的年份不会永久持续下去。在雀鸟观察队的焦急等待中,1982年年末,达芬·梅杰岛一带出现了多年不遇的最大降雨量。岛上的植物生长茂盛,到1983年6月,植物种子几乎是前一年的12倍,其中软小的种子占多数,因为多雨适合较小植株的生长。结果,雀鸟数量迅猛增长,而且,“自然选择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了作用。身大喙大的雀鸟在消亡,身小喙小的雀鸟兴旺发达了起来”。[1]104原因是,大地雀和喙较大的中地雀啄食小种子时比较笨拙,而喙小的地雀较适合啄食小种子。在一般情况下,大、中、小三种地雀之间极少交配,但在雨量大、生存条件较易的情况下,偶有中地雀与小地雀交配,甚至与仙人掌地雀交配。这表明,大、中、小三种地雀,乃至仙人掌地雀,并非完全独立的物种,而是正在形成中的物种,因为生殖隔离(在自然条件下互不交配)是区分不同物种的主要标志。总之,多雨的自然条件使雀鸟的喙向小的方向变异。
达芬·梅杰岛上多雨年份之后又是数年干旱。岛上“久旱逢雨”式的气候,决定了地雀的喙既不会一直向大的方向进化,也不会一直向小的方向进化,三种地雀更不会因个别个体的杂交而出现融合现象,而是呈现分化的大趋势。地雀之喙的差异,使其在岛上经常出现长期干旱的自然环境的生存压力下,在寻觅极其有限的食物时的无声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彼得·格兰特在上述观测基础上认为,聚集在同一岛上的地雀为觅食而进行的无声的生存竞争,“迫使其后代出现分化……竞争使雀鸟向新物种的产生迈进了一两步”。[1]156在韦纳看来,格兰特夫妇的雀鸟研究团队所观测到的“活生生的”进化生态过程是:达芬·梅杰岛“久旱逢雨”式的自然环境不断引发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喙能适应相应环境的地雀幸存下来(适者生存)——适应环境的形体特征不断遗传,导致越来越明显的趋异进化——出现新物种;而且,这一过程即是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证据。
需要强调的是,达尔文是“在过去两、三个世纪的生态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人物”,没有另外一个人像他那样“对西方人的自然观念有着那样大的普遍影响”;[5]而“1993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将近半数的美国公民不相信进化论,而相信现在的生命形式是上帝在1万年前创造的”。[1]295-297因而,1994年韦纳《雀鸟之喙》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生动、详实的描述,使进化生态学家格兰特夫妇的雀鸟研究团队20年辛勤努力的科研成果——“活生生的”进化证据以及相应的进化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走向大众,使达尔文的进化生态思想再次焕发青春。就是说,该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通过展演进化生态学家的最新科研成果,在达尔文首次撼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使大众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自己的本源,以及在生物圈中所处的位置:与其他物种一样,从原初的生命体进化而来,是生物圈生态共同体的普通一员。
二
韦纳在展演达芬·梅杰岛上大、中、小三种地雀进化过程的生态机制时,除描述当地的气候条件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外,还揭示了人类活动对生物的生存环境和进化进程的影响。他叙述说,根据格兰特夫妇的观察,圣十字岛的阿约拉港由于人类定居,具有比较丰富的水和食物,使周围的雀鸟大量繁殖,生存竞争的强度减弱,导致了类似1982年该区域的大量降雨那样的效果:雀鸟种群增大,而且杂交雀鸟增多。在无人定居的岛屿,多雨后的连年干旱,可使有融合趋势的地雀再出现分化,但人类改变自然环境造成的地雀融合趋势,却不会逆转。格兰特推测,在圣十字岛,“人类能破坏雀鸟分化与融合的均衡”。[1]241这表明,作为生物进化历程和生物圈居民中的后来者,人类即使无意中改变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也会影响现存生物正常的趋于分化的进化过程。
韦纳认识到,人类这一后来者的一些无意的行动,也能导致不少物种的灭绝。他举的例子之一,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超大雀鸟的灭绝。他写道:“人类的到来给当地生态带来了冲击。基本可以断定,岛上修建的殖民地监狱是超大雀鸟灭绝的原因。”[1]245他阐释说,三百多名厄瓜多尔流放囚徒被迫在岛上开荒种地;他们带来了牲口、山羊、猪、猫和田鼠。尽管他们很快被撤走,他们带来的动物却留了下来,世代繁衍。他引用彼得·格兰特的观点:“这种鸟的飞行技能可能很拙劣,容易遭到猫和鼠的捕食”;但更关键的原因是,超大雀鸟以圣十字岛上的超大仙人掌种子为食,由于被囚徒遗弃的牲口的践踏,“岛上的仙人掌所剩无几。没了仙人掌,超大雀鸟就失去了生存条件”。[1]245-246就是说,后来的人类无意中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毁坏了超大雀鸟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了它的灭绝。
韦纳还引述格兰特夫妇的研究成果,揭露人类现当代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对大气环境及生物进化的重大影响。彼得·格兰特认为,人类近百年的生产和生活排出过量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气温升高导致太平洋的洋流异常,引发1982年末反常的“厄尔尼诺”现象,致使西太平洋1983年发生大旱,东太平洋发生大涝,殃及加拉帕戈斯群岛,从而影响达芬·梅杰岛上雀鸟的正常进化,使其从分化转向融合。格兰特夫妇推测,要使岛上的雀鸟再分化到原来的状态,“可能需要100年,而在这期间,大、中、小三种地雀可能会融合成一种鸟”。[1]271不难看出,在现当代,人类对环境和进化的影响的范围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
韦纳通过讲述当代人滥用农药与抗生素,分别诱发烟蚜夜蛾与细菌进化出更强的抗药性的故事,进一步彰显人类由于对进化生态知识的无知或无视的严重后果。在1940年以前的美国,烟蚜夜蛾生活在树林和灌木篱中,靠吃野草为生。1940年,棉农开始在田里喷洒DDT,杀死了许多昆虫,也使许多吃虫子的飞鸟一命呜呼;棉田没了昆虫及其天敌,烟蚜夜蛾纷纷从森林和灌木篱墙飞向棉田,吞食棉花。有些夜蛾能抵御DDT活下来,其后代逐渐进化出越来越强的抗药性;虽然农药的毒性和用量不断加大,这种蛾子却继续危害棉花,以致路易斯安那州的棉农说“不想种棉花;虫子会把棉花一扫而光”。[1]253韦纳引用研究进化的博士后泰勒的说法:“棉农要求禁止宣传进化论,可他们的棉花却因进化大受其害。”[1]255相似的情况是,五十多年来,人类也一直对自己体内的生物细菌滥用抗生素,使其针对抗生素的抗药性与日俱增。韦纳引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罗德的述说:“‘1941年,每天给病人注射4次,每次注射1万单位青霉素,4天内就可以使患有双球菌肺炎的病人痊愈。’如今病人每天的用药量达2400万单位青霉素,却仍会死去。‘细菌比人聪明。’”[1]259-260韦纳因而指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我们对一个物种盲目发起攻击,就会引发进化,进化的方向往往与我们的期望相反。”[1]262这充分表明了人类对进化生态知识的无知或无视的后果:滥用农药和抗生素,不仅破坏了昆虫和细菌原有生存环境的生态平衡,使其天敌——相关鸟类和人类自身的免疫力丧失殆尽,而且给昆虫和细菌的生存造成压力,使其进化出更具抗药性的后代,带来更大危害。
另一方面,韦纳严厉谴责转基因工程师滥用进化生态知识,有意地操纵生物进化,“制造多样化”。他讽刺说:“他们创造了新玉米、新水稻、新细菌、新豚鼠(一种具有专利的实验动物)。如果公众不反对的话,他们还想用同样的工具和技术重新塑造人。”他严正指出:“人类加速生命的核心进程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对进化科学很及时,也很痛苦。我们改变生命环境的速度越快,遗传机制的变化也越快。所有这一切就是所谓的G.O.D.——多样性产生,同时也是在制造毁灭。”[1]274-275显然,他坚决反对人们通过滥用进化生态学知识,去干预生物正常的生存环境、存在形式和进化过程。他认识到,人类既要重视进化生态学知识的重要意义,又不能滥用这些知识。诚如美国生态批评家格林·A·拉夫所指出的:“捍卫科学并非支持打着科学的幌子犯罪——如失控的技术那样,而是要肯定科研方法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世界、找到解决日益恶化的污染、人口爆炸及环境掠夺等的最好手段。”[6]
韦纳还引述植物学家埃德加·安德森和里德亚德·斯特宾斯的观点,昭示人类这一“生态新主宰”肆无忌惮、僭越大自然的行为的灾难性后果。安德森和斯特宾斯认为,“近期野草和半野草的迅速进化表明,只要一个物种或多个物种在生态中处于主宰地位,就会使现存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地质史上曾经出现的情况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人类的影响下,“进化的速度大大加快”;这种事件“意义重大,表明了在生态的新主宰(人类)的影响下,进化的进程究竟能达到何种地步”;“我们正在重复恐龙做过的事情,只是速度更快”。[1]244就是说,已经进化出了超常能力的人类,若不限制自己的行为,将不仅仅会影响其他生物的进化进程,更严重的是,将会像恐龙那样,破环整个生物圈的生态平衡,进而殃及自身的生存。
在《雀鸟之喙》中,韦纳实际上已阐明了该部作品对现实的警示意义。他说,“当今,超乎寻常的变化使整个星球和所有生物以宏大的规模展示了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情况只是整个进程的缩影。”就是说,人类在现当代无意或有意的对环境的大幅度改变,导致了生物的生存状态和进化过程普遍的异常。他明确地指出这种异常的起因和后果:“许多变化是因人类的兴起产生的。人类是地球上的主宰物种,我们既是进化的起因,也是进化的结果——既是进化的主人,也是进化的奴隶”;“我们正在改变生存斗争的条件:改变与我们共生共长的所有物种的生存条件。//从来没有任何灾难是由单一物种的扩张而引起的,从来没有哪个主要演员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和结果,并产生罪恶感”。[1]276-277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和其他生物,乃至整个环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若对自己僭越大自然的行为无动于衷,必将自食其果。他警告说,人类的能力“使我们成功地驾驭了其他物种,但这种成功伴随着悲剧”;“如果一个物种的生存给周边的物种造成动荡,那么它自己也身居险境”。[1]289毋庸置疑,他力倡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存在物共生共荣,坚决反对人类过度地运用自己的能力,超限地改变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同生存的环境,肆意地消灭或制造物种。
三
《雀鸟之喙》还反映了达尔文以来生态学家生态意识的“进化”。达尔文认识到了特定区域的生物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物种起源》中的一些理念“标志着生态科学的确立”,[1]225但达尔文在行动上缺乏环保意识:他像同时代的大多数博物学家一样,为了研究,捕杀鸟类相当随意。韦纳透露,“1837年1月4日,达尔文把从加拉帕格斯群岛带回的鸟皮以及其他猎物全部捐赠给了伦敦动物学会”;[1]28在加拉帕格斯群岛考察时,达尔文“登上圣克里斯托尔岛的第一个小时,就用枪把鹰从树上打下来”。[1]224直到1952年,美国进化生态学家罗伯特·鲍曼“为了搞清楚雀鸟以什么为食,用猎枪打下几百只雀鸟,查看它们胃里的东西”。[1]145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生态思潮兴起之前,不少生态学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没能做到知行合一。
近几十年来,格兰特夫妇的雀鸟研究团队及其他的进化生态学者形成了很强的环保意识。据韦纳描述,在二十余年的研究中,格兰特夫妇的雀鸟考察队采用鸟儿看不见的透明网笼捕鸟,测其喙长及体重,在其腿上套上轻便的标号环,或取其血样,进行研究,然后放生。此后再数次捕来做跟踪研究时,仍用此法。进化生态学家多尔夫·施吕特推测,两种不同的刺鱼间的差异是由竞争选择形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需要用自然湖里生长的两种刺鱼作实验——把其中的一种取走,看另一种是否向中间形态进化;但鉴于该种刺鱼已收录在加拿大的濒危动物名单上,他特地“在校园挖了13个池塘”,[1]188把两种刺鱼放养其中,作长期实验。这样,无论是达芬·梅杰岛上的地雀,还是自然湖里的刺鱼,都没遭到研究者的伤害。
即使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当地居民,也清楚雀鸟研究人员的护鸟意志。据当地的导游讲述,他居所隔壁的一个老太太,以雀鸟损害其庄稼为借口,偷偷捕杀雀鸟,烹其肉吃,还熬汤喝,但话锋一转:“这是违法的!研究站里的人非找她算账不可!”[1]237-238
不仅如此,研究站的工作人员还呵护整个海岛上的生态平衡。他们正在努力拯救岛上的各种动物,包括蜥蜴、象龟和黑腰海燕。每次从圣十字架岛到达芬岛的登陆礁和热那亚岛的达尔文湾时,格兰特夫妇都格外小心,以免把怀孕的火蚂蚁带到岛上。“火蚂蚁能杀死所有蝎子,大概还能杀死所有蜘蛛,”彼得·格兰特说,“由于海岛太小,蝎子和蜘蛛可能会绝种。”“如果它们杀死蝎子,熔岩蜥蜴能否活下去也成了问题。”他们反对在岛上建度假村或旅店,因为这样会“把外面的植物、昆虫、老鼠和猫带进来”;若“再引进鹦鹉和相思鹦鹉”,“那就把达芬岛和热那亚岛全毁了”。[1]247-248这些进化生态研究者非常清楚,一个地区的生物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整体;带进外来物种,将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使原有物种面临灭绝危险;而且,他们把生态意识付诸实践。
韦纳对当代生态学者的生态意识和环保实践的生动描述,建构了人类善用科学知识,和大自然共存共荣的生态存在典范,不仅可以增进公众的生态意识,而且也为公众树立了行动示范,引领大众善用进化生态知识,呵护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生存与繁衍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类自己“进化过程中的伙伴”。
综上所述,《雀鸟之喙》展演了进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根基上再次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使公众明白人类的本源以及在地球生物圈中所处的位置。同时,该部作品警示人类,人类的活动,无论是由于对进化生态学知识的无知,还是滥用,都会超越人类应有的位置,僭越大自然,从而产生严重后果。此外,该作品彰显了进化生态学者生态意识的“进化”,引领大众要善用进化生态知识,呵护自然环境和“进化过程中的伙伴”。显然,《雀鸟之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是一部优秀的绿色科学散文作品。这些生态意蕴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和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既要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又要坚决杜绝滥用科技和人类能力的行为。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何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教授高度重视同时蕴含科学知识和生态伦理的文学作品的创作、研究和教学,并指出:要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在读者中培育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并将可持续的价值观植其心中,“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架起文学与科学之间的桥梁”。[7]
参考文献:
[1]Weiner, Jonathan. The Beak of the Finch: A Story of Evolution in Our Time[M].New York: Vintage Book, 1994.
[2]Keller, David R, Frank B. Colley. The Philosophy of Ecology: From Science to Synthesis[M].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243.
[3]王智翔. 进化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J].生态学杂志,1989 (6): 52-55.
[4]王崇云. 进化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
[5]唐纳德·沃斯特.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蕙,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145.
[6]Love, Glen A.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M].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46-47.
[7]Slovic, Scott. Going Away to Think: Engagement, Retreat, and Ecocritical Responsibility[M].Reno &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2008: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