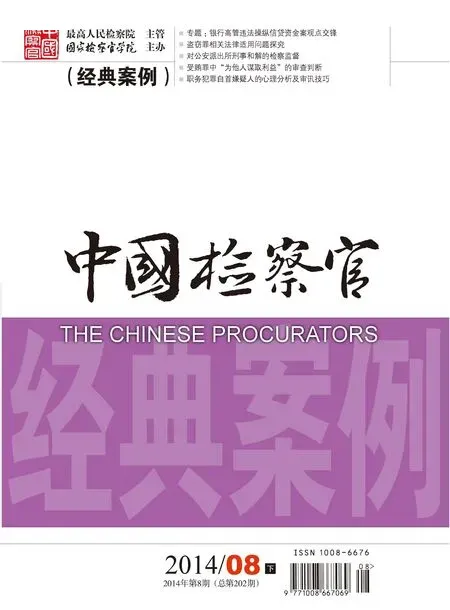强制医疗程序中严重危害行为的标准及继续危害可能性的实践把握
文◎付继博季松博
强制医疗程序中严重危害行为的标准及继续危害可能性的实践把握
文◎付继博*季松博**
本文案例启示:强制医疗案件中,对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理解,司法实践中宜采《刑法》第20条的标准,危害行为未得逞的也可依据行为危害性决定强制医疗。判断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是对未来的判断,不能采用“确定性”而应采取“盖然性”的标准。
[基本案情]涉案精神病人董某某于2013年7月3日凌晨,至海门市临江镇丁陆村8组樊某某家,欲对樊某某实施奸淫,被发现后逃离现场。2013年7月13日早上6时许,董某某至海门市临江镇丁陆村6组邓某某暂住地,欲对邓某某实施奸淫,因邓某某大声呼救而逃离现场,当晚董某某再次进入邓某某暂住地,窃得现金人民币300元。2013年7月20日凌晨,董某某至海门市临江镇丁陆村6组张某某暂住地,欲对张某某实施奸淫,因张某某大声呼救而逃离现场,后被张某某丈夫尚某某抓获。经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鉴定,董某某罹患精神发育迟滞(中度),无刑事责任能力,作案动机是出于满足其原始低级本能的生理需求。
一、司法实务分歧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目前对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标准及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把握尚无司法解释,因此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认定存在一定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董某某的行为(多次欲强奸但未遂)是否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程度,董某某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是否应当对董某某强制医疗?对此,有以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当对董某某强制医疗。董某某虽然实施了强奸行为,但均未遂,且其本身不具有暴力攻击性,只要监护人严加看护,即可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也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对董某某强制医疗。董某某多次实施强奸行为,既能证明其行为的严重性,也能证明其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二、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对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理解,司法实践中应采《刑法》第20条的标准,危害行为未得逞也可以依据行为危害性决定强制医疗;判断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是对未来的判断,不能采用“确定性”的标准,应采取“盖然性”的标准。
(一)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标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一读稿”)曾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仅适用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众安全或致人死亡、重伤的精神病人。在法律修改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司法实践中精神病人致人死亡、重伤案件较少,多数精神病人行为的危害后果并未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但有的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其危害后果虽未达到致人死亡、重伤的程度,却同样具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险性,法律规定不宜过死。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包括致人死亡、重伤的情形,但并不限于此两种情形,也包括其他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并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1]从立法过程来看,可以明确的是严重程度不仅限于死亡、重伤,但司法实践显然需要更加具体的标准。
首先,从法律精神来看,危害行为应当达到刑法规定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程度。《刑事诉讼法》第1条(任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强制医疗虽然是特别程序,但也应当受《刑事诉讼法》总则的指导,从刑诉法的任务来看,只有受刑法调整的行为才适用刑诉法,如果行为还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自然不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其次,并不是所有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都系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应当严格依据刑法条文的精神,对于何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进行解释。对此,刑法总则中恰好有类似表述,《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对行凶的理解,理论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行凶”可以成为进一步明确“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行为标准。我们认为在出台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前,严重危害行为的认定可以参照刑法第20条,即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与这些行为严重程度相当的暴力行为。
本案中,涉案精神病人董某某的强奸行为虽未得逞,但从其行为来看,已经达到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标准,且行为严重程度达到《刑法》第20条的标准,故董某某的行为虽未得逞,但已达到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标准。
(二)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判断
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危害可能性的判断还是要依据现有的证据材料来判断,但应当采取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具有较高的可能性。“盖然性”这一概念,与“确定性”相对,意味着认知未获得确定性知识之前的状态。
第一,盖然性相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低,但是符合强制医疗程序案件的特点。强制医疗程序并不是对涉案精神病人的惩罚,而是预防和保护的结合。因此,只要存在较高的可能性就应当决定强制医疗,如果僵化的按照刑事案件的标准进行判断则违背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初衷,可能会再次上演卢祥文式的悲剧。[2]
第二,在世界范围内,目前的医学技术依然无法对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准确判断和预测,[3]司法实践中有法官要求对危害可能性做出鉴定,否则没有依据裁判,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混淆了证据证明与司法裁判的关系,要求对危害可能性给出确切的鉴定意见有推责之嫌,也是不现实的。虽然我国是条文法国家,但是法官还是拥有一定的裁量权,精神病专家或医生只能提供涉案精神病人的精神病种类、程度、治疗情况等信息,至于继续危害可能性的判断还是应由司法者根据案件的证据材料综合做出。
第三,强制医疗程序包含定期评估制度,以确保涉案精神病人的权益。《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强制医疗不像刑罚一旦发生错误即不可挽回,定期评估发现涉案精神病人好转不再具有危害可能性时可以立即解除强制医疗。
第四,对于危害可能性的判断,除了参考精神病鉴定和专家意见外,还要重视涉案精神病人相关亲友、邻居等人的证人证言及意见,对涉案精神病人的病史、平时表现、稳定性进行综合了解和把握。
本案中,判断董某某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应当综合相关证据判断,采取“盖然性”,而非“确定性”的标准。从行为看,董某某多次实施强奸行为,但监护人未能有效控制,有继续危害的可能;从鉴定意见看,其对女子实施强奸行为完全是出于原始低级本能的生理需求,没有改善;从相关证人证言来看,其智力水平很低,常常不回家,有危害可能性。
注释:
[1]孙谦、童建明:《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2]该案如下:四川省雷波县汶水镇狮子村2组村民卢祥文于2005年3月10日上午11时,用一把菜刀把母亲砍死在自己家中的床上,警方将其押解到成都市,委托华西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精神病鉴定,结论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他被警方释放回家,未对其进行强制医疗。2006年3月1日凌晨,他用“二锤”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全部杀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个精神病患者居然接连杀死四位亲人,而后一起案件本来可以避免。参见《法制早报》,2006年4月30日。
[3]纵博、陈盛:《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若干证据法问题解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226100]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员[22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