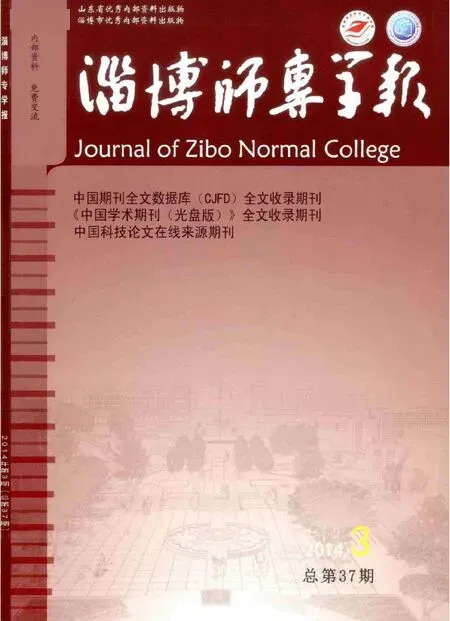从符号式人物到标杆式人物的转变——《左传》《列女传》中秦穆姬形象比较
郭 姣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秦穆夫人,是秦穆公的夫人,晋献公之女,太子申生的姐姐。秦晋向来有姻亲关系,遂有“秦晋之好”。秦穆姬在《左传》《史记》《列女传》等文本中都有记载,但各有不同,对此,我们不妨将《左传》和《列女传》中的秦穆夫人形象进行比对、分析,探寻二者的记载呈现不同的原因,进而分析她在《左传》《列女传》中所扮演的女性角色。
一、《左传》《列女传》中秦穆夫人的文本对比
在《左传》中,有关秦穆夫人的记载共有四处,分别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1](P238-239)《左传·僖公五年》记:“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1](P311)《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 纳 群 公子,是以 穆 姬 怨之。”[1](P351-352)“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罃、弘与女儿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绖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1](P358)
据《列女传》卷二《贤明传·秦穆公姬》记载:“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晋献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与惠公异母,贤而有义。献公杀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号公子夷吾,奔梁。及献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纳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被秦赂。晋饥,请粟于秦,秦与之。秦饥,请粟于晋,晋不与。秦遂兴兵与晋战,获晋君以归。秦穆公曰:‘扫除先人之庙,寡人将以晋君见。’穆姬闻之,乃与太子罃、公子宏与女简璧,衰绖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灾,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乃以兴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晋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图之!’公惧,乃舍诸灵台。”[2](P60)
从《左传》和《列女传》中对秦穆夫人的记载来看,可以发现文本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两者都记载了秦穆夫人的身份、地位。如,《左传》记载“晋献公……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列女传》载有“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晋献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其次,两者都记载了秦穆夫人劝晋惠公纳群公子,而惠公不用这一历史,展现了秦穆夫人的政治远见。如,《左传》有“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列女传》“始即位,穆姬使纳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再次,两者都记载了秦穆夫人为救父国不惜以死相争,表现了她舍身取义精神。如,《左传》有“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罃、弘与女儿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绖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列女传》“穆姬闻之,乃与太子罃、公子宏与女简璧,衰绖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灾,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乃以兴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晋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图之’”。
但是,《左传》和《列女传》在文本记载上又存在一些不同之处。第一,《左传》交代了秦穆夫人的出身,是“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即说明了秦穆夫人是“烝”婚所生的子女,而《列女传》对此并无记载。第二,《左传》并未对秦穆夫人进行直接的价值判断,可是《列女传》却是直接肯定她“贤而有义”。第三,《左传》记录了秦穆夫人的陪嫁情况,而《列女传》并无记载。第四,在晋惠公纳群公一事上,《列女传》加上了秦穆夫人的劝谏之词,直接体现了秦穆夫人之贤。第五,对秦穆夫人甘愿赴死救晋国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有不同,《列女传》中秦穆夫人的“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直接体现了她维护父国的角色。第六,《列女传》还对事件的结果进行了明确的说明,肯定了秦穆夫人的行为效果“公惧,乃舍诸灵台”,亦带有作者刘向的价值取向。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左传》《列女传》在对秦穆姬这一人物相关记载上呈现出诸多不同之处,这与作者的创作宗旨有很大关联。
二、《左传》《列女传》之创作宗旨
《左传》作为一部先秦史著,其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以人记事,力求以具体的见闻对历史现象作形象、直观的描述,以记言叙事来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而不是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作理论分析和情感评价。“《左传》作者深谙选材与写人的辩证关系,善于在历史人物自己的全部言行中选择最富于典型性的部分加以描绘,以使人物的性格特征随着 他富有特征 的 行 动突现出来。”[3](P93)《左传》在记事的同时描写了许多人物,但每个人物的描写都是以是否参加某个事件来决定的,所描写的人物往往也只是选取他参加事件的有关言语活动来表现,实际上只是展现其性格特征的某一个方面。但由于其注重记事,人物虽有一定的形象性,但不典型。所以《左传》的目的并不在写人,但却从侧面地展现了数以百计的女性人物,并用简练概括的语言文字反映了春秋时代的女性在国家政治大事、家庭生活以及婚姻方面的实际状况,展示了当时女性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人物如秦穆夫人在《左传》中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的,并没有蕴含作者太多的主观评价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却起到了意外的效果,正如刘知幾说的“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4](P156),即不说人物性格如何,其性格自然显现,不表明自己的主观爱憎,其爱憎自然明了。
到了汉代,史传文学方兴未艾,《史记》之后,中国的传记文学更是朝着史传文学和杂传文学两个方向发展。在此,我们就有必要谈一下《史记》对人物描写的开创性。《史记》的主要目的在于以人见史,从而达到对历史的再认识,所以“《史记》对人物的描写,是建立在对人物整个一生行为的概括上,是建立在对人物一生性格特征发展的提炼上,以集中而清晰的传记形式表现出来,人物形象因而是鲜明完整与典型的”[5](P33)。汉代杂史杂传继承了《史记》传统,所描述的中心是历史人物而不再是历史事件。而到了刘向的《列女传》更是直接给女性作传,将百余名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女性作为描写中心。所以汉代的传记作品突出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作者在表现人物和事件时,更多地注入了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认识和褒贬及好恶之情。据《汉书·刘向传》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6](P1857-1958)所以刘向写作《列女传》的动机是试图用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来规整婚姻关系,以达到“正世风”的目的。《列女传》记载了某些女性的嘉言懿行,对通才识德、奇节异行的女性进行歌颂,展示了从先秦到汉代的女性风采,并以此作为榜样,树立衡量女性行为的准则。但需要注意的是,刘向所说的“列女”并非后世所谓的“烈女”,清代的章学诚也一再强调,“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也,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7](P829)。至此,《列女传》中的女性不再作为一个符号式人物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榜样化形象来达到“布教化”的目的。
正因为《左传》《列女传》的创作宗旨不同,所以二者呈现出的女性角色也有不同。
三、《左传》《列女传》之女性角色
《左传》时期以“礼”作为评判标准,《礼记》相应地提出了对女性的具体要求,结婚前,《礼记·昏义》有:“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8](P917)即要求女性具有贞节恭顺的品德、言谈应对的技巧、得当的容态举止以及纺织、做饭等家务劳动技能。“按照传统,结婚是女子从娘家转到夫家。婚前她是父母的女儿,婚后她成为丈夫的妻。随此一转她有了新的责任和义务。”[9](P21)婚后,女性不但遵守日常生活的各类细节要求,而且必须尽心侍奉公婆、对丈夫忠贞不二。也就是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由此可见,春秋女性的地位不高。另外春秋女性一般不能过问国家大事,否则会被视为“非礼”。但是由于身份以及其他不同的原因,仍然有一些贵族女性跳出“送迎不出门”的礼教条框范围,热切关注国家大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到了《列女传》时期,社会关系中男尊女卑倾向、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仍然十分鲜明。由于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的进一步完善,汉代女性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婚姻关系和政治生活、社会活动中,而“妇女的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婚姻关系基本面貌的缩影”[10](P118),但同时时人对女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女性在“相夫教子”等家庭活动之外更要注重品德的培养,包括女性要深明大义、贤明仁智、贞顺节义、机智辩通等。
(一)婚姻选择中的女性角色
童书业认为:“周人‘同姓不婚’,此为氏族制残余,并遗留后世。春秋时贵族家庭犹保有甚浓重之家长制色彩,故男女关系较为通融,平辈间、上下辈间皆可发生婚姻关系,而最突出者为子承生母以外之诸母与弟之接嫂;此均家长制大家庭之特色。”[11](P313)《左传》记载了秦穆夫人的出身,“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即烝婚下所生的子女。由此可见,“烝”这种婚制在当时社会是得到许可的,并不以乱伦处之,它是符合周代“同姓不婚”原则的,属于合法婚姻。正如顾颉刚所论:“‘烝’这一事在春秋时代自有它的一定的社会基础,换言之,这是春秋时代被人公认的一种家庭制度,所以这种行为并不为当时舆论所贬责。”[12](P451)“烝”婚下所生的子女,同样享有合法的社会地位,仍可做诸侯的世子或嫡夫人。而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渐确立起来,小农经济成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封建制度下的伦理道德规范,不符合这一规范的“烝”、“报”婚制便逐渐消失了。到汉代,烝报婚等原始婚俗已基本绝迹,稳定的一夫一妻婚姻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封建伦理观念也被汉代思想家系统整理出来,所以刘向的《列女传》中对此就不再记述。因为社会的进化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提高,汉代人对血缘关系密切的亲族之间的通婚给后代造成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汉代的婚姻法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限制某些亲族之间的通婚,如后母和子之间。也就像顾颉刚所说的:“到了汉代,正值封建社会定型时期,那时的统治阶级严格地讲父子间的尊卑,男女间的有别,所以《礼记·曲礼》上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决不允许‘烝’制的存在。”[12](P451)因此,《春秋左传注》里解释说:“上淫曰烝。”“淫”,当然是被人所贬责的,而“上淫”,更是不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自然更不应该存在。
其次,《列女传》之所以不取此事是因为它无法集中体现秦穆姬的贤且义。从《左传》到《列女传》,两者都对春秋时代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在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及其精神面貌的一般情形。《左传》作为先秦的史传文学,记载了秦穆夫人的出嫁,“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汉代杂史杂传在体例上受先秦史传,特别是受《史记》传记文学的影响最深。”[5](P398-399)《列女传》作为汉代的杂史杂传文学,必然是在参照《史记》等传记文学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对《史记》文本记载的继承性不言而喻,所以在这里,一方面《史记》就可以作为《列女传》的补充材料来研究。《史记》在“厥协六经易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基础上同样对秦穆夫人的出嫁作了记载,《史记·秦本纪》有“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13](P186),《史记·晋世家》“其冬,晋灭虢,虢公丑奔周。还,袭灭虞,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13](P1647)。另一方面,刘向本人喜好《春秋左氏传》,所以有“刘向采《左传》中人物故事及其他先秦典籍史料辑成其《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中的部分内容”[3](P139)。值得注意的是《列女传》对“以媵秦穆姬”这一事件并无记载,由于“媵”这种婚制到汉代已经改变了,所以尽管刘向受《史记》影响颇深且喜好《左传》,但对此并没采取《左传》《史记》的相关记载,而是采用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异国通婚成为春秋各国最为常见的婚姻形制,其中的女性一出场,即被以各种名目、形式嫁到另一国,都是以顺应政治需要为前提的,都是为了通过姻亲关系来巩固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盟,所以也就有了“秦晋之好”这个成语。不得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贵族女性的确在政治活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减少了两国之间的战争,使列国形成新的政治格局。
(二)婚姻状态中的女性角色
《左传》和《列女传》都表现了秦穆夫人的政治远见,于此可能由于选材和历史、人物的原因,《史记》并无记载。如,《左传》“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列女传》“始即位,穆姬使纳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作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夫人,“侍君以色”之外还需“以德”,此外还需有必要的政治远见和胆识才能,这就为后面秦穆夫人勇于牺牲作了铺垫。在晋国和秦国发生冲突时,秦穆夫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全晋国的利益,并以死相拼,最终挽救了晋国的形势。正如《〈左传〉女性研究》所讲的那样:“这些女性在显现其重要意义的时候都已嫁为人妇,但当大事发生的时候她们却不约而同地以女儿之情彰显自己的家国情怀。她们的作为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对与错、是与非、智与愚来进行评断,因为来自父系的家族伦常已深入她们血脉,让她们无论何时都抛不下深重的家国重负,面对这一神圣的职责,牺牲夫与夫国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都已成为她们毫不吝惜的代价。”[14](P19)在父国与夫国的二难选择中,秦穆姬勇于牺牲自我来成全父国利益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令人为之震撼。客观地讲,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对其以后的生活状况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面貌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总之,如果说在《左传》中秦穆夫人是作为一个符号式人物出场的话,那么到了《列女传》,秦穆夫人就成为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了。《列女传》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将女性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类,而秦穆夫人被列在“贤明传”一类。据《列女传小序·贤明传》说:“惟若贤明,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循法兴居,终日无殃。妃后贤焉,名号必扬。”[2](P1)由此,《列女传》里更多肯定的是秦穆夫人的品行才德,即贤明。作为一般的女性人物,仁惠、慈爱有宽宏之德就是贤惠,而对于在政治上有地位的贵族女性来说,能够辅佐男性如父、夫、子,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就可称为贤能。《贤明传·秦穆姬》里称秦穆夫人“贤而有义”,这里体现的女性意识就更加明显,肯定了秦穆夫人富有仁贤之德,见微知著,深明大义。此外,《列女传》在末尾还添加有颂词,通过这种征引评论,直观清晰地表明了作者自身的叙事立场和褒贬态度,正如张涛所说的,“《列女传》颂首重以《春秋》笔法褒贬人物,感情色彩十分浓重”。据此,“秦穆姬”颂曰:“秦穆夫人,晋惠之姊。秦执晋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及将赴死。穆公义之,遂释其弟。”[2](P60)同时,《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必然与作者头脑中的女性意识观念密不可分,以此类推,作者的女性意识观念又必然与作者所处年代的女性意识息息相关。“妇女形象是在特定文化环境的期望和规范下形成的,侵润着作者头脑中的性别观念,既担当着社会文化为她们安排的社会性别角色,又承载着阶级(或阶层)、民族等赋予她们的责任和义务,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性别制度的内容。”[15](P1)秦穆夫人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显露出了女性的智慧和素养,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决和果断,以及轻己重义、有胆有识的精神,这与作者所处时代的女性意识是分不开的。所以,《列女传》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女性这一历史群体的关注,对她们在历史、政治、家庭、生活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从《左传》到《列女传》,则更多地投入了作者的感情色彩,对女性意识有了更多的展现。这些主要表现在:第一,认识到女性力量的存在,承认她们在国家政治和家庭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并歌颂了一些女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秦穆夫人;第二,要求女性要遵礼行义,但是一旦义和礼发生矛盾,难以两全时,礼则可以适当变通,以完成行义。由此,对历史上富有贞贤之德的女性的描述构筑了一种女性德行的道德标准,并极力以礼和义来规范女性行为。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3]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4]刘知幾.史通通释(卷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冯友兰.冯友兰经典文存[M].洪治纲(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10]彭卫.汉代婚姻形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顾颉刚.由烝报等婚姻形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A].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卷4)[C].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高方.《左传》女性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5]张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