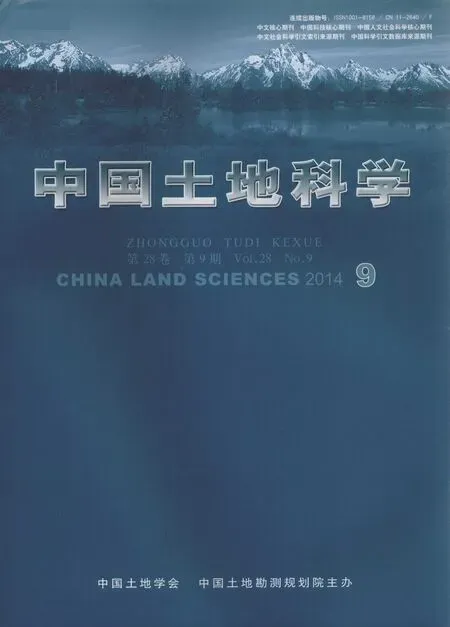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讨
——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圆桌论坛(2014)观点综述
朱道林,王 健,林瑞瑞
(1.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北京 100193;2.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北京 100193;3.国土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讨
——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圆桌论坛(2014)观点综述
朱道林1,2,王 健1,2,林瑞瑞1,3
(1.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北京 100193;2.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北京 100193;3.国土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研究目的:归纳总结“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圆桌论坛(2014)”的典型观点,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研究方法:综述分析。研究结果: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理论上尚存争议,但实践已在推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的权能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予以法律界定;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过度追求土地收益、非农非粮利用倾向。研究结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是改革的必然选择,需要进一步细化三权的权利内涵,探索三权的权能关系和实现形式;农村土地市场化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应防止过度资本化和非农非粮利用。
土地制度;土地政策与法律;农地改革;农地经营权;农村土地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等”一系列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安排,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在中国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实现城乡统筹的决心。然而,新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土地本身的问题,牵涉的是“农业、农村、农民”的整体问题,牵涉的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问题,甚至牵涉的是社会公平与稳定问题,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2014年9月20日,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圆桌论坛(2014)”,聚集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围绕“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一主题,共同解析和探索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方向。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论坛伊始的致辞中表示,现有土地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不可持续,改革的呼声很高,但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改革路径,仍需要加强研究,凝聚各方共识来共同推进。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历史环境,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着如何确保土地权利在各权利主体中合理实现、如何兼顾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如何完善农村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如何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一系列尖锐问题,对土地科学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1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由“两权”变“三权”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在论坛主题发言中表示,新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私有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后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相分离,承包经营权由政策调整到法律调整、由债权性质到物权性质,以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为标志,确认了这个时期的农村土地改革的成果。两权分离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人民的一项伟大创造。
针对当前的改革,甘藏春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两权分离的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方面,对农民来说,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要求要稳定,流转要限制;另一方面,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又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流转交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三权分制的思想,这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长期稳定,经营权要放开搞活,这就为推进农地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针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中央农办赵阳表示,根据2014年6月的调查数据,全国流转耕地面积约3.8亿亩,占全部承包地的28.8%,其中,出租和转包方式(非自耕农方式)占78.6%,完全转让承包权方式占6.0%,再次转让方式占3.2%,由此可见实践中三权分离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经营权不在承包者手里这种现象占比较大,涉及大概26.0%左右的农户。他表示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现象已经客观存在。
2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实践突破与现实困境
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的探讨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研发现,在农村集体土地转让、抵押、租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还未出台的情况下,北京、广东等地城市郊区大部分的村庄已经进行了土地的转让、抵押和租赁等活动,实践早走在了政策的前面,并形象地说,“这就类似孩子已经生下来都要上学了,但是还没有户口”。
对农村土地改革实践的讨论中,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正河教授提到,在过去几年中,对中国经济排名靠前100位的村庄经济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村庄经济好的地方,均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改革和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跟现行法律规定的制度有所区别。在广东、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或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切实好处,既能得到出租土地的收益,又能参与土地经营,实现就业保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进一步提到,土地的出租、转包、转让在中国农村地区已不鲜见,土地制度改革在实践中也在不断突破,但是在土地政策体系内和制度设定内还未作出明确的认定。
3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所有权实现困境
在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实现和表现形式的探讨中,甘藏春表示完善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核心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形式。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涉及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所有权的主体究竟是村还是村民小组,二是以什么样的财产组织形式来构建农村集体所有的实现形式。现在的研究多是借鉴企业制度来解决集体土地所有制问题,所有制本身的前提是带地入股,当年实现合作化是带着土地入股的,有股份性质,也有强烈的身份性质,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问题还在于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财产组织形式。总之,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核心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形式。
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在主题发言中提到,1980年的中央文件在强调“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前提下,允许各地探索多种经营形式。1982年“一号文件”也是在强调“中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前提下,承认“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1983年中共中央文件在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合理性的同时,也强调“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自此,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避免了因道路之争而夭折,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得以在全国普遍化。
刘守英认为,此后的制度完善也是搁置所有权、强化承包经营权权利体系的努力,包括在政策和法律上将家庭承包制确立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明确土地家庭承包制权利内涵,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承包权与承包经营权分别赋权。然而,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建立、被承认、普遍化是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允许承认使用权权能的改革。那么,继续搁置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仅仅在“三权分离”上做文章,难以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制度问题。继续沿着两权分离改革逻辑,延伸到三权分离,搁置集体所有制问题,在法律和制度运行中都面临困境。
刘守英进一步分析,根据《物权法》的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明确为“成员权”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土地作为一种不动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应属于所有集体成员,也就是说,集体所有制变成成员共有制。每个集体成员的承包经营权由集体所有成员确定分配方案后委托给集体组织发包而来,因此,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有期限的用益物权,享有法定期限内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农地农用范围内的转让权包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是法律赋予承包经营权的一束权利,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但是,这套法律制度安排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集体所有变成成员所有后,集体成员受法定人口增减变化影响,成员资格变动就产生变动集体土地和收益分配的要求;二是集体所有土地与承包土地的发包关系,即土地承包权是债权,不是《物权法》旨在赋予的财产权;三是集体组织作为土地发包方,接受集体成员土地发包和收益分配、处置的委托,造成委托代理问题;四是尽管土地转让权从承包经营权派生出来,但是对于土地转包主体(原承包人)与土地接包主体(经营主体)的权利责任关系没有清晰的法律表达。因此,集体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与流转经营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利规定是残缺的。
4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能关系尚存争议
在对承包经营权进一步的讨论中,甘藏春表示,虽然社会认为承包经营权应该放开,但是必须考虑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关乎社会稳定。一是承包经营权放开进程和中国城市化速度相协调,二是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应有法理界定,可否借鉴英国的Free Holding的地权制度,值得研究。
刘守英认为,从法律层面上看,在《物权法》中有关农村土地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是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层。其次,在所有权层面规定,所有权是“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等”,“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最后,在“承包经营权”层面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等,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不得收回承包地”。
针对如何改革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刘守英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集体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在成员权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固化成员权身份资格,落实“长久不变”,变有期限的承包制为无期限的土地制度。另外,还要强化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属性。在改革集体所有制的同时,改目前集体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发包承包关系,集体所有成员使用自己的土地,长久不变实施后,土地即为固化后成员的财产。完善土地使用权赋权,含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担保抵押权、继承权。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任大鹏教授认为,从经营权的由来看,中国经营权是国有企业对国有财产行使的权利,并认为土地中的经营权仅是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权能而已,跟承包经营权、所有权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能上升到权利的角度。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朱启臻教授在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上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从农村土地的功能解析,一是保证国家农业安全。农业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发财的工具;二是保障农民生活。研究集体土地权利要从农民角度去思考,进行土地流转,只有在农民不需要土地保障功能时才需要流转土地。政府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会伤害农民、伤害农业。由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与经营权利是一体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不需要分离,承包权和经营权代表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而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
对此甘藏春表示,放开搞活经营权是当前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放开搞活经营权关键是要厘清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之间的权能关系。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关系,承包经营权是所有权派生的用益物权,所有权对承包经营权的处置和收益存在制约。《民法》中关于所有权和地上权的理论关系可以适用于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关系,但也存在很多特殊性。关于承包经营权和经营权的关系,承包经营权已明确为用益物权,那么经营权到底是债权还是物权呢?假定只是债权,那么抵押、担保在法理上说不通。经营权放开搞活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抵押、担保的问题。那么,抵押的到底是什么,应该在经营权权能上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民法和物权法理论。
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问题,赵阳表示,虽然现行法律规定承包地不能进行抵押,同时《担保法》第75条规定债权、股票等可以用来质押,即经营权的收益权可进行抵押,但第74条同时又规定,质权和债权不能同时存在,质权消失的同时债权也消失,因此,难以解决抵押融资的问题。承包经营权不允许抵押,但其派生出来的经营权却允许抵押。反映到现实中即是这样一个困境,农民不能将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但其转包给他人之后却又允许抵押了,这似乎难言合理。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咨询委员黄小虎针对土地抵押,认为抵押是一种市场行为,是银行向用户放贷,是合约关系,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应该由银行来考虑抵押物是否具有还贷的前景,从而由银行确定能否抵押。对于国有土地抵押而言,中国《担保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抵押,但目前政府征地后并未出让土地就将土地进行抵押,严格来说,“法无许可,就是禁止”,那么这一行为就属于违法的,但对于银行而言,政府信用抵押的贷款就是优质贷款。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志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分离主要是用于支撑土地流转,这一问题的症结主要是抵押和担保。在中国人均耕地那么少的情况下,银行并不看重经营权的抵押,因此,可以回避抵押这个问题,认为经营权只是支撑流通、规模经济和农业效率的提高,而不作为抵押物。对于在不抵押的前提下,农民如何获取资金则可以解读为技术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解决农民的资金问题,如国际上的小额贷款,或由政府成立专业担保机构,让商业银行放心地为农民、农业贷款。他表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抵押问题还是有解决途径的,因此,回避了抵押问题后三权分离还是正确的。
5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论坛研讨中,与会专家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推进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具有某种共识。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朱道林教授在主题发言中表示,农村土地市场化是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严金明教授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应是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私有制。当前,私有的观念比较流行,特别是经济学家从供需的角度认为私有的配置效率最高,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最高呢?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土地问题的影响因素较多,既有社会因素、经济因要素,又有政治因素等。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认为,可以从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为切入点,对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出发,土地市场化过程中私有制未必是有效的。
朱道林教授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应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资源再配置,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土地生产功能的充分发挥,改革过程中必须防止土地过度资本化、地价过快上涨、土地过度增值等对土地生产功能的影响和制约。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改革过程必须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土地生产功能与投资资本功能的关系,二是土地流转收益与土地用途管制的关系,三是工商资本下乡与农人经农的关系。关于这三个关系,朱道林教授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农村土地应该市场化,但基本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资源有效配置,必须防止过度资本化对土地生产功能的冲击;第二,农村土地应该流转,但是必须要符合用途管制要求;第三,农村和农业发展需要工商资本的支持,但是要防止工商资本在农村圈地获取更高的非农经营利益。
北京大学林坚教授认为,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上看,经营权分离出来主要是用于支撑土地流转,满足市场机制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
针对农村土地市场化的问题,张正河教授介绍,通过对比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土地用途收益差别可以看出:在发达地区,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效益较好,但把土地转为工业和房地产用地效益更高;在粮食主产区,即使用于房地产开发,跟发达地区相比土地收益仍旧较低。另外,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中部地区所受冲击更大,且恢复时间较长。因此,他认为,中部地区的土地可以主要用于粮食生产,尽量避免其向工业、房地产开发用途转变;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可将其工业和房地产开发的收益在全国层面进行调整,以补贴粮食主产区。
朱道林教授结合在福建、江西、上海等地的调研数据分析认为,土地流转以后的利用变化基本是从大田农业向高端经营转变,从种粮食作物向种经济作物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土地流转必然引起非粮、非农利用,因此要鼓励与引导土地流转,但是流转以后必须符合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要求,要制约非粮利用,制止非农利用。如何制约?首先,对于非粮利用,需要开展基础研究,如基于大数据的粮、菜、果、经需求比例,为确定生产比例提供依据,进而出台政策进行种植结构引导与控制。其次,对于非农利用,要进行严格的规划管制,同时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实施增值收益的税收调节,并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
(本文责编:仲济香)
Outlook for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Land System Reform: Reviews from“Roundtable Forum for Land Policy and Law 2014”
ZHU Dao-lin1,2, WANG Jian1,2, LIN Rui-rui1,3
(1. Department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 The Center for Land Policy and Law, Beijing 100193,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Land Quality,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Beijing 100193, China)
The Center for Land Policy and Law, affiliated i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ld a “Roundtable Forum for Land Policy and Law 2014” on September 20th in Beij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participator's presentations in the forum. The agreement with all the researchers in forum is clearly that even there were many practice, the controversy of China's rural land tenure reform exists in the theory.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right, contracting right and management right of collective land in rural areas needs more research and legislation. What need to keep watchful views is the trends 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farmland. It is inevitable to separate rural land right, but we need more attentions to clear the significant connotation for the land. We can use the market's power to make the land resources use more efficient, but also need to prevent the over capitaliz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ization forcollective land in rural areas.
land institution; land policy and law; collective land reformed; collective land management right; rural land system
F301.1
A
1001-8158(2014)09-0089-06
2014-09-22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资助项目(201211001)。
朱道林(1966-),男,安徽金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与土地政策。E-mail: dlzhu@c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