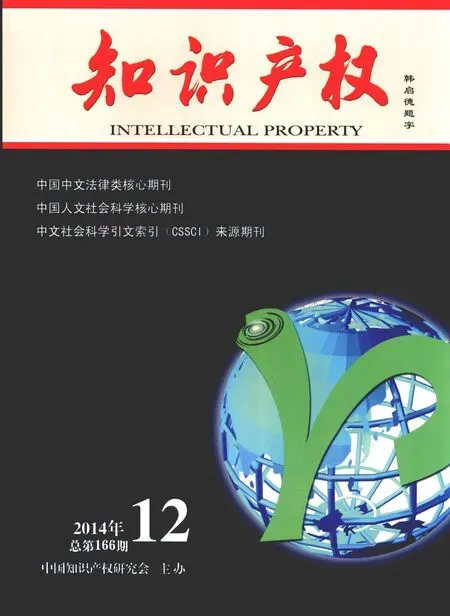传统植物药的可专利实用性研究
陈 庆
传统植物药的可专利实用性研究
陈 庆
通过利用现代制药技术萃取植物药中的有效物质成分申请专利已经为各国专利法所普遍接受,但该角度的专利保护无法为基于传统知识披露的传统植物药提供全面合理的保护。对于传统植物药以传统知识形式披露的药物价值用途可以成为医药用途专利,对其实用性的考察应从“产业可利用性”到“有用性”的演化过程入手,以期符合传统植物药医药用途专利的实用性要求。
传统植物药 专利 实用性
引 言
传统植物药区别于生态意义学上的普通植物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植物本身所蕴含的药用价值,并且这种药物价值用途是以传统知识的方式所披露,这一点也是区别于以现代制药技术萃取药物有效成分的现代植物药的不同所在。
传统植物药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及宗教环境因素,对其药物价值用途的揭示并不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其体内具有治疗某种疾病用途的物质认识的结果,而是经过千百年传统部族、社区基于特殊的宗教信仰、人文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基础上对某种植物的反复实践,从而证实其具有治疗某种疾病的医药用途,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就是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于传统植物药用价值用途的认识过程。在专利领域,将过去从未被用于治疗疾病的某种已知物质用于治疗某种疾病称为第一医药用途。作为传统植物药来说,在人类未发现其药用价值用途之前,其只作为生态意义上的普通植物而存在,人们对于这种植物药存在的认识与否,则取决于人类的认知程度。但不管怎样,我们假设,这种植物的医药用途是人类新发现的,或者说是人类早已经发现的,但尚未被公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植物药符合专利法上所说的第一医药用途。
以传统知识披露的传统植物药,其医药用途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则是仰赖于一种特定的信仰体系,治疗时通常是以人工操作方式对传统植物药进行加工、处理,因此,治疗经验因人而异,很难达到一致,从工业意义上来讲,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传统知识的创新并不能像遗传基因一样可以采用定量化或克隆方式确定下来。对于传统植物药的医药用途而言,其是否具备专利法上所说的实用性,值得研究。
一、从“产业化利用”到专利的“有用性”分析
在判断一件发明创造是否可获得专利权,首先要判断的是该发明创造的实用性,《TRIPS协定》采用industrial application和usefulness/utility术语,industrial application即产业可利用性,也有翻译成工业化应用,各国对实用性的判断标准不一,但基本上都普遍接受产业可利用性/工业化应用这一标准。而usefulness/utility一般翻译为“有用性”或“实用性”,是美国等国家对发明创造实用性的表述,与欧洲国家的相关表述不同,不再要求发明创造能够被工业制造和使用,而重点强调发明创造的有用性。《TRIPS协定》一方面采用工业化应用术语,另一方面又以有用性与工业化应用实为同一意思备注,是否暗示其在试图寻求一种国际一体化标准的努力?a《TRIPS协定》在备注项里加入一条“are capa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译为产业上利用或工业上应用的可能性,与usefulness/utility有用性或实用性为同义语,通常是指某项发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复制成一个或多个原型,并且可以实现批量化生产”。
工业化应用到有用性的出现无疑是科技革命带来产业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物基因技术和一些方法发明创造无法挤入工业化应用的门槛,产业利益的驱动使得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敢于突破传统的专利工业应用性标准,进而变革专利实用性标准。美国的这一做法无疑也为我们应对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重新认识“实用性”标准提供了制度思考空间。在历史中,这种演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对于我们传统植物药专利实用性标准的建立有无影响,值得思考。
专利权理论基础是发明人公开其技术发明内容,以换取国家给予其一定期限的市场独占权。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讲,专利权的产生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如果发明的内容不能实施,不能产生经济效率,专利申请人便失去了申请专利的动力,因为对于专利申请人来讲,申请专利远不是获得一纸证书,而更多的是换取一定期限的市场独占权,以期产生经济利益回报。对于社会来说,公开的技术发明不能实施,不能市场化,也失去了保护其独占权的意义。
而工业化应用正是市场机制下的产物,可再现性与工业应用性两概念其实是来源于知识产权固有的市场机制,换句话说,这种发明是配合工业的机械化及其相适配的生产流水线要求量身定做的,bPatents and Plants:Re-Think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lation to the appropri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Uses of Plants(TKUP),S.J.D.Thesis,Dalhousie University,2001:320.Unpublished,转引自Chidi Vitus Oguamanam ,International Law, Plant biodivers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 Exam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Relation to Traditional Medicne,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pril10,2003,P310.知识产权保护的是发明专利的市场利益,而这种市场利益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所决定的,而不是农业经济时代小商品经济简单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因此可再现性与工业批量化生产的市场机制才是知识产权固有的本质特征。因此,这种实用性或有用性则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TRIPS协定》建立的最基本目的也在于发明者发明产品是为了销售并获得经济利益,而这正符合贸易的本质要求。
由此推导,专利的实用性完全可以由市场来检验,市场可以淘汰哪些专利申请不具有实用性。这一做法在20个世纪20年代中期被美国所接受,但是这一做法存有明显的缺陷,也不具有普遍操作性。当涉及到人用药品时,因关乎人体生命健康权的维系,我们无法等药品全部上市之后,看其市场运作情况再决定其是否具有实用性,这一做法不仅荒谬也极其危险,药品须经过药品监督机构的安全有效性检验才能上市,而这要履行严格的药品审查制度,无异于将药品专利的审查与药品安全有效性的评估等同起来,丧失了专利制度应有的激励功能。另外,实用性由市场检验的观点也无法解释一些可以获得专利保护但由于法律规定不能上市销售的发明创造,如国家禁止销售的武器。
实用性作为可获得专利权的条件之一,其立法最初的本意只是在于该发明方案能够实现,或有实现的可能,其发明的用途达到可以制造或使用的程度。有表述为具有产业上可利用的价值,或有供产业上可利用之可能等。这种可能的成立依赖于一种科学价值的判断。如德国法上对产业的可利用性强调实际上、市场导向的用途而为技术性格要件所涵盖,则此一要件应可包括一般所承认之可实施性,特别是该发明已完成而可被重复实施。所谓产业可利用性,只要该发明客体依其种类可被生产或使用以从事上述广义之企业活动即可。c许忠信著:《国际专利公约及发展趋势》,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出版,国立台湾大学科际整合法律学研究所编印2009年版,第32页。
“可以制造或使用”尽管解释为一种产业利用上之可能,但其工业化应用标准仍然未变,真正促成“产业化利用”到“有用性”的转变,其内在的动因则需要考察专利实用性应对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产业”领域的扩张。
传统的工业化应用/产业化利用经过几次科技革命发展,已经完全由原来的单纯机械制造业扩大到包括电力、化学、农业、渔业、畜牧业、医药、交通等领域。然而,对于某些产业领域,特别是涉及到服务业及医疗产业,因其工业化生产特征不甚明显,在国际上仍然存有争议。
有学者提出服务业是否属于此处所说的产业,反对者籍借因服务业很少借助利用自然力之技术思想,不赞成将服务业纳入到此处产业范畴。然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展中国家发明示范法》第116条规定,“对工业应用应做最广义的理解,包括手工业、农业、渔业和服务业在内。”由此可见,科技带来的进步使得“产业”界限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一种国际趋势。而后,诸如美国商业方法发明的出现又再次突破传统产业领域,纵观各国专利法对实用性的审查标准,唯有美国对商业方法的实用性审查,采用是否产生“实用的、具体的和明确的结果”作为判断标准。美国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将专利审查的重点从技术性(useful arts)转向了实用性(practical utility),而这其实是将公司的经营策略、管理方针、投资模式等原本属于“抽象概念”或“智力活动规则”不具有利用自然规律之力的客体,通过与计算机的结合而获得专利保护。d张平:《论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载《网络法律评论》2002年第2期,第145页。
在医疗产业方面,欧洲专利公约规定,人体或者动物体的外科手术方法或治疗方法或者在人体或动物上实施的诊断方法不应被认为是具有“工业应用性”的发明创造。在日本,人体之诊断、治疗及手术方法的发明被认为无产业上利用之可能性而不授予专利权,其成立基础即在于认为医疗非产业。e仙元隆一郎:《特许法讲义》,第52页,转引自杨崇森著:《专利法理论与应用》,三民书局出版2006年版,第90页。对医疗行为不赋予专利权,一般是出于其会阻碍公平适当与迅速治疗,在人道上并不适宜,而与产业上是否可利用性无关,更不能认定为医疗业非产业的结论。然而,在美国对遗传因子治疗却可获得专利保护,只要符合有用的标准,都可成立有产业上利用的可能性。美国对实用性的审查其仅要求该发明能够达到最低程度的实用效果即可,并不要求发明必须优于当时现有的产品或方法,而只要求其具有一定实用性而可供现实世界来使用,换言之,专利仅要求发明人提出一个新而不同的发明,并不要求其须较好之发明。
对美国来讲,产业领域的不断扩张导致其实用性审查标准的一再降低,特别是在生物基因技术、医疗方法的可专利性问题上,这反映了美国在应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已经将专利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竞争工具自始至终服务于产业利益的功利性一面。f张勇、朱雪忠:《专利实用性要件的国际协调研究》,载《政法论丛》2005年第4期,第91页。
受美国影响,为了能在生物基因技术和医疗产业领域搏得一席之地,欧洲专利局、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在其实用性审查标准中加入“有用性”条件。英国专利局在2002年公布的有关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申请审查指南中,对基因片断必须说明其具体和实在的功能(specific and substantial function),才成立工业可应用性。2003年受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技术的影响,借鉴美国实用性审查标准的做法,日本特许厅修改审查指南,放宽工业应用性标准,降低了医疗方法的专利性门槛。
二、传统植物药的专利实用性审查
很显然,依据上述解释,工业化应用和可再现性并不十分适合传统植物药,即使是审查标准只要求具有某种“可能”的产业化利用。传统社区的商业资本化较少,对传统植物药的处理其即不是基于严格的工业化标准,也不是基于商业价值,而更多的是一种生态体验。传统植物药不管是其种植还是收获,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文化习俗背景下发生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与之相联系的特殊信仰。换句话说,传统知识是可以某种方式再现的(或再生的),但这种方式一定是基于一种特殊的生态、社会和人文环境下才会再生。而对于传统植物药的治疗方法而言,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种治疗方法或经验,因此,传统知识对知识产权规则的挑战是十分明显的。gChidi Vitus Oguamanam ,International Law, Plant biodivers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 Exam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Relation to Traditional Medicne,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pril10,2003,P310.
上述观点是否成立,工业化应用标准能否为传统植物药所接纳?如果不能,产业领域的扩张导致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的改变是否会为我们提供另一个解决途径和方式,仍然需要我们对专利实用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一)“基础研究工具”对传统植物药实用性误区分析
传统植物药作为一种自然界已经存在的植物(不管是否被人们所认知)具有治疗某种疾病的用途,尽管我们目前并不清楚地知道该传统植物药体内哪一种物质或哪几种物质在发挥治疗疾病的作用,但我们无法掩盖其传统植物药本身的药用价值用途。对于某类已知的物质或物质组合物应用于某种疾病的治疗可以成为第一医药用途发明专利,符合专利法上的实用性要求。那么,对于这种传统植物药体内将来有可能予以挖掘并产业化的未知的物质,或者说这种未知的物质作为现在一种研究药物的基础工具是否符合专利法上的实用性标准,是我们解决满足传统植物药成为第一医药用途发明实用性条件的重点所在。
《TRIPS协定》第27条第1项要求发明专利须具有产业可利用性,此一要件是为了使专利权被运用到目前尚未被确定而具有实际运用可能的科学知识,例如不知其使用方法或使用目的。h许忠信:《国际专利公约及发展趋势》,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出版,台湾大学科际整合法律学研究所编印2009年版,第70页。因此,其对产业可利用性的标准可以是对未来某种知识技术可产业化的一种预期,是一种可期待的权利。而这种理解对化学与生物科技及传统植物药的发明较为有利,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很多物质并不具特定效用或者说目前暂未发现其有特定效用而仅是作为其他研究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尚未进入到应用研究,这时研究者并不知道该物质是否真的具有产业上的可利用性,为了保护后期可能存在的产业利用,研究者亟需通过专利权来保护后期市场的独占性,排除竞争对手,再对后期研究成果进行完善并予以市场化应用。
对于传统植物药而言,未知物质发挥着治疗某种疾病的作用,换句话说,在传统植物药体内一定存在某种可以治疗疾病的物质,只是由于技术有限目前尚不能进行有效的提取,对该传统植物药进行研究一定能够实现药物未来前景的肯定性预期,因为我们有着多数植物提取药物成分的成功经验,而我们只需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肯定这种预期即能满足专利法实用性的要求。对于这种解释看似存在合理之处,却存在明显的缺陷,撇开前面所述基础研究工具是否可以成立产业利用之可能性问题,传统植物药的模式为:某种植物具有治疗某种疾病的用途——植物体内存在治疗该种疾病的某种或某几种物质——这种物质是未知的。而基础研究工具的模式为:对某种物质进行研究——该种物质并未被完全揭示,这种物质具有可能治疗某种疾病的用途——该种用途尚未被完全证实,有待进一步研究。
很显然,通过这种模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模式存在的差别,对于基础研究工具而言,对某种物质的研究应该具备基本的认知,如对某化合物的研究,对其分子结构的模式应该已经基本清楚,一旦发现该化合物有着治疗某种疾病的特性,即使还不确信该化合物是否真的具有这一治疗疾病的用途,研究者也会立即寻求专利保护,但可能其寻求的只是对该化合物的保护而不是用途发明保护。而对于传统植物药模式来说,顺序正好相反,清楚知道某种植物具有某种治疗疾病的特性,但无法清楚地知道是哪种具体的物质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实现对未来产业可利用性的某种预期?
各国专利法对实用性的解读趋向于“具有在产业中被制造或使用”的可能,那么对于传统植物药而言,如果不知道哪种物质在发挥作用,也就无从实现该种物质制造药品的可能,更何况,对传统植物药的有效成分的提取也并非易事,需要上千次的反复试验排除,最终获取有效成分,然而获取有效成分之后能否制备成具体的药物仍然需要克服很多技术问题,于此而言,“皮之不存,毛将焉乎”。
上述这种缺陷无疑是明显的,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植物药“可以被制造或使用”可能性。然而,导致这种结论的最大原因在于我们重蹈了化学、基因物质提取和纯化的发明创造专利审查的误区,传统植物药的可专利性保护主题并不在于具体物质的提取和纯化的专利保护,而在于传统植物药传统治疗信息及其医药用途主题的专利保护,当然不能再次套用化学、基因物质提取和纯化的审查标准和方法。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发现了某种新的物质,但是却不知道它的具体用途,专利法也是拒绝对这种新的物质提供保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专利法不管是提供产品专利保护还是方法专利保护,其最终目的是物尽其用,可以通过对该发明创造的利用而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那么,对于某类发明创造来讲,用途才是最为最要的,由于用途具有非物质化特点,专利最初无法通过某种语言来保护这种非物质化形式的发明,只能借助有形实体予以间接保护,尽管我们后来发明了用途限定产品发明的权利要求,但我们仍然确信专利法通过保护产品进而保护其用途。而这种用途要达到实用性的标准并不在于工业化应用,而在于一种抽象的“有用性”理论适用。
(二)“有用性”在传统植物药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中的应用
尽管美国的实用性标准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宽松再到严格的过程,但其实用性的审查标准与欧洲各国所使用的“工业应用性/产业利用性”标准相比较而言,确实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美国专利商标局于2001年公布了实用性审查标准,要求发明创造须具有“具体的、实质的与可信的(a specific、substantial, and credible utility)”。
美国的“有用性”审查标准,使得美国在审查发明创造实用性条件时极少构成障碍,因为它仅要求该发明创造能够达到最低程度的实用效果即可。其并不要求发明创造必须优于当时现有的产品或方法,而只要求其具有一些实用性可供现实世界来使用。换句话说,发明创造的优劣并不是专利审查的范围,只要该发明创造达到新而不同就可以了。iR. Schechter&J.Thomas,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West, a Thomson business, St.Paul,2004,P62.这种实用性虽然不一定要考虑它的优劣,但是却必须是那些有真正价值(real word value)或者有实际用途(practical utility)的发明创造,它要求发明应该拥有可以识别的价值而对公众提供直接的有益用途(beneficial utility)。
那么具体如何评判这种实用性呢,USPTO专利审查标准为我们提供三个判断标准,即具体的、实质的和可信的。
具体的实用性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指发明申请保护的主题须是具体的,而不能是一种宽范围的表示;另一种是指发明申请保护的技术手段须是具体的,而不是无法实现的虚假技术手段。对于第一种理解,专利法侧重于具体物质的存在或具体方法和用途的存在,如某种植物可做药用于治疗某种疾病,但缺少对具体什么疾病的披露,则不被认为是具体的。
第二种理解更多侧重的是一种产业可利用性问题,即该发明能否被制造或使用,而没有体现美国专利法实用性之“有用”的特点。因此本文更趋向于第一种理解,应是指保护的主题应该具体明确,对于医药用途而言,这种用途须是具体明确的。依据《实用性指南》,具体用途(specific utility)是指所要求保护的客体的独特用途,而不是一个宽泛类别的发明所具有的用途,而这种用途应该是指一项现实世界的应用(“real world”use),如果这种用途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或证实的现实用途,则非实在用途(substantial utilities)。
实质的实用性,一般也有翻译成实在的实用性。英文substantial可以延伸翻译成大量的、有充实内容的,较之于汉语表达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在医药用途发明中,即是指该发明创造须要具有“真正、实在的”用途,而不能是未知或不确定的用途。如果通过科学技术提纯,发现某种传统植物药体内含有某种物质,并可以用清楚的用化学结构予以表征,但是却不知道具体的医药用途,那么这种情况下会被认为没有满足实质的实用性而拒绝授予专利权。在基因技术中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清楚披露基因的某一种用途,即使对其基因序列进行提取,也不能获得专利权。
具体与实质的两者之间界限似乎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对于医药用途而言,都是指这种用途须具体、确定的。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比如发明人发明了一种传统植物药未知成分物质的新的萃取方法,该案只满足了“具体的实用性”要求,而未满足“实在的实用性”要求,因为该萃取方法能够提取和制造所述的成分物质,但是这种未知物质是什么及有什么用途皆不清楚,难以达到“实在的实用性”要求。
而可信的实用性是指该发明创造申请的根据所提供的材料能够实现申请中所描述的用途。即对于所申请的发明专利来讲,该发明是可以实现的或有实现可能的。根据美国实用性审查指南规定,专利申请所陈述的实用性,如果该实用性陈述背后的逻辑没有严重的缺陷或者其所依赖的事实与该陈述背后的逻辑相一致,则被认为具有可信的实用性。例如永动机的发明就被认为是不具有可信的实用性,依法不能授予专利权。
由上可知,美国专利法上实用性要求发明须具有实际存在的用途。并且这种用途应该是明确或者可以完全预知的、可信的,而并不需要其“能够制造或使用”。
三、结 论
传统植物药医药用途发明并不是以现代西方医药学提取物质成分的方式实现的,其专利的保护主题涉及到传统植物药治疗疾病的传统知识信息及医药用途,而医药用途的发明在传统发明领域需要有具体明确的物质存在,方可实现产业利用性可能,亦即我们所说的可复制性。传统植物药以传统知识形态存在的情况下,实现这种产业可复制性具有一定操作难度,但其医药用途的有用性及医药用途的确定性却是毋庸置疑的。根据以上对美国专利实用性标准的解读,可以看出,传统植物药传统知识意义下的医药用途发明可以契合这种以生物技术发明所建立起来的“有用性”标准。正如学者所言,可重复性要求因生产产品的技术的常规性、稳定性使然,而产品或方法的有用性却往往是待证的。技术上的差异使得产品或方法的“有用性”要求在生物技术发明专利领域中更加凸现。“能够制造或使用”的判断标准不再适合。j张勇、朱雪忠:《商业世界Vs.思想王国——以实用性要件为主线的专利制度发展研究》,载《科技与法律》2006年第2期。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it is widely accepted in the patent law over the world that extracing the effective composition of plant medicine by using the modern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is patentability, patent law cannot provide comprehensive reasonable protection for traditional plant medicine which is based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sclosure. The medical valu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lant medicine based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sclosure can be applied for medical use patents. In order to meet the practicability requirements of medical use patent of traditional plant medicin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xamination of practicability should follow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to “Usefulness”.
traditional plant medicine; patent; practicability
陈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
本文受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项目(编号:SS14-A-19)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