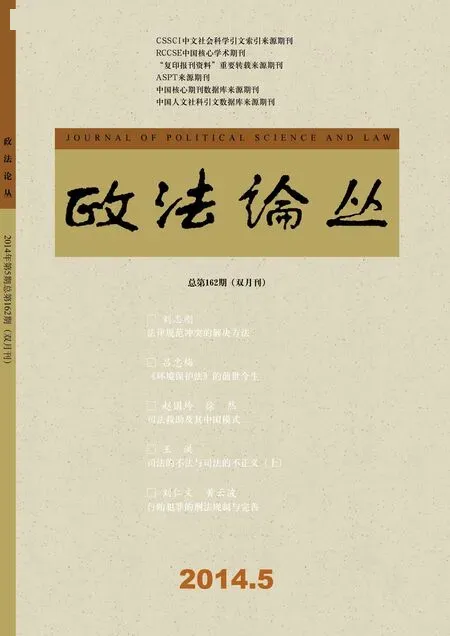当罚、可罚与要罚:犯罪构造客观要件的逻辑递进*
刘 军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主客观相统一”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所有客观方面的事实都需要有主观方面的认识或者认识可能性,主客观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应”、“不统一”,或者,至少是不能要求完全一一对应。易言之,在犯罪的成立条件上,既存在着没有客观事实对应的主观要件,如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目的,也存在着无需主观认识的客观事实,如纯粹的启动刑罚权的条件;前者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主观的超过要素”,后者的情形则是“客观处罚条件”。①总而言之,在立法上确实存在着主客观不相统一或对应的实证,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需要进行借鉴处理的现实问题。
大陆法系的这一立法现象也为我国学者所重视并运用于解释我国的刑法,如,张明楷的“客观的超过要素”、陈兴良的“罪量要素”、周光权的“内在和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更有学者认为,数额等规定也是一种“处罚条件”,或者就是“客观处罚条件”②。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借鉴客观处罚条件理论,如黎宏就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当中,不可能有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或者与其类似的因素存在的空间”。[1]P22可见,我国关于“客观处罚条件”等类似的立法现象及其功能、体系定位等观点的争论还远未达成共识,这不但会影响到我国的犯罪论体系,而且会极大地影响到具体案件的适用。在笔者看来,从犯罪成立的客观要素观之,各要件要素之间存在着当罚、可罚与要罚的逻辑递进,是为区分“内在”与“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的标准。
一、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缘由
我国学者对类似于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现象作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的解释,有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构造了全新的犯罪论体系。但是,客观处罚条件的理论毕竟来源于大陆法系,追根溯源明晰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目的和缘由,并探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于1872年由弗兰克(Francke)和宾丁(Binding)分别提出。据称,宾丁最初提出客观处罚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区分违法和犯罪,每个违法都违反了一个特定的规范,宾丁将这些组成违法的要件称为规范违反性要件或者违法要件,故意和过失原则上只需要概括到违法要件,不需要覆盖到与规范无关的组成部分,因此客观处罚条件是不需要被罪责包含的。[2]虽然宾丁提出了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但是却限制在可罚性③的范围之内,只是基于其规范说的立场,认为对于规范的违反才是违法的本质,因此责任只需要及于此即可。不过绝大多数犯罪并不是只要求有责的行为便可罚,还必须要有其他的客观事实的出现才成立犯罪,这便是客观处罚条件。易言之,宾丁所指的客观处罚条件仍然是可罚性的客观事实,并与行为直接相关。宾丁提出的客观处罚条件的重大意义在于,非常鲜明地指出这些客观事实是犯罪成立的实体性要素,但却与违法和责任无关,并因此无需进行故意或者过失的判断,当然也不及于认识错误问题,这与当前主流的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如耶塞克、魏根特认为,“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它们与行为直接相关,但既不属于不法构成要件也不属于责任构成要件。”[3]P667再如,罗克辛认为,“对于具体行为构成来说,除了不法行为的责任之外,是否还必须具有其他的情况,才能出现刑事可罚性,或者,特定情况的存在,是否会排除本来就可能出现的刑事可罚性?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还存在着……人们的共识仅仅在于:这种特征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属于不法或者罪责。”[4]P690但是,如果将客观处罚条件仅仅定义为与违法和责任无关的决定行为可罚性的客观事实,④那么至少可以包括与行为直接相关的客观事实(“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和与犯罪行为本身及其组成部分无关的外部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两大类,是为广义的客观处罚条件概念。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就是值得处罚的行为,就会成立犯罪并具备可罚性。但是,现实中立法者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将行为的可罚性以及要罚性与某种客观事实联系起来,并成为决定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实体性条件。根据客观处罚条件的分类,其立法目的和缘由也各不相同。
对于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主要是为了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从刑事政策的层面对“要罚性”进行考量,如果不存在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即使存在不法和责任,也会否定其构成犯罪。如《德国刑法》第104条a规定,对于“针对外国的犯罪”,“只有当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具有外交关系,并订有互惠保护协定的外国请求处罚,且行为时此等协定仍然有效”时才可以追诉。[5]P111这种客观处罚条件与“个人之阻却/解除刑罚事由”(如亲属间的盗窃行为等)具有类似性,即都是基于刑罚的必要性从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以及其他刑事政策目的进行考虑是否对违法且有责的行为进行处罚。这种外部的实体性要件是“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因为其与犯罪行为本身及其组成部分无关,根本就不存在“还原”为不法要素的问题,责任主义原则也根本不及于此,其功能和作用就是限制刑罚权的发动。虽然也有个别学者否定此种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3]P669但是对于承认客观处罚条件的学者争论并不大。
对于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排除责任主义原则的适用,或者说,是为责任主义原则创造例外,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刑法适用中的重要后果,如无需考虑对于客观处罚条件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从而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实际上是扩大了处罚范围,因此是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如《德国刑法》第231条规定的“参与斗殴罪”,造成死亡或者重伤的结果仅仅是对参与斗殴行为予以刑法评价的前提性条件,无须判断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更无须关注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这种立法模式实际上是将参与斗殴的行为由侵害犯转而规定为抽象的危险犯,实际效果是,即使无法查清究竟是谁造成的死亡或者重伤的结果(如果能够查明因果关系则构成第226条的伤害罪),仍然可以按照参与斗殴罪追究刑事责任,从而在终极目的上严密了法网,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再如《德国刑法》第323条a规定的醉酒行为,理论上被称作“原因上的自由行为”,即醉酒的行为是有意志自由的,易言之,对于醉酒而言至少是有故意或者过失的,否则不构成犯罪。但是即使行为人对于醉酒有过错,如果没有在醉酒的状态中发生侵害法益的行为,对于醉酒的行为仍然是可以容忍的,或者尚未达到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因此,醉酒状态中的违法行为就是客观处罚条件,无需证明其主观的认识以及责任能力问题。在这两个立法例中,都存在一个与行为直接相关的结果,或者说这个结果仍然处在刑法之内,或者本质上应当属于不法构成要件,但在形式上将之规定为客观处罚条件,目的就是消解责任主义原则的限制。耶塞克、魏根特将这种情形称为“伪装的刑罚加重事由”[3]P669,亦即,虽然构成要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罚性,但是在后续出现的违法行为或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实际上是“可以容忍”的,并没有成立犯罪。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耶塞克、魏根特称之为“被隐藏的构成处罚的行为情况”[3]P670,即《德国刑法》第186条规定的“恶言中伤罪”。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所主张事实的真实性,即使真诚地相信该事实是真实的并据此而行为,也应当成立犯罪;反之,如果能够证明所主张事实的真实性,则不成立犯罪。亦即,散布不真实的事实是行为不法的内容,但是行为人对该事实究竟是一种如何的主观态度确实无法证明,为了割断其与故意或过失的联系,才将之规定为客观处罚条件。
意大利刑法理论也支持这种内在客观处罚条件和外部客观处罚条件的划分。如帕多瓦尼认为,行为可罚性的实现需要客观条件,意味着行为本身就“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只是出于适当性的考虑,法律才将某种特定结果作为行为“必须受到惩罚”的条件;另外一种情况,可罚性的客观条件在很多情况下又表现为犯罪典型危害性发展的新阶段或加重方式,这种可罚性客观条件又被称为“内在”条件,与此相应的,第一种客观处罚条件因为与犯罪的危害本质没有内在联系,因此属于“外部”条件。[6]P387这是典型的“区分说”,即将客观处罚条件在种类上进一步区分为纯正的和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肯定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除此之外,大陆法系中还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或“还原说”,主要是基于刑法解释的不同立场所产生的不同观点。概而言之,行为无价值论者均肯定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肯定说),而主张结果无价值的学者都否定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认为可以将客观处罚条件还原为违法要件要素(否定说或还原说);[7]P45-49其中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是争论的焦点,在客观处罚条件的功能、性质、体系地位等都分歧巨大。[8]但是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在本质上属于不法的内容,均可以“还原”为不法要素,有的是构成要件的要素,有的是加重的结果,但是,均基于规避责任主义的目的而将之规定为客观处罚条件,实质上是对责任主义原则的限制,或者说是责任主义原则的例外,从而成为事实上的扩张刑罚事由⑤。易言之,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仍然属于可罚性的范畴,应当经由可罚性的论证为刑罚提供正当性根据。
如此,客观处罚条件依据其与构成要件行为的关系可以划分为内在(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和外部(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分别由可罚性和要罚性/需罚性提供理论支撑,成为扩张刑罚的事由和限制刑罚的事由。从立法目的上来看,客观处罚条件具有其存在的实践理由与理论优势。
二、客观处罚条件的功能性区分
“客观处罚条件,可以说是刑法体系化、精致化之后的产物”,[3]P671也可以说,客观处罚条件使得刑法进一步体系化和精致化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客观处罚条件的功能、作用和体系性地位还需在整个刑法体系的层面来认识与理解。
“外部”条件是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与可罚性本身无关,是实现可罚性的条件,在此之前,行为本身就是应当受到处罚的。申言之,违法且有责的行为通常即具有可罚性,是值得处罚的行为,但是如果可罚性的实现还需要其他客观的条件,说明立法者考虑了其他的立法目的,才将某种与行为并无直接关联的客观事实或情形规定为行为“必须受到惩罚”或“需要受到惩罚”(要罚性/需罚性)的条件,这也是刑法谦抑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可罚性是国家刑罚权的界限,表达的是社会共同生活需要刑法介入的必要性。一个行为即使是值得处罚的违法且有责的行为,但是如果从预防犯罪的意义上来看是没有必要惩罚的,那么也无需动用刑罚权;另外,如果基于国际法或双边条约互惠规定如果没有必要动用刑法,那么也不构成犯罪。概而言之,要罚性(刑罚必要性)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在具备了可罚性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利益衡量,因此,要罚性是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与违法责任要素的界限,同时也是与诉讼条件的界限,因为要罚性还说明客观处罚条件属于实体性条件。至于说要罚性的考量是否仅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为了刑法的进一步体系化,或者对刑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完全可以发挥要罚性的重要作用,将要罚性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在可罚性考察之外进一步考察刑罚权启动的条件。
与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不同,“内在”条件本来应当属于可罚性的范畴,或者说是为可罚性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客观条件。申言之,立法者表面上将构成要件的行为规定为值得处罚的行为,但实际上仅有构成要件行为尚不具备可罚性,而只有与以客观处罚条件的面目出现的“结果”或“行为情状”结合在一起,整个行为才是可罚的。因此,如果不具备这种客观处罚条件,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其可罚性是不足的。易言之,如果不存在客观处罚条件,则构成要件的行为是不可罚的,由此,也就不存在未遂的问题。同理,客观处罚条件出现之前对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帮助等也不构成共同犯罪。当然,在结局上也使得本来是“可以容忍”而无需处罚的行为因为被规定为构成要件行为,因此也便具有了行为规范的功能,因为构成要件具有行为定型的功能,具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般是“当罚”的。“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是一种影响可罚性依据的客观条件,从而在刑法解释上也便具有了多种结论的可能,“还原说”便是其中较为有力的一种理论,尤其是从法益保护说或者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上来看,更是如此。
既然“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是为可罚性提供依据的,那么,是否可以将其“还原”为构成要件要素呢?易言之,在犯罪论体系上是否可以将“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作为构成要件或者违法的要素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是立法者有意而为,或者说,立法者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处罚条件与构成要件或违法要素的区别,目的是维持责任主义这一教义学原则,同时隔断某些本来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故意或者过失的关系,以便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对责任主义原则做出限制;另外,某些客观处罚条件与行为之间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也存在问题,常常仅具有偶然或间接的联系,或者在司法证明上存在明显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在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客观处罚条件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还是可取的;最后,“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的设置使得行为与结果或者其他处罚条件出现了一定的分离,在构成要件上更加强调“行为”的无价值,其直接的效果是彰显了刑法(以构成要件为形式标志)的行为规范机能。在这个意义上,“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着实是一种实用的立法技术。
从以上分析来看,无论是“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还是“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论体系上都适宜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以便使得刑法体系更加完善、逻辑思路更加清晰。但是,从可罚性和要罚性的分野来看,“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因为是影响可罚性的客观处罚条件,因此,在刑法解释上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或者说,作为一种立法技术是可取的,因为其可以规避现实存在的各种难题。但是在刑法解释上却需要在整个犯罪论体系内与违法和责任要素进行结合:就违法要素而言,如果缺失该客观处罚条件则可罚性存在不足;就责任要素而言,虽然割断了与故意和过失的联系,但是至少应当具有预见可能性,否则不具有可罚性。因此,对于“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还应当在法治国的层面上、在构成要件的保障机能上,作为责任主义原则的例外进行恰当的理解和解释,而不能过于机械和绝对。
三、我国刑法中的客观处罚条件
在大陆法系国家,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呈现逐步扩张的趋势,这与“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特殊风险有关,存在着需要扩张刑法而进行规范的行为,或者说需要进行法益保护前期化的现象,甚至有学者主张所谓的“风险刑法”,以便与刑法保护法益的现实需要相契合。
我国刑法中也存在类似大陆法系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包括“内在”的和“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二者的界限就是可罚性和要罚性的区分。我国刑法中典型的“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规定,如《刑法》第129条“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如果不存在“严重后果”的要素,仅仅丢失枪支而不报告的行为并不足以支持该种行为的可罚性。易言之,该处罚条件实质是扩张刑罚的事由,因为该严重后果已经涉入了第三人的行为,本来应当阻断了前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却以客观处罚条件的面目让前行为具备了可罚性,在结构上属于“伪装的刑罚加重事由”,在刑罚的效果上实质是扩大了刑罚的事由,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对该“结果”的主观态度的争论问题。再如第241条第6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属于事实上的排除刑罚事由。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阻碍被买妇女按照其意愿返回原住地,对被买儿童存在虐待行为,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其实就是客观处罚条件。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属于状态犯,行为完成之后不法状态将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持续存在,如果仅仅是收买,并无其他违法行为,并不强力维持该不法状态的存续,其行为的可罚性尚且不足,并未达到值得动用刑罚手段的程度。易言之,只有出现了进一步的行为,如“阻碍被买妇女按照其意愿返回原住地”、“对被买儿童存在虐待行为”或者“阻碍对被拐卖儿童进行解救”,才具备了可罚性。这种情形的客观处罚条件其实是应当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只是为了彰显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表明立法者对该种行为的否定性态度,才将其他要素分离出来规定为客观处罚条件。易言之,此种立法模式还可以凸显刑法的行为规范机能,以达到规范公民社会行为的功效。
我国刑法中,也存在着“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即纯正的、对刑罚权起着限制作用的客观处罚条件。典型的立法规定,如《刑法》第196条“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中的“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主要是在刑事政策的层面,从“要罚性”上对刑罚权进行一定范围的限制。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不归还的行为本身即具有可罚性,但是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证明,因为信用卡本身即允许持卡人进行在一定的限额和期限内的透支,而且实践中也存在由于过失而没有归还的可能性,因此需要附加“经发卡银行催收”的限制条件。当然,“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本身也证明了透支的“恶意”性和行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该客观处罚条件属于“外部”条件,与构成要件行为及其组成部分并无直接的关系,实际效果上则限制了刑罚的范围。类似的规定还有《刑法》第201条的“逃税罪”,第4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易言之,经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仍然不缴纳税款和滞纳金,尚未收到行政处罚的,有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在此之前,行为已经具备了可罚性,仍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第4款后半句的规定就是对这种观点的印证,“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亦即,第4款前半句规定的客观处罚条件与可罚性无关,仅仅是“外部”的限制刑罚事由。
以上列举了我国刑法中存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按照本文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分析和认定,虽然如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识别并认定为客观处罚条件却是极困难的事情,争论也不可避免。“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因为与犯罪行为本身及其组成部分并无直接关联,与行为是否值得处罚无关,因此,其判断标准比较明确,即只有与行为是否值得处罚的判断无关的犯罪成立要素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与此不同,“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本身是影响可罚性的客观条件,或者说,本来应当归属于构成要件或违法的要素,如何与其他违法要素相区别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从立法目的上来讲,是为了限制责任主义原则的适用,但从司法实践上来看,这些客观处罚条件或者是因为介入了第三者的行为,或者是存在证明上的困难,或者在“行为”时不存在可谴责性,总而言之,的确存在理论解释或实践认定上的困难。因此,虽然“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仍然属于可罚性的范畴,但毕竟只是影响可罚性的条件要素而非决定可罚性的要素,仍然属于“条件”的范围,⑦这也是“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需要成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原因。如有学者认为,《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第3款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因此,认为“有意诬陷”是客观处罚条件。[9]之所以会出现此种误解,主要是借鉴德日刑法中关于“诽谤罪”要求“事实真实性证明”的规定。但是,我国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中“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是构成要件要素,也并没有被要求转移证明责任,因此,本罪中的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其实仅仅是提示性规定,提示司法部门在认定犯罪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没有该项规定对于该罪的犯罪成立条件的解析不会出现任何的不同,因此,“有意诬陷”不是客观处罚条件而是构成要件的要素。
四、客观处罚条件的体系性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客观处罚条件自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我国学者也大多能够认可类似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现象,认为其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要素不同,而且在与主观认识的责任要素的关系上也大不相同。但是我国学者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结合困扰我国刑法理论的“罪量”因素一并进行解决,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莫衷一是,容易引起理论上的争论甚至是混乱。⑧如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直接将数额等罪量要素等同于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构成之外另外附加犯罪成立条件,这实质是对客观处罚条件的误解;再如陈兴良在赞成罪量要素为构成要件说的基础上将犯罪构成体系解析为“罪体-罪责-罪量”,[10]实质是将罪量因素从需要主观认识的客观要素中独立出来,单独作为一个犯罪成立的要件,在体系地位和功能作用上与客观处罚条件无异,但问题是“罪量”要素并非客观处罚条件,而是可罚的违法性需要考虑的问题。申言之,如果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为参照,在罪体和罪责之间其实还应当存在违法性的实质判断问题,而这恰恰才是解决罪量问题的阶段,亦即,陈氏犯罪构成体系应当为“罪体-罪量-罪责”,在此之外才是客观处罚条件;相比较而言,张明楷的“客观的超过要素”更加符合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但是因为在体系上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合二为一,统称为违法构成要件,[11]P109-132从而失去了违法性的实质判断阶段,或者说,其所主张的构成要件包括了实质判断,属于实质的构成要件理论,因而构成要件的要素也包括了在违法性阶段需要解决的可罚的违法性问题(罪量要素)。那么如何解决无需主观认识的客观要素问题呢?“客观的超过要素”的概念便水到渠成,但是其所谓的“客观的超过要素”无疑也包括了许多本来应当属于可罚的违法性要素,而并非仅局限于客观处罚条件,或者说,实质上也是混淆了客观处罚条件与可罚的违法性要素。
以上各种观点,基本出发点都是解决罪量等要素是否需要行为人主观认识的问题,其中主要借鉴的理论就是客观处罚条件,但是却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客观处罚条件与罪量要素混同。当然,二者也的确有类似甚至相同之处,即“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和可罚的违法性都是与可罚性有关的客观要素,都是构成要件以外的违法要素,也因此都是无需主观认识但是至少具有认识可能性的犯罪成立要素。不同之处在于,罪量要素是需要进行实质违法性判断的要素以决定犯罪是否值得惩罚,而客观处罚条件只需要判断有还是无,犯罪成立与否一目了然。申言之,罪量要素是决定可罚性的客观要素,需要进行具体的、非定型化的、价值的判断,而“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则是在传统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之外、以有或无的方式影响犯罪成立的可罚性的客观要素。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构成要件具有行为类型化的基本功能,对立法上值得处罚的行为进行一般的、概括的、抽象的规定,以界定罪与非罪的大前提,因此,只有在具备了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形式判断的前提下,才可能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实质判断。这是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罪刑法定之“罪之法定”的最直接表现,实现的是刑法保障机能,防止被告人被不当追诉。另外,构成要件还具有“故意规制机能”,即故意认识的范围只能局限于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反之,凡是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也是故意犯所需要认识的内容,否则不成立故意犯。因此,罪量要素不属于构成要件的要素,而是需要进行实质判断的违法性要素。如果将罪量要素放在构成要件之中,不但在成立故意犯时需要判断是否已经认识到,否则就需要界定为“超过”要素,而且因为需要进行实质判断从而也冲淡了构成要件的行为定型功能,这违反了形式法治的基本前提,甚至可能出现司法权过度解释侵及立法权的现象,罪刑法定原则也将形同虚设。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给我们的启示是,罪量要素的判断应当置于构成要件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
如此,客观处罚条件和罪量要素都是独立于构成要件的犯罪成立要件,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中二者又是如何的关系呢?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之外还存在排除犯罪化的事由(正当行为),其实就是进行实质的违法性判断。《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但书部分以及其他罪量要素都可以在这个阶段进行判断,凡是不具备“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不足不值得动用刑罚的行为在这个阶段被排除出去。易言之,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中,可以将犯罪构成仅仅看作是犯罪成立的一个要件,或者将其改造为一个形式判断的阶段,以决定是否具备“刑事违法性”,是否“该当”刑罚;然后再进行“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罪量、正当化事由等实质违法性判断要素可以放置于此;最后进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判断,从刑罚的必要性、刑事政策上进行考虑是否需要动用刑罚,客观处罚条件也便获得了恰当的位置。⑨这是一种司法的立场,形式的判断相对于实质的判断应当具有优先性,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就容易受到侵蚀。
刑法和刑法理论需要解决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核心问题是谁应当受到处罚?处罚多重?[12]而这些都需要从整个刑法的体系进行理解与解释。从犯罪成立的客观要素观之,各要件要素之间存在一种当罚、可罚与要罚的逻辑递进,从形式到实质、从一般到具体、从根据到条件,而故意的认识范围仅及于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除此之外的客观要素仍然需要按顺序进行判断,如此这般则,不仅解决了主客观不相统一的问题,也为我国犯罪论体系(犯罪成立条件)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注释:
① 不同的学者对“die objektiven Strafbarkeitsbedingungen; die objektiven Bedingungen der Strafbarkeit”的翻译并不完全相同,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徐久生)、刑事可罚性的客观条件(王世洲)、客观可罚性条件(林山田)、客观处罚条件(蔡墩铭、许玉秀、林钰雄)等,因为本文区分了可罚性与要罚性的概念,并将之作为区分违法要素与客观处罚条件的核心标准,为避免中文不必要的误解,直接采用“客观处罚条件”的翻译。
② 参见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4页;周光权:《论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页;赵秉志,肖中华:《如何理解犯罪故意的“明知”(下)》,《人民法院报》,2003-5-19。
③ 可罚性(Strafbarkeit)具有多种涵义,本文中的“可罚性”是在对行为进行实质评价是否“值得处罚”的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参见冯军:《德日刑法中的可罚性理论》,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1期,第106-107页。
④ 应注意区分“个人之阻却/解除刑罚事由”(日本称为“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与“客观处罚条件”的区别,二者都是不法与责任之外的决定刑罚是否存在的刑法实体性要件,但是前者是与身份等个人的特殊情形有关,如国会议员身份、亲属身份关系等,而后者则是具有一般意义的客观条件,如果不存在客观的处罚条件则无论任何人都不受处罚。
⑤ 台湾学者许玉秀认为所有的客观处罚条件其实都是刑罚扩张事由。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6页。
⑥ 有学者认为,“在客观的刑事可罚性条件和事实的排除刑罚的根据之间所存在的区别,纯粹是形式上的”, 本文赞成此种观点。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91页。
⑦ 这是与结果加重犯的重要区别,而且结果加重犯按照目前的通说认为至少是过失,而客观处罚条件则与故意和过失无关。以此标准观之,张明楷所列举的许多所谓的“客观超过要素”其实都是结果加重犯中的结果,属于构成要件要素,是“当罚”的客观要素。参见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3页。
⑧ 因为“外部”的客观处罚条件与可罚性无关,是从刑事政策的层面对“要罚性”考量以限制刑罚权,不会与可罚的违法性相混淆,因此容易发生混淆的是“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与可罚的违法性要素。
⑨ 从目的解释论来看,“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是影响可罚性的客观要素,似乎也可以作为违法性要素,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只需要判断有无,因此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中,放在“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判断阶段比较适宜。
参考文献:
[1] 黎宏.论“客观处罚条件的若干问题[J].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
[2] 王钰.对客观处罚条件性质的历史性考察[J].清华法学,2012,1.
[3]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5] 德国刑法典[M]. 徐久生,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6]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 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J].清华法学,2009,2.
[8] 黑静洁.客观处罚条件之理论辨析———兼论客观处罚条件理论在中国刑法中的定位[J].政治与法律,2011,1.
[9] 周光权.论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J].法学研究,2010,6.
[10] 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J].环球法律评论,2003,3.
[11]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2] [美]保罗·H. 罗宾逊.进行中的刑罚理论革命:犯罪控制意义上的公正追求[J].王志远译.当代法学,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