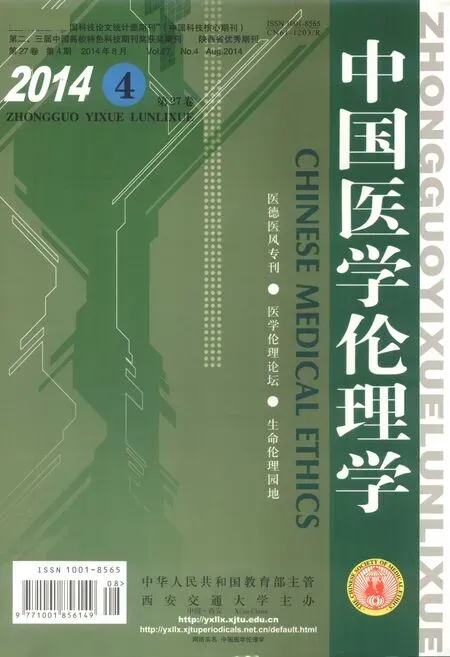提高生命伦理学学术交流的质量
吉鹏程
会议综述
提高生命伦理学学术交流的质量
吉鹏程
国际生命伦理学研讨会(2014·南京)于2014年3月8~9日在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研究员、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翟晓梅院长、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史兆荣院长、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杨国斌副院长、英国《生命伦理学》杂志(Bioethics)Ruth Chadwick主编、英国One World Analytics Anthony Mark Cutter主任、《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王明旭主编、《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编辑部李恩昌主任、副主编等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杨国斌主持了开幕式。史兆荣致开幕辞,他在开幕词中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他说,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医学伦理学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得益于各位专家的支持与帮助,把会议交给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承办,是对医院的肯定和鼓励。这次会议必将是一个学术盛宴和文化大餐,相信各位会有很大的收获,他希望各位领导与专家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医学伦理工作,推动医学伦理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Ruth Chadwick在致辞中谈了加强中英生命伦理学交流的必要性,并介绍了英国《生命伦理学》杂志的基本情况。
李恩昌在讲话中说,我国生命伦理学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形成了生命伦理学学科群,进入了分化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大批学科,如:临床医学伦理、护理医学伦理、科研伦理、基因伦理学、军医伦理学、卫生改革伦理、健康伦理学等。随着学科的分化发展,中国生命伦理学人才辈出,灿若群星,涌现了邱仁宗教授、翟晓梅教授等一批著名的生命伦理学专家。学科的分化就是学者的分工、学者们自身的定位。没有分化就没有学科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就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极可能出现重复劳动。而《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就目前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应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才素质,提高研究质量。而加强国际交流的宽度与质量对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一是促进中英两国学者面对面交流,二是把Bioethics这样一本国际著名期刊介绍给中国学者,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坛上交流自己的成果提供阵地。
Ruth Chadwick以Where is the Person in Personlised Medicine(“个体化医疗中的‘人’在哪里”)为题作了演讲。她说,个体化医疗因表观基因而变得复杂。就医疗而言,医学一直是个体化的,是将具体的方案应用于个人身上。病人有自我认知、有梦想,人不是疾病或者症状的载体,人有更丰富的概念和含义。我们目前处在基因组时代,当前个体化医疗更多的和基因组联系在一起,这就带来了一些伦理问题。比如药物基因组学、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可以根据人群特性给药或者给予营养,这就会对人群进行分层,但这可能会引起不同层次人群之间的不同对待。分层后,人该处于什么位置?再者,为了实现“个体化医疗”,就需了解所有的基因组信息。这就产生了基因测序、隐私保护问题。同时,环境也会对基因产生影响,所以基因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这样的个体化医疗会根据疾病给病人分层、根据疾病给药,这就带来了治疗平等的问题。所以,应该关注疾病类型而不是关注基因。她在最后说,她并不是反对或赞同“个体化医疗”,只是把其中的伦理问题讲出来。
邱仁宗就“转化医学中的伦理问题”作了学术演讲。他论述了转化医学的伦理问题,他还就临床前研究向临床试验转化的伦理问题和与会者作了交流。在这一部分,他先提出了药物研发过程中开始做试验时的伦理问题:该药物在动物中是否已经充分展示临床上的前途?参加试验的是否应该仅限于患难治疾病的病人?是否应该将试验视为治疗性的?研究者是否已经将风险充分地最小化?他以“司马希特的研发”为例,就以上伦理问题提出对策:预测与伦理决策,预测的局限,预测时的证据,使用临床前报告和效度,证据保守主义,用更广泛的证据作预测,鉴定参照类、扩大证据基础。
翟晓梅就“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问题”作了学术演讲。她说,从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脑死亡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脑死亡概念和器官移植的发展是相互独立进行的,只是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迫切。但要强调的是,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器官移植,但器官移植的迫切要求不能成为脑死亡标准确立的理由。在实践工作中需要特别强调器官移植要与脑死亡的判断以及可能伴随着的器官摘取与移植脱钩,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她还就增加同意率的问题和与会者作了交流,她认为,大量的潜在捐献者来自外伤现场和ICU治疗,有组织、有计划的提高捐献者意识的工作,会增加捐献者的数量。外伤医务人员和急救护理人员必须意识到获得的重要性以及掌握优化潜在捐赠者捐赠的技能。提高捐献率要有积极的医疗策略,积极救治和器官维持不会影响捐献率。
杨国斌以《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冲突与对策》为题,介绍了在医学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广应用背景下,医患关系和临床医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伦理冲突。其伦理冲突具体表现有:沟通障碍,医患情感淡化;设备障碍,医患关系物化;技术指导,人文关怀弱化;费用昂贵,医患关系激化;广泛应用,生存状态异化。对此,他提出了伦理对策:加强人文素养培育;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开展高新技术宣教;强化绿色医疗理念;推动卫生体制改革;把握科学发展方向。通过伦理实践和课题研究,加强医学伦理知识的普及,积极应对高新技术的冲突,增强医学伦理审查的效力。
王明旭作了题为《中国死刑犯的器官捐献儒家伦理反思》的演讲。他认为,器官移植是挽救终末期脏器衰竭患者生命,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但是器官来源形势严峻,严重制约器官移植发展与终末期脏器衰竭患者的救治。通过分析中国器官捐献的背景情况和国际上的对比情况引出中国死刑犯的器官捐献的系列问题。他分析了中国器官捐献实践的三个特征:受人际关系影响明显,从道德监管逐步走向法律监管,从地方试点到国家统一规范的过程。认识到对待中国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必须寻找其“道德”的根,认识到中国“教化为体,刑法为用”重原则的德治传统,接着他讲到了儒家伦理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支持。分析了儒家伦理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控制,但死刑犯的器官捐献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完善法律和秩序,确保家庭知情同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在最后的小结中指出了器官捐献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李恩昌作了题为《中国患方临床决策的三种基本模式研究》的演讲。他在一开始讲到尊重个体在医疗决策中的自主权是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家庭决定在中国有其传统并被一些学者所倡导。在经过研究学习后,认为在中国社会,患者临床医疗决策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患者自主决策,家庭决策模式,患者和家庭共同决定,这三种决策方式又各有利弊。在分析了利弊之后,对如何选择决策模式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确定选择模式的标准;进一步学习、宣传相关法律,尊重和维护患者的权利;法律制度需要将患者自主权进一步细化。
Anthony Mark Cutter作了题为Bioethics and Practical Policy Making(生命伦理学与现实决策)的演讲。他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实践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分析、讨论为将来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需要一定的方法和信息,这样才能够影响伦理决策。他认为,政策制定要与人们利益相符合。他还对德尔菲法进行了分析与说明,并介绍了德尔菲法在生命伦理学决策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他说,伦理学问题会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发生,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预测医学、伦理等对社会的影响。
黄钢作了题为《医疗技术临床准入伦理审查评价指标构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报告。他说,当下中国,医疗技术临床准入的伦理审查已成为一道法定门槛,如何把好这一门槛,以充分实现伦理审查降低医疗技术的负作用的目标,最终达到技术与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状态,伦理审查模型的构建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对伦理审查评价指标的问卷调查制定医疗技术临床准入伦理审查标准体系理论设计表,为构建医疗技术临床准入伦理审查模型提供理论支撑,为我国医疗事业作出贡献。
李红英的讲演题目是《从医方视角关注人文教育创建和谐医患关系》。她首先分析了2008~2013年对北京、辽宁等九省市45家医院调查的医务人员从业状况,认为诱发医患矛盾原因有医方、患方、政策、管理、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接着着重强调关注人文教育,减少医源性矛盾。医患沟通是信息和情感交流的过程,要保证医患良好的沟通,必须有充足的交流时间、良好的交流环境;人员学识、临床经验、交流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患者理解、接受能力不同,医患沟通的效果也会不同;知情同意和持续知情同意的理解认识。接下来通过几个案例分析了人文教育和知情同意的理解缺失导致的问题。她还指出要关注人文教育、培养临床抉择能力、创建和谐医患关系。
邓蕊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大陆人体研究中以家庭为基础的二元决策模式》。她首先指出在医学研究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尤为重要,成年受试者是隐性弱势人群。再通过两则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国大陆个人自主同意的不足。还指出“以家庭为基础的二元决策模式”的主要特点。她认为家庭在决策中主要起到一种意见支持或精神支持的作用,它是一种“支持性决策”而非“替代性决策”,家庭意见与个人意愿构成了一个整体决策,这样的整体决策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受试者的利益,而且维护了家庭的整体性,保持了家庭的和谐关系。
杨同卫以《致力于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伦理评析》为题作了学术演讲。他说,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首先体现在要重视基层医疗卫生;其次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最后在新医改的目标下,坚持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和医疗卫生服务筹资的公平性。在做好这三个方面工作的同时,应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并积极提出对策和建议,最终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结果的公平。
贺苗作了题为《儒家伦理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双重效应》的演讲。她讲到,儒家重仁、重孝,其人伦实践的载体是家庭,这对20世纪医学前沿科学发展的新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来说具有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又挑战着传统的儒家伦理,如使传统家庭关系改变、生育与婚姻分离、双胞胎妊娠日显危害等。最后她说到:面对这种双重效应,我们应从医学、伦理、法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认识与利用。
赵菁作了李中琳和她的题为《科学健康观与生命伦理学》的报告,她说科学健康观为新医学模式的社会化、实践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社会支持系统,把现代医学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构建了现代医学与党、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为医学真正发挥它的健康功能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动力和支持。而生命伦理学对科学健康观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进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郭卫华作了《论医学的道德精神》的报告,报告中说:当前,医学面临着很多的道德难题,比如说医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既要以科学为基础,对生与死进行“是”的定义,又需从特定的文化出发,追问生命与死亡的“应当”性。再如现今人类对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无限性要求与现有的可用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些难题要求作为医者一定要具有医学的道德精神,即仁爱、公正、尊重。这不仅是医疗卫生制度的道德追求,也是医务人员的个体德行的体现。
王彧作了尹梅和她的题为《IRB:真的以我们看见的方式实现正义》的演讲,她向与会者解释了什么是程序正当、为何会有程序困境、怎样才能够实现程序正当几个问题,让与会者充分理解到程序正当是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之上,她又提到了伦理审查的诸多问题,并指出只有通过完善建制、有效回避、程序申诉、跟踪审查才能确保实现程序的正当。
程国斌以《从‘儒家生命伦理学’到‘医疗生活史’——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建构路径反思》为题作了演讲。他说,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着一些危机,在这些危机下,产生了“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两种主要态度、论据和观点。为此,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尝试,应以“儒家生命伦理学”为代表,提出具体主张。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从生命伦理学自身的特性出发,进行思路转向,解决最大问题,为发展中国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观提供理论准备。
郑金就2013年版《赫尔辛基宣言》的变化作了解读。她通过对《赫尔辛基宣言》新旧版本进行比较,指出其中的新变化,对所体现的新观点和新要求进行简要分析,从而加深对医学伦理原则的认识,进一步规范临床研究,指导医学伦理审查工作。
何翠媛的《医学伦理在医学生的传承与发展》,张洪江的《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反思》,尹洁的《基于脑扫描得到的心理学研究能解释道德性吗?》,苏永刚的《大陆临终关怀的困境思考》,佟晓露的《新医改对新疆医患关系的影响》,李鸿浩的《转化医学时代的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从研究走向应用》,雷虹艳的《基于中国本土化的患者知情同意制度完善研究》,董屹的《村落人际关系与差序格局中的医患信任》,胡兵的《论墨子的生命伦理精神、原则及其实践方式》,陈幼堂的《康德哲学中的尊严与权利》,王德国的《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及对策》,姜欢的《器官移植的几个生命伦理学问题探究》,付洋的《从“常回家看看”入法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下的养老》13篇论文在专题会场作了交流。
王明旭、Ruth Chadwick、杨国斌分别作了总结发言。王明旭在会议总结中说,演讲发言群英荟萃、精彩纷呈,演讲的内容具有国际化、本土化、多样化、年轻化的特点。会议的召开凝聚了同仁、提高了生命伦理学的影响,推动了学科的发展。Ruth Chadwick讲到,中国和英国在生命伦理学方面有一些差异,会议讨论了许多话题,有实际中的问题,也有理论上的概念。中英之间有很多相似的事情,比如器官捐献。而英国的医患关系和中国的不同,医学职业道德已经融入社会各个层面,已被大家接受、理解,医患关系问题需要多学科携手解决。杨国斌在总结中祝贺会议取得了成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力,感谢与会专家、代表给予的支持帮助。祝愿同仁们继续努力,研究出更好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李恩昌代表与会代表对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对会议的精心组织和严谨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修回日期2014-05-17〕
〔编 辑 李丹霞〕
Promoting the Academ ic Quality of Bioethical Communication
JIPengcheng
R-052
A
1001-8565(2014)04-0580-03
2014-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