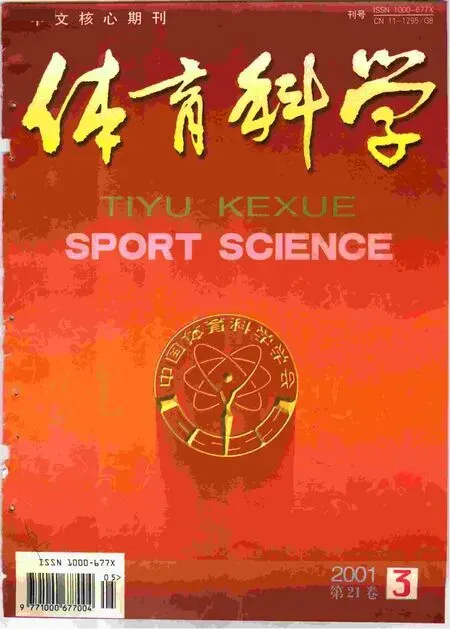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在场、脱域与出场
——以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为例
罗 辑
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在场、脱域与出场
——以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为例
罗 辑
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家族传承的历史存在,承载着族群文化与族群记忆;“物”的脱域是在民运会规则下的创新与再造,是在空间与行为上进行的适应性转换与重构;“物”的出场是民运会场域中的竞技表演,同时,也是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传播。
少数民族武术;物;在场;脱域;出场;民运会
:The presence of the "objects" is the history existence as folk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family inheritance in ethnic Wushu,and bearing the ethnic culture and memory;the disembedding of the "objects" is the innovation and recycling under the rules of ethnic games,and the adaptive con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behavior;the appearance of the "objects" is not only the athletics and performing in the ethnic games field,but also the spread of ethnic Wushu culture.
“物”一般是指器物,在武术中主要是指器械,少数民族武术中的“物”亦是器械之意。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民运会”)的武术比赛中,人们能看到风格各异的少数民族武术,特别是少数民族武术器械。与竞技武术中千篇一律的刀、枪、剑、棍等不同的是,这些来自不同少数民族武术的器械(以下简称“物”),风格各异,形式多样,每一件“物”都代表着不同族群的文化,是不同族群的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我们被大量的符号与群体身份包围,有些是活生生的,有些则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有些虽仍存在,但其意义对于处在特定场所中的我们而言已没有了,因为我们无法贴近而感觉到它们所传达的意义”[7]。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武术中的“物”一直隐于民间,处于自发传承的状态,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濒临消失,即使存在,也由于缺少竞技表演的场域,在平时也难得一见。民运会武术比赛正好给少数民族武术搭建了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和平台,暂且不论竞技场上所呈现出来的竞技表演水平的高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中“物”的出场,展现的更多的是其身后独特的族群文化。“若我们随意取一器物,而想加以分析,就是说想设法去规定它的文化的同一性,我们只有把它放在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说明它所处的地位。换言之,就是说明它如何发生文化的功能”[9]。同理,对于少数民族武术中的“物”,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为民运会武术竞技表演的道具,而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认识和理解它,将其视为一个族群文化的符号和载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物”的文化表征,认识到“物”的深层文化意义。
在历届民运会上,代表贵州少数民族武术先后出场的有侗族的“铁镋”和布依族“铁链械”和“布依猫叉”。文章以“物”的在场、脱域和出场3个维度对三者进行文化人类学阐释,借以深入了解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与意义。
1 “物”的在场:历史存在与时空特征
由于地缘的原因,长期以来,贵州社会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即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其开放程度也明显落后于中东部省(市)。在贵州省内,仍有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山区村落,仍然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社会以村落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单元。”[5]他们生活的“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1]也正是由于相对封闭的原因,才使得地域性民族文化得以较为原生态的形态保留下来。
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中的 “物”始终“在场”,大多保持了原生态的样式,族群特色与民族风格也较为独特。在时空维度上,少数民族武术中的“物”表现出较为悠久的历史性和较强的地域性。“物”的源起与变迁也承载浓郁的族群文化,侗族的“铁镋”又名“月牙翼齿镋”,因其形似月牙而得名,铁镋大小各异,一般重约10公斤左右,直径在1尺到3尺之间,长约3尺,为侗族的古兵器,为侗族武师龙大正于清同治年间所创。相传有一年冬夜,一虎潜入侗寨,偷吃猪仔、并叼走一小孩,龙武师闻讯,情急之下,操起一把钉耙直追猛虎,并与虎搏斗,后与乡亲一起击毙猛虎。在这之后,龙武师根据钉耙的样式,创制了专门对付老虎的兵器——铁镋。遇虎时,可将铁镋杀入虎口,老虎吞吐两难,即可趁机猎杀。后来,龙武师将铁镋之技传与侗家子弟,现仅存于贵州天柱县高酿、蓝田、芹香乡镇等地。
布依族的“铁链械”,相传为南宋时江西农民起义首领徐良所创,用铁链将两段长80~90厘米的木棍相连即成兵器。类似武术中的梢子棍和双节棍,梢子棍是梢短棍长,属长兵,双节棍较短,属短兵,铁链械虽然也是将两段木棍用铁链连接而成,但两段木棍棍身等长,又比双节棍长,可视为长双节棍,应归为长兵之列。因起义失败,徐良被流放贵州,定居花溪湖潮一带,将铁链械带到湖潮,并在当地传授铁链械之技,后又融入当地地戏之中,流传至今。
与“铁镋”与“铁链械”传承一样,“布依猫叉”也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同样具有一定的族群性。“布依猫叉”又名“三股叉”,多为铁质木杆,有大、中、小3种型号,起源并流传于黔南布依族民间,为布依族古村寨狩猎、护寨之用。据“布依猫叉”当代传人阿莫(独山县麻尾镇塘香村人)介绍:“塘香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祖祖辈辈都习武。‘布依猫叉’是自家祖传,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布依猫叉”的具体始于何时难以考证,但历经数代人传承,亦有上百年的历史。“铁镋”、“铁链械”和“布依猫叉”作为服务于族群的特殊工具,通过民间生活保留与家族传承,三者均有着一定的历史性;同时,作为贵州少数民族武术“物”的代表,由于始终受“在场”的支配,在空间维度上又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并呈现点状的村落分布,或为一个族群的部分地域所特有,或为一个族群的部分家族所独具。“铁镋”分布于天柱,“铁链械”仅存于花溪,而“布依猫叉”则传于黔南独山一带。
美国人类学家怀特认为:“一切人类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中产生的”[6]。同时,“一切群体所创制的行为规范,以及其他所谓文化等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3]。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在场”,总是契合了特定时空背景下当地人们特定的需要。如虎患之备的“铁镋”、义军之兵的“铁链械”和狩猎之用的“布依猫叉”,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由此产生的行为——“物”的运用技术,从武术技术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击、刺、扫、劈、挡等较为朴实的攻防动作,“铁镋”、“铁链械”和“布依猫叉”三者的功能均始于实用。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的行为总是策略性的,“行为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对于规则或规范的遵从。因为,正如‘行动者’这个标签暗示的,行动者在其日常实践中,尝试沿着制约与机会的曲径运动,而这个曲径是他们通过过去的经验并在时间中不完全地把握到的”[11]。在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产生是根据特定的需要,其运用技术也多是出于经验的总结。在长时间的传承过程中,“物”的功能也并非一层不变。追根溯源,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其原初的功能及其变迁。侗族武师独创的“铁镋”最初主要是用来防虎患之工具,后来演变成当地侗族人健身习武的器物;农民起义首领徐良所创的“铁链械”是农民起义军用来的兵器,后流入民间并融入地方戏剧之中,成为戏剧的道具;而“布依猫叉”则最早为狩猎、护寨之用,继而成为家传练武之器。但无论怎样变迁,都不影响“物”的文化作为直接服务于人的手段。
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中的 “物”不仅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和实用导向性,还是群族文化的符号和载体。“铁镋”、“铁链械”和“布依猫叉”作为族群文化的符号与载体,对于族群的和谐团结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文化符号,它们是族群关注的焦点,具有情感连带,延续着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作为文化载体,它们承载着族群生活、生产和习俗文化的记忆。对于族群而言,它们是以符号为基础的、共享的、习得的和融合的族群传统文化。长期存续于族群母体文化中,时至今日,仍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了民族的自然风情。
2 “物”的脱域:规则下的文化赋值与套路创编
民运会作为一个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同时作为一个体育赛事,有着自身的逻辑。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技术实用性导向使其表演性弱化或缺失,一招一式朴实的格斗动作并不能适应民运会比赛需要。为适应民运会竞赛和表演的需要,需要对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中的“物”的文化进行适应性转换与创造,对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武术进行时空分离,走出原有的生存空间,走向民运会的赛场。这无疑是一种“脱域”的过程,“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同时,在“脱域”的过程中,在民运会竞赛和表演规则导向下对将其行为从遵循策略转向遵循规则,实现“物”的文化的再造。毕竟规则是体育赛事必要构件,没有规则,就没有赛事。民运会一般设表演项目和竞赛项目两大类项目,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表演,按表演项目比赛规则,属于综合类下的集体武术;“物”的竞赛,根据少数民族武术竞赛规则,则属于器械C类项目。在民运会规则导向下,在对少数民族武术中的“物”进行“项目的挖掘、整理和重新编排中,必须强调突出其民族性、传统性和体育性,防止本末倒置”[4]。要从中把握 “物”的鲜明而独特的族群性,即明显不同于其他族群的、自身独有的族群心理倾向和功能特征;从文化层面挖掘其意义、传承脉落、功能价值等;从技术层面整理其攻防动作、风格与特征;最后结合“物”的文化、技术、功能表达进行套路创编。在整个套路创编过程中,需要尊重传统、对其进行文化、技术和表演艺术赋值,最终通过整套动作的意义表达,达到再现传统的目的。
在参加民运会时,侗族“铁镋”与布依族“铁链械”选择了表演项目中综合类集体武术的形式;“布依猫叉”则选择了竞赛项目中的武术比赛器械C类项目。在对其进行文化赋值与套路创编时,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器械的竞赛表演性处理,原生态的“铁镋”、“铁链械”与“布依猫叉”出于实际的攻防价值取向,器械都较重,在实际的竞赛表演中,演练起来难度较大,对此,取其形,弃其重、对其进行复制与再造,以便于在竞赛表演的演练。在实际的民运会表演与比赛中,“铁镋”与“布依猫叉”都相继采用了铝合金再造,重量变轻,演练起来变得轻松得多。经过转换的器械已不是原来真实的“物”,而是保留了少数民族武术 ‘物’的文化符号;其次,需要对其进行竞赛和表演性提炼、赋值和创编,要做到以民族性与传统性为核心,体育性和表演艺术性从属于前者。在实际的操作中,情境引入与族群叙事有意义表达不失为少数民族武术文化赋值与套路创编的上佳选择。根据表演性项目集体武术的比赛规则,侗族“铁镋”与布依族“铁链械”均采用集体武术的形式,有10分钟的场上表演时间。侗族“铁镋”可忠于虎患之备,通过情节引入,以出场、逐虎、与虎搏斗、胜利庆功的逻辑,编排与演绎一段武师与集体打虎护寨的故事;而布依族“铁链械”则可根据其义军之兵,分正、邪两派角色,演绎一段集体“铁链械”抗苛的故事。而作为武术竞赛项目器械C类的“布依猫叉”则是单人项目,根据少数民族武术竞赛规则规定,民族特色的器械的时间1~2分钟,对风格、法势、劲力、动作、内容、结构、神韵和节奏均有要求。在实践中,以2011年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武术比赛为例,“布依猫叉”传人阿莫代表贵州参赛,虽有一定的比赛经验,也有固定的猫叉套路,但赛前阿莫与教练员还是进行了创新,在原的基础上,再一次对其进行了创编。在创编过程中,除了通常意义上猫叉的上撩、下插、前刺等攻防动作外,通过情境引入和狩猎叙事,融入了具有狩猎情境中的“磨叉”、“掷石”、“猫步”等动作元素,就这样,一幅布依猫叉狩猎情景图呈现出来。同时,一套既保留了民族性和传统性,也不失体育性的少数民族武术器械竞赛套路也应运而生。
经过“物”的“脱域”,在规则导向下,通过器械与行为的转换,引入情境和族群叙事,经过文化赋值与套路创编,得到的是富含族群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武术套路,这正是民运会集体武术表演和竞赛所需要的。经过创新、再造的少数民族武术,不再是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武术,而是以原生态武术为原型的重塑,是在民运会竞赛和表演规则下对原生态少数民族武术的升华与再现。相对于原生态的简朴,再造的少数民族武术,具有少数民族文化气息与现代竞赛表演的双重属性。但光有套路还不行,民运会毕竟是体育竞赛表演,编排再好的套路也需要有人去呈现,接下来的工作便是组织运动员进行训练,力争在竞赛表演中更加完美地将套路编码及其意义呈现在裁判和观众面前。
3 “物”的出场:民运会场域中的竞技表演
出场一般是指场域的转换,同时伴随着表现模式的转换。“对置身于一定场域中的行动者产生影响的外在决定因素,从来也不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只先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一个场域越具有自主性,也就是说,场域越能强加它自身特有的逻辑,强加它特定历史的积累产物”[2]。特定的比赛规则决定了民运会的表演与竞赛场域自身的逻辑,对于上场参与表演、竞赛的行动者(运动员)必须事先经历数次练习和模拟实践。对 “物”进行适应性转换,从原生态的村落生存空间转换到了现代体育竞赛、表演的比赛空间,同时,在规则导向下对器械的技术行为进行转换。少数民族武术的中“物”的出场,是在特定时空——民运会场域下对脱域再造的少数民族武术套路的呈现。
从根本上讲,武术套路表演和竞赛都是要求运动员在规定的时间、在特定的空间,完成一整套按相对顺序预先编排好的武术动作。在少数民族武术套路编排中,编码者事先进行了族群文化和技术赋值,套路具有一定的族群文化内涵,这要求运动员在场上通过身体动作,在完成套路的过程中,抽象表达出来。在正式的表演或竞赛中,作为比赛与文化传播者的运动员具有主体性,作为解码者的裁判员与观众则具有客体性,主体的意义表达与客体的意义解码统一于比赛的场域中。对于作为解码者的裁判而言,表演与竞赛规则就成了他们解码评判的准则,而对于观众,更多看的是比赛中身体抽象呈现的意义。在民运会的场域中,贵州少数民族武术“物”的“出场”,是以竞赛和表演的形式,将脱域、再造的少数民族武术纳入到现代竞赛表演的视域下。在比赛中,身着民族服饰、手持少数民族武术器械的运动员,在表演和比赛规定的时间内,既在较高水平地完成动作,同时又要展现出贵州的独特的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侗族“铁镋”表达了侗族狩猎、御敌、农闲健身的族群武术文化;布依族“铁链械”威武、彪悍、雄健的表演风格体现了古时作为军事兵器之用,其中,在第9届全国民运会武术比赛中,代表贵州出场的 “布依猫叉”的带给裁判和观众的不仅是精彩的表演,从意境的角度来看,更是一幅布依猫叉狩猎图。用民运会竞赛表演的规则来审视,展现给裁判的更多是一种具有富含浓郁民族文化的竞赛、表演套路,而呈现给观众(无论是在场,还是非在场的)则更多的是具有竞赛、表演性质的少数民族武术文化。
少数民族武术“物”的民运会出场不是原生态武术文化的直接呈现,而是经过脱域再造,在保留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在民运会场域下的竞技与表演。“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超越,永远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10]。在脱域过程中进行民运会表演和竞赛的适应转换,在文化赋值与套路创编中对历史在场状态进行创新,在民运会比赛的场域中完成对传统的超越。正是民运会给予了少数民族武术一个展示自我的文化空间,一次出场的机会。
4 结论
少数民族武术“物”的出场,是传统武术历史语境、生存空间和行为的转换,也是传统武术现代化的结果。由于“传统武术现代化出场路径对出场语境具有深度依赖性。因此,我们既要深度解读传统武术文本的意义和形态,又要深度考察传统武术文本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8]。对于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在场的意义与形态的深度解读,是其脱域与在民运会出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充分把握住了“物”的在场特征,才能在“物”的脱域过程中进行有意义的文化赋值和套路创编。同时,也只有在“物”的脱域中对其进行恰当的空间与行为的适应性转换,才能适应民运会出场的需要。“物”的出场不仅是民运会场域下的竞技与表演,也是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有意义地表达与传播。对于少数民族武术“物”的现代性出场,需要从在场、脱域和出场3个维度对其进行整体性把握,协调并处理好原型与创新、技术与文化、表演竞技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6-18.
[2]布迪厄(法),华康德(美).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44.
[3]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01.
[4]冯胜刚.对我国表演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整理和编排问题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03,(2):80-84.
[5]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3.
[6]莱斯利·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M].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22.
[7]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5.
[8]李龙.论传统武术的出场学研究范式[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6):69-72.
[9]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9.
[10]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两个循环[J].学术月刊,2008,(9):42-47.
[11]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4.
ThePresence,DisembeddingandAppearanceofEthnicWushu—TakingtheGuizhouEthnicWushuasExample
LUO Ji
ethnicWushu;object;presence;disembedding;appearance;NationalGamesofMinorities
1000-677X(2014)03-0072-04
2013-10-18;
:2014-01-19
贵州省民委-贵州师范大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专项资金青年项目(黔族专2012917)。
罗辑(1980-),男,四川邻水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E-mail:luoji198003@126.com。
贵州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G85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