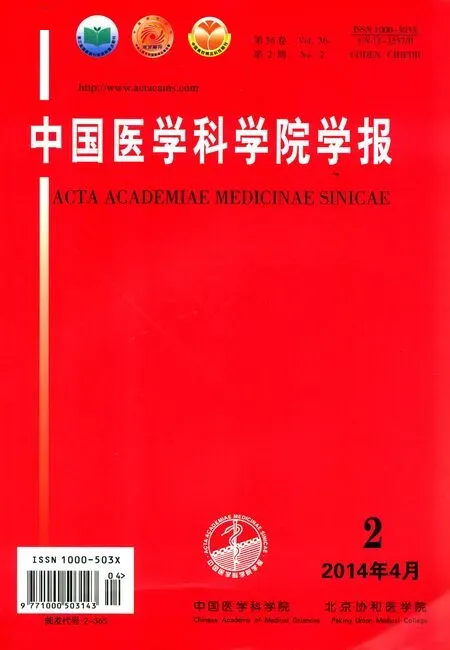颌面外科医护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潜在危险因素分析
姚志涛,王 茂,买买提吐逊·吐尔地
1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颌面外科,乌鲁木齐 830054
2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口腔科,乌鲁木齐 830000
颌面外科医护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潜在危险因素分析
姚志涛1,王 茂2,买买提吐逊·吐尔地1
1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颌面外科,乌鲁木齐 830054
2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口腔科,乌鲁木齐 830000
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事件;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危险因素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对创伤等严重应激因素的一种重度精神反应,它发生在经历过灾难性事件的人群或特殊职业人群,对PTSD的研究有利于结合医学、护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知识来提高疗效[1]。它主要导致该个体持续重复体验创伤事件经历,逃避回忆及反应麻木,警觉增高。PTSD只用于心理创伤和应激,而不包括躯体创伤和应激。PTSD导致的心理反应是缘于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由既往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感限度,大脑失去对事件不良后果的控制,因而导致心理应激反应的发生。巨大灾难事件可以导致急性应激障碍,而随之出现的创伤后延反应以及其他生活事件带来的创伤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反应[2-3]。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990年各种创伤的致死人数为510万人,预计2020年会增至840万人,口腔颌面部损伤在全身损伤中占重要地位,是全身创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有资料显示,颌面部创伤发生率占全身各个部位损伤的34%[5],虽然颌面部损伤大部分不会导致生命危险,但是其对颌面部外型、功能的破坏以及伴随的心理障碍远远高于身体其他部位,本研究主要探讨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潜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危险因素。
对象和方法
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对口腔颌面外科接触1个月的54名口腔专业的轮转实习医生以及40名轮转实习护士,用刘贤臣等[6]编制的自评量表进行评价。其量表理论上可划分为对创伤事件的主观评定 (条目1)、反复重现体验(条目2、3、4、5、17、18、19)、回避症状 (条目6、8、9、10、16、21、22)、警觉性增高 (条目 7、11、12、15、20、23) 和社会功能受损 (条目 14、24)5个部分。每个条目根据创伤事件发生后的心理感受分为无影响到很重1~5级评定,累积24个条目得分为50分者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得分越高应激障碍越重。
结 果
自评量表调查显示创伤事件的主观评定表示有影响 (2分以上)的为59人,反复重现体验 (2分以上)为35人,回避症状 (2分以上)80人,警觉性增高 (2分以上)43人,社会功能受损 (2分以上)12人。62人总分接近50分 (差距5分之内),2人50分以上。
讨 论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性事件的主观评定威胁到个体的生命、身体或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异乎寻常痛苦的人生遭遇称为创伤性事件。创伤性事件并非罕见,我国仅各类自然灾害平均每年就使2亿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加上人为事故、交通意外、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以及随着社会发展,高竞争、快节奏、环境改变、拥挤、污染、人际冲突所带来的负性生活事件,已经构成了不容忽视的一个巨大群体。经历创伤性事件带来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的改变,从多方面影响身心健康,并可能导致长期存在的严重心理痛苦和精神障碍[5]。PTSD是创伤性事件所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指对亲身经历的或目击的导致或可能导致自己或他人死亡或严重躯体伤害的意外事件或严重创伤的强烈反应。患者经历创伤性事件后,仍对该事件反复体验,并有避免引起相关刺激的回避行为和高度的警觉状态,病情持续以至引起主观上的痛苦和社会功能障碍叫做创伤性事件的主观评定,由此可以得出创伤性事件为潜在的危险因素。
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不仅是事故、灾难的直接受害者,PTSD也可以发生在工作环境中见证过恐怖事件的人群。Everly[5]认为,PTSD的高危职业人群是消防、救灾、公安、执法及医务人员。医务人员由于经常面对死亡、疾患和各种创伤情境,相对于其他人员,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最大的。每卷入一场事故或灾难,他们就有患上急性应激障碍的可能,而急性应激障碍是PTSD的重要危险因素。口腔颌面外科的医护人员经常暴露于拯救创伤事件的患者,经常面对最初、最血腥的场面。Jonsson等[7]在瑞士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医疗人员经历过创伤性事件,其PTSD的终身患病率超过15%。Ravenscroft[8]的研究显示15%的医疗工作人员有PTSD症状。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是抢救颌面部创伤患者的主体,担负职业使命,处处为诊疗思考观察。因而,各种压力源在其身上体现得更为集中与明显,更易导致PTSD的发生。另一方面经常倒班及繁重的工作,由于创伤事件发生量大,突发事件多,工作节奏快,患者病情复杂多变且难以预见,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必须经常处理急症病例和危急情况,不能按时下班,经常倒班,生活无规律,身心得不到调整,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频繁的轮班影响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的社交活动和家庭生活,造成情绪波动和不良心理状态,导致出现睡眠障碍、四肢乏力、疲劳感等,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回避症状与警惕性增高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虽然不是事故、灾难的直接受害者,但经常接触死亡和悲惨事件,比如意外交通事故、暴力、猝死、严重烧伤、谋杀等。参与救援剧烈而长时间的目击或感受对创伤的描述,对创伤反应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常有反复再现的情境或恶梦,就好像亲身经历过患者的创伤事件,并出现焦虑、失眠、易惊醒、注意力集中困难、警惕性增高,或抑郁、情感淡漠、与旁人疏远、回避生活、回避工作等心理和行为表现,这样的情感反应被称之为间接精神创伤或二次创伤压力[9]。Figley[10]认为不同性质的应激源对产生回避症状以及警惕性增高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创伤性事件的类型及其发生率。Greenberg等[11]认为,患者创伤后的血腥场面的刺激对医护的心理影响比每天处理危重患者产生的心理影响大得多,产生回避症状和警惕性增高的可能性大。因此长期、反复暴露于压力事件即高发生率是形成回避症状和警惕性增高的重要因素。
个体易感因素
年龄:医务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的承受能力在不断增加。年龄小、工龄短的医务人员往往采用不成熟的应付行为来处理应激,这与年龄小、工龄短的医务人员心理素质不成熟、颌面部创伤诊疗业务技术不熟练、心理承受能力差有较大关系。本研究出现回避症状80人,警觉性增高者43人,均为年龄小、工作时间短、诊疗业务不熟练。
性别:男性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危险性高于女性,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均数大于女性,但经历创伤事件后女性发生PTSD的比例几乎是男性的2倍。Kessler等[12]报道女性PTSD的终生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 (分别为10.4%和 5.0%,P < 0.05)。汪向东和姜经纬[13]对181名张北地震后灾民的研究表明,3个月内PTSD的患病率男性为13.5%(10/84),女性为24.7% (24/97)。因此女性发病率远高于男性,然而在医学领域内女性人数远大于男性。
个性特征与应对方式:个性特征、应对方式与创伤后社会心理调节及适应密切相关。刘光雄等[14]的研究表明,个性特征表现为情绪倾向不稳定、高掩饰性的个体更易患PTSD。吴兴曲等[15]对高原汽车兵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性格外向、乐观者易采用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面对压力事件,比如转移注意力或分散精力、写日记或找好友宣泄、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等,而这些干预措施均有利于降低PTSD的发生率。
社会支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减少PTSD的发生[15]。在创伤后因素中,受害者如能找到适宜的应对方法或获得相应的有效支持则可避免发生PTSD,而使受害群体的PTSD发病率降低,相反,即使是相对较轻微的创伤,如得不到相应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受害者则易患PTSD。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管理者的支持是影响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最有效方式。然而,有研究表明67%的医护人员认为发生创伤性事件后,她们不能从医院管理层获得充分的社会和心理上的支持[16]。
综上,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产生PTSD的潜在危险因素包括创伤性事件、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个体易感因素、社会支持因素。目前年轻的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是该卫生事业的主体,其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医疗服务质量,像口腔颌面外科这样容易发现PTSD的领域,建议应遵循循序渐进的思路逐步诱导年轻的医护人员接触创伤患者,并及时了解其心理状况,同时呼吁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口腔颌面外科医护人员PTSD问题,关注其身心健康,促进口腔颌面外科医疗事业的发展。
[1]谢巧明,向虎,黄键,等.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应激源类型分析 [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1,11(2):103-104.
[2] 张勇辉.创伤后应激障碍 [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2011,28(3):159-162.
[3]Breslau N.Epidemiologic studies of trauma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other psychiatric disorders[J].Can J Psychiatry,2012,47(10):923-929.
[4] 李祖兵.口腔颌面创伤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51-52.
[5]Everly S,Ehlers A.PTSD symptoms,response to intrusivememories and coping in ambulance service workers[J].Br J Clin Psychol,2009,38(1):251-265.
[6]刘贤臣,郭传琴,刘连启,等.Aohenbach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7,11(4):200-203.
[7]Jonsson A,Segesten K,Mattsson B.Posttraumatic stress among Swedish ambulance personnel[J].Emerg Med J,2003,20(1):79-84.
[8]Ravenscroft F.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ego defense mechanisms and empathy among urban paramedics[J].Psychol Rep,2010,79(1):483-495.
[9]Bryant RA,Harvey AG,Dang ST,et al.Treatment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a comparison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and supportive counseling [J].J Consult Clin Psychol,1998,66(5):862-866.
[10]Figley CR.Compassion fatigue as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anoverview [M].New York:Brunner/Mazel,2005:111-112.
[11]Greenberg MT,Feinbery ME,Meyer-Chilenski S,et al.Dimensions of life events that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distress:an evaluation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J].J Prim Prev,2007,28(6):485-504.
[12]Kessler R,Sonnega A,Bromet E,et al.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J].Arch Gen Psychiatry,2011,52(1):1048-1060.
[13]汪向东,姜经纬.创伤后应激障碍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 [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2,23(5):159-162.
[14]刘光雄,杨来启,徐向东,等.车祸事件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1(1):69-70.
[15]吴兴曲,王倩云,杨来启,等.1312名高原汽车兵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调查 [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2,20(6):431-433.
[16]Everly MJ,Heaton PC,Cluxton RJ Jr.Beta-blocker underuse in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J].Ann Pharmacother,2004,38(2):286-293.
买买提吐逊·吐尔地 电话:13899898797,电子邮件:maimaitituxuntuerdi@hotmail.com
R782.4
A
1000-503X(2014)02-0206-03
10.3881/j.issn.1000-503X.2014.02.018
2013-04-22)
·综 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