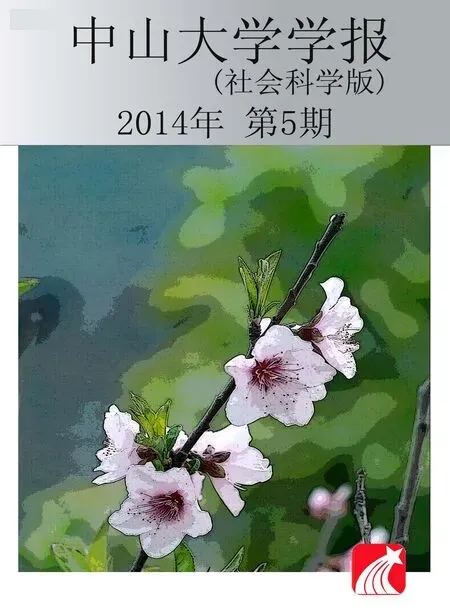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承继及其师门护持之功*
张 天 杰
黄宗羲(梨洲,1610—1695)是晚明清初的大家,也是蕺山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然而论其学者却极少提及其老师刘宗周(蕺山,1578—1645)。事实上黄、刘之间的关系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①目前关于黄宗羲与刘宗周关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大多仅以《明儒学案》之《师说》或《孟子师说》来讨论其承继关系,相关成果详见下文说明。其他论文则重在比较哲学思想而对学术传承讨论不多,如朱义禄:《黄宗羲、刘宗周思想比较初探》,《浙江学刊》1987第2期;[日]难波征男著、钱明译:《念台学与黄宗羲的道统意识》,《浙江学刊》1992年第1期;吴光:《从阳明心学到“力行”实学——论黄宗羲对王阳明、刘宗周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与理论创新》,《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3期;杨祖汉:《黄梨洲对刘蕺山思想的承继与发展》,杨祖汉、杨自平主编:《黄宗羲与明末清初学术》第2章,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21—46页。另外还有论及黄宗羲从学刘宗周一事,然就二人学术关系却讨论不多,如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44页;方祖猷:《黄宗羲长传》第2章第3节,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4页。。黄宗羲受蕺山学的影响很大,他对刘宗周也极为推崇,并以传承蕺山学为己任,为承继先师未竟之事业、护持师门之宗旨不遗余力。自从受父命而从游刘宗周之后,黄宗羲就经常跟随刘宗周,听讲于绍兴的证人书院。刘宗周去世之后,黄宗羲成为《刘子全书》编刊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又编撰了《子刘子行状》与《子刘子学言》。黄宗羲从刘宗周的遗著之中得其为学宗旨,此后便致力于承续先师未竟之事业,完成了《孟子师说》与《明儒学案》的编撰。黄宗羲自己的著述与讲学可以说是在刘宗周的方向上继续开拓,他的《明夷待访录》也有着刘宗周学术的影子,他讲学于甬上证人书院之初曾大力弘扬蕺山学。为了维护刘宗周“意为心之所主”等宗旨,保存老师学术的本来面貌,黄宗羲对其他蕺山学派的同门篡改先师遗著等行为多有批评,其中体现了大学者的严谨与学术史的高度。黄宗羲自许为师门之薪传,他光大师门的努力也得到了同门及其他同时代学者的认可,将其与孔门之曾子、朱门之黄幹相提并论。黄宗羲在使蕺山之学“如日中天”的同时,又超越于师门之“藩篱”,开创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继承与超越双丰收之取得,与他对“师门”采取“护持”而不“卫道”的态度有关。
一
天启六年(1626),黄宗羲十七岁。其父黄尊素(白安,1584—1626)被阉党所逮,黄宗羲送至郡城绍兴,当时被革职在家讲学的刘宗周特地到城外的佛寺,为黄尊素饯行,于是黄尊素命黄宗羲师事于刘宗周*[清]黄炳垕:《黄宗羲年谱》,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页。。随后黄尊素被害,黄宗羲当时并未留在绍兴受学。
崇祯四年(1631),刘宗周与陶奭龄(石梁,1571—1640)举证人社讲学于绍兴,黄宗羲就前去听讲。后来因为讲学宗旨之争,证人社出现分裂,黄宗羲等人“于是邀一时知名之士数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而此数十余人者,又皆文章之士,阔远于学,故能知先生之学者鲜矣”*[清]黄宗羲:《思旧录》“刘宗周”条,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341—342页。。黄宗羲是支持刘宗周讲学的重要弟子之一,但是在他看来,当时的刘门弟子大多不能懂蕺山之学,甚至连他自己也是如此。因为与其他士子一样,黄宗羲也致力于举业文章。他曾回忆:“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清]黄宗羲:《恽仲昇文集序》,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4—5页。《鲒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对此的说法略有不同:“公尝自谓受业蕺山时,颇喜为气节斩斩一流,又不免牵缠科举之习,所得尚浅,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为之尽释,而追恨为过时之学,盖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黄宗羲这样说,有自谦的因素,但也是实情。从别处相关的记载来看,当年的黄宗羲与其师也多有不合之处。他说:
先生题魏忠节公主,羲侍先生于舟中。陈几亭以《与绍守书》呈先生。先生览毕付羲。其大意谓:“天下之治乱在六部,六部之胥吏尽绍兴。胥吏在京师,其父兄子弟尽在绍兴,为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子弟,则胥吏亦从之而化矣。故绍兴者,天下治乱之根本也。”羲一笑而置之,曰:“迂腐。”先生久之曰:“天下谁肯为迂腐者?”羲惕然,无以自容。*《蕺山学案》,[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版,第1546页。此事《思旧录》也有提及而略有不同(见《思旧录》“陈龙正”条,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372页)。
崇祯七年(1634),刘宗周的弟子魏学濂(1608—1644)为其父、刘宗周的友人魏大中(1575—1625)举行葬礼,特请刘宗周题写神位,因为黄宗羲之父也是魏大中的友人,故二人同去同回。从舟中的讨论可以看出当时作为党人或名士的黄宗羲,与已经是粹儒的刘宗周的差异,也可以从此知道当时的黄宗羲对于蕺山之学确实并未能真正窥探其门墙。他自己还说:“甲戌岁,随先师至嘉禾,陈几亭以遗书为馈,先师在舟中阅之,每至禅门路径,指以示弟,弟是时茫然。”*[清]黄宗羲:《与顾梁汾书》,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212页。《明儒学案》记此事为:“然当《高子遗书》初出之时,羲侍先师于舟中,自禾水至省下,尽日翻阅。先师时摘其阑入释氏者以示羲。”(《蕺山学案序》,[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册,第1509页)黄、刘谈论陈龙正书信及其所赠《高子遗书》,黄炳垕《黄宗羲年谱》25岁条也有记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2册,第25页)。当时对于儒释之别,黄宗羲也较为茫然,直到后来读了刘宗周的《论学书》等著述才渐渐心中明了起来。
顺治二年(1645)六月,绍兴太守降清之后,黄宗羲与刘宗周曾有一次会面。黄宗羲从绍兴郊外,赶至刘宗周绝食避难地杨塴。他后来说:
乙酉六月□日,先生勺水不进者已二十日。道上行人断绝,余徒步二百余里,至先生之家,而先生以降城避至村中杨塴,余遂翻峣门山支径入杨塴。先生卧匡床,手挥羽扇。余不敢哭,泪痕承睫,自序其来。先生不应,但颔之而已。时大兵将渡,人心惶惑,余亦不能久侍,复徒步而返,至今思之痛绝也。*[清]黄宗羲:《思旧录》“刘宗周”条,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342页。
这最后的会面没有谈及学术,不过刘宗周那种殉道而死的精神,应该会对黄宗羲触动很大。他回家之后,就奉母避地于余姚一带的山野乡村之中。
虽然当年的黄宗羲并未真正于蕺山之学有所得,但他还是以得闻蕺山之讲学而自豪。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曾侍蕺山夫子,往往得闻绪论,今亦荒落久矣。”*[清]黄宗羲:《与顾梁汾书》,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211—212页。黄宗羲真正从事于蕺山之学的研习并有所得,然后继承刘宗周事业,已是老师去世之后。他说:“某幼遭家难,先师蕺山先生视某犹子,扶危定倾,日闻绪言,小子蹻蹻,梦奠之后,始从遗书得其宗旨,而同门之友,多归忠节。”*[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序(原本)》,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78页。其《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也说:
昔者,阳明之良知与晦翁之格物相参差,学者骇之,罗整庵、霍渭崖、顾东桥龂龂如也。然一时从游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师说,而与晦翁并垂天壤。先师丁改革之际,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吴磊斋、祁世培、章格庵、叶润山、彭期生、王元趾、祝开美一辈,既已身殉国难,皋比凝尘。曩日之旅进者,才识多下。*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55页。黄宗羲关于师门冷清的记述颇多。如《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嗟乎!阳明身后,学其学者遍天下,先师梦奠以来,未及三十年,知其学者不过一二人……”《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二稿):“环视刘门,知其学者亦绝少。徒以牵挽于口耳积习,不能当下抉择,浅识所锢,血心充塞,大抵然矣。”(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225、362页)
黄宗羲指出:与王阳明(1472—1529)论辩的学者众多,如罗钦顺(整庵,1465—1547)、霍韬(渭崖,1487—1540)、顾璘(东桥,1476—1545)等,因为师从王阳明的弟子众多,而且都能够发明师说,所以能够光大阳明之学。但是刘宗周死后,诸多取得功名、有一定影响的高第弟子如金铉(伯玉,1610—1644)、吴麟征(磊斋,1593—1644)、祁彪佳(世培,1602—1645)等人都已经殉节。与阳明后学相比而言,蕺山后学确实显得特别冷清。还有,在黄宗羲看来,“才识多下”的大概是指入清之后蕺山学派其他弟子诸如刘宗周之长子刘汋(伯绳,1613—1664)以及张履祥(杨园,1611—1674)、吴蕃昌(仲木,1622—1656)等偏向程朱之学的刘门弟子。也正因为如此,黄宗羲才感到振兴师门责无旁贷。
二
黄宗羲入清之后的大半生,致力于学术。其中特别关键的几项则都与其师刘宗周有关,可以说也是承继了先师未竟的事业而后才能有所开拓。黄宗羲一生都对刘宗周极为推崇。他说:
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清]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221页。
制科盛而人才绌,于是当世之君子,立讲会以通其变,其兴起人才,学校反有所不逮……逮阳明之徒,讲会且遍天下,其衰也,犹吴有东林,越有证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于是。*[清]黄宗羲:《陈夔献墓志铭》,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452页。
黄宗羲指出:无论是从明代学术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还是从明代讲会之发展来看,刘宗周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对黄宗羲来说,刘宗周是其一生最为重要的老师,他后来所做的事业,无论是相关著述还是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都是以承继蕺山学为己任的结果。因此,与黄宗羲亦师亦友关系的李邺嗣(杲堂,1622—1680),称其为“刘门之曾子”:
昔者夫子之门,惟曾子为最少,而于圣人之传独得其宗……孟子既殁,千余年而有宋诸大儒起,后三百年而有阳明子,复百余年而有子刘子。先生少侍教于刘门,得传其学。及子刘子从容尽义,先生日侍其侧,年只三十有五耳。自后晦盲风雨,先生抱蕺山之遗书,伏而不出,更二十余年,而乃与吾党二三子重论其学,而子刘子之遗书亦以次渐出,使吾道复显于世,有以待夫后之学者,是则先生之功,固亦刘门之曾子也。*《黄先生六十序》,[清]李邺嗣著、张道勤校点:《杲堂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34—435页。
后人认为曾子传《大学》《论语》等孔门之教,黄宗羲在传承先师学术上所做的努力则远远超越了曾子,这个比方还是比较恰当的。黄宗羲的《孟子师说题辞》说:
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羲读《刘子遗书》,潜心有年,粗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未备,或不能无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学者纠其谬云。刘门弟子姚江黄宗羲识。*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48页。钟彩钧就刘宗周关于孟子的论说与黄宗羲的《孟子师说》进行过比勘,认为两者对孟子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异:“其实《孟子师说》已经采取了与蕺山不同的研究方向……对孟子年代的考证、对故籍的考证、对历史的考证、与博物之学等等,都不是蕺山学说所能范围的,而可嗅到新时代的气息。”(钟彩钧:《刘蕺山与黄梨洲的孟子学》,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408页)
其中不无将自己看作是蕺山学派之大弟子,真正承续于蕺山之学的意味。无论《孟子师说》与刘宗周的学说有无出入,承继先师未竟之事业的意思还是在的。全祖望也说:“梨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师说》,以蕺山已有《大学统义》、《中庸慎独义》、《论语学案》,惟《孟子》无成著,故补之也。”*《鲒埼亭集》外编卷27《跋黄梨洲孟子解》,[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280页。
黄宗羲承继先师所做的事业之中,最为重要的自然还是编撰《明儒学案》。陈祖武先生早就指出,对于黄宗羲影响最大的是其师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陈祖武:《明儒学案杂识》,氏著:《清儒学术拾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明儒学案》卷首的《师说》就是刘宗周原本为《皇明道统录》所撰的“断论”。黄宗羲自己也说《明儒学案》的编撰是在继承先师的事业,并且姜希辙(定庵,?—1698)与董玚(无休,1615—1692)等刘门弟子也有参与。他说:“余于是分其宗旨,别其源流,与同门姜定庵、董无休操其大要,以著于篇,听学者从而自择。”*《明儒学案序》,[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第8页。《明儒学案》编成之后,黄宗羲序云:“某为《明儒学案》……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序(原本)》,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78页。可见黄宗羲兢兢业业编撰《明儒学案》,旨在对老师的学术有所发明,故而才将《师说》置于全书卷首。再说《明儒学案》先编撰的是《蕺山学案》,完成于康熙十五年前后,董玚曾为之写序,认为黄宗羲“有功于师门”,如朱门之有黄幹(勉斋,1152—1221):
黄子既尝取其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道统之著者述之,而又撮其《遗编》,会于一旨。以此守先,以此待后,黄子之有功于师门也,盖不在勉斋下矣。世有愿学先师者,其于此考衷焉。*[清]董玚:《刘子全书抄述》,载[明]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692页。
黄宗羲在与董玚、姜希辙等人一起完成《刘子全书》的编辑、刊刻以及撰写《子刘子行状》之后,就开始编撰《明儒学案》,全书又以《蕺山学案》殿后。黄宗羲在此学案的序中说:“识者谓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蕺山学案》,[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册,第1514—1515页。在他看来,刘宗周的学术达到了整个明代学术的最高峰,将《蕺山学案》放最后也就是以此为有明一代之理学,乃至整个宋明之理学做一总结。从此也可得知,黄宗羲之所以如此编撰《明儒学案》,与其先师刘宗周关系甚大。
还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也可以找到刘宗周的影子。刘宗周的外王理想常常碰壁,这恰好是因为他对于君主专制有所思考,甚至也有一些较为激烈的批判。这些思考应该对黄宗羲全面地批判君主专制以及形成更为系统的外王之学,有一定的影响。此处特别选择被黄宗羲选入《子刘子行状》卷上的刘宗周奏疏之中的言论,简要说明这种影响:
——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不得尽其忠,则陛下之耳目有时而壅矣;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陛下之意见有时而移矣。
——臣闻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曰“君职要,臣职详”。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亲。群臣奔走受成之不暇,益相与观望,为自全之计。致一人孤立于上而莫之与,岂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讲与?仰惟陛下躬亲圣学,法尧舜之明目达聪,而推本于舍己,亟舍其聪明而归之暗。非独舍聪明,并舍喜怒、舍好恶、舍是非,至于是非可舍,而后以天下之是非为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聪明为大聪明。
——今日第一义,在皇上开诚布公。先豁疑关,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慨然引为皇极主。于是进贤才以资治理,开言路以决壅闭,次第与天下更始,宗社幸甚。*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216、230、236页。
刘宗周外王思想的本质还是传统儒家的“得君行道”,核心问题在于“格君心之非”,希望皇帝从事圣学、收拾人心。他也注意到君主专制的弊病,提出天下不可一人理,应该还天下于天下;舍己,舍去自己的聪明、喜怒、好恶、是非而归之于天下;“公天下”必须先“格君心”。《明夷待访录》则几乎彻底放弃了“得君行道”,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正是君主专制本身。黄宗羲说: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2—3,4—5,10页。
这些思想恐怕是刘宗周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就“天下不能一人治”、“以天下之是非为真是非”等观念而言,黄宗羲与刘宗周非常相似。他说: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③[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2—3,4—5,10页。
关于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黄宗羲与刘宗周比较接近,不过他提出为臣当是“为天下”而不是“为君”,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又深了一层。在刘宗周思想的影响之下,进一步发展了的还有论学校的作用。黄宗羲说:“学校,所引养士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④[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2—3,4—5,10页。刘宗周提出应该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其前提是君主的“开诚布公”、“进贤才”。黄宗羲则提出更广阔的思路,还要公是非于学校,因为学校是培养士大夫的地方,治理天下的方略皆处于学校。关于黄宗羲政治思想与刘宗周的关系,张灏先生指出:黄宗羲继承了刘宗周的那种内化超越意识与致用精神并进一步发展,不但要落实于个人道德的实践,而且还要植根于群体的政治社会生活,最终形成黄宗羲式的经世精神;黄宗羲思想中特有的高度批判意识,其结果不但是以师道与君道对抗,甚至完全突破纲常名教中所蕴含的宇宙神话,而提出有君不如无君的观念*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刘宗周对黄宗羲的影响,还有对于人格、节操的特别坚守。黄宗羲入清之后成为遗民,从黄宗羲一直到之后的全祖望,将史书的人物列传转型而成为彰显人格、节操的仁人志士的列传*参见蒋年丰:《从朱子与刘蕺山的心性论分析其史学精神》,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3年,第1137页。,最后形成了“讲性命之理必归究于史”的浙东史学传统,其中当有刘宗周的影响所在*杜维明、东方朔:《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三
刘宗周去世之后,刘汋、黄宗羲、董玚、姜希辙等刘门弟子参与了《刘子全书》的整理、选辑、刊刻工作;刘汋编撰了年谱;黄宗羲与恽日初(仲昇,1601—1678)编撰了行状;选编刘宗周讲学语录的比较多,主要有张履祥《刘子粹言》、陈确《山阴语抄》(又名《蕺山先生语录》)、恽日初《刘子节要》以及黄宗羲《蕺山学案》与《子刘子学言》。如何来编全书、选语录,是关系到刘宗周学术解释权之争的重要问题,其中也体现出蕺山学派内部在学术上的分歧。黄宗羲是刘门弟子之中参与相关工作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可以说起到了师门护持之功。
《刘子全书》最后得以保存原貌,正式刊刻为《刘子全书》40卷,黄宗羲的作用尤为关键。其《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说:“王颛庵先生视学两浙,以天下不得睹先师之大全为恨,捐俸刻之。东浙门人之在者,羲与董玚、姜希辙三人耳。于是依伯绳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数本不同者,必以手迹为据,不敢不慎也。”*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55,55页。
王颛庵,即王掞(1644—1728),当时为浙江学政。黄宗羲原有家藏刘宗周遗书的抄本,又因为其女婿刘茂林即刘汋之子、刘宗周之孙,故得到刘宗周的原稿与刘汋的整理稿,从而《刘子全书》才得以精心校勘。此处黄宗羲之所以特别指出“以手迹为据”,是因为刘汋在整理过程中曾对原文有所删改。
刘汋是《刘子全书》前期整理最为重要的参与者,但黄宗羲对他多有不满:
当伯绳辑遗书之时,其言有与洛、闽龃龉者,相与移书,请删削之,若惟恐先师失言,为后来所指摘。嗟乎!多见其不知量也。④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55,55页。
夫先师宗旨,在于慎独,其慎独之功,全在“意为心之主宰”一语,此先师一生辛苦体验而得之者。即濂溪之所谓“人极”,即伊川所言“主宰谓之帝”,其与先儒印合者在此。自“意者心之所发”之注,烂熟于经生之口耳,其与先儒抵牾者亦在此,因起学者之疑亦在此。先师《存疑杂著》,大概为此而发。其后伯绳编书,另立《学言》一门,总括先师之语,而《存疑》之目隐矣。*[清]黄宗羲:《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224页。标点有所改动。
黄宗羲对刘汋整理《刘子全书》的批评有二:其一,刘汋对刘宗周著述之中与程朱之学有抵触的地方,曾与张履祥、吴蕃昌等同门协商,认为应该删去,以免先师失言而被后人指责;其二,刘汋擅自将刘宗周辑为《存疑杂著》的一部分语录,与其他的语录一起共同编为《学言》,这样就把刘宗周存疑而另立一册的原意给掩盖了。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刘汋似乎并不认同刘宗周“意为心之主宰”,因为这一观点与程朱之学有冲突,程朱一系都认为“意者心之所发”。
无独有偶,另一刘门高弟陈确(1604—1677)对刘汋也有同样的不满。他说:
《年谱》出绳兄手笔,自另成一书,不妨参以己见,然关系先生学术处亦自宜过慎。至于《遗集》言理之书,或去或留,正未易言。无论弟之浅学不敢任臆,即如绳兄之家学渊源,表里洞彻,恐亦遽难裁定……然则先生之学亦岂易言乎?与我见合者留之,不合者去之,然则岂复为先生之学乎?以绳兄之明睿,万万无此虑,而弟犹不敢不偲偲过虑者,只见其不知量耳,而不能自已。*《寄张奠夫刘伯绳两兄书》,[清]陈确撰:《陈确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7页。
陈确认为刘汋编撰《蕺山刘子年谱》代表了自己对于刘宗周思想学术的理解,所以即使掺杂以自己的理解也无大妨,但编辑《刘子全书》则不能任由自己的主张而决定去留,因为刘宗周的学术不易理解,为先人整理遗书,还是应该以存真为原则。这些看法与黄宗羲相同。也就是说,在编辑刘宗周遗书这件事情上,真正与黄宗羲观点一致的,大概只有陈确一人。其他偏向程朱之学的张履祥、恽日初等刘门弟子与刘汋的观点一致,都认为“意为心之主宰”等与程朱有冲突的地方应该谨慎处理。
黄宗羲对师门的护持,除了编撰《刘子全书》相关的争论之外,还在与恽日初的相关论评文字之中可以看出来,这也可更为明确地看到其对于“师说”解释之重视。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曾为恽日初文集写序,其中说:“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发。盖仲昇之学,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故其言与先儒或同或异,不以庸妄者之是非为是非也。”*[清]黄宗羲:《恽仲昇文集序》,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5页。黄宗羲此处的观点,与其对陈确评价的早期文字接近,既肯定了恽日初学术的价值,有诸多“发先儒所未发”之处,这种创见“不以庸妄者之是否为是非”,恽日初与陈确一样都有一种独立精神,不是人云亦云;也肯定了恽日初治学的“务得于己”,重视自己的践履体验。但是,从此处也可以看出来,黄宗羲对于师门之护持极为严格,并不轻易认可恽日初对蕺山之学有了真正的承继。
后来,恽日初完成了《刘子节要》选编。黄宗羲看到之后,无论从编撰的体例,还是对刘宗周语录的选择,都极不赞同*关于黄宗羲与恽日初的学术分歧,参见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289页。。于是,本来恽日初是要黄宗羲作序,黄宗羲非但没有作序,还写了严词切责的回信。其中说:
——夫先师宗旨,在于慎独,其慎独之功,全在“意为心之主宰”一语,此先师一生辛苦体验而得之者……故于先师之言意者,一概节去以救之。弟则以为不然。
——《人谱》一书,专为改过而作,其下手功夫,皆有涂辙可循:今《节要改过》门无一语及之,视之与寻常语录泛言不异,则亦未见所节之要也。
——今先师手笔粹然无疑,而老兄于删节接续之际,往往以己言代之,庸讵知不以先师之语,迁就老兄之意乎?《节要》之为言,与文粹语粹同一体式,其所节者,但当以先师著撰为首,所记语次之,碑铭行状皆归附录;今老兄以所作之状,分门节入,以刘子之《节要》,而节恽子之文,宁有是体乎?*[清]黄宗羲:《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224—225页。
其一,黄宗羲指出“意为心之主宰”乃师门之重要宗旨,所以恽日初删节刘宗周“言意”的语录,是其坚决不能认可的。其二,黄宗羲认为《人谱》是刘宗周讲下手工夫最重要的著述,恽日初将其当作普通语录而未曾选录,也是不能认可的。在黄宗羲看来,恽日初对于先师刘宗周思想的认识很有问题。还有,《刘子节要》一书的编撰体例也存在重大问题。恽日初将自己写的《子刘子行状》作为正文分门别类,然后节要而插入刘宗周语录;而且在删节接续的地方,用自己的话来代替老师的话。这些做法就有以自己的意思来组织老师本意之嫌疑,最后就会模糊老师的思想。无论是对老师的理解正误,还是如何编撰才能正确传递老师的思想,这两个方面黄宗羲的批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文章最后,黄宗羲又说:
嗟乎!阳明身后,学其学者遍天下,先师梦奠以来,未及三十年,知其学者不过一二人,则所藉以为存亡者,惟此遗书耳!使此书而复失其宗旨,则老兄所谓明季大儒惟有高、刘二先生者,将何所是寄乎?且也,阳明及门之士亦多矛盾,以其学之者之众也,有离者即有合者;先师门下,使老兄而稍有不合,则无复望矣。*[清]黄宗羲:《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225页。
对比阳明学派的发展,王门弟子论学常有矛盾,王门后学与阳明主旨有离也有合。因此,黄宗羲指出,维护师门宗旨的关键就是保存先师遗书的传播的正确性。关于恽日初《刘子节要》一书请黄宗羲写序的情况,《明儒学案序(原本)》的记述也可作为补充:
岁己酉毘陵恽仲昇来越,著《刘子节要》。仲昇,先师之高第弟子也。书成,某送之江干,仲昇执手丁宁曰:“今日知先师之学者,唯吾与子,两人议论,不容不归一,唯于先师言意所在,宜稍为通融。”某曰:“先师所以异于诸儒者,宗旨正在于意。宁可不为发明?”仲昇欲某叙其《节要》,某终不敢。是则仲昇于殊途百虑之学,尚有成局之未化也……*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78页。
恽日初为学也有所转向于程朱,所以对刘宗周“言意”之处不同于程朱的地方,不能认同。他希望黄宗羲在“言意”问题上能够通融,然后为其作序,黄宗羲则终究“不敢”。在恽日初看来,为了传承蕺山之学,某些问题上可以通融。黄宗羲却认为,正是为了使得蕺山之学得以传承下去,所以在关键之处决不可迁就。黄宗羲对恽日初再三批评,就是因为他对刘宗周学术宗旨的理解有问题。他还指出恽日初为学的弊病就在于过于固执,“于殊途百虑之学,尚有成局之未化也”。
从黄宗羲对刘汋、恽日初等人的种种批评来看,他为了护持师门之宗旨,可谓用心良苦。这种护持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全书或语录的选编,黄宗羲认为必须要以“存真”为原则,保持老师著作的原貌;一是对于先师学术宗旨的认识,黄宗羲认为不能掺入己意,即便与先儒不合也不应轻易怀疑。从黄宗羲师门护持的言论来看,有着大学者的严谨态度,达到了学术史的高度。黄宗羲后来自许为在世的刘门弟子之中惟一能够继承先师学术的学者,这种“自许”也确实合乎事实。
四
作为蕺山学派最为重要的传承者,黄宗羲得到了刘门及许多学者的认可。当时都认可他作为刘门的大弟子,比如曾问学刘宗周的施邦曜(1585—1644)就说:“余友黄太冲,蕺山之高弟子也。”*[清]黄宗羲:《思旧录》“施邦曜”条,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347页。这种看法不只是在刘门内部,当时浙东一带的士人阶层中都有这样的看法:“时阮大铖以定策功骤起,思修报复,遂广揭中人姓名,造《蝗蝻录》,欲一网杀之。里中有阉党某,首纠念台先生及其三大弟子,则祁都御史世培、章给事羽侯与公也。”*[清]黄炳垕:《黄宗羲年谱》35岁条,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2册,第30页;[清]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清]黄炳垕撰、王政尧点校:《黄宗羲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年,第65页;《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216页。崇祯十一年(1638),阮大铖(1587—1646)在南京为阉党翻案,黄宗羲与东林子弟、太学生等一百四十人愤起贴出《南都防乱公揭》揭露其丑行。福王政权建立之后,阮大铖以《南都防乱公揭》中的署名图谋报复。黄宗羲家乡的阉党党徒叫嚣要先纠出黄宗羲等刘宗周三大弟子,后因南京战事之起而得幸免。此事《鲁之春秋》也有记载:“大铖嗾使私人朱统镇首纠左都御史刘宗周及佥都御史祁彪佳、给事中章正宸与宗羲,时称宗周三大弟子。”*《鲁之春秋》卷10《黄宗羲》,[清]李聿求撰、凌毅标点:《鲁之春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黄宗羲光大师门的努力主要还是在清初,当时的同门陈之问(1616—1684)说:“黄子于蕺山门为晚出,独能疏通其微言,证明其大义,推离还源,以合于先圣不传之旨,然后蕺山之学如日中天……”*陈之问为黄宗羲所撰写的寿文,见黄宗羲《陈令升先生传》引述(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600页)。这一评价可以代表入清之后的刘门弟子对黄宗羲的看法。黄宗羲撰写《子刘子行状》等阐发先师学术的文章,确实做到了“疏通其微言,证明其大义”等等,对于蕺山学的发扬光大有着极大的推动。更为详尽地评价黄宗羲对蕺山学的推动的是全祖望,他说:“南雷自是魁儒,其受业念台时,尚未见深造,国难后所得日进,念台之学得以发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则又轶出念台之藩,而窥漳海之室。然皆能不诡于纯儒,所谓杂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学言之,有明三百年无此人,非夸诞也。”*《鲒埼亭集》外编卷44《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695页。从发明蕺山学的角度来说,黄宗羲确实功莫大焉。全祖望更为肯定的还是黄宗羲“兼通九流百家”,其治学规模已经超出了蕺山学派。
黄宗羲自许为师门薪传,以倡明“师说”为己任,但是其治学规模远远超过其师,无论治学的范围与方法都与刘宗周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如何来理解他们之间的学术承继关系呢?当代学者赵园曾说:
黄氏本人虽以师门薪传为己任,但其学之规模、气象,非所谓“师门”所能涵盖。黄宗羲虽以倡明师说为己任,未见得即以“蕺山”为门派。他的辨明师说,也不取卫道姿态,见识明达,境界迥出俗流。令后人称羡的明清之际学术气象,也应由此种人物造成。*赵园:《刘门师弟子——关于明清之际的一组人物》,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编:《新国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0—201页。
黄宗羲护持师门之宗旨、承继师门之学术,但是他并没有狭隘的“卫道姿态”,不为门户所局限,而是持有“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就了梨洲之学的博大精深,以及清代浙东学派的辉煌。
——保山县学官先师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