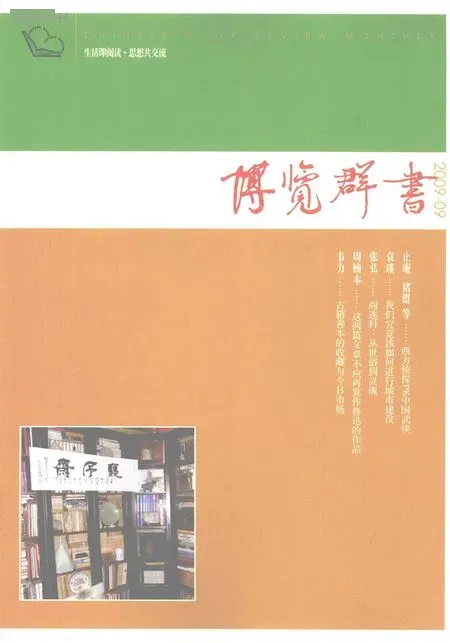顾诚门下问学记
○陈宝良

顾诚(1934—2003),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
光阴倏忽,转瞬先师顾诚教授谢世已近八载。对我来说,先师去后,确有“德孤”、“道孤”之感,决然离开自己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跼蹐西南一隅,遁迹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之螺壳室中,继续我的教学与研究生涯。离开将近六年,却一直无缘重回京师,拜谒先师墓前,行弟子一炷清香之礼。这是我最大的歉疚。话虽如此,我却一直秉持“心丧”之说,先师形象几度入我梦中,且每年的6月25日,都会献上一瓣心香,默默告慰先师在天之灵。
作为先师的开门弟子,很多熟识的学界师友无不以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应该已经得其真传。其实不然。反思自己求学、治学历程,我实属“不肖”弟子。理由有如下四条:第一,1987年初夏,当我硕士毕业之时,历史系决定让我留校任教,这也是先师的愿望。我却违背师愿,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职。第二,大约上世纪90年代初,先师刚获招收博士资格之时,我曾参加考试,却因英语差了几分,最后失去重回师门的机会。第三,俗云师规弟随,先生研究的兴趣与领域,诸如明末农民战争、元末明初与明清之际的史事考订、明帝国的耕地与疆域、明代的卫所制度等,我都不曾涉足,先师衣钵,没有很好传承。第四,囿于自己个性刚而鲁莽,负气出走他方,致使先师开拓的明史研究学科,一时断了学脉。上面几条,如果再有机缘质之先师,他一定颇为失望。
即使如此,若论对先师学问的了解,在同侪中应该无人出我之右。我与先师相识,得其亲炙,是在入师门之前。犹忆1983年的下半年,他开设“明末农民战争史”选修课。当时系中老师、学长盛传,先师教学,近乎苛严,选修其课者,得一良好成绩已属不易,稍有不慎,即有沦为不及格的惨境,得一优秀,更是奢望。我却年少无畏,更多的还是好奇,毅然决定选修此课。记得开课第一天,他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扣上风纪扣,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手提一个黑色人造革的包。这是他的典型打扮,几十年如此。仔细算来,当时他年近半百,面容清瘦,却又矍铄,两眼炯炯有神,讲课之时,声音显得低沉,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先师授课,大多板直地坐着,看着讲稿,不紧不慢地说出几经斟酌的史实,无演说家眉飞色舞之态。不过,说及一些较有意思的史事时,偶尔也会为之动容。因为没有过多地添加佐料,课前没有做足功课者,或许稍感枯燥;而对那些对史事已有所了解者来说,却能增广见闻,听之津津。期末考试采用的是课程论文的形式。我在听课之余,喜欢阅读相关史料加以印证。读夏燮所著《明通鉴》等史籍,谈及潜山之战时,称绰号“一堵墙”者为官军所杀。然在翻阅刘献廷《广阳杂记》时,却明言“一堵墙”为孙可望的绰号,一直活到永历朝廷,成为四将军之一。于是,广泛查阅史料,撰就《潜山之战小考》一文。出乎意料,此习作深得他的赏识,获得88分的佳绩。得此鼓励,第二年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有幸名列弟子籍。
先师门墙峻严,名闻遐迩。招收弟子,一以“读书种子”为标准,若是言谈中稍露混文凭并藉此作为敲门砖者,一概拒之门外。记得1983年,先师第一次招收硕士生时,只有同系79级一位学兄,笔试已过,面试之后,则又名落孙山。1984年,与我一同应考的一位女同学,好学文静,堪称才女,人又秀气,也是笔试已过,仅因在面试时流露出学成之后不愿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之意,被先师断然拒绝。很多师弟师妹都有同感,他们在求学期间,得先师批评者多,赞誉者少。尤其是到了撰写毕业论文之际,无不神经紧张,心中惴惴。他们有时向我抱怨,认为只有我才得先师宽纵。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在学问上,先师只对事,不对人,对我亦与其他同门一样,从未放宽尺度。毕业论文一事,让我终身难忘。记得在确定硕士论文题目时,先师鉴于我对学术史的兴趣,建议我关注明末“经世致用”之风。为此,我拟定《晚明“实学”思潮的起源及其流派》一题,进而完成此文,获其首肯。其后,又另撰《明代文化的动态研究》一文,写成之后,他也觉得满意。毕业前夕,经他同意,我将论文交付学校印刷厂铅印。就在论文已经付梓,且准备呈送校外答辩委员之时,先师突然骑车到了我的宿舍,告知我经过再三斟酌,还是提交关于晚明“实学”的论文为好。一听此言,我是满头大汗,惶恐之状,溢于言表。当时正好我将母亲接到北京游玩,听我解释之后,也不停地用家乡话说“倷个小人”如何不懂事理之类的话数落我。先师的母亲祖籍浙江,他尽管不能听懂全部话语,只懂“小人”(孩子)之意,但我母亲为此焦急的心情,大抵也是意会的。当我正着手将论文重新付印时,先师又骑车到了我的宿舍,告诉我论文不用再重印了。尽管只是虚惊一场,但事后向先师垂询为何有此波折,他直言相告,认为关于“文化”之文,时间跨度长,涉及问题多,难以把握,极易在答辩时露出诸多破绽。仅此而已。经此一事,我深为先师对待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所折服。
先师教书育人,只求大体,不求细末。换句话说,他以身体力行,教会了学生坐冷板凳的真功夫。这我深有体会。记得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第二年暑假,得知我将回老家的消息后,他突然把我叫到家里,给我开了三本书的书单,让我替他到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将三书抄录下来。为此,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辗转于南京龙蟠里、上海南京西路、杭州孤山三地,因是善本,且时间所限,只能用铅笔,不加标点地将此三书抄录下来。回到家中,我再作整理,加以标点,用钢笔重新誊写一遍,开学回京后交差。何以有此一举?其实,先师并非出于为了自己能看到此三部书的目的,而是为了通过此举,一则教会学生“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功夫,二则考察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而从效果上看,这让我确实受益匪浅。交差之后,在随后的交谈中,先师曾对我的标点或某些字提出过异议,但大抵还是得到了他的首肯。而我自己亦从抄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过去不曾知晓的知识。其中印象最深者,就是吴晋锡所著《半生自纪》一书,正是通过此书,我才了解到明代的总督有文、武之分。
先师治学之勤苦,在学界有口皆碑。王春瑜先生称其为学术“苦行僧”,不失为一种形象的比喻。他所研究的问题,均是教学上无法避开的重大问题,尽管多有新见,却不喜与人争论,写与人商榷的文章。私下他曾对我说,新见问世之后,自然会引起争论。这是好事,一切留待后世的检验,不必啧啧烦言,替自己辩解。若是动笔一辩,反而又为争辩者提供一次发表文章的机会。这可以拿一件事作为例证。先师自发表《明初耕地数新探》一文之后,学界曾有人撰文提出商榷。然先师对自己的见解很有自信,从无就此问题重作申论。记得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张海瀛先生通过新找到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就此撰文,提交大会。正是这新发现的史料,在耕地数的登记上,明确分为“军事”、“民事”两大系统,最终印证了先师之说不谬。我曾躬逢盛会,记得在小组的讨论上,主持者在作总结发言时认为,此争论可暂时告一段落,亦得到商榷者的认可。即使如此,先师犹有遗憾。在自传性文章《我与明史》中,深以未能事先获见此书为恨,且自认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他写过一篇《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文中引用大量史实,对姚氏之说多有纠谬,甚至不乏针砭,文笔酣畅淋漓。其实,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有些复杂。姚氏自小说《李自成》出版后,一度以明史研究者自任,对郭老旧说,颇多讥议,引起一些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同仁的反感,拟加以反驳。为避嫌疑,他们希望由所外且对明末清初史事有精深研究的学者撰文,为此找到了先师。先师尽管在观点上与郭老多有相左之处,但一则缘于情面难却,二则对姚氏之见甚至学风多不认同,才勉强撰得商榷一文,其反响之烈,出乎意外。
先师学有专攻,却又兴趣广泛。治史之余,尤为关注明清通俗小说。年值七龄,识字不多,即抱“武松会打虎,我会绕过拦路虎”的信念,开始阅读家中所藏残本《水浒传》。自后,又分别从同学处借阅了《三国演义》、《封神榜》、《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说唐》、《乾隆游江南》、《施公案》、《彭公案》、《江湖奇侠传》等。有此经历,实已为日后治史厚殖文字根柢。每阅史籍,除了摘录供治史的史料之外,诸如奇闻异谈之类,他亦多加注意,生前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一文,即为其证。又如明代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好长生之术,引发臣下大谈祥瑞之风,各地纷纷呈献玉兔、灵芝之类。玉兔者,即白兔,在今日已为平常之物,并不稀罕,何以作为一种祥瑞之物而进献皇帝?当时我正好对嘉靖崇尚道教之事颇感兴趣,曾就此事质之先师。他直言相告,明代的兔子多以灰兔为主,白兔较为稀有,故有祥瑞之征。先师曾云,退休之后,将不再撰写长篇的史学论文,专写文史札记。事实上,却是退而未休,文史札记的撰写,竟成遗愿。
古云学有“三证”,即出处、取予、生死。所谓的取予,就是如何过得“名利”一关。先师不逐利,清苦自持,不嗜厚味,身居陋室,甘心寂寞,不求闻达,却有“孔颜之乐”。他曾云,学者的最大幸福,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为后学提供帮助。尽管如此,其学术成就却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记得我在京都大学访问讲学时,日本知名学者夫马进先生曾与我谈起他与先师认识交往的经历。早年夫马先生到北京访学时,曾问及著名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在他相识的中国学者中,何人最有学问,陈高华先生脱口以先师应之。为此,夫马先生专门拜访先师,成就了中日学者相交的一段佳话。古云:“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揆之先师,确乎堪称“体道合德”的上士。古又云“没世而名不称焉”,一个“称”字,已有称道、名实相副二解。先师没世,做人处事,为人称道;其名虽不出史界,却是真正的名至实归。
从学风上说,先师学术渊源,似乎是远承乾嘉,近师援庵。其实不然。先师治学,无所依傍。我曾与他谈及学术渊源之事,他直言“我就是我”!师门问学二十载,从未听先师津津乐道于前辈学者。惟一的例外,就是他多次提到谭其骧先生。此是何故?当时不曾追问,现在更不好蠡测,就让它成为一个谜罢。
——保山县学官先师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