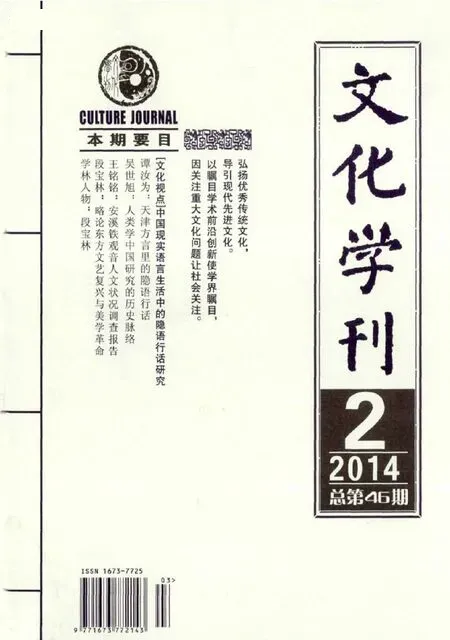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历史脉络*
(沈阳师范大学,沈阳 110034)
对于以“地方性知识”为学术思考之源泉的人类学来说,特定地方或区域的社会与文化至关重要,它们不仅仅构成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与之共同形塑了学术史中各具特色的“学术区”,从而推动着人类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作为整体人类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走过了百余年的学术历程,虽然还很难和诸如美拉尼西亚研究、非洲研究、南美研究这样的学术区相提并论,但也曾有过世界性的声誉,并因其复杂文明社会的特征而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和广阔的理论前景,因此,在宏观上对这段历史的脉络加以梳理,是现今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根基所在,也是迈向前辈学者早有预期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之首要任务。总体而言,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大致经过了1860-1920时期的异域星火、1930-1940的黄金时代、1950-1970时期的海外典范和1980年以来的全面复兴这几个时期。
一
在人类学兴起的初期,中国及其社会与文化便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在以进化论和传播论为主流的古典人类学中,它们不过是建构宏大理论的片段素材而已,真正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具有现代气质的少数异域人类学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延 (Jakob de Groot)、鸟居龙藏(Torii Ryuzo)、葛兰言 (Marcel Granet)和史禄国 (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他们的研究对人类学中国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甚至在整体人类学中也影响深远。
高延和葛兰言都具备汉学和人类学的双重学养,而且都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看待,试图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探讨其在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间的转化。不同的是,前者曾在海外华人社区和中国本土有过长期的田野作业,与民间社会有着密切的接触,并将田野经验与经典文献结合起来展开研究;后者则仅在北京有过短暂的停留,接触的对象也仅限于当时的文人阶层,主要基于经典文献进行研究。在理论倾向上,高延从民众的现实生活出发,采用自上而下的理论视角,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来自精英阶层;葛兰言则从经典文献出发,采用自下而上的理论视角,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出自民间社会。高延的代表作包括两卷本的《厦门岁时习俗》、六卷本的《中国的宗教体系》和《中国的大乘经研究》等,葛兰言的代表作则是《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和《中国文明》等。
高延和葛兰言的理论见解在人类学史中意义深远,后者的研究甚至对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当时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主要存在于汉学界,高延曾三获被誉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儒莲奖,葛兰言则两次获此殊荣。对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来说,二者的重要性直到1950年才引起了西方人类学者的关注,比如,英国汉学人类学的奠基人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不仅专门撰文推介、阐释其理论,而且计划为二人立传,遗憾的是因英年早逝而未实现。中国本土人类学界早在1930年便把葛兰言的著述译介过来,他的研究甚至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为此杨堃还著专文介绍乃师的理论并为之辩护。近年来,本土人类学者再度对葛兰言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专门论述问世。相比而言,高延的研究并未得到本土人类学者的及时关注,系统的理论介绍更是付之阙如,虽然其煌煌巨著《中国的宗教体系》的英文本于1950年在台湾再版,但其中文译本直到今天还未问世,所幸本土宗教学者正在做这个工作,而且近年来本土人类学者同样表现出了对高延的浓厚兴趣。以现在的学术眼光来看,高延和葛兰言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历史的视角和文明论的态度,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价值所在。
高延早在1877年便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堪称在中国进行人类学意义之田野作业的第一人,鸟居龙藏则紧随其后,从1895年开始便先后在东北、台湾和西南进行实地调查,算得上是在中国做田野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人类学家了。鸟居龙藏并非是一个欧美意义上的人类学家,其田野作业也不像正统人类学那样执着于“分立群域”的整体性调查,在学术取向上则融考古学与人类学于一体,结合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在重视考察古迹文物的同时,对不同族群的历史、体质、语言、宗教和习俗进行分门别类的的研究。鸟居龙藏在理论上并无太大建树,但对中国历史古迹与风俗习惯的调查与记述却是细致而详实的,其著述之丰也是同时期其他几位人类学者不可比拟的,代表作有《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满蒙古迹考》《黑龙江与北桦太》《老学徒手记》等,其所有著述都收录在共十二卷的《鸟居龙藏全集》中。
如果说鸟居龙藏以其全面的记述为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素材,那么,史禄国在东北及其它地方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在民族志记述方面成就显著,而且在理论建构上为后人留下了值得深究的学术遗产。史禄国曾在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受过正规的教育,随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十月革命”之后流亡中国。1915年到1918年之间,他数次在东北进行实地调查,1920年之后又在福建、广东和云南等地做过实地调查,出版了《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满族的社会组织》和《通古斯人的心智丛结》等著作。史禄国以通古斯人的研究闻名于世,并且早在欧美人类学族群研究兴起的几十年前便提出了族群性性和心智丛结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族群认同问题和不同文化间的历史互动。在他看来,族群是基于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具有自我认同意识的人类群体,特定族群是相对于其他组群而得以存在的,并且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生理与心理特点和人文条件这三个变量紧密相关,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便历史地存在于这几个变量的交错互动中,从而是每一个族群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尽管史禄国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的功能论,但他的人类学研究却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80年之后才逐渐为学界瞩目,虽然本土人类学者近年来也对史禄国表现出了的浓厚兴趣,但对其理论的解读与挖掘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值得一提的是,史禄国和鸟居龙藏都曾在中国的高校有过任教的经历,对中国的人类学教育起到过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他们的理论倾向在本土人类学中并未得到应有的传承,除了二人的自身情况外,本土人类学对英美学术传统的推崇,是其根本原因。这里极具象征意味的个案是,史禄国在清华大学招收的唯一一位人类学硕士生费孝通在读了两年后便匆忙毕业,转投到马林诺夫斯基门下,成为马氏功能主义在中国的传承人,而史禄国为之精心制定的涵括了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六年学习计划也因此中途流产。
二
如果说早期异域人类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如同星星之火的话,那么,本土人类学则在经过“癸卯学制”施行之后而逐渐呈现出燎原之势,并在1930-1940年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构成了人类学中国研究黄金时代的中流砥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早期的人类学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西学东渐,不仅有大批年轻学子负笈西游以求学术救国,并在归国后推动了本土人类学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国外知名人类学者来中国讲学甚至任教 (Robert Park)、拉德克里夫·布朗 (Alfred Radcliffe-Brown)、史禄国和鸟居龙藏等知名学者。1930-1940年期间,本土人类学已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北派”和“南派”,前者主要沿袭英国功能主义的理论传统,采用源自马林诺夫斯基经典民族志的社区研究法,对中国的村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代表作诸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和许烺光《祖荫下》等,不仅在当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而且至今仍是欧美人类学学生的必读作品;后者则师法德国的传播论和美国的历史特殊主义,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对中国的少数族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如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和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都在人类学中国研究中影响深远。
本土人类学的“北派”之形成与吴文藻紧密相关。虽然他留美期间主攻的是社会学,但也受到博厄斯 (Franz Boas)和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的影响,而其开创性论文“民族与国家”便写就于攻读硕士期间的1926年。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后,吴文藻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在邀请如派克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等海外知名学者来中国开设讲座课程的同时,也亲赴欧美结交当时如马林诺夫斯基等著名人类学家,并先后将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得意门生送到海外深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通过与海外学者的交流明确了中国研究的理论倾向,而且通过师生间的学术传承造就了诸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基于对中国社会之乡土性的认识,吴文藻在理论与方法上越来越倾向于英国的功能主义,不仅撰写了很多关于功能主义的介绍性文章,而且确立了社区方法在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统治性地位,“北派”诸多代表作便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中诞生的。尽管如此,“北派”的研究并非完全执着于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而是随着开枝散叶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与吸纳,如李安宅对互惠研究法的设计、林耀华对均衡论的借鉴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文藻逐渐淡出学术舞台,学成归来的费孝通开始成为“北派”的标志性人物。虽然带领其研究团队偏居云南一隅,他仍然在条件艰苦的“魁阁时期”实践着乃师的社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比较的成分。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研究团队成员学源各异,加之对“席明纳”的热衷,其内部的学术讨论之风甚为浓烈,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研究深度与广度。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都是“魁阁时期”的代表作,而许烺光的《祖荫下》与《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也是基于这一时期的实地调查而写成的,单从题目便可知当时这批学者研究的范围和关注的问题是何等广泛了。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诸如弗里德曼和利奇 (Edmund Leach)这样的西方学者眼中还很难与整体性的中国研究相提并论,但却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相伴其中的深入探讨,为后来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费孝通1940年代后期的著述便是明证。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和《中国绅士》等著述中,费孝通以差序格局、皇权与绅权等核心概念对整体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简出的分析,在强调绅士对于中国政治结构之形塑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将诸如“隐”等本土概念提升到了社会意识的抽象理论层面,其中表现出的历史主义倾向,在关于中国经济级序的探讨中同样非常明显,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对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关于中国市场区系的著名研究,有着潜在的影响。
本土人类学的“北派”以社区研究法为核心,试图通过经验性的村落研究及其比较来达到对整体中国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在整体学术倾向上受英国功能主义的影响较深。相比而言,本土人类学的“南派”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较为密切,从而在整体学术倾向上更容易与德美的传播论和历史特殊主义相结合。
“南派”的形成与蔡元培紧密相关,在吴文藻“民族与国家”一文问世的同一年,他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对作为人类学之组成部分的民族学做出了细致的解说,强调其与历史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紧密关系。与吴文藻及其弟子们寓于高校不同,以蔡元培为精神领袖的“南派”人类学者则主要依托于科研机构,先后成立的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是“南派”人类学者赖以存在的重要科研机构,杨成志的云南彝族调查、颜复礼和商承祖的广西瑶族调查、黎光明的四川羌族调查、林惠祥的台湾高山族调查、凌纯声和商承祖的东北赫哲族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凌纯声和陶云逵的滇西民族调查等,都是在上述机构的支持下完成的。与“北派”集中于汉人社区的调查不同,“南派”的调查多以边疆少数族群为对象,注重对特定区域之群体及其历史与社会的全面考察,而非聚焦于特定的微型社区。在理论倾向上,“南派”侧重的是文化而非社会的概念,强调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流变,这在部分“南派”人类学者移居台湾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从而使其理论更倾向于古典人类学中的传播论,比如凌纯声对环太平洋文化的研究。
尽管本土人类学的“北派”和“南派”在学术倾向上各不相同,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交流借鉴的可能。“北派”虽然以社区研究见长,但其理论成就却离不开对历史的重视,并因此在“长时段”历史的意义上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独到的见解;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大批学者的南迁,很多“北派”人类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了边疆的少数族群,比如田汝康的傣族研究和林耀华的彝族研究,虽然仍旧采用社区研究法,但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理论探讨都较早期的“北派”研究有了不小的变化,又如李安宅关于藏族的研究,由于受美国人类学的影响,也带有明显的“南派”色彩,而他带领华西协和大学的研究团队所展开的研究甚至被后人以“华西学派”称颂之。
如果说本土人类学的“北派”和“南派”是人类学中国研究黄金时代的中坚力量,那么,这种力量的形成显然与彼时极具包容性的学术环境密不可分。实际上,在“北派”和“南派”之外,不仅有“华西学派”这样的团队,还有更多取向各异的人类学者包括海外学者关注中国研究。但是,这种建基于本土人类学兴盛之上的辉煌时期并未延续更久,而是在随之而来的新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陷入低迷,人类学中国研究随后转入以英美学者为主导力量的海外典范时期。
三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随着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被取消,本土人类学的发展空间很大程度上被压缩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本土人类学者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学术生命,而是在诸如“民族识别”等国家事业中,继续将自己的人类学知识投入到实践之中,并且进一步地丰富了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度理解,可以说,“民族识别”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田野作业的机会。尽管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此时已经辉煌不再,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毫无生机,而是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积蓄了难能可贵的理论潜能,比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便是在这个时期基于大量的“田野作业”而获得了经验支持和理论提炼。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本土人类学从1950年开始陷入一个漫长的低迷期,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及其世界影响,在欧美学界却涌现出了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热潮,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弗里德曼和美国的施坚雅及其弟子们。
弗里德曼是从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研究转向中国研究的,其学术背景是英国新一代人类学者基于非洲政治制度研究而对传统的功能主义的反思,在理论倾向上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代表作是《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弗里德曼思考的问题是,在无政府、无国家的非洲社会秩序的建构依赖于世系群,并以裂变的方式维持着整个社会的运转,那么,在有中央权威的中国社会中,与世系群相类的宗族组织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又在整个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通过对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研究,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的宗族在整体上存在着一个由A模式到Z模式的一个系谱,它们并非像非洲那样是由部落裂变而来,而是相对于中央权威而存在的地方组织,并且表现出严格的结构与功能;宗族以共同祖先和共同祖产作为社会与文化认同的符号,内部存在着权力的分化,其中掌握权力的精英分子有利于把宗族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使之免受强大邻族的欺凌,并减轻国家对地方的剥削;边陲状态、水利建设与稻作生产是造成中国东南宗族组织发达的根本原因。尽管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在很多理论细节方面遭受了中外人类学者的诸多批评,但他建构的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不仅使黄金时代本土人类学的潜在理论价值得到廓清和提炼,也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人类学中国研究,尤其是几乎没有人可以绕过他来谈中国的宗族。弗里德曼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中国这个文明社会的整体性研究的强调,其研究堪称是对马林诺夫斯基预期之“文明社会的人类学”的实践。
与弗里德曼相比,施坚雅对中国的整体性研究更加深入,他借用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 (Walter Christaller)和洛施 (August Lsch)的“核心地点”理论,对中国的整体结构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市场区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中国习以为常的行政区系背后隐藏的是因经济交换而形成的市场区系,尽管二者都属于核心地点的系统,但后者才是造就中国整体区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的系列论文中,施坚雅对市场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建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传统中国的所有核心地点都源自阶序化的市场体系,在理想的区位体系之中,高阶的地点涵纳了一定数量的低阶地点,并为其提供自身无法供给的物品和服务,从而形成由村落到标准市镇、核心市镇、地方性城市和区域性城市的阶序化体系。在随后的研究中,施坚雅进一步完善了其市场区系理论,在理想的二环结构基础上,引入了边界性、需求、人口、运输等变量,认为中国可以划分为包括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九大宏观区域,其中每个区域都是由村落、集镇和城市的市场阶序所建构,并处于历史的周期性发展之中,中国的朝代更迭与这些宏大区域的周期性变动紧密相关。施坚雅对市场、区域和历史的强调,摆脱了传统的社区或区域研究的窠臼,村落或区域不再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成为研究者提取研究素材的空间,而是构成一个阶序化的体系推动着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迁,从而成为研究者的分析对象。
弗里德曼和施坚雅都是在意识到中国之复杂文明特性的基础上,探讨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前者关注的是宗族问题,后者则关注市场体系。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典范的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海外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发展。尽管1950年以后近三十年间,海外人类学者在中国大陆进行田野作业已经不可能,但港台田野地点的开放,却为其提供了替代场所。1960年之后,随着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影响不断加深,一大批欧美人类学家涌入港台,其中焦大卫 (David Jordan)、武雅士 (Arthur Wolf)、雅汉 (Emily Ahern)、巴博德 (Burton Pasternak)、孔迈隆 (Myron Cohen)、葛希芝(Hill Gates)、郝瑞 (Steven Harrell)等人在台湾,波特 (Jack Potter)、华琛(James Watson)、裴达礼 (Hugh Baker)等人在香港,进行了大量的田野作业。在方法上,这批人类学家并未像弗里德曼和施坚雅那样以宏观区域为单位来获取资料,而是主要采用社区研究法,通过对特定村庄的经验调查来获得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识,并以此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他们仍然延续着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兴趣,对家庭、宗族、市场等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探讨占据主流地位,同时伴随着象征人类学的兴起,也对民间宗教及其象征做出了新的探索,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与他们的导师形成争论。虽然田野作业的港台实践为这批欧美人类学家提供了难得的体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机会,使其对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更为深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弗里德曼和施坚雅寄予厚望的文明社会研究之历史维度加以探讨的深度。尽管如此,大批海外学者的不断关注,不但使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而且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建构上形成了富有弹性的讨论空间。
四
自1970年以来,人类学中国研究进入了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海外人类学家能够进入中国更多的地区进行田野作业,而且使本土人类学的复兴成为可能,同时,台湾本土人类学也在“南派”的传承和海外人类学者的熏陶之后转向以多学科合作、原住民研究等为标志的新阶段,香港的人类学也因相关高校院系和研究机构的建设而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很多前期在港台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海外学者把目光转向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他们关注的理论焦点。在1980年,弗里曼 (Edward Fridman)、毕克伟 (Paul Pickowice)、赛尔登 (Mark Selden)的五公村研究,陈佩华 (Anita Chan)、赵文词 (Richard Madsen)、安戈 (Jonathan Unger)的陈村研究,萧凤霞 (Helen Siu)的环城公社研究和波特夫妇的增埗大队研究等,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在权力更迭和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所面对的政治、经济与道德变迁以及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农民所遭遇的命运转折。这样的研究思路既延续了前一时期的理论思考,又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论的探讨而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从而使人类学中国研究之历史维度的探索成为可能。至1990年,海外人类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研究,不仅在东南地区已经积累颇深,形成了中外学者共同参与合作的所谓“华南学派”,而且开始把目光转向西南地区,围绕族群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与东南研究相对应的西南研究。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萧凤霞、科大卫 (David Faure)、刘志伟、陈春生等人,他们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共同关注,是弗里德曼和施坚雅以降的西方人类学与傅衣凌一脉的本土历史学之间进行交流与融合的基本前提。虽然这样的结合对于拓展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潜在的价值,但就具体实践而言,在历史探索的深度上,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中西学者对历史的理论认识也各不相同,比如对历史过程与结构过程的理解。西南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郝瑞 (Stevan Harrell)和王富文 (Nicholas Tapp),他们不仅一改海外学者执着于汉人研究的学术风气,而且引入了族群性等概念,在推动人类学中国研究由东南转向西南的同时,也催生了由族群认同理论引申而来的文明互动研究。
与海外学者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一样,作为人类学中国研究分支的台湾人类学也具有学术史的连贯性。在经历了日据时期日本学者的“土俗研究”和“南派”的文化史研究之后,台湾人类学在1980年之后的多学科合作和原住民研究,是本土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表征。与此同时,香港也在1980年进入本土人类学快速发展的时期,并在物质文化和全球化研究方面用力颇多。对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全面复兴来说,中国大陆的本土人类学构成了最重要的学术力量。随着人类学学科在特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恢复,中国大陆的人类学教育重现生机,不仅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开创了人类学本科教育的新局面,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诸多高校实践着人类学研究生教育,甚至通过“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样的形式来弥补多年来人类学教育的缺失,从而为越来越高涨的人类学研究热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本土人类学在忙于学科重建和学术译介的同时,在具体研究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冲击力。自1980年以来,随着老一代人类学者的回归和新生代人类学者的崛起,本土人类学者的中国研究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前者以费孝通最为突出,他所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理论,都具有强烈的理论指引价值;后者则以阎云翔、刘新、王铭铭、景军等具有留学经历的青年学者最为典型,阎云翔关于下岬村的研究、刘新关于自我结构的研究、王铭铭关于泉州的研究、景军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理论示范的价值。
总体而言,1990年以来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村落研究、区域研究这两个领域。村落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黄金时代社区研究的继承,但其中的着力之作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村落本身共时性的整体描述,而是表现出了对社区史的高度关注,比如王铭铭关于溪村的研究和景军关于大川村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不同层面之历史的细致分析。对社区史的重视也引发了回访研究的兴起,诸如江村、西镇、黄村、台头村、禄村、那目寨、南景村等黄金时代人类学研究的社区都在1990年成为回访的对象,对社会变迁的历史重构和前人研究的理论批评构成了这些研究的核心内容。相对于村落研究,区域研究不仅把历史纳入到理论思考之中,同时也将文明的概念置于探讨的核心,在特定区域的历史回溯中,探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及其后果,比如王明珂关于华夏边缘与羌族的研究和王铭铭关于藏医走廊的研究,都是在这种学术思路下展开的。
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全面复兴主要体现在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成果的增多,尽管其中不乏具有大家气质的学者和具有典范潜力的理论,但相对于黄金时代和海外典范时期而言,这个时期还有着巨大的理论提升空间,并且正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

泥模艺术——寿堂琵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