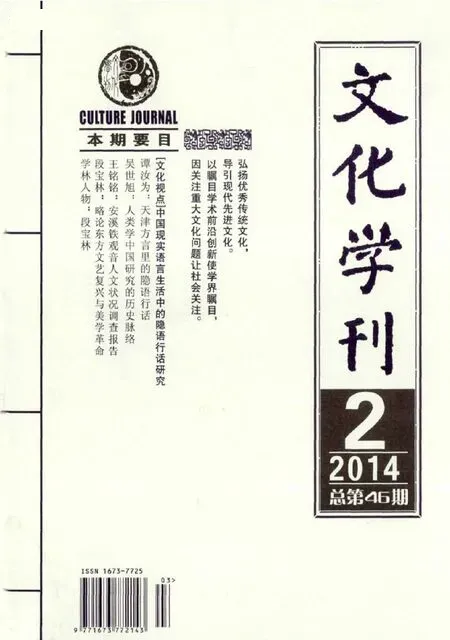兰芳公司:南洋华人独立求存的历史缩影
——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读后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1)
一
作为荷印殖民政府设置在西婆罗洲(今东南亚马来群岛中的加里曼丹岛)的翻译官,在其从1880至1883年的任期内,高延陪同他的上司在当地做了大量的公务旅行,与东万律的最后一个华人社会组织——兰芳公司有密切的往来。他和兰芳公司年迈的头人刘阿生及其女婿叶湘云等首领建立了友谊关系,并跟他们学会了客家话。由于意识到公司组织及其制度的重要性,而且预感荷印当局很快即将强力解散公司,高延尽其所能,历时三年发掘、收集了兰芳公司及其他已被消灭的华人金矿公司的文字和口传资料。
1885年,兰芳公司的头人刘阿生死后,高延原来的预感变成了现实。荷印殖民当局马上派遣军队进驻东万律,决定以武力解散兰芳公司。公司民众武装起来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殊死反抗,最后归于失败。矿工们流离失所,逃散到新加坡、吉隆坡、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和其他地方。这是当时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一大政治事件,在荷兰本土也引起强烈反响。与公司有过密接触的高延认为,消灭公司是荷印政府的严重政治错误,而导致这一做法的根源是执政当局对殖民地华人社会的性质与制度的无知。为此,他立即撰写了火药味十足的长篇大论:《婆罗洲公司制度——关于殖民地华人政治联盟的基础与性质的探讨,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文中高延就强调19世纪的欧洲汉学只关注中国的精英文化和儒家学说,虽然出版了几部中文字典、翻译了一些古代经典,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却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英、荷殖民地政府对最早开发东南亚、对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华人移民都普遍实行极不公平的种族歧视政策。因此,研究中国、了解华人社会刻不容缓。
二
初次接触到此书的读者,从题目恐怕以为这本书应该是研究印尼华人在当地开设公司的经济学作品,本书的题目也的确有令人困惑之感。而当读者开卷进入到高延所描述的兰芳公司,逐渐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及背后的主旨时,一系列的问题就会源源不断地显现出来:“兰芳公司”乃至于婆罗洲的所有华人开设的“公司”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为何华人会在婆罗洲建立起如此稳固的集团组织?此种稳定背后的支撑是什么?荷印政府为何会有权力毁灭这种自治的公司?而殖民政府毁灭这种华人公司的意图又是什么?这样的行动对于生活在当地的华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当地的经济、政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作为关于婆罗洲公司制度描述和讨论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高延在书中尝试着阐释“公司”这种华人移民组织的来源及性质。高延笔下的婆罗洲公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公司,它专指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里,在西婆罗洲所聚集的华人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最早源于婆罗洲西海岸的南吧哇酋长从文莱招募的十几名华人到当地开设金矿,结果金矿的运作给这些华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于是其他的华人也纷纷效仿。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大批的华人,尤其是广东嘉应州 (梅州)、潮州、惠州和福建的客家人蜂拥而至,并形成了三沙、巴坜、会等矿业组织。从华人在婆罗洲发展的历史来看,公司的含义多种多样,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组织机构,可以是一个依托于共同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是一个共和国,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秘密会社的团体组织。关于公司制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全书的第一部分,他首先翻译考证了兰芳公司的发展历史。在利用《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录的基础上,高延向读者介绍了兰芳公司的早期发展历史;与大港、三条沟等其他金矿公司的关系;与当地马来君主及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后期同荷印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根据高延描述,在婆罗洲很早就有华人定居生活,从事贸易的占大多数,他们往往组成自己的公司,以罗芳伯为首的兰芳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对南洋的侵略加剧,罗芳伯顺应时势和当地华人以及为保护自己生存权利的落后民族,于1770年建立兰芳公司,定都东万律,他被拥戴为大总制。在南洋国家之中,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建元兰芳,公元1770年为兰芳元年。他仿效西方当时才出现的民主制,规定公司的大小事情都必须咨询民众之后才能施行。最难能可贵的两点是:他没有称帝,帝制自为。兰芳公司建立不久,他就派人到北京向中国中央政府汇报相关情况,并进贡方物。又拒绝了人们要他称王的请求,而是称总制、大唐总长,并且规定,他及后世领导人都不能把兰芳公司变为一姓人的“家天下”。
兰芳公司先后民选了12任领导人,他们领导华人以及归附的落后民族改进农业技术、扩大矿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组织军事训练,使兰芳公司的实力和影响大增,更多落后民族前来归附,兰芳公司的版图迅速扩展到整个婆罗洲。
兰芳公司的发展壮大遭到了西方殖民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南洋落后民族的嫉恨。随着中国大陆的日益沉沦,失去了祖国支持的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组织,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进攻。兰芳公司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这个华人组织也不幸灭亡。
从第二部分开始,高延开始了对于公司制度的人类学阐释。文章描述了这群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的客家人和福佬的历史背景,对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一个充满着未知和危险的矿区从事及其艰苦工作的动机和行动逻辑做了分析。这群缓慢而执着不息的移民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不屈而激烈的生存斗争,他们也许不用暴力,但却难以抗拒,最终这些北方汉人吸收、排挤、取代了原住民。他们始终一个接一个或一群接一群地散居在陌生而敌意的民族中。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艰苦磨难,客家人具备了世界最佳殖民者的素质,他们努力、勤奋,尤其在农业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经历可以解释他们在面对艰苦工作时的坚韧不拔精神,也能说明他们善于适应各种环境并能够与各种不同的民族打交道的优秀品质。这群客家人没有背弃自己的民族,没有背离祖宗的礼法,在荷印东印度群岛千变万化的环境中,他们并不是单枪匹马闯天下的冒险家,而是有组织的移民者,并通过建立的公司组织不断得到来自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补充。利用这部分的内容作为铺垫,紧接着高延开始对他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开始了论述:
公司的特征是什么?婆罗洲的公司和这些客家人在中国时所生活的村落中的组织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讨论中国乡村组织的本质来寻找西婆罗洲华人公司的原型。另外,这些华人如何能够在没有祖国政府的支持前提下建立起强大、稳定、独立、秩序感井然的“共和国”?这种所谓的“共和国”同荷印政府所极力遏制的“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之间有没有关联?二者各自的本质是什么?高延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来谴责荷印政府以及多数的殖民官员,攻破当地的殖民学者针对华人公司所散布的不实谣言。他还希望透过此研究还原华人公司本来的面目和性质,说服荷印政府修改对于殖民地华人的政策。
高延试图通过下述的逻辑来探讨他所提出的问题。首先,他发现客家人在印尼社会的适应能力极强,这个群体很快就能够发展出一种适应环境的机制:“他们没有背弃自己的民族,没有背离祖宗的礼法;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千变万化的环境中,他们并不是单枪匹马闯天下的冒险家,而是有组织的移民者,不断得到来自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补充。……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让自己的人民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那里极少有同胞、祭坛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敌视他们的异族人。他们并非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副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是一个接一个以小组的形式前进,最勇敢的人当先锋,每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机智与道义自力更生。”[1]
其次,高延在兰芳公司中发现:第一,公司的组织者和成员基本来自中国普通农民阶层,无论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这样的移民群体建立起来的公司却发展出了空前的组织秩序;第二,兰芳公司内部实行的是强烈的共和式民主精神。对于上述两个特点,高延认为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底层的社会组织——村社机构”寻求答案。他认为:“每个中国村庄都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就像每个家庭都有家长一样,每个村庄中的每个族房也都有各自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最明智、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担任。而如果其中的某一房在某一时期在村里占了上风、或是由于人多财富、或是因为人才辈出,他们当中最出色、最年长或最能干的成员自然而然成为全村的村长。村长的产生几乎不经过竞选,通常是采取默认的形式,而且村长的就职典礼并不要求村民直接参与。因此,地方社会组织明确显示了寡头政治共和国的特征。中国的村庄不存在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村里的事情完全由村民自己做主,也就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村长来安排。政府将村长视为其基层统治必不可少的中介人,由此中国的村社自治是在法律上被认可的国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有这样一种独立的村社制度,必然也存在一种强烈的合作团结精神,使每个人都对公共福利具有高度热忱。”[2]
村落社会的成员除了对于公共福利体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以外,互助精神也是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重要机制。高延强调:“除了难以预料的歉收与灾荒,事实上在中国只有因为个人过失才会挨饿,只有懒惰成性或者行为不端被驱逐出乡族的人才会如此。中国人是那么愿意与兄弟同居,那么愿意为公共事业出力,所以,别想在那里找到那种拥有健康体魄、能够并愿意劳动,却无工可做缺衣乏食的受害者。一旦有人暂时没有工作,就会有许多人准备伸手接济直到日子好转。由此不难看出,从村社管理的角度来看,家族制度其本质就是作为互助精神的孕育者,作为个人赖以抵抗天灾人祸的保护者,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稳定性。”[3]这种兄弟般的合作互助精神,正是海外华人最重要的生命线之一,是荷印华人始终强烈表现出来的、引人注目的团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了中国南方的乡村社会组织后,高延转向婆罗洲公司社会。他指出公司是华人在海外实现的中国乡村社会和宗族组织的重建。传统村社制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与共和民主倾向,这是被历代中国统治者所认可的,正是村社制度孕育培养了下层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建立独立平等的社会组织的能力。海外华人强烈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根源,主要出自对村社自治的热爱,而这种自治却是西方殖民者所不能容忍的。[4]
在此书的最后部分,针对荷印政府和当时社会对于海外华人的普遍歧视和偏见,高延动用了不少的篇幅陈述华人公司于“天地会”这样的“秘密会社”之间的区别。他承认,包括兰芳公司在内的华人组织的确在其发展过程中被迫需要同“天地会”打交道,另外,社会整体以及荷印政府之所以视当时兰芳公司这样的华人组织为“天地会”,原因部分地在于后者确实在对于荷兰殖民统治的抵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即便如此,高延也强调华人公司组织内部并无任何神秘性可言。而被荷印政府看成是“秘密会社”,实际上体现的是华人组织在地方高压统治下必然表现出的一种反抗,反抗荷印政府强力取消华人的自治制度。他们只是希望求得在异国统治下的生存权利和空间,而不是一定要推翻殖民统治。
三
纵观全书,作为人类学史上首部关于婆罗洲公司制度的研究,开拓了海外华人研究的领域,高延对婆罗洲公司制度以及中国南方传统村社组织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创见性,同时他对于华人社会基本特征的揭示也可谓真知灼见。尤其是对于“孝”作为村社组织制度核心的讨论甚至影响到了其后的一批汉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村社的认识,葛学溥就是其中之一。[5]
综合婆罗洲华人组织的描述和中国传统村社制度的讨论,我们发现公司制度更为恰切地应该被认同为是一种普遍的地方庙宇组织在海外的发展。也就是说,公司制度基本上是基于宗教性而建立起来的,宗教性成为了该组织凝聚力维系的重要精神内核。人类学家魏捷兹在澎湖群岛的红罗村调查中发现,村民将“公司”同社区性集体仪式活动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全村所有宗教场所的维修、在宗教场所举办的仪式、代表参加联盟村落所举办的宗庙宗教活动以及跨村的王爷活动。简言之,这里的“公司”指的是不同的职位和身份的村民依据股份来确定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宗教共同体。[6]此种共同体同荷兰学者高延在婆罗洲所记录的华人开设的公司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
历史学家科大卫在其著作《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解释中国的公司制度时也提到了中西方关于公司概念的差异,他说:“18世纪时,中国的公司建立在礼制的基础上,在公开的宣称中,其设立并不是直接服务于成员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持对于祖先和神明的祭礼。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公司类似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名义上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而建立,但却自始至终是经济发展的中枢。”[7]
正如魏捷兹和科大卫所认识到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宗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组织设置,即被称为“会”的宗教组织。它在地方事务,尤其是农业灌溉、村社防卫等集体事务中体现出了极其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在高延描述中的婆罗洲华人社会,正是这种“会”的制度起到了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的关键作用。这一点高延在《公司制度》书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只是隐约地让读者能够感觉到这种设置的存在。之所以没有明确地将其作为重点论述内容,可能是因为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将其作为论战的武器弹药,直接针对荷印殖民当局对于华人组织的无知。而将华人公司组织制度做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剖析容易节外生枝,让重点模糊,所以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高延要大大简化公司本质的讨论,或者是轻描几笔就带过了。
无疑高延对于婆罗洲华人公司组织的讨论是精到的,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理论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其不加界定地将闽粤地区的地方性文化特征等同于中国整体社会中的村社制度。同时其对于公司内部的民主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的过分美化,也是读者在把握此书的理论框架时需要提高警惕的。

泥模艺术——太君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