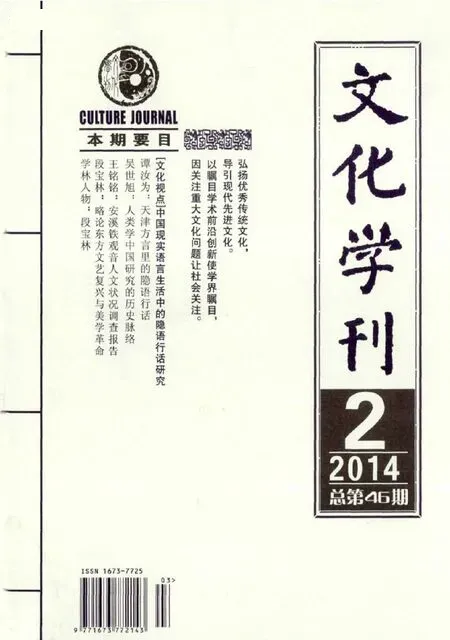当代语言生活中的反切秘密语现状及其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反切秘密语是运用反切原理,按照一定规律改变原字字音和音节而产生的秘密语形式,又称为切口、切语等。作为隐语行话的一种重要形式,反切秘密语也同样是某些社会集团或群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一套用于内部言语或非言语交际的,以遁辞隐义或谲譬指事为特征的封闭性、半封闭性符号体系,是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1]反切语既不是封建皇帝的御用工具,也不是犯罪团伙的专属品,正如张天堡先生所言,使用反切语的主要群体是城镇市民,以及由市民阶层派生出来的小商贩、江湖艺人、手工业者及小学生等等。[2]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言:“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3]可见,早在汉代人们就已经使用反切语了,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反切秘密语依然在我国民间的各类社会群体中传承使用。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9)》显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隐语行话仍然活跃在我国民间众多社会群体中,这一语言生活状况引发了社会媒体的密切关注,并一齐聚焦这一古老神秘的语言现象,向专家学者求援解析这类反切秘密语。如何正确认识民间反切秘密语?如何抢救和保护反切秘密语这一文化遗产?面对公众的疑惑,这些问题都已成为当前语言学学者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以近年来的相关媒体报道和学术关注两方面的研究资料为例,来概述反切秘密语的研究情况。
一、社会媒体对反切语的关注
(一)河南林州秘密语
2007年3月6日,林州新闻网一则《马军池流传神迷语言》的新闻报道了位于河南林州河涧镇东北部的马军池村存在一种独特语言——“跩语”,据村上懂得该语言的靳才法老人介绍,这种语言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每个汉字都分成两个音节来读,比如:中华,在“跩语”中,“中”被读为“zhuai gong”, “华”被读为“huaigua”,系反切语的一种。这种“神秘”的语言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年4月10日的《大河报》刊登了《林州紧急抢救神秘襥语——宋徽宗被俘时曾用过》的新闻,据称,在林州还流传着另一种神秘的语言——“襥语”。有人说它是民间艺人之间的行话,有人说它是宋徽宗在狱中使用的暗语。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襥语”曾流行于当地,之所以有此称呼,是因为说的人很少,会说这种话的人就显得很“襥”。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地已经很少有人会说这种语言了。为保护先祖留下的语言文化,林州市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该种语言的起源、形成、保护展开系统的抢救工作。[4]

(图片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同年11月,央视网和新华网等网站用不同的新闻标题转载了来源为《东方今报》的关于林州“江湖暗语”的报道。报道称,在林州一些乡镇,曾经有一种叫做“跩语”的暗语在盲人和民间艺人中间流传。相传这是宋徽宗创立的。虽然如此,但河南大学的语言学专家段亚广还是认为,作为反切语的活化石,“跩语”在研究旧时艺人生活状况时无疑提供了语言学和民俗学的范本。[5]
(二)山东莱西“切语村”
《中国文化报》在2006年7月20日文化遗产专刊上刊登了《莱西文化资源普查发现“切语”村》一文,新闻报道了山东省莱西市文化局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普查中,发现莱西市店埠镇前寨村存在古老的“反切语”文化现象,当地群众将“反切语”俗称为“切语”。目前,专家正在对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发掘保护,已初步认定该村为“切语”古文化村。[6]
2008年10月13日,青岛新闻网等多家网站转载了《青岛早报》题为《莱西某村流传千年切语,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闻,据村民说“我们村有些老人会说切语,是老辈传下来的,据说有几千年历史了”。村中有很多老年人都会这种语言,仅凭发音作为载体,没有拼音、也没有文字。经莱西市文化局考证,这种语言叫“切语”,也就是反切语,现已濒临失传。目前,莱西市文化局打算将“切语”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7]
2013年7月16日,山东经济网转载了《半岛都市报》题为《莱西非遗"切语":能说不能写面临失传》的新闻,并呼吁保护反切语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北京“天语”
2008年8月20日,《北京晨报》刊登了题为《老汉说"天语",70年没人能听懂》的新闻,报道了北京75岁的陈老先生会说一种无人能懂的“天语”,念一个字能发两个音,特向社会求援,希望能破解这种“天语”。此报道一出,立即引发社会热烈反响。全国各地40多位读者致电或致信,纷纷推测这一语言现象的产生机制,解说大致分为5种:①“童年游戏”说 (17人);②“江湖行话”说(11人);③“徽宗语”说 (6人);④“地下工作者暗语”说 (4人);⑤“香港女中S语言”说 (3人)。
辽宁社科院的曲彦斌研究员对“天语”很感兴趣,作为民间语言的研究专家,曲彦斌先生告诉记者,这其实是一种民俗语言现象,是汉语隐语的一种,也可以称为民间秘密语,陈老先生的这种主要用来作为游戏语。对于读者给出的5种说法,曲先生评论说:“主要用途还是游戏。有时也用作行话,但不是黑话。另外,徽宗语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它是另一种汉语隐语。说到作为地下工作者的语言,其实只是临时借用,地下工作也用过方言当交流语言呢。至于香港女中的S语言,其实是另外一种游戏语。”曲先生表示,这种话曾大范围流传过,是需要保护留存的。“这是一种民俗文化,即使没有实际使用意义了,也有民俗研究的价值,不能让它消逝。当然,也用不着扩大。”[8]
二、学术界关于反切秘密语的研究
反切语在汉代即已兴起,但一直以来,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甚少,直到1924年民俗学家容肇祖在《歌谣》周刊第52期发表了《反切的秘密语》一文,这种语言文化现象才走上科学化研究的道路。语言学家赵元任在1931年发表于《史语所集刊》第2本3分册的《反切语八种》全面论述了八种反切语的种类、地位、名称和拼读规则等,从此拉开了全面系统研究反切语的序幕。此后不断有学者关注研究反切秘密语,并陆续有研究成果发表在报纸杂志上:1939年,陈志良先生更大规模地调查了上海地区的种种反切语,在《说文月刊》上发表了《上海的反切语》一文,详细描述了上海各种不同的反切语;陈叔丰在1940年于《中国语文》第3期发表了《潮汕的反切语》一文,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为反切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后30年,反切语领域的研究成果几近空白,成了中国科学园圃中一隅荒芜之地,然正如曲彦斌先生所言“冷寂往往是一种积聚和准备的过程,而不是静止”。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反切语的研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渐渐复苏,关注反切语的学者越来越多,相关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学术价值含金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一)反切语溯源与正名
1.溯源
反切语古已有之,但是源起何时何地一直以来并无定论,究竟哪些群体在使用,为何目的而使用,使用过程中又有哪些规则发生了变化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陈振寰、刘村汉的《论民间反语——兼说反切起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01期)一文对民间反切语与反切的关系做了探讨,认为反语在民间从上古时即已存在,并推测反语是反切的前身,找到了先汉反语,也就证实了反切根植中土。作者还对桂东各县,及广东梅县和湖北部分地区的反切语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这一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反切语分为换音反语、换位反语、增音反语、增音换位反语四类。文章还讨论了反语和反切的名称、关系,现代反语的声韵和入声韵尾等问题。
张天堡先生的《切语初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一文也阐述了切语产生的历史源头及古代切语的特点。作者辨析了切语与反切的不同,切语的目的在于求意,反切的目的在于正音;人民大众创造了切语,使切语在社会上流行,引起文人重视,才进一步制定出反切法。作者还总结了现代切语的特点,详细介绍了北方现代切语的规则,并指出虽然反切语还有三合、四合、五合等形式,但是流行广影响大容易被人接受的切语还是一个字分成两个音的结构形式,多了累赘,反而达不到交流思想的目的。
论文发表后,周长楫写了《评<切语初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一文,对张天堡先生的《切语初探》进行了客观评价,首先肯定了《切语初探》的学术价值,评价文章以较丰富的材料说明了切语产生的历史及其性质特点,阐述了切语与反切的关系,立论正确,分析细致,是一篇较好的文章。接着作者从社会功用的角度指出,在提倡普及全民共同语普通话的今天,不鼓励使用切语,这不仅有利于四化建设,也能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最后,作者肯定了张天堡先生在《切语初探》中的观点,认为张天堡先生分析得出的切语与反切有所不同而又密切相关,反切是在切语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结论“事理俱在,可信可靠”。
此后,张天堡先生进一步对反切语进行了研究,他的《中国民间反切语简论》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月第22卷第1期)一文介绍了反切语使用的人群、流行的地域、各类名称等,概述了反切语的结构形式。作者认为反切语和反切原来是一家子,先由人民群众创造了反切语;反切语比反切生命力要强,至今还存活在老百姓的口头生活用语中;反切语不影响正常的语言,不应把反切语看作是语言中的“沉渣”或“垃圾”。
赵德祥的《切语初探》(《大连大学学报》1996年3月第6卷第1期)一文对反切语也进行了宏观描述,作者认为切语主要流传于盲人之间,是一种秘密口语,并指出其拼读规律,即将每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拆开,按一定规律再分别补上新的韵母和声母,从而使该字由一个音节表达变为由两个音节来表达。作者还强调了切语有顺说、例说之别,顺说流传极广,例说知之者甚少。文章探讨了切语在流传过程中的嬗变及盛衰,并分析了其社会原因。作者认为切语的发明创造者一定是文化层次较高,在语言学和语音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
2.正名
反切语在旧时由于被一些小偷、流氓、算命瞎子所使用,被人误会为“贼语”、“黑话”、下流的语言,不登大雅之堂。[9]但事实上,使用反切语的大部分都不是此类为害社会群体,而是城镇市民中的小商小贩,江湖艺人等。
郭青萍率先用“徽宗语”来为反切语正名,他发表的《徽宗语》(《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一文介绍了“徽宗语”这一反切语的名称来源,文中讲了宋徽宗被金人囚于地窖期间讲暗语联络收买金朝狱卒以求自保的传说,这种暗语便是“徽宗语”,“徽宗语”也因此而得名。文章还根据安阳音系考察了“徽宗语”声母、韵母、声调的表示法,试图以此来找出“徽宗语”使用规律,揭示“徽宗语”的语言系统。
张天堡先生在《徽宗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一文中进一步介绍了“徽宗语”这一反切语名称的几种来源,并且论证了“徽宗语”并非黑话,而是一种全民性的语言形式。作者认为:广义上,北方流行的mai-ka式、mei-ka式、mai-1a式都可以称为“徽宗语”,此外作者还总结了“徽宗语”的特点,强调指出“徽宗语”对正常语言没有坏的影响,隐语并不全是“坏”的语言。
(二)不同地域的反切语
反切语这种秘密语形式,广泛存在于我国各个地区,赵元任先生在《反切语八种》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北京、常州、昆山、上海、余杭、武康、苏州、广州、东莞、福州地区的反切语情况。此后不断有学者关注我国各个地区的反切语情况。
1.山东地区
姜元昊的《胶东mε-ka式反切语研究》(《汉字文化》语言文字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详细介绍了胶东地区mε-ka式反切语的来历和流传情况,分析了胶东地区mε-ka式反切语的语言规律,并介绍了其发展和使用情况。
2.淮河流域
张天堡先生在1992年8月中旬对淮河流域的临淮关、蚌埠、寿县正阳关一带进行考察后,发表了《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的运用、该反切语在当地的名称以及它们的切音结构等情况。
此后,张天堡先生和陈娟在《安徽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的构成式》(《方言》2012年第1期)一文中进一步介绍了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情况。作者调查了安徽境内淮河流域凤阳县临淮关、五河县临北关、寿县正阳关、蚌埠市、淮南市潘集区等地的民间反切语使用情况,总结了这些民间反切语的构成形式。通过调查,作者认为,淮河流域的民间反切语没有被黑社会、流氓集团、小偷和算命瞎子等利用的痕迹,是一种全体城镇居民所共用的隐语,即全民的“语言”,普通老百姓讲,小偷讲,官员也讲,它不是行业语言,没有阶级性。作者进而指出,反切语是一种供人消遣、开心的字谜性的语言,是人类文明、人民智慧高度发展的产物。
郑勇对地处淮河流域的寿县正阳关地区的民间反切语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正阳关反切语解读》(《巢湖学院学报》2011年第13卷第2期总第107期)一文,指出正阳关反切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方言,是中国民间反切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主要从这种切语的名称来源、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的不同特点,以及当地汉、回等民族百姓使用这种隐语时的不同表现,来展现寿县正阳关反切语的结构特点。此外,作者提到这种隐语还存在着三合切、四合切等少见反切法,并指出其使用面正日趋变窄,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贡贵训也对正阳关一地的民间反切语进行了考察,他在《正阳关“反切语”可“保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6日第015版语言学)一文中介绍了正阳关反切语的两种形式,即反切和嵌字。作者认为研究民间反切语对研究当地方言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正阳关反切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产生与历史上正阳关的经济繁荣有密切联系,因为商人使用反切语可以保守商业秘密,从而保护自身利益。
3.闽南地区反切语
马重奇的《闽南漳州方言中的反切语》(《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一文把漳州方言中的反切语按照赵元任的命名方法分为la一mi式和ma一sa式两类,分别加以介绍,并将其与福州的“仓前廋”“嘴前话”等反切语进行比较。比较得出以下结论:漳州la一mi式反切语与福州“仓前廋”在定音方法上较为相近;ma一sa式反切语与福州“嘴前话”不太相同,却与福州另一种反切语——“切脚词”用法十分接近,它们有一个特点,即“皆以口语为根据,或颠倒其双声叠韵,或搀杂无谓之韵纽,以混人闻听”。
(三)少数民族反切语研究
反切语不仅广泛存在于汉民族聚居地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有反切语形式的秘密语,而目前对少数民族反切语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还需语言学者进一步关注。
王春德在《燕子口苗语的反切语》(《民族语文》1979年02期)一文中介绍了贵州燕子口一带苗族百姓所使用的反切秘密语,并指出它是当地的部分苗族人在交谈时使用的一种隐语。贵州省毕节县燕子口一带的苗族人把它叫做“翻话”或“隐话”,其构成方式是在正常语的每个音节前面增加一个音节,新增加的这个音节的声母是k’,韵母和声调与原音节的韵母、声调相同。如果原音节的韵母是和,则新增加的音节的韵母为i。
(四)反切语的多方位、多视角研究趋势
曲彦斌先生有言:“直接由民俗学和语言学孕育而出的民俗语言学,是一门借鉴了多种传统科学和现代科学发展而来的新兴人文科学,其广泛的边缘性和开放性,必然地导致了对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的民间秘密语研究的多方位综合性研究倾向。”[10]近年来,对于反切语这种民俗语言现象的研究,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反切语”这一研究本体的苑囿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置于开放的学术视野中,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全息”研究。
吕玲娣的《“反切语”修辞格的构成及其文化心理探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月第9卷第2期)一文,认为“反切语”是利用反切原理表达隐义的一种特殊修辞方式。“反切语”不仅是一种语音现象,也是一种修辞格。文章分析了反切语修辞格的构成方式,即单反式、双反式、三反式,同时探究了“反切语”这种修辞格背后隐含的汉民族趋吉避凶、委婉含蓄、调侃戏谑的文化心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反切语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魏以降,其作为一种民间的口头隐语,代代相传逾两千年。直至当代,反切语还依然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声息活跃,究其原因,是其自身契合了当时当地人们语言生活的需求。这一语言现象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和各个族群间表现形式各异而又有所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学界同仁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们仍要看到,作为一种隐语行话,反切语体现的文化内涵是包罗万象的,其引发的一系列语言现象和相关问题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