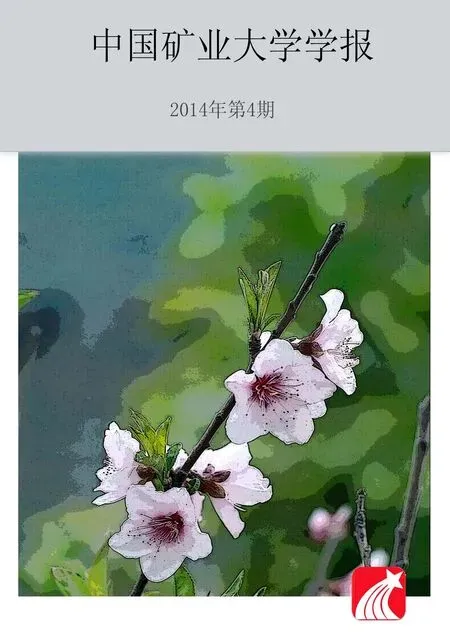冯叔鸾“戏学”的丰富内蕴及文化旨归
——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二十
赵兴勤,赵 韡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冯叔鸾,原名冯远翔,笔名马二先生、马二、叔鸾、楼桑、楼桑村人等,室名啸虹轩,自号啸虹轩主人,河北涿州楼桑村(一作江苏扬州)人。他是民国初年风云一时的剧评家,目前生平事迹已少为人提及,学术贡献更近乎湮没无闻。个中原因,除了他发表之成果与当今学院派主流之研究旨趣不符外,还在于其政治问题与人格操守(曾出任维新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如皋县长等伪职)。笔者曾撰专文,考订其生平史实,对各家记载予以纠谬,认为冯氏生于1884年,卒年当在1944年以后,或即1946年,并对他的戏曲活动予以钩沉*参看赵兴勤、赵韡:《冯叔鸾生平考述及其戏曲研究的学术价值》,《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3期,即刊。。文章谓:
冯叔鸾戏曲研究方面开创了若干先河。在研究领域的创辟上,首次提出“戏学”概念,将戏曲纳入科学范畴予以考量,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客观上提高了戏曲的研究地位;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率先对新、旧剧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早于佟晶心《新旧戏曲之研究》十数年;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倡导“探讨根本上之组织而为学理的研究”。以上,均显露出超越那个时代的具有现代学术气质的治学精神。胡适曾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看待出处大节有亏的冯叔鸾,亦应“持平”。只有摈弃成见,“不以其过没其功”,方能还原百年学术史之真相[1]。
然限于篇幅,对其提出的“戏学”这一重要概念的丰富内蕴未及展开。因此撰作本文以申述之。
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来被视作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不为正统文人所重视。在他们看来,“六经”乃是用力之所在,“诗,小技,不足为也”[2],更何况戏曲?直至上个世纪初,依然如此。“向来的学者文人不但视为小道,且以为它卑鄙龌龊,不值一谈”[3]。吴梅执教北大,教授戏曲,被讥嘲为“不识时务”、“误人子弟”[4]。所以,历史上操觚染翰、从事戏曲创作者,虽不乏其人,然大多作为官场失意之落寞生活的一个点缀。至于染指戏曲研究者,则屈指可数,不过王骥德、李渔数人而已。直至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始将古代戏曲研究变成“专门之学”。这一“空前绝业”,得到梁启超的极力赞誉,谓:“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5]王国维本人也不无自豪地声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6]他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壬子岁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6]壬子,乃民国元年(1912)。故而,学者据此推论,该书完成于1912年底至1913年春初*参看黄仕忠:《论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对王国维的影响》,刘祯主编:《中国戏曲理论的本体与回归——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439页;苗怀明:《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中华书局,2013年,第19页。,时静安氏旅居日本。
值得关注的是,王国维将近代科学方法引入古代戏曲研究,并将戏曲与诗、词之学相提并论,无疑提高了戏曲的地位,开戏曲研究风气之先。然其所涉及的主要为元杂剧之前的各种戏曲形态,对之后的大量戏曲现象则未作表述。而且,他的著述中似乎并未出现“曲学”、“戏学”、“剧学”之类字眼,倒是梁启超以“治曲学”称之。据有关学者考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乃其“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一九二三年冬至一九二五年春之间”[7]。由此可证,梁启超“曲学”之说,当晚于冯叔鸾之“戏学”差不多十年光景。亦可知冯氏当为较早将戏曲表演与研究视作独立学科并称之为“戏学”的学人。故而,其曾充满自信地宣称:“戏学之成立及戏学名词之成立,皆始于我之《戏学讲义》,前此盖无有也。”[8]
那么,冯叔鸾所指称的“戏学”,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是否已具备学科层面的意义,他又是如何为自己所标举的“戏学”下定义的呢?在《戏学讲义》中,冯氏对这些问题均有所回应。他说:“戏学者,研究演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之学科也”[8],“戏学者,研究演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之方法而成为一种学科者也。”[8]在其看来,老伶工教徒弟手、眼、身、法、步,唱曲先生说戏教唱,均为知识、技能之传授,还不能算作学问,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知识、技能的场上运用,至于为何如此,则不甚了了,不能将所掌握的零散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并说出其中的所以然,故不能目为学问。如老农认识许多草木、渔民能辨识多种鱼虾之类水产,但不能称他们是植物学家或水产学家,“盖彼辈有材料而无条理,知应用而不究原理故也”[8]。“区别知识与学问,皆以有条理、无条理为断”[8]。
由此看来,冯叔鸾的“戏学”,似乎是指“专用以学戏者”[8]。其实不然。在他的《戏学讲义》中,却涉及戏剧之分类、京戏之源流流派、京戏之板眼、腔调及唱法、戏行术语、名伶小传、新剧之流行、编剧理论、表演技巧、演员之饰演与场上布景设置、新剧家传略、女剧之兴起与男女合演、客串、伶人演出及观众接受之心理、戏班行规与陋习、剧场筹划与促销等多方面的内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关注的是史的线索勾勒,而冯叔鸾的《戏学讲义》则重在戏曲本体、场上伎艺及发展趋势的表述,有相得益彰之趣。
几乎生活于同时的齐如山,在《国剧艺术汇考·前言》中,曾不无感慨地批评当时的研究者,只关注戏曲的“历史的关系”[3]2,“但是对于台上演的戏剧,是怎样的来源,怎样的组织法,其原理如何等等,却是没有人研究,不但现在没有人,就是几百年来,也没有人注意及此”[3]2-3。这未免言之过当。该书1962年出版,对冯氏《戏学讲义》之内容却只字未提。齐氏1928年出版的《中国剧之组织》一书,曾有冯叔鸾、张豂子等人为之作序。可见,齐、冯二人当有所交往,按常理推断,齐如山对冯叔鸾的成果不会一无所知。其中之原因,耐人寻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研究者大多留意的仍是戏曲文本的研究。某些戏曲史,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以戏曲文本研究为主体的“史”的线索描述,对于场上之表演,由于隔膜甚或不屑,只是三言两语、略略提及。正如同有人所说:“和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等明确的艺术门类不同,戏剧戏曲学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为大家所认识和了解的,至今《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对‘戏曲’一词的解释仍是‘一种文学形式’,长久以来的文学式定位使得对戏曲的创作、评判、理论研究一直局限在文学的范畴内。”[9]直至1990年7月,国家学科目录进行了调整,“艺术学”及其分支学科正式建立。戏剧与戏曲学作为二级学科位列其中。由于戏剧与戏曲学学科的建立,人们对戏曲学的内涵才逐渐清晰起来。有学者曾强调指出:“戏曲学的研究对象,绝不能仅仅视为剧作家创作的文本,而且包括剧场演出在内,从导演、演员、场景到观众的一整套表演和接受体系。”[10]理应涵盖“具体的创作和演出问题”[10],如剧场学、演出学、观众学之类。“戏剧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剧诗、剧本、舞台艺术等,不如说是更宽阔的包括观众在内的剧场或剧场经营”[11]。也就是说,“戏剧学研究的除了戏剧的文学性之外,还必须研究戏剧的非文学性一面,如演员、导演艺术等”[11]。
很难想象,至今还不时困扰我们的有关学科界域的辩难,以致为“戏剧”、“戏曲”之内涵争执不休,而早在一百年前,冯氏的论文已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所谓“研究演戏之一切原理及其技术之方法”[8]的理性表述,无疑具有很鲜明的超前意识,远非所谓“专用于学戏者”。这一概念包蕴着有关学科构建的大胆设想以及与此相关的多层面的丰富内容。约略说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论演员素质——伶人场上之艺术表演,亦是一种学问。
伶人若想提高演技,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功底、理解能力、鉴赏眼光。冯氏这一观点的提出,显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封建时代的伶人,大都因家庭贫困,失去了上学读书、接受教育的机会。投身戏班,不过是为谋生计。从师傅那里接受的一招一式的表演伎艺,不过是比葫芦画瓢的外在程式而已。至于为何如此表演,这一表演与人物刻画之关系,则大多不甚了了。当然,饥寒所迫,也无暇计此。至于唱腔与宾白,也是口口相授。表述何意,有无错别字,多无从得知。冯叔鸾认为,戏曲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浅近可也,粗俗亦可也,别字连篇不能句解不可也。今之皮黄词曲中,每患此病,则以俗伶目不识字,口相授受,故谬种日滋也。”[12]作为一个文人,有责任帮助伶人提高文化素养,纠正此类弊病。他指出:“艺之精拙优劣,岂有他故哉?亦惟学而已矣。是故戏也,非学则不足以成家。然则我《戏学讲义》之作,非漫为夸张也。无学之戏,固不成其为戏也。”[8]
所谓学问,是指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一般认为,它为博学多识者所掌握。这里径称台上伎艺表演也是一门学问,将伶工伎艺与学人问学相提并论,无疑是在提高为世俗所鄙视的伶人的社会地位方面,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在作者看来,伶人在前辈那里所接受的表演程式及演唱方法,非常零散,不成系统,难以称得上是艺术,只能算作应付场上演出的一般常识,亦即技术,尚达不到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层面。所以,他强调,若想不做“泛泛而生,泯泯而殁”的碌碌余子,而成为“一曲名闻天下”的程长庚、余三胜之类名伶,必须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深化对表演艺术的理解。在场上艺术实践中,不仅应明白“怎样做”,还应明了为何这样做,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将所掌握的表演技术条理化、理性化、艺术化,由生搬硬套提升为一种表演上的艺术自觉。不能只“知应用而不究原理”[8]。如此,才能适应“嗜戏者日多”[8]、“知音”者日多、“戏剧之盛,于今为烈”[8]的客观情势。
第二,论戏曲盛衰之原理——戏曲作为大众艺术,应雅俗共赏。
戏曲,包含了音乐、舞蹈、杂技、美术、文学等诸多艺术成分,既是一项综合艺术,同时,它借助演员对剧中人物的扮饰,通过对白与演唱,敷演具有一定时间长度与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故又是一门表演艺术。“综合”云云,是针对其艺术形态而言;而“表演”之说,则是在强调其作为场上存在的艺术形式的实质内容。从根本上说,戏曲的产生与发展,与市井村陌之民间生活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粗犷质朴、雅俗共赏,当是其本来面目。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就曾在《闲情偶寄》中强调,戏曲创作不能带“一毫书本气”[13]24,“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13]22,“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13] 28,“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13]28这些看法,无疑切中元代以降戏曲创作越来越雅之时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无独有偶,生当清末民初具有相当舞台经验的冯叔鸾,对演出主体及接受者心理均十分熟悉,自然也明了此中之道理。面对“梨园子弟知昆曲者渐少,习皮黄者遂日众”[12]这一客观形势,他敏锐地意识到作为称盛一时的“雅部”——昆曲衰落的根本原因:
盖声乐之道,达雅与通俗二者,初未可以偏重。昆曲文章优美,词藻典严,然宜雅不能宜俗。试问:“趁江乡落霞孤鹜,弄潇湘虚影苍梧”,“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此等曲词,岂一般贩夫走卒、妇人孺子所能骤解?不宁闻者莫名其妙,即寻声按拍之俗伶,恐亦第如鹦鹉之学舌,习其音而不达其意也。至于皮黄则不然,“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我本是卧龙冈散淡人”,任为何人,无不一听即可了然于胸。而其最普通习用之词,总不外于“我好比”、“听分明”、“叫一声”、“好不伤心”、“细说端详”等语。是故人之诟皮黄为鄙俚不文者以此,而我则以为其能战胜昆曲而风行全国者,亦正在此也[12]。
是昆曲词语的过于藻丽高雅,拉大了与普通接受群体之间的距离,使“贩夫走卒、妇人孺子”不明其所以,隔膜得很,无法欣赏其高妙之处。甚至只会拍曲而识字不多的俗伶,也只能如鹦鹉学舌一样进行生搬硬套,至于词句之内涵,照样不明所以。而新兴的皮黄戏则不然,语句浅显明白,多采用白话入曲,接受者“无不一听即可了然于胸”,故赢得普通市井大众的青睐。冯氏是从传播者与接受者不同的层面,论述了戏曲盛衰的深层原因,无疑是客观并切中肯綮的。谭正璧在大约八十年前论及小说之盛衰时曾经讲过,“无论何种文学,皆始由民间产生而末则趋向贵族化,至十足贵族化时,此文学乃至末路。”[14]戏曲艺术何尝不是如此?昆曲的由盛转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论场上表演——对唱工、做工、武工的要求。
冯叔鸾所指称的“戏学”,既然包括演戏之一切原理及技术,那么,场上演唱及表演伎艺,自然在其密切关注之中。戏曲乃是表演艺术,作为表演主体的伶人,自然要唱工、做工、武工俱佳,始能真切再现剧情所预设的特定情景,以及剧中人物在不同条件下心境的曲折变化。如悲欢离合之情,或悲壮苍凉,或激昂慷慨,就适合用婉而有致的唱腔来表现;而忠奸斗争、儿女之情、滑稽诙谐之类内容,借用做工表现会更具艺术感染力。“喜怒哀乐、忠奸善恶,皆一一为之现身说法,使观者如遥对古人,如身临其境”[8],才能达到应有的戏剧效果。英雄传奇、妖魔鬼怪故事剧之表演,则要靠演员的武工了。他们“或矫捷如猱,为飞檐走壁之大侠;或猛鷙如虎,俨然辟易千人之猛将。又捉妖斩怪,变化多端”[8]。惟其如此,方能赢得接受者的喝彩,这就对演员艺术素养的提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既而,冯氏又对演员的演唱要求,作了进一步细化。强调唱腔不能太随意,应该“有规矩”,懂板眼,知某字落于某板,某板转于某眼,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当然,仅知板眼还远远不够,还应仔细揣摩声腔之变化,根据剧情的需要而行腔,“不可徒恃气长喉咙声便任意拖沓缭绕,以博一般门外汉之喝彩则可矣”[12]。要努力做到“高而不亢,低而不闷,长而不冗,短而不呆”[12]。若能“以极短之节奏,行极波折之腔”[12],“字字合板”、“字里行腔”,则是戏曲演唱的更高境界。要根据个人嗓音的条件、气力来练习唱腔,初可模仿名伶,逐渐“脱胎换骨,自成一家”[12]。嗓音分洪、细、高、低、尖、沙等几类,数者兼备较难达到。然而,根据自身条件,善于用嗓,突出某一方面,经过苦练,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刘鸿声“嗓音尖亮,又善于运用,遂乃名噪一时”[15],即是一例。可见,充分发掘个人潜力,使洪者“宽而能亮”、高者“宽而能高”、尖者“戛然直上”、细者“委婉有致”、低者“沉郁有容”、沙者“苍老而遒劲”,恰适宜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
对于最能体现“戏”(戏剧性)之层面的“做工”,冯氏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强调“戏”之凸显在于“做”,谓:
有唱工而无身段,直一留声机器而已。然而“身段”二字,谈何容易哉?科班出身者,大概身段皆习过,三步到龙口,整冠投袖,五步半到台口,退半步,念引子,转身就坐,此类动作皆优为之,顾多执泥成法,食而不能化,遂演成一种刻板戏文,仅足为前三齣开锣戏之用。至于票友,天分稍好者,则又多缅越规矩,自以为是,或者袭其皮毛而不能体贴入细。久之习非成是,求得一能存前辈典型者,杳不多得[12]。
在他看来,何时出场、何时迈步、何时整冠投袖、何时“转身就坐”,仅仅搬用这套程式,充其量只能算作技术的演示,使得表演刻板拘泥,了无生气。同样,“缅越规矩,自以为是”,其表演更令人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依然无法令观众接受。如此之类,均难以称得上是表演艺术。
场上演员的表演,应“依剧情之规定”[16],紧密结合剧作内容实际,“不得以不合情理之服饰及动作博人笑噱”[16]。在场上表演时,应顾及表演与身份之关系,熟悉各社会阶层中人之性情状态,“并须能粗悉三教九流之大概状况,始足以因应不穷”[16]。还要考虑到表情与剧作中人物行为之关系,“悔恨必顿足,大乐必拍手,是则点头,否则摇首,詈人必拍案或戟指,思索必俯视而搔首,此皆常人之恒态,亦即剧中表情所不可不知者也”[16]。
至于表情,更要仔细斟酌、体味。“表情不佳则剧情必因而减色,故表情佳者,剧之精彩必百倍。表情之要有四:一、不可不明瞭,不明瞭则无生气;二、不可不熨帖,不熨帖则觉其生硬刺目;三、不可不于紧要节目中加意体会;四、不可不于闭幕时注意使观者留一有余不尽之意味”[16]。除此之外,还应注意表情与动作的谐和统一,“坐应如何,立应如何,卧应如何,步应如何,姿势是矣,而地位应在何处。怯场者,往往以背向台下;不知地位者,往往立身于墙隅;甚至叩首者耸臀以向看客,对语者乃游目及于包厢,此皆不明剧中表演之理法者也”[16]。只有对剧中人物或悲或喜的命运遭际“体贴入微”,“凡演一剧,必将此剧之事实源(原)委记清,剧中人之身分性质研究透熟,夫然后一举一动,乃得合于理法;一哭一笑,皆足以觇见艺术之高下”[16],才能做到表演程式为情节表现、人物刻画服务,心中有“人”,身上带“戏”,而不是生搬硬套或故意卖弄,“全置剧情于不顾”[16]。
名伶谭鑫培,“所娴戏至夥,不下四五百齣,而每奏必有惊人之艺。如《奇冤报》中毒时之翻桌,只一按而过,莫测其用力之处。《卖马》之舞锏,《琼林宴》之甩鞋,《骂曹》之击鼓,《斩马谡》升帐时之台步,《定军山》之舞刀,《四郎探母》之一场急促一场,种种描摹设想”[15],均切合剧情及人物心理,被誉为“集戏学之大成”[15],即是成功一例。
冯氏对场上之表演技法多所表述,且不乏独到之见解。然而,齐如山却称:
自有戏剧以来,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但没有一人,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它,当然也就没有人写书了,偶有一两种,则都是关于南北曲,与现在风行的皮黄格格不入,而且都只是研究歌唱,还谈不到全体的戏剧,尤其舞台的演法,更没有人谈过[17]180。
齐如山之《说戏》刊于1913年,是其研究京剧艺术的第一本书,略早于冯叔鸾的《戏学讲义》。然而,后来齐如山又在《回忆录》中对此书之学术价值予以否定,认为“太错”[17]201。至于另一本《观剧建言》,则认为“不够理论”[17]201,所以只把《中国剧之组织》当作“写的最早的一部书”[17]200。如此看来,真正对皮黄之“全体”作系统研究、理性思考者,冯叔鸾当是第一人。可齐氏却称,皮黄在当时“没有一人,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它”、“舞台的演法,更没有人谈过”,则未免武断了些。
第四,论戏曲的编剧——对剧本创作方面的要求。
冯叔鸾活跃于上海剧坛,正值戏剧改良面临严峻考验之际。当时,“上海新剧团风起云涌,进化团而外,有所谓新剧同志会、开明社等团体”[16]。“癸丑(1914)之秋,有所谓新民社者出现于上海之谋得利戏馆,主其事者曰郑正秋。入冬更分为民鸣社,逾岁而开明社、春柳社剧场等纷纷复起,各树一帜。其间旋生旋灭者,不下十数团体”[16]。“新剧团立于海上者不下二十。团之人数自二三十以讫于六七十,统而计之,所谓新剧家者,殆不下千人”[18]。
提倡并搬演新剧者,大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如“新剧同志会之社员大半为留东学生。彼等在东土时即有春柳社之组织,其演艺胎于日本之新剧”[16]。“进化团之任调梅,亦尝在日本西京大学教授华语,故其演戏亦多取法日本”[16]。戏曲活动家王钟声则曾留学德国。他们在戏剧编创及演出时,均有意识地吸收了域外先进文化,不仅在剧作内容上有意创新,反对专制,干预时政,将时事编入唱词,鼓吹独立自强,在表现形式与格局上也标新立异,别辟境界,以致洋装戏、时装戏“两下锅”,孟姜女着洋装、秦时人裹小脚等充斥于舞台,甚至出现了用京剧的唱腔和锣鼓伴奏,演唱外国有关黑人题材故事,搬用西洋布景的情况[19]。表演团体众多,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演、创者风格与追求亦各不相同。如春柳社“演艺重脚本,尚理法,分幕较少,每幕情节或有极复杂者”[16]。但因其所演剧作,多是翻译自外国名著,所以,演出时不仅普通市民不明所以,即使“中等社会人,多猝不能解,比较的反不若进化团派之易于普及,故剧虽高尚,而营业上往往不能发达,所谓曲高和寡也”[16]。而任调梅为首的进化团派(无知派),“人数极众,分子极杂,其演剧不用脚本,专尚随口应对,分幕极多,而每幕中之情节极简单”[16]。有的戏剧演出拖沓冗长,拉杂而出,一段说白,竟达数千字之多,有似政治讲演。或“似影戏,又似走马灯之演艺,无数人物、无限布景纷纷不断,一幕幕演了去,至少五个钟头。也有二三十幕,岂特全剧无有结构,即每夜所演,亦无一定之交代”[20]。“是故看客既不知讲求,则演者又安得而不胡闹?只须广告中说得天花乱坠,哄得人来,台上花花绿绿,耀得俗眼撩(缭)乱,便可称为新剧。安有所谓演艺,更安有所谓文学的演艺?”[20]
在冯叔鸾看来,“中国目下新剧之不能发达,非缺乏演剧的人才,实缺乏良好的脚本也。”[16]既是戏剧,就不能胡拼乱凑、粗制滥造,而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文学性。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戏曲创作主张。
首先是强调戏剧创作“须有主旨”。“一剧必有一种命意之所在,此所谓主旨也”[16]。其实,他所说的主旨,就是剧作的主题,亦即作品的主干内容应明确,围绕一个中心铺展情节,展开戏剧冲突,而不能漫无目的东拉西扯、胡乱凑合。正如清人李渔所说:传奇戏的写作,应“立主脑”。“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13]14相反,若率性而为,信口应对,就会凌乱无章,主次混淆,“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绪,观者寂然无声”[13]14,如坠五里雾中。冯氏所言,恰与李渔戏曲创作主张多相呼应。他曾在《啸虹轩剧话》中这样描绘视演戏为儿戏、恃才情恣意妄为的“自由演剧者”,说他们:
不读书,不用脚本,且不必预备练习即可登台是也。彼辈所恃以为戏中关键者,一张幕表而已。表上所列,只登场者之人名而已。……言词如何,动作如何,一任其自由主张,随意增减,故甲演此剧万言不尽者,乙演之或三五语而尽焉。甲主激烈,而乙尚温和,于是戏之情节犹是也,而十人演之,则十人各异。此新剧社与彼新剧社所演又大异,不特此也。一人演两次,则前后互异,语言、表情、举止、动作无一不异,时间亦因之而可长可短也[20]。
作者不无愤慨地质问道:“剧者,一种专门之艺术也。天下宁有不须研究、不必练习、无条理、无根本而成之艺术哉?”[20]很显然,冯氏强调剧作乃戏曲表演之根本“要素”,演艺应“重脚本”、“道行惟谨”,戏曲创作必须突出“命意之所在”。实在是有感而发。
其次是强调结构之谨严、完整,注意情节的起伏照应。在冯叔鸾看来,戏剧创作,应在情节构筑、结构完善上下功夫,“结构不佳,则其文斯不足观。同一剧也,结构一佳,则其精彩顿异”[16]。他举例说,同是一部《家庭恩怨记》,春柳社以七幕之长度敷衍情节,以其照应绵密,“起伏相应”,故深得观众欢迎。相反,进化团派演出该剧时,却将它拉至十数幕至二十余幕,“拉杂拖沓,直不知其所以然”[16]。演出或许也热闹,但因情节涣散而难以招徕观者。就戏曲创作而言,“全在针线紧密”[13]14。“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13]14。若有剧本而不依,不加细读,更不去研究,“每夕七八时登台,而五六时尚不知自身所扮为何人、所演为何剧,临上装时,始对壁上所悬幕表稍一注目,复向主任者请示一二语,于是遂居然出台演剧矣”[20]。“言词如何,动作如何,一任其自由主张,随意增减”[20],章法一失,结构大乱,情节岂能不“拉杂拖沓”?
再次是化实为虚,虚实相映。冯叔鸾认为,剧中所搬演的时间、空间都是虚拟的,所选取的事实也不过是根据现实人生中的某个镜头而加以铺排、渲染,使之具有了典型意义,而不能照搬事实依葫芦画瓢,他说:
演剧之空间、时间必不能如真,是故战场千里、沧海无涯,则以布景代之。由少及壮,经年累月,则以数十分钟或数小时代之,由此类推,则剧中之事实不过取真事之烧点而为一部分之形容。故剧中之事实,乃为抽象的[16]。
虽然表述得还不够具体、确切,但已意识到舞台表演的化实为虚、虚实相映之类戏曲艺术的本质性特征问题。戏曲艺术源于生活,但不是生活的照搬或模仿,而是采取艺术的手法将生活中的某种行为、物象加以提炼、升华,使其实现华丽转身,既具有视觉的美感,又与现实人生保持适当的距离,还能令观众意识到所表达的意义。正如学者所论,戏曲艺术“所表现的是高度戏剧化了的人生,因此它不能用写实的和摹拟的手法表现,而必须充分运用非写实的和虚拟的手法,使舞台上的人物和行动明显地与实际人生拉开距离。”[21]戏曲表演对时空的处理,“是不以模拟生活时空来再现情节时空,而是故事讲到哪里,时空发展到哪里,呈一种线性的流动”[22]48,不受生活中空间、时间的限制,“对时间、空间的延长、压缩(以至省略)和转换,是高度自由的。这种假定性的时空关系,使戏曲能更自由地反映生活,它不用把人物、场面人为地集中在一起,而能使剧情获得流畅的发展”[22]48-49。早在百年前,冯氏已意识到戏曲表演艺术对“虚”、“实”关系的斟酌与把握,还是很难得的。
还有,就是对戏剧文学审美意义的重视。冯叔鸾称:“剧为文艺美术之混合物。剧之取材与构造,必以美术为归。枯涩无味、纷乱无序,皆在摈忌之列。”[16]这里称文学剧本所用素材当为美术的。一般认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均为“美术”所涵盖。然据《辞海》解释“美术”一词曰:
欧洲十七世纪开始用这一名词时,泛指含有美学情味和美的价值的活动,及其活动之产物,绘画、雕塑、建筑、文学、音乐、舞蹈等,以别于具有实际用途的工艺美术。也有认为“美术”一词正式出现应在十八世纪中叶。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后,技术日新月异,商业美术,工业美术,工艺性的美术品类日多,美术范围益见扩大。目今属于美术领域的,有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包括青铜、陶瓷艺术、家具制作、编织艺术和装潢设计)等,在东方还涉及书法和篆刻艺术等。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普遍应用这一名词[23]。
陈独秀在《答张豂子》一文中,论及传统戏曲时说:“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邪?”[24]其所谓“美术的”,实际上就是指的审美情趣、美的价值。如此看来,这里所说的“美术”,就不单指绘画、雕塑之类,而还应带有审美的意义。在他看来,戏曲乃文学、文艺、绘画的综合体。它的素材的选择、情节的结撰,都应具有审美意义。场上演出,既要考虑“愚夫愚妇”的接受能力,还应顾及“淑媛贤妇,硕学通才”的心理感受;既要注意内容的提炼、升华,还应照顾“梨园营业”、“招徕生意”。所以,他反对“极淫亵不堪或粗鄙之戏”[25]充斥舞台,又对“梨园营业者只求号召座客,更不复计及与世道人心有若何影响”[26]表示不满。曾指出,有些剧作刻意好奇,“支离不完,以戏剧言,固曰艺术消沉,是文学上之退化,实则淫靡相袭,即社会腐败之明徵,足为世道人心之隐忧,不仅于区区艺术之盛衰已也。有志改良戏剧者其念之哉!”[20]同时,他既不赞成将戏曲艺术作为纯然政治宣传的工具,谓:“社会教育家多以演戏为社会教育之一种,而演戏者遂亦侈,然以社会教育为己任。然就事实考之,殊不尽然。”[25]也反对将戏曲艺术与现实人生割裂,曰:“夫戏剧虽小道,而与社会文化有密切之关系。”[20]并进而申述道:
夫演剧故美术的与文学的也。美术家有画春宫者,文学家有著《金瓶梅》者,夫岂可谓美术及文学与教育无关?然亦观其用之如何耳。故演戏亦犹是也。谓演戏与社会教育无关系,固不可,然竟以凡演戏便是当社会教育,则又断断乎未必然也[25]。
意思是说,戏剧剧本的写作,既应考虑其“娱耳目,悦心意”的功能,也不能为博世俗一笑而胡编乱造,无视“与世道人心有何影响”。应在保持戏曲艺术娱乐性的同时,寄寓对“世道人心”的感染功能。此外,还应进一步提高剧作语言的表达能力,力改旧戏曲词“鄙陋”的现象,“新剧中万不可多加演说,盖演说自演说,剧自剧,若剧中多加演说,则非剧矣”[26]。
第五,论当时之演出——对上海剧坛现状的审视与反思。
在戏剧改良上,冯叔鸾有着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旧剧中存有许多落后陈腐的东西,固然应该改良,然新剧虽说参合中外,自成一家,有其独到之处,如春柳派就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能因一己之好恶而不顾事实地乱加褒贬,或讳言其短,或掩其所长。他认为,新剧之发展出现变数,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自身的因素,亦即一味迎合市井大众中某些闲杂人等的口味需求,而缺乏对文化销售市场的引导之力,仓促上阵,穷于应付,只知被动听从,而不能主动引领。剧作粗制滥造,而精品又无暇打磨,处处为“看客”所左右,则愈发助长了这一浮躁风气。曾言:
大抵观新剧者,既无歌曲可听,则专以情节为尚,每每一览之后,即不愿再观。于是每星期中,必须有一两本新编之剧,方足以号召座客。故新剧社之脚本著作者,殆等于小说杂志中之主笔,按期必须有若干新作,宁滥毋缺。刻烛成,文艺安能工?此其所以辗转因袭,卒无佳构也[20]。
为追求票房价值,“欲以‘新’之一字为号召之具。一演之后,即可弃置不顾,则脚本之结构好与不好一也”[20]。或只是为了赚钱,“当其第一次开演,固已骗得座上客满,流水账便添有几千几百之进项矣”[20]。他们所追求的是典型的短期效应,根本无视戏曲的发展与未来。流风所至,天下风靡。“北方风气刚劲,崇拜侠义之心普及”[20],《施公案》、《彭公案》之类侠义公案戏便大行其道,盛行一时;“南土淫靡之风炽”[20],《遗翠花》、《阴阳河》等风月剧则普遍流行。结果,整个剧坛,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言英雄总不外乎打家劫舍,霸占妇女;而言儿女,又总不外乎郎才女貌,密约幽期”[20]。而所谓新剧,“更删去打家劫舍一部分而仅有幽期密约之情节,每况愈下,改良云乎哉”[20]?针对这一积弊,他才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如改良先从剧作始,强化精品意识与整体观念,一改“旧戏脚本多支离之病”[20],“避熟就生,极力求新”[20],打破旧戏因循守旧之习。提高演员的角色意识,“一经登台,则我即非我”[20],投入剧本所规定的剧情之中,在表演技巧与人物性格揣摩上下功夫,而不能“徒以虚誉骄人,以诈术博外行之欢迎”[26]。赢得观众,靠的是场上的真本领,而不是连篇累牍的广告、耀人眼目的服饰或布景。
冯叔鸾还对表演主体、接受群体的心理作了一番探究。在“伶人的心理”一节中,他列举了十七种情况,如:“凡演戏尽其所能,以博台上看客之彩声,于是脚跟立定,遂不患无噉饭处,此是一般普通伶人之心理。”[25]“临场不苟,务求胜人,此是具有专长不甘埋没的心理。”诸如此类,均具有普遍意义。他如“怀才不遇,抑郁自弃”、想“走红运而无本领”、“卖老牌子”、怕演砸、想出名、故卖弄等等,亦道出伶人表演之时的某些心理层面。至于观戏者之心理,则列举了十六种现象,如不懂装懂、“羞称不知”,假充内行、妄加雌黄,虚于应酬、炫耀阔绰等等。上述种种,不仅为戏曲艺术传播方式的不断调整提供了依据,还为探窥上海市井之风俗呈示出形象画面。
至于为何研究伶人与看客的心理,冯叔鸾并未明言,但由“舞台经验谈”所列举的演艺界“排斥外行”、“巧言诋諆”、“要挟无厌”、“名伶骄倨”等种种陋习来看,又似与伶人心理分析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在他看来,伶人有种种不健康的心理并不可怕,关键是掌管戏班者如何正确引领,让他们摆脱心理障碍的束缚,将精力投入到表演伎艺的提高上来。且舞台是一盘棋,若要下得好,离不开伶人之间的互相支持与配合,红花还要绿叶衬,越是名角,越应大度,后来者伎艺若能胜己,则应“避路让贤”,而不应“嫉妒为心”,暗中使绊,“贪鄙为怀”。
而对观众心理的分析,其作用除上述之外,似乎还另有意味。如“凡收拾得齐整非常、油头粉面、香气四溢方去看戏,是一种吊膀子的心理”[25]、“凡男客忽看髦儿戏,女客忽看新剧,至于每日必去者,必有一种希冀非分的心理”[25]之类,对备受恶势力歧视、地位低下的伶人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当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在当时众多看客中,“游目四座”、“藉嗅脂粉余香”[26]者或不乏其人。
还有,就是对男女合演问题的态度。我国剧坛,历来多以男子扮女色,这成为一种惯例。至上个世纪初,始有改观。据赵山林等编著的《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所载,上海滩的男女合演肇始于宣统元年(1909)的正月初一。其时,“原女班戏园丹凤茶园开始添聘男班名角,实行男女合演,并在布告中称此举为‘开通风气,以兴市面’”[27]220。不几天,“会审公廨谳员宝颐就丹凤茶园男女合演事上书上海道台蔡乃煌,称该戏园‘虽名为分剧演唱,然经卑谳调阅戏单,其配角之中实系男女混杂。伤风化而败治安,莫此为甚,亟应严行禁止。’”[27]221所上条文虽未能立即生效,但毕竟给演艺界带来不少冲击。而在冯叔鸾看来,女子之审美情操尽管“较男子为充裕”,然由于她们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又无正当职业,在接受表演伎艺的训练上由于封建势力、道德观念的束缚,又面临许多难题。即使伎艺学成,以售艺为能事,也难免遭到旧势力“以色字为招徕之具”[28]的攻讦。而在冯氏看来,“天津梨园男女合演之风最盛,然其淫靡之习视沪上未尝有加也。即以沪上而论,法界各馆虽有男女合演者,而自一般观剧者视之,与非男女合演者亦无大异”[28],“是故男女合演,于艺术上有莫大之便利,而于风化上初无若何之影响,决非不可能之事。惟男伶女优,混处一舞台之中,如何而能使之专心艺术,勿堕情魔,此则剧界内部之道德问题,于社会上之风化,初无所涉也,更何用鳃鳃过虑为哉?”[28]他明确强调,有伤风化,并不在于男女合演,而在于伶人道德自律上发生问题。当事者若引导得法,不仅有助于表演艺术的丰富完善与提高,亦有利于女子潜能的发掘。况有赵紫云、金月梅、刘喜奎诸范例耶?“紫云演武生,能不露丝毫巾帼气”[28],金月梅被誉为“有学问之女伶”[28],刘喜奎“演花旦,每登台,座必为满。戏毕,下装登车,围而观者常数百人”[28]。所论似有与封建势力唱反调之意。如此看来,冯氏当时之观点,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当然,冯叔鸾的“戏学”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止此,如还包括化妆、布景、导演等诸多层面。尽管他对中国戏曲史没有作过多追溯,但对当时剧坛的关注却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冯氏作为戏曲研究史上的“失踪者”,与郑正秋、柳亚子、傅斯年、周剑云等人一起,共同为戏曲的推陈出新、传承发展提出了许多可资参照的意见。尤其是他所倡导的创立“戏学”学科,对戏曲研究的深化与学科建设内容的丰富完善,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兴勤,赵韡.冯叔鸾生平考述及其戏曲研究的学术价值[J].社会科学论坛,2015(3)即刊.
[2] 张廷玉,等.明史(第十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4132.
[3] 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第一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 王卫民.吴梅评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3.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520.
[6]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M]//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3.
[7] 朱维铮.校注引言[M]//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2.
[8]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未完)[J].游戏杂志,1914(9).
[9] 陈娟娟.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对门类艺术学的促进作用——以戏剧戏曲学为例[J].艺术百家,2013(4):193-196.
[10] 徐子方.戏曲学——中国戏剧学论纲[M]//曲学与中国戏剧学论稿.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28.
[11] 叶长海.曲学与戏剧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0.
[12]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续)[J].游戏杂志,1914(10).
[13] 李渔.闲情偶寄[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4]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M]//谭正璧学术著作集(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
[15]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续)[J].游戏杂志,1915(11).
[16]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续)[J].游戏杂志,1915(12).
[17]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8] 马二先生.新剧不进步之原因[J].游戏杂志,1914(9).
[19] 赵山林.中国近代戏曲编年(1840—1919)[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10.
[20] 马二先生.啸虹轩剧话[J].游戏杂志,1915(18).
[21] 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196.
[22] 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中国昆剧研究会.中国戏曲艺术教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23] 辞海·艺术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457.
[24] 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266.
[25]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续)[J].游戏杂志,1915(14).
[26] 马二先生.啸虹轩剧话(续)[J].游戏杂志,1915(19).
[27] 赵山林.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8] 马二先生.戏学讲义(续)[J].游戏杂志,19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