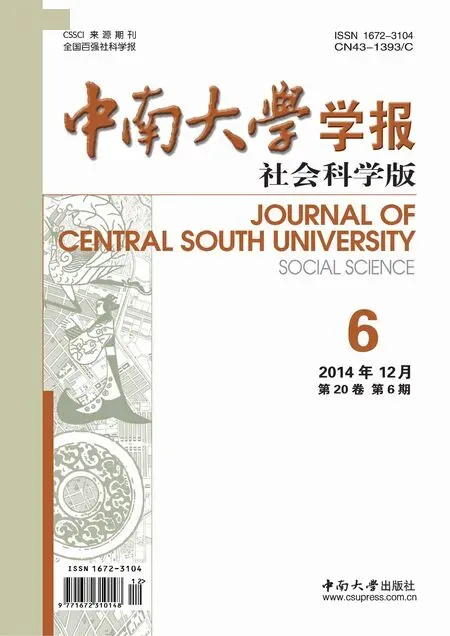家园体验与汉晋纪行赋山水物色的呈现
程磊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家园体验与汉晋纪行赋山水物色的呈现
程磊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羁旅纪行中的价值困境引发向往家园安顿的精神需要,山水作为补偿家园失落的重要文化因素,就成为展现行役之人追询家园的心理流程的典型形式,这也是山水审美依托行旅活动得以萌发产生的重要文化动因。汉晋纪行赋中山水物色的呈现形态,延续着《楚辞》模式中的楚调山水,逐渐发展为重视描写技巧和山水形质美感的山水赋,由对立于家园感的异己形态转变为怡情畅神的亲和形态,这种文体变迁与晋宋山水审美思潮的发展脉络是相应的。从“居”与“游”的角度看,陶、谢田园山水在文化意蕴上的差异,也可以从家园体验这一独特视角找到解释的依据。
家园体验;汉晋;纪行赋;山水物色;山水审美;描写技巧
《文选》赋类中列“纪行”一类,李周翰注曹大家《东征赋》云:“以叙行历而见志焉。”李善注潘岳《西征赋》引臧荣绪《晋书》:“岳为长安令,作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1]基本概括出以行役路程为线索来铺写风物、抒情言志的创作模式。纪行赋中常渗透着深沉的羁旅漂泊感,思家念亲、政治失意等个体的行役经验构成了情理冲突的内在张力,将此种价值困境引向对家园安顿的深思求索。笔者曾考察士人羁旅行役中的家园感与山水意象之间的联系[2],中国人的家园感是一种虚灵的心理体验,常在与人亲切相依的自然和生活中,通过对应的物化形态或特定情境呈现出来,自然山水作为引发家园忆念、补偿家园失落的重要文化因素,就成为展现行役之人追询家园的心理流程的典型形式。
一、羁旅悲吟与楚调山水
首先仍须从《楚辞》说起。《诗经》中的《陟岵》《扬之水》《伯兮》等行役、征戍、思妇之词,主要是以温情的伦理联系和安宁的田园生活来凸显家园渴望,其情感类型和意象选择,如《君子于役》中的黄昏意象及其透显出的朴素深醇的家园呼唤,都极具文化原型的示范意义;《楚辞》则展现了与家园疏离的巨大哀伤,自然因素带有浓郁的楚调色彩,也成为后世羁旅诗中重要的文化基因。就个体的羁旅经验而言,屈原的放流迁谪之诗最具代表性,完整而鲜明地展示出体味生命漂泊、反思价值困境、追询精神家园的精神历程。屈原最后以沉江自杀的仪式,将身、家、国各个层面的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将文化困境的质询推向了超越历史、叩问天道的理性高度,同时也以惊采绝艳的瑰奇意象、浓烈深挚的情感力度,迸发出怨愤哀伤、悱恻缠绵的主体之悲,开创了不同于《诗经》而极具楚骚品格的羁旅抒情模式。《楚辞》中的自然山水,虽仍有神话想象、神灵祭祀等南方巫风的影子,但对诗人的特殊魅力,“是因为在僻远的山林中或洲渚上,生长着象征高洁与理想的草木;而且山的高峻和水的奔泻产生一种洗涤心神的力量,能起舒愁疗忧的作用”[3],自然山水实际上成为诗人的人格象征和气质情感的对应物。结合家园体验来看,早期羁旅行役诗中的自然,总是着意突出与温馨家园的对立性质,节序物候的迁逝瞬变、自然环境的凄凉险恶,都渲写着一种置身异域之中无主无依的羁旅悲吟。如《九章·涉江》: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
其中的舟行陆进、朝发夕宿,是最典型的羁旅叙述模式,突出人在旅途中的时空流动感。王逸注:“乃从枉陼,宿辰阳,自伤去国益远。”指明离根失土的行旅之悲,此是一层;又以“儃佪”“迷不知吾所如”烘托生命飘荡的无目的性,以及美政理想无处施展的无价值依托感。王逸注:“思念楚国,虽循江水涯,意犹迷惑,不知所之也。”[4]这样就把游于家国之间、两端无所依凭的价值困境直观表现出来,此是二层;深林杳冥、峻山雨雪,都点明山水非人所居的荒野特质“(猿狖之所居”),是陌生的异己的所在,无疑表现了一种从外部环境到内心感受都无法融入、无法认同的漂泊的悲哀,此是三层。这种经主观情绪濡染而极具个性特点的荒野山水,正是顾彬所说的“理想与现实的割裂”之中,自然作为“哀伤的投影”的集中体现[5](40)。其它如《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悲回风》:“凭昆仑以瞰雾兮,隐□山以清江。惮涌湍之礚礚兮,听波声之汹汹。……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所描绘的自然景象,都具有类似的激楚悲凉的品格,成为表现“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的内心郁结的外在媒介。《哀郢》写“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的羁旅所见所感,汪瑗《楚辞集解》解得甚为精当:
其所叙流离等语,非述一己之怀也,盖将以众人之忧为忧也。
今顺此风波,纵其漂流而洋洋乎,果将安所而为客邪?盖故设为无所归止之词,以见去故乡而就远也。
方将运舟而东浮也,则又将上洞庭逆流而溯矣。方且逆流而溯也,则又将顺流而下江矣。二句之间,其道里之萦纡,迁客之颠沛,俱见之矣。
登大坟以回望故都,本欲聊以舒吾之忧心,然故都平乐之风土,日邈以远,而漂泊于此大江之介,感风景之殊,使吾之心益哀而悲焉。
乘此陵阳之波,淼然南渡大江矣。果将何所归而何所往耶?实反言以深见迁客之流离,故都之日远也[6](173-177)。
上摘引数条,皆探得屈子放逐流离之深旨,屡言风波漂荡之间的“无所归止”“何所归而何所往”,都准确地抓住了那种置身茫茫江湖而无处归趋、无所止泊的羁旅心态,且又以风景之殊作为远离“故都平乐之风土”的反衬媒介,将陌生的异域之感化为异己的山水形质,因而此时的自然尚未能直接作为家园感的情感形式。汪瑗又评曰:“尝谓此文似一篇游山之记,盖有得乎《禹贡》纪事之法,但脱胎换骨,极为妙手,非后世规规模拟者比也。……今瑗所注者,特按文画图,以意推测而言之,未知其果是否也。尝欲裹粻,直至郢都遵江夏以遨游而遍历其地,亲访遗迹,则此文之妙,当有出于想象之外者矣。”[6](177)实际上,《楚辞》中的自然大体是幻想性强于现实性的,常在客观自然的基础上加以主观情感的点染改造,甚至阑入驰骋浪漫想象的梦幻神仙世界,用以寄托在此世无所容无所归的精神,这样依于山水的羁旅浪游往往引向通过幻想的天宇神游,“物的自然变为幻想的自然”[5](47)。如《远游》“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将化解价值困境寄于超现实的神游解脱,幻想离开此世而进入到一个无限、永恒的空间,这与羁旅山水在自然的感觉世界里执守现实的态度不同,实为求索精神家园的另一路向。钱锺书先生指出:“《楚辞》始解以数物合布局面,类画家所谓结构、位置者,更上一关,由状物进而写景。”[7]尽管此时山水自然尚远未能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在诗文中,但诗、骚(尤其是屈骚品格的楚调山水)无疑构成了后世羁旅纪行诗文的久远的精神源头。
二、贤人失志与汉代纪行赋
受天人感应思维模式的影响,汉人眼中的自然蒙上了附会阴阳灾异、牵合政治人事的神秘面纱,先秦以来人与自然的亲合关系变得僵化,导致汉代自然观在一定程度上的倒退。但自然观呈现于文学上的主要形式——汉赋,则在自然景物描写的分量、技巧和气势上仍有巨大进步,在骚体赋向汉大赋发展的过程中,赋体踵事增华、铺陈堆砌的特征逐渐定型,通过对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夸饰陈列,展示出汉人“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雄心伟力。汉赋集中展现了汉人对理性精神的审美把握并形之于独特的审美形态[8],对自然美感写物图貌的认识和表现是中国人自然审美意识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点在纪行赋中尤为明显。纪行赋通过叙写行程来串接观览风土、吊古评史和描写风景,转变大赋中空间方位的辐射视角,抛开主客问答的落笔套路,远离献赋君王、润色鸿业、表彰隆盛的宫廷化趣味等,而以行踪游移为构思线索,以内心自白直陈胸臆为表达方式,加重了个体经验的介入和抒情言志的艺术感染力。纪行赋的创作动机,大抵是“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汉书·艺文志》),是因价值追求受阻而陷入困境体验,因此纪行赋中的自然风景就不再像大赋中那样,仅作为宫室苑囿之间的点缀摆设,或者是巨细靡遗、整然成序的排队罗列,“虽纷披繁密而生意索然”[9];而是作为赋的有机部分为纪行述志的主题服务的:
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兮,沙埃起之杳冥。回风育其飘忽兮,回颭颭之泠泠。薄涸冻之凝滞兮,茀溪谷之清凉。漂积雪之皑皑兮,涉凝露之降霜。扬雹霰之复陆兮,慨原泉之凌阴。激流澌之漻泪兮,窥九渊之潜淋。飒凄怆以惨怛兮,慽风漻以冽寒。兽望浪以穴窜兮,鸟胁翼之浚浚。山萧瑟以鹍鸣兮,树木坏而哇吟[10](232)。(刘歆《遂初赋》)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10](255)。(班彪《北征赋》)
刘歆因在朝受到排挤而外贬五原太守,“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议论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文选》李善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11],催逼行旅的外力因素虽各有异,但都将人抛入无所援助的困境体验中则是一致的,赋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的特性尤其适宜对困境体验作详尽地铺陈渲染,极尽文辞安排之能事。纪行赋对“游子悲故乡”主题的反复书写,仍沿袭着《楚辞》的声调口吻和情感旋律,不过更加据景写实,少了遨游天地的幻想,更注意从耳目身观的行旅感觉来描摹荒野萧条、陵谷盘纡、风霜憭慄、鸟兽窜伏的具体情境,以刻画行旅的艰辛和漂泊的痛苦,景物描写所渲染的行旅氛围与悲凉凄伤、激烈沉痛的主体情思也相得益彰,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着意突出自然苦寒险阻的性质表明时人仍将它作为家园安顿的对立面来处理,同时感情基调也是沿屈骚一脉而来的“凄怆以惨怛”“怆悢以伤怀”,几乎构成了后世纪行赋的固定模式。如蔡邕《述行赋》:“山风泊以飙涌兮,气懆懆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渐唐。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隤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曀曀而不阳。”[10](567)摹仿《遂初赋》的迹象便很明显,连有感于宦官专权、朝政腐败而“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的撰作动机也都相仿。主题的因袭意味着背后承担着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诉求,即羁旅带来的生命流离之苦和家园失落之悲,因此需要有特定的形式加以宣泄,文学传统的确立就是在形式的因循中又有文化心理的承传,围绕此轴心而复中求变。汉代纪行赋在总体上反映的是士人对政治本体的归趋与认同,由于这一认同的过程受到梗阻,因外力不可抗拒的因素而行旅漂泊,所以在纪行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朝其复归的价值指向;潜含的政治郁结与浓重的忧患意识使行旅者尚无法对旅途风景作细致的赏玩品味,只有暂时抛离了现实的利害关系,进入到一种全无功利目的的审美状态,山水自然才能成为诗人自觉的审美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以张衡《归田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开始对隐居生活中的山水情致予以赞美和向往。《归田赋》首陈“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的遁世之意,接着描绘“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的闲居之乐[12],在这里,“居”的安顿意味与优美的田园景致、清新明亮的山水风光结合,这恰与羁旅中的身心拘役、倦游疲累以及灰冷色调的景物描写形成鲜明对比。仲长统“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帀,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居处美愿[13],又何尝不是流离颠沛的行旅者的一致向往呢?山水要真正成为温暖家园的直接显现形式,就必须经过从羁旅苦叹到停驻乐赏的“游”的转换,这在自然审美意识日渐觉醒的魏晋时期越来越成为主潮,《归田赋》即透露出些许消息。
三、羁旅游览与魏晋纪行赋
建安以来,文人纪行赋主要反映了战乱流离与从军纪行等现实内容。前者如王粲《登楼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起,以“遭纷浊而迁逝”转,以“惧匏瓜之徒悬”结[14](104),三段式的结构清晰地展现了身逢乱世遥瞻故土的流离之悲,以及有志于用世而壮怀难伸的失意之叹,再一次强化了屈骚以来游走于家国之间、行役奔走和负志不遇相糅的悲剧主题;后者如阮瑀《纪征赋》、徐幹《序征赋》、繁钦《述征赋》《述行赋》、杨修《出征赋》、应玚《撰征赋》《西征赋》等,集中展现士人为谋求建功立业而随军出征的闻见感受。这些赋作延续了纪行赋的创作模式,但开始有大段铺陈的自然风景和繁复的描写技巧,或以衬托军容肃整和军威显赫,或是展现军旅征伐的艰辛,如王粲《浮淮赋》:“从王师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兮,望马邱之高澨。泛洪橹于中潮兮,飞轻舟乎滨济。建众樯以成林兮,譬无山之树艺。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濑潭渨,滂沛汹溶。钲鼓若雷,旌麾翳日。”[14](99)三曹父子同题的《沧海赋》《济川赋》《临涡赋》《登城赋》《述征赋》等,虽或有遗佚,但从标题可看出片段化、背景式的景物描写逐渐发展为全幅整体性的自然赋咏,显示着赋家穷形写物的兴趣转向;并且随着贵族文士宴集群游风气的流行,也开始有曹植《节游赋》“浮素盖,御骅骝,命友生,携同俦。诵风人之所欢,遂驾言而出游”这样纯粹的游览赋出现[15]。群游乐赏的风尚与魏晋以来自然审美意识的自觉相交汇,最终促成了“以山水描写为目的”的山水赋在东晋正式出场[16],这条线索与山水诗的孕育诞生是相呼应的,反映出时代审美思潮对于自然美的关注愈趋浓厚。
然而以纯粹审美态度进行山水描写的山水赋,其发生线索仍是曲折隐晦的,在支撑山水游览的外部物质基础、审美主体的内在建构等条件完全成熟以前,山水赋的产生仍不得不依附在纪行赋的传统抒写格局里,因为这种摆脱身心羁绊、追求愉情悦志的“神游”,有时也必须以背负世务目的、依托山程水驿的“身游”为导引和载体。胪列晋代以来的纪行赋,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因循传统结构模式外,又大幅提高了山水物色的篇幅比例和描写技巧,对山水美感的体察和感受愈趋自觉而细腻,行旅漂泊的楚调悲吟也逐渐转变为特定羁旅情境中的山水乐赏,显示出向山水赋的潜移嬗变。如傅玄《叙行赋》、潘岳《西征赋》、潘尼《西道赋》、陆机《怀土赋》《思归赋》、陆云《南征赋》、张协《登北芒赋》、胡济《瀍谷赋》、江统《徂淮赋》《函谷关赋》、郭璞《流寓赋》《登百尺高楼赋》、曹摅《述志赋》、袁宏《北征赋》等,大体都沿着传统主题进行开掘,以印证和维系着这种恒久萦绕于士人心头的羁旅情结。所不同的是,自然描写的层次感增强了,技巧手法更趋精致娴熟,山水的形貌特征和细节生动突出了,尽管仍依循着羁旅的流动视角而出现,但不再是行役中耳目身观的背景,而愈益成为可供游赏玩味的独立对象;不再作为外部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总凸显出凄风寒雨式的阴冷色调,而是开始给人以明快愉悦的精神抚慰。
不妨对比一下陆机《行思赋》、潘岳《登虎牢山赋》和张载《叙行赋》。陆赋是正宗的纪行赋格调,随行踪变换而连缀旅途风景,逗引出浓郁的悲秋之情,又以山鸟归林反衬宦游在外的乡关之思。就景物因素而言,仍是楚调山水与汉代纪行赋的延续,但突出了“感物”的心理活动,正如其《思归赋》所云:“岁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风霏霏而入室,响泠泠而愁予。既遨游乎川沚,亦改驾乎山林。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深。”[17](306)感物以兴思起情的美感经验无疑得到加强,使旅途山水与羁旅情思进一步交融。潘赋仍有故乡辽隔、归思纡轸的惯有悲感,但开始舍弃了屈赋那种夸张浓烈的感情宣泄,而显得较为克制,景物所带的主观情绪也较为缓和,“仰荫嘉木”以下数句,风景的舒畅怡人化解了羁旅中自然意象过于郁结凝重的紧张情绪,使传统的登山临水式的羁愁旅恨得到淡化,反映出景物性质的转变。张赋笔墨落在剑阁蜀道的真切描绘上,崖壁峻险、峰峦峥嵘、林木幽深、浮云缭绕,给人以惊荡心魂之感,以前行客是无心欣赏风景的,这里则点明一个“玩”字,随行踪移动而详描细写,羁愁反倒成为陪衬,反映出时人山水自然美观念的转变。到东晋袁宏《东征赋》:“即云似岭,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云霓生于浪间。嗟我行之弥留,跨晦朔之倏忽。风褰林而萧瑟,云出山而蓬勃。”[10](413)则几乎全以山水描绘为重心,不但笔调轻灵流畅,已不似前人的阴沉涩重,且以白描写山水,声色形貌都能毕现于目前,显示出东晋士人在山水美感的表现方面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创作经验了。这一潜在的变化反映出东晋以来日益成熟的山水审美意识对辞赋创作的影响,玄学审美精神对主体人格的本体追求、老庄逍遥之旨注重在自然山水间的虚静领悟、清谈风流雅重对自然之美遗貌取神的片言赏味、山林嘉遁之志促使士人乐于深入山水体玄识远等,都共同塑造了一个自内在觉醒了的审美主体,从而才能自觉发现山水之美并形之于艺术创造,山水从单纯的客体转而与人的生命情调发生密切的联系。羁旅纪行本是因现实世务的逼迫而无奈地奔波于旅途之中,山水往往显示着与家园疏离对立的负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懂得主动发现山水之美的审美主体的成立,羁旅与游览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旅”的实践活动最终促成了“游”的审美体验,山水就成为体验家园的亲和形态而吸引诗人到山水中去适性畅神、体玄悟理,获得审美意义或哲学解悟上的精神安顿,到南朝如谢灵运《归涂赋》、鲍照《游思赋》、谢朓《临楚江赋》、沈约《愍途赋》等,“羁旅山水”的传统已大致定型下来。
四、余论
总结来说,纪行赋因内容题材的限定性和情感抒发的独特性,决定了在传统主题的重复创作下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特别就山水物色的描绘而言,纯粹的山水赋以表现山水美或体任自然的玄意感受为中心主题,如木华《海赋》、郭璞《江赋》、庾阐《涉江赋》、孙绰《游天台山赋》、顾恺之《观涛赋》等都能毫无现实牵绊而沉浸于山水之美中纵意神游、潇洒超脱;纪行赋则必须限定在羁旅行程的价值链条中,为山川阻隔、故乡邈远的漂泊苦况服务,为家国两失、无处安顿的价值困境服务,因而自然景物蒙上了负面消极的色彩,具有置身异域、悖离家园的情感指向。羁旅行役总是不自由的,解脱的渴望无时不在,山水或加剧着这种不可解脱的痛苦,就化为自屈子以来的羁旅悲音和楚调山水。然而,自然又具有转移、化解、安慰悲情的作用,尤其是人的自然审美意识觉醒、自然美感逐渐被发掘而呈现出来以后,山水对于士人精神世界的补偿意义和价值确证就开始突出了。山水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澄净的审美空间,使人在此涤荡凡俗、洞见真我,与自然宇宙冥合感通,旅人游于其间也能暂时忘却羁旅烦忧,感受家园安慰,中国人对山水的钟爱渴恋,实包涵有以自然宇宙为最终精神归宿的深刻民族心理在内。我们通常以行旅为山水诗发源萌芽的一种助力,归因于行旅流动使人获得了与山水足履身接、深入赏会的外在机缘恐怕失之肤浅,深层的原因应是羁旅漂泊的切身体验在山水之美中获得了生命的交流、回应和反馈,由此产生家园安顿的精神需要。因山水而获得生命止泊的精神感动,与因生命漂泊而发现了山水之于人生安顿的文化意义,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在山水审美意识萌发并呈现为艺术形式之前,山水所附带的比德内容或神灵色彩往往遮蔽了山水美对于塑造心灵、提供精神归宿的潜在作用;当时代思潮与构成山水审美的主客观历史条件成熟后,自然作为人的精神安顿之家这一深层文化心理,才真正落实在具体的山水审美活动中,也才能渗入到羁旅行役的具体情境中,上述二者的交融促生便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了。纪行赋中的自然山水,便不再只有渲染漂泊的意义,而同时具有提供安顿的意义,赋体的铺排空间有利于以更多篇幅锤炼山水描写的技巧,为山水诗的正式出场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
了解以上这层关系,方可理解大谢山水的时代意义,它正是纪行赋向山水赋蜕变的合题收束。谢灵运对山水的发现、欣赏与创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羁旅人生的机缘:因政治失意外放永嘉,价值追求的受挫使其一腔怨愤之气尽情发泄在旅途的山水之中,由此发现了一个不必在政治体系内寻求认可、而在荒僻山水之间获得自我确证的审美新天地,从而才有其游屐踏遍永嘉、会稽的山水游览人生,可以说大谢极好地完成了从“旅”到“游”的审美心理转换,才促成了山水诗蔚为大观的诗坛局面。辞永嘉太守返故乡始宁时所作《归涂赋》序云: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徙,或述职邦邑,或羁旅戎阵。事由于外,兴不自已。虽高才可推,求怀未惬。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泽,经涂履运,用感其心[18](222)。
这里所述说的种种不自由的人生样态,都是羁旅纪行赋中所常见的,皆缘于“事由于外,兴不自已”,因此文化心理中那深藏的对精神家园的不懈求索,就在“经涂履运”之间有所感发,形诸山水。赋中说:“舟人告办,伫楫在川。观鸟候风,望景测圆。背海向溪,乘潮傍山。凄凄送归,愍愍告旋。”以极富行旅痕迹的笔调诉说身在旅途、深入山水的因由;然后就是“舍阴漠之旧浦,去阳景之芳蕤。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发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诡状,山侧背而异形”的山水描写,有了审美心境的沉入。他的山水诗也基本遵循着这种赋体格式,起首总要交待羁旅行程或陈述山水游览的因由,铺开一层情感郁愤的基调,然后才是深入山水之间观览顾盼、仰观俯察,以赋体的铺陈手法工笔刻画出山水形貌的美感特质,在此过程中家园失落感在山水审美的净化中消释淡化了,代之以停留在“迥秀之句”中的精神愉悦。如《登上戍石鼓山》:
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汩汩莫与娱,发春托登蹑。欢愿既无并,戚虑庶有协。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苕,绿苹齐初叶。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燮。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惬
联系汉晋以来的纪行赋传统,大谢山水诗中的精神线索规规可循,贯穿在这种文体承袭嬗变间的红线,不仅是羁旅、山水等显而易见的内容题材的延续模写,更有对士人羁旅情结中的家园体验这一深层文化意识的反复吟味和体认。须知家园感的获得需要诗人为之付出不懈的践行和努力,它在特定的审美情境中以山水意象呈现出来,最后积淀为心灵的成长丰富和人格境界的提升,就是在这一提升的过程中才给予人以生命安顿的满足和人生的自我超越。要指出的是,大谢诗中以山水作为家园的直接显现形式还未能纯熟,原因在于他不能真正安于在山水审美境界中获得安顿,而总是顾念着现实的政治利害,有难以泯除的士族傲气,往往需要借助于玄佛义理的理性化遣来获得暂时的平静,以致他出处反复,在山水与廊庙之间挣扎往返,始终未能找到价值安顿的定位,最后以悲剧收场。经过南朝诗人洗汰玄理的情感提炼,山水始展现出清新自然、情景交融的美感形象,在唐诗中家园感与山水意象则已融浃无痕,成为中国人山水美感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了。
附带提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篇赋是离职彭泽县令而归家之作,从精神指向上看,它与纪行赋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离家向外寻找价值,结果寻觅不得而戚戚哀叹;前者则是舍弃外向仕宦的政治追求,反以回归田园、躬耕自足为精神的安顿之处,其中的深刻文化意味不能仅以远离官场、洁身归隐来限定。赋前小序交代了“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的出仕因由,实际上这也是广大士人为口腹生存、建功用世而自觉踏上羁旅行役之途的普遍缘由。但陶很快以“世与我而相违”“以心为形役”放弃了这一由家到国的传统价值建构之路,陷入了游于家国之间的价值困境(陶任职军幕期间所作纪行诗即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困境体验)。他的解脱途径不是继续执著羁旅之游,而是以田园生活为基点作审美之游,完成自我的精神超越。赋中洋溢着的欣喜恬然之情,与朴素明净的田园风光的自然之美,都与前引纪行赋的悲怨情调形成鲜明对比。田园在陶渊明这里被赋予了更坚实、更广大的文化意义,与主体的性情人格交融浑化,其诗文所营构的陶式的田园境界,也成为晋宋之际士人在自然中体验家园感的一种特异的审美范式,这也是自然(山水物色)的两种分化形态——山水与田园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蕴的内在根由[19]。联系前面提及的张衡《归田赋》,则士人矫正“旅”的价值追求所带来的漂泊悲情,转而以隐处田园来获得“居”的家园感受,这条暗脉真正在陶渊明的人生实践中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田园与山水所代表的两种歧异的人生形态,在唐人那里方才合流融一,而唐诗的山水美也显示出一种进取轩冕之志与泛咏皋壤之趣并行不悖的从容裕如,这与唐代政治本体化高度成熟下士人家国价值建构链条的顺畅调整是深有关联的,关于这一点,当另文申论。
[1] (梁)萧统编, (唐)李善等注. 六臣注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85-187.
[2] 程磊. 羁旅山水与家园体验——论羁旅行役诗中家园感呈现的意象形态研究之一[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1): 45-53.
[3] 王国璎. 中国山水诗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6.
[4] (宋)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30.
[5] [德]顾彬(W. Kubin). 中国文人的自然观[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6] (明)汪瑗. 楚辞集解[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7] 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613.
[8] 冷成金. 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63.
[9] (清)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98.
[10] 费振刚, 等. 全汉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1] (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425.
[12] 张震泽. 张衡诗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43-245.
[13]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644.
[14] 俞绍初. 建安七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5] 赵幼文. 曹植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83.
[16] 程章灿. 魏晋南北朝赋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138.
[17] 韩格平, 等. 全魏晋赋校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18] 李运富. 谢灵运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19] 程磊. “家园体验”与陶谢田园山水诗的文化差异[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5): 169-175.
Home experiences and the imagery embodiment of landscape in Jixing Fu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CHENG L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value dilemma in business trip triggering a spirit need for home experience, landscape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compensate the lost home becomes a typical modality to show the process of how travelers seek spirit hom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germination of landscape aesthetic activities in business trip. The imagery embodiment of landscape in Jixing Fu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following the model of Chu Ci and evolves into landscape Fu, shows a converting from contrast to affiliation about home experiences. The change of writing style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wave of landscape aesthetic activities in Six Dynasties. It is also an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o Yuan-ming’s pastoral poems and those of Xie Ling-yun’s.
home experiences; jixingFu; poetry image of landscape
I222.4
A
1672-3104(2014)06-0271-06
[编辑: 胡兴华]
2014-05-11;
2014-09-10
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51006)
程磊(1985-),男,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