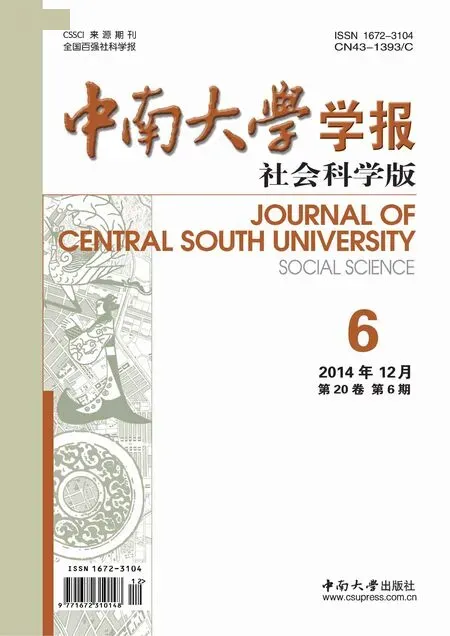流散作家哈金的中国想象
欧阳婷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流散作家哈金的中国想象
欧阳婷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作为在中国长大,后落户美国的流散作家哈金,当面临两栖身份的文化矛盾时,他选择用“他者”的眼光看待和想象心目中的中国,用自己的童年记忆来代替集体无意识,并基于这样的立场来表达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民族根基感,以求找到精神归宿,实现个人价值。哈金的“中国想象”具有人文体验性、艺术创造性等特点;但同时亦存在个人想象与集体记忆的落差、流散身份与本土生活的隔膜和外文写作之于他国读者期待视野的迎合与误读等局限。
哈金;流散作家;文化两栖;他者;中国想象
“流散”一词来自英语“Diaspora”,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最初是专指犹太人的移民和散居现象,后来逐步用来泛指所有的移民族群。随着世界移民潮的出现,那些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的作家或文化人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他们即被称之为“流散作家”。流散作家的创作往往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们既可以用“他者”的眼光审视本土文化,同时又可以鲜明的民族特征跻身于世界文学大潮;既长于表达漂泊游子对故国的眷念,又能够用“局外人”的立场抒写异域风光,或反思文化落差中的烦恼和困惑,因而,他们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创作风景。美国华裔流散作家哈金就是他们中较有成就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一、文化“两栖人”的流散书写
哈金自幼在中国接受传统教育,上世纪80年代随留学大潮到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哈金的母语是中文却一直坚持用所在国语言(英语)创作,进入美国文坛短短几年时间就连续获得多项美国文学大奖①,这几乎算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作为文化的“两栖人”,哈金远离故国,散居海外,处于多重身份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不论在地理空间还是文化空间都处于族裔母体文化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在居住国的主流文化中,他又总是处于外来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地位。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夹在两个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经验到了两种在某种意义上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个或与之达成较深刻的和谐。”[1](101)面临这种两栖身份的文化矛盾,哈金选择用文学书写来表达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根基感,以求找到精神归宿,寻求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在竞争激烈的美国文坛求得生存。因而在谈及为何用英文写作时,哈金曾说:“我是移民,用所在国的语言写作理所当然。大家都是为了生存,都写得很艰难,不容易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但正因为难,才有人来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能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最难的。”[2](42)
对于在中国长大,然后落户美国的哈金而言,即便改变了固有的身份(国籍或成为“绿卡族”),但文化上的无所归依和异质文化的疏离感受是一直存在的,而这种边缘人心态,隐含着巨大的酸楚和疼痛。无论怎样费尽心力去贴近和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他对于家国故园的记忆和文化身份的归宗,依然潜伏在灵魂深处,这也是足以激发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哈金在接受访谈中曾坦陈:“在美国生活下来,并不是太难,但是如何使存在有意义,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了。对于我来说,证明自我存在的独木桥,就是写作。”[3](85)曾经的中国经历和文化体验成为他进入异国他乡的人生背景和重新出发的重要基础,不仅见证了他的文化身份,更是他打入美国文坛的重要文化资源。纵观哈金的作品,在近20年创作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描写发生在中国平凡小人物身上的故事。通过作者对中国故事的娓娓道来,展示了繁复的细节,并让西方读者感受到完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经验。如哈金代表作《等待》里孔林、淑玉和曼娜的三角恋爱关系中没有扣人心弦的爱情,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却以一种平实、缓慢的笔调诠释了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失望。他的长篇小说《池塘》中国营工厂的工人邵斌为了抗议厂长和书记对自己的不公正待遇而奋起反击,用绘画和书法做武器不断画讽刺漫画寄给北京的报纸,为自己谋取正当利益。但作为普通人,他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在“丰收化肥厂”这个小池塘里,他也只是一条小鱼。即便跳出这个“池塘”,也只能在另一个“池塘”里获得有限的自由。再如哈金2011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把笔触投向中国南京,记录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件。整本书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4](2)。
中国成长和美国生存的双重人生体验,在哈金那里形成了一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包容、既互相对峙又互相解读的矛盾统一体。这种两栖身份的文化矛盾促使他试图用英文的思维描写最传统、最正宗的中国故事,并以此来摆脱“夹缝式”的文化身份困惑,找回自己的精神自信。而不同于其他华裔作家以往塑造的内在坚忍和顽强的中国人的群像,哈金非常智慧地利用两栖文化身份优势,用质朴的英文描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中国乡村小人物的故事,其所体现出来的主人公在特殊历史时期或顽强或消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各种权力欲望、人性悖谬、伦理错乱等生存处境的描述,形成了独特的交叉式文化视野,并显示出流散书写的文学张力效应。
二、“他者化”的中国想象
海外流散作家往往是带着双重生存经验而形成的文化身份来进行文学创作,这是文化劣势,却也是他们独具的创作优势。作为少数族裔,尽管在所在国主流文化面前时常处于边缘性的尴尬地位,但这种尴尬对于哈金而言,是一种洒脱,更是一种自在,一种张力。正是这种“夹缝人”的生活,使哈金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历,通过这种对比和反思,往往更能深刻体验到故国经验和异国生活对其创作心境、创作灵感潜在或显在的影响,使他可以不必拘泥于某种政治形势而用“他者”的眼光看待和想象他心目中的祖国,自由逍遥地抒写和表达内心的家园情结,尽管此时的家园已经不再是那个原生本真的“家园”,而是浸染了异域生活痕迹和文化色彩的“他者化”的家园,但对作家而言,这样的家园依然是值得去真诚书写的心灵寄托。这里有两种表现形态:
一是以“他者化”想象去表现家园情结。不同于上世纪50~60年代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人的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和浓烈的寻根意识,哈金作品建构的文本话语,因其与故土的“熟悉”与“隔膜”,包含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作家对不同生活的本质性审视和文化解读,促使他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差异中,表达出属于他的“他者化”想象的家园情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他认为这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5](16)。哈金笔下的中国想象一方面意在探寻不同文化之间的兼容并蓄,以此调适自身,学会适应美国的图书市场求得自身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企冀在坚守中向往灵魂栖居之所和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其结果是洞开了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这种带有更多思考的认知和表达,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重审式”的流散书写和“他者”表达,以此展现出一个更具世界性视野的艺术世界。如在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里,哈金通过十二篇故事描写了文革前后一个叫歇马亭(Dismount Fort)小镇上老百姓的生活,他让“有些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重复出现,整本书构成了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6](6),展现出的血腥残酷和温情感伤、滑稽戏谑与虚伪做作,构成了一个个意蕴丰富的集合体,展示出一副充满中国乡村风情的画卷。第一篇《光天化日》(In Broad Daylight)以一个孩子的视角书写了文革年代,貌美的穆英因通奸而挨批斗的悲惨故事,从不同层面平实地刻画了老百姓传统积淀的心理和心灵世界:乡村男女老少对暴力的狂热,处处可见的国民劣根性,对现实处境的无奈屈从以及对美好生活无法压抑的渴望;另一篇小说《主权》(Sovereignty)出自哈金读到的一个小小的法律公案,即两家的种猪互斗,一方的种猪咬伤了对方孩子的事件。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将其扩充为极富原始乡村色彩的暴力美学篇章,惊心动魄的斗猪场面描写使乡间民趣也随之跃然纸上,整篇故事短小精悍,极具海明威的风采。此外还有《最阔的人》(The Richest Man)里,写主人公李万在“文革”之前的节俭、小气、吝啬的性格和超出一般人水平的富裕,引起周围人的眼红和诅咒,就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极好展示。哈金在整部小说集里一直以旁观者的角度,用冷静的笔调,对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细致地描摹和刻画了乱世中的各色人物的生存现实,同时又是蕴含了“他者化”评判的中国想象和故国家园。
二是精神家园的重构。哈金在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中认为“家”除了带给人美好的记忆之外,还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走到哪,背到哪。因而,天涯游子的精神家园不仅需要寻找,需要表现,更需要建设和重构。他说:“许多流亡者、流散者、移民和被政府驱逐出境的人都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有朝一日回到自己的故里。思乡之情使他失去了生活的方向,而使得他无法在任何地方扎根;错置感毁了他们的现在和未来,离开自己的家给予他们的是无尽的痛苦。”[7](63)由此可见,作为流散作家,如何建设乃至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萨义德认为,放逐或流亡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涯的一种必要而且必然的状态,放逐状态固然有着诸多的艰辛与痛苦,却自有其独特之处,即处于局外或边缘,拥有“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反而可以摆脱主流文化的控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思考的精神[8](54)。哈金的小说创作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的双重生存经验和双重文化视野带来两大挑战:一方面是其早年在国内成长的经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意识已内化成一种精神觉醒;另一方面是他在异国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诘问。这样的“双重视角”会有意无意地影响他的创作,并由此而引发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思考方式,这便有了“重构家园”的可能。在创作中,哈金往往是用跨文化的眼光去观照和检视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普通人的故事,用敏锐的触须隐约传达出历史的沉重感和纵深感,并善于把中华民族传统的内容和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技巧融合起来,凝聚成具有鲜明美学特征和文化价值的书写,他的精神家园就是这样重构出来的。比如哈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集《新郎》(The Bridegroom),以作者虚构的木基市(Muji City)作为背景,有意展现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对某些新事物的态度,或者对一些旧事物的新反应。与集子同名的小说《新郎》,形象地展示了“同性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武松难寻》(A Tiger Fighter Hard to Find)则展现了建国后全社会弥漫着无处不在的英雄崇拜情绪,这样的家园书写就是作者在流散心态下“重构”出来的。
在哈金的笔下,作为精神家园的中国的生活风物和文化底色被不断解构和重建,成为文化双栖的“他者”实施中国想象的特殊的文本,这种跨地域、跨语境、跨时空的话语空间是家园之外的中国书写,是在异质土壤的故国之思,其所蕴含的能“入”而又能“出”的文化认同,让哈金的精神家园的艺术重构过程不时闪耀着锐利的批判锋芒和思想的火花。这也验证了哈金在《移民作家》的结尾提出的观点:“家(祖国)更意味着到达,而不是回归。”他强调“传统意义上家的双重含义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Homeland一词离不开home,而这个家作为移民应该在自己的故土以外构建,因此,祖国就存在于你构建的家园之中。”[6](84)
三、“中国想象”的价值和局限
作为母语非英语的流散作家,哈金的作品能屡获美国主流文学大奖,除了其独特的表达视角和语言风格外,其作品里浓郁的“中国想象”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其他海外伤痕文学、海外文革小说的家族式书写或自传式书写的写作方式,哈金的文革小说并没有着力突出“文革”本身,而是凭借灵敏的文学感悟力,并从不同层面刻画了老百姓传统积淀的心理和心灵世界,拓展出富有个性化的审美表现形态,为我们打造出另一种新的语言叙事空间,在人文体验性、艺术创造性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如小说《辞海》(Ocean of Words:Stories),全书用十二则小故事描述军营的众生相,从不同侧面展现军人的生活:《空恋》讲述了无线排接线员们借助空中电台与女兵谈了一场柏拉图式的虚无恋爱的故事,主题涉及两性之间的恋爱心理;《党课》则讲述了两个指导员司马林和裴连长之间的互相戒备,他们双方都想找机会抓对方的“小辫子”以维护自身利益,得到上级的赏识,小说形象地说明阶级友爱的温情面纱下隐藏着人性的自私和卑劣。在哈金的笔下,青春的骚动、无望的爱情、性的压抑、集体性的谎言以及阶级情感掩盖下的妒嫉、排斥和倾轧等,均活灵活现并触目惊心。他通过描摹和刻画笔下人物的生存现实,以逼近生活的真实,既表现了政治教条和道德训诫下隐藏的人性之恶,也展现了人性中尚未泯灭的善良、纯朴和美好的感情。虽然故事中的时代背景相对比较模糊,但仍能看出“文革”这个怪兽的狰狞面孔潜在地威慑着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乃至左右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升降浮沉和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这本获得“海明威基金会小说处女奖”的小说正如评审所说的那样:“本书(《辞海》)最优秀的故事在苦难中宣泄欢悦,回响着讽喻。这种讽喻将人物和读者拉近,并淡远了他们的严酷世界。”②出于种种原因,其他海外作家在作品中很少暴露底层民众身上的弱点抑或丑恶,而哈金却始终关注并挖掘潜藏在普通人行为、思想和心灵中的国民劣根性,用带有纪实性的书写方式和融入自身的生命体验,营造出寓意深邃的文本结构,这是对一种特定背景下生命过程的反思和批判,而反思的视角和批判的锋芒是中国的、家园的,却又是异域性的、他者想象的,是空间距离感和主体他者化折射下的家园书写,这正是他作品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这种生存境遇、个体生命、双重视野等多种元素所构成的文化策略,乃是民族自省和历史反思的双重展示。从这个角度说,哈金作品的流散书写显示出其在整个移民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此外,异域生活和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和交融,让哈金融入自身生命体验的“中国想象”凸显出另一种不同的品格,即哈金以及他的作品除了对萦绕于个体生命中民族文化情结的眷恋外,更以纯粹的主体生命立场去寻求自身文化的闪光点,继而清醒而透彻地重审自身的传统文化。他的文本中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展开的深入思考,重新赋予了文学以人文关怀的深度模式,满足了人类普遍需求的期待视野,显示出独具特色的张力效应。这反映在文学母题上,则是饱含文化精神的再现和重构,把中国人的个体遭遇提升到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用文学性的语言和手法表现作品思想内容的广泛性和兼容性,在更为宽广的东西文化视野中寻找对象,以显示文化整合中的生命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哈金的“中国想象”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是个人想象与集体记忆的落差。哈金的“中国想象”通过追忆单个的、具体的人在政治的雨骤风狂摧折下的创伤性记忆与体验,用个人的“小”历史聚焦并廓清了被遮掩的国家的“大”历史。如哈金的短篇小说(集)《好兵》《光天化日:乡村的故事》以及长篇小说《等待》等获得美国文学大奖的作品都书写了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特殊背景下的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他是用自己曾经的记忆来代替集体无意识,基于这样的立场来表现记忆中的中国,展现出了一幅或残酷、或温馨、或荒唐、或无奈、或痛苦、或阴暗、或猥琐的人世图景,而这幅想象性的图景是有选择性的,也是与实际的历史经验有落差的。
其次,是流散体验与本土生活的隔膜。在这方面,刘登翰描述“台湾文群”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的两轴性放在哈金身上仍然有效,“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9]作为新一代流散作家,哈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苦苦寻求着自己的精神基点,这种寻求异常艰辛。他可以熟练地运用外国语言写作,却很难轻易获得外国人的价值立场。即使终于获得了他国的自觉意识,也很难用这样的意识来反观中国。因为身处异国,脱离了国内生活每天压在肩头的真实的重量,脱离了本土生存群体心心相印、生死相依的精神寄托,很容易“两不着边”,既难以获得异质文化的意识来梳理自己的中国记忆,又无法从本土当下的生活和不管怎样总算挣扎于其中的本土知识分子的精神中汲取同情的力量。对外既隔膜,对内亦脱节,因此不管在文学描写技术上有何种突破,在文学的真正内核——自我意识的建构上——却很容易“缺氧”。因而虽然他的作品表现出底层中国人的善良、忍耐和卑微,对生活的盼望,常常被捉弄的可怜的爱情,以及出奇的愚昧、迷信和残忍,但除了哈金特有的稳健、简洁和清晰的笔法外,他开掘这些主题时所达到的深度远在写同类题材的余华、苏童等国内作家之下。无论对中国当代生活的体验还是“笔法”本身,哈金如果脱下“美国货”(英文写作和美国作家班的笔法)的外壳而与国内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比较的话,并无优势可言。
最后,是外文写作之于他国读者期待视野的迎合与误读。哈金除了将文化回归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心理外,小说采取的英文写作策略也特别注意迎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如在《等待》中饱受争议的小脚,美国评论家Dan Schneid在评论这部作品时曾尖刻地说,小说最大的卖点是异国 (exoticism),是所谓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即政治正确)让哈金获得评委青睐,“美国国家图书奖”是为了照顾少数族裔才颁奖给他[10]。虽然说法偏激,但也不无道理。从美国出版的《等待》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中也可看出端倪:鲜艳的中国红做底,暗含了西方人一贯对“红色中国”的解读,居中那条垂下来的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这反映出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文化误读和先期预判。这实际上是将身处弱势文化的“我们”被强势者——“他们”的文化预期和意识形态误读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企图通过文学书写跨越“大写的异己读者”的阻隔,客观上满足西方读者窥视“铁幕中国”的欲望[10](232)。
注释:
① 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曾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视角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PEN/Faulkner Award),打破并改写了美国畅销书市场长期由华裔女性作家占主角的历史局 面,为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华裔作家。此外,哈金创作的许多短篇故事入选美国最佳短篇故事选。他的故事集《辞海》(The Ocean of Words)于1996年获得美国笔会/海明威奖(PEN/Hemingway Award),同时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于1997年获得短篇小说弗莱尼里欧克纳奖 (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反映中国志愿军战俘的作品《战废品》(War Trash)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也为他第二次赢得了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并跻身于普利策奖的决选作品之列。
② 哈金. 好兵[M]. 扉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 2003. 此为1997年美国笔会—海明威基金会小说处女作奖评审评语。
[1] 米兰·昆德拉. 被背叛的遗嘱[M]. 余中先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3.
[2] 江迅. “谜”一样的哈金[J]. 上海采风, 2001(7): 42.
[3] 邱华栋. 哈金: 中国底片和美国景深[J]. 南方文坛, 2009(6): 85.
[4] 哈金. 南京安魂曲[M]. 季思聪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5]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6] 哈金. 光天化日[M]. 王瑞芸译. 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社, 2001.
[7] J Ha. The Writer as Migran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8] 爱德华· W·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9] 刘登翰.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M].上海三联书店, 2007.
[10] Dan Schieder, “Waiting by Ha Jin”The International Writers Magazine:Book ReviewMarch 2006.
China as imagination in diasporic writer Ha Jin’s writing
OUYANG 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s a diasporic writer of American new immigrant Chinese writers, Ha Jin chooses to regard and image China of his own expectation from the “Other” perspective when he faces with 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a sense of “dual identity”. He uses memories of childhood to replace the community unconsciousness, and relies heavily on this standpoint to express the root foundation as a typical “diasporic” intellectual, revealing desire for spiritual return to shape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value. “China as imagination” in Ha Jin’s writings on the one hand embodies som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humanity experiences and art creativities etc.; and on the other hand manifests some limitations. These issues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gap between the personal imagination and the community memory,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 diasporic identity and native life, and also his English-language texts, thus shaping by the western readers’ horizons of expecta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Ha Jin; Diasporic Writer; Dual-Cultural Identity; the other; China as Imagination
I106
A
1672-3104(2014)06-0266-05
[编辑: 胡兴华]
2014-07-25;
2014-10-28
欧阳婷(1982-),女,湖北十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博士,德国萨尔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华裔流散文学,比较文学,审美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