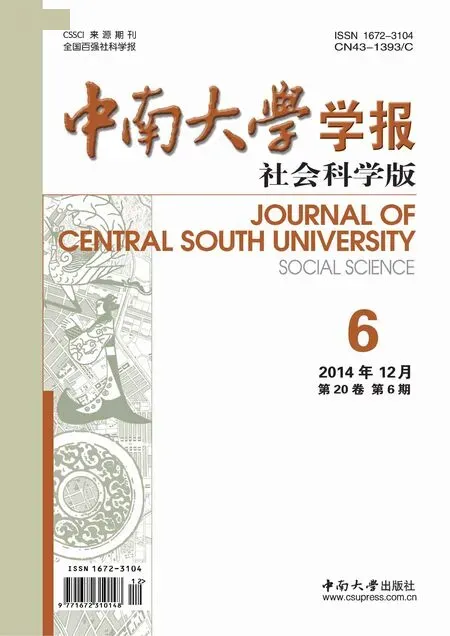论十七年时期散文的时间叙事
颜水生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论十七年时期散文的时间叙事
颜水生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十七年时期散文在时间叙事方面具有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时间的意识形态化、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化方法三个方面。在十七年散文中,时间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负载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符码;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紧密关系,遵行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把时间放置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认识,或者把时间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对比,体现出一种历史主义态度。
十七年时期;散文;时间叙事;历史化方法;时间的意识形态化
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却又是客观存在的,散文如何把握这种看似玄妙却又极其简单的时间,至今在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时间不但作为一个哲学、政治和叙事学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作为一个叙事学问题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时间修辞不但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叙事长度、结构,也决定了作品的结局和美学性质,会影响和规定一部作品是喜剧、壮剧还是悲剧”[1]。巴赫金、昆德拉等学者对小说的时间叙事作出了堪称伟大的发现,杨义和陈平原对小说的时间叙事也有独到分析,但散文不同于小说,散文研究不能照搬小说的时间叙事。马克思主义认为,“时空和人类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的时间理论才明显超越于前人的时间理论,因为他注意到了‘人’的因素,从而使时间与人类生命的价值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理论对散文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2]。本文以杨朔、秦牧、刘白羽、巴金、冰心、曹靖华、魏巍、柳青、秦兆阳等作家为例,主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理论,分析十七年时期散文的时间叙事,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化、历史决定论、历史化方法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一、意识形态化与时间叙事
在文学作品中,时间的设置都不是空洞无意义的,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蕴含了某种美学价值、历史意义或者政治内涵,因此可以说,文学中的时间都是意识形态化的。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中国”不仅体现在“空间的新”,更表现在“时间的新”,十七年文学鲜明地表现了“新中国”蕴含的丰富的时间内涵。由于散文在体裁上的特殊性,时间的意识形态化更为明显,尤其是在十七年散文中,时间承载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时间甚至成为意识形态叙述的重要载体或手段,意识形态是时间表现的内容和目的,通过时间的意识形态化从而表现了时间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时间的意识形态化成为十七年散文把握时间的基本方式。具体来说,十七年散文的时间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自然时间的现实化。时间是客观、具体的自然现象,意识形态是主观、抽象的思想,意识形态作为抽象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现实针对性,因此,时间的意识形态化首先表现为现实性,尤其是十七年散文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使时间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在十七年散文中,无论是对过去时间的回忆,还是对将来时间的想象,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种特征在刘白羽、秦牧、魏巍等作家的散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刘白羽《长江三日》,长江三日原本是客观、具体的自然时间,在这个自然时间内,作者看到了长江雄伟壮丽的景象,但自然时间并不是作者表现的重点或主题,作者赋予长江三日以意识形态内容,表现意识形态化时间的伟大与崇高,作者在文中多次情不自禁地抒发了对意识形态化时间的感慨。作者写道,“过去,多少人,从他们艰巨战斗中想望着一个美好的明天呀!而当我承受着象今天这样灿烂的阳光和清丽的景色时,我不能不意识到,今天我们整个大地,所吐露出来的那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这社会主义生活的呼吸,正是全世界上,不管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在美洲还是在非洲,一切先驱者的血液,凝聚起来,而发射出来的最自由最强大的光辉。”[3](196)这段话的时间序列是“过去——明天——今天”,作者赋予过去以“艰巨战斗”的意识形态内容,赋予明天以“美好”的意识形态内容,赋予今天以“最自由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内容,随着时间序列的不断演进,时间的意识形态内容越来越丰富,作者无论是对过去的回忆,还是对明天的想望,都是为了表现“今天”,“今天”是作者叙述时间的最终目的,作者对“过去”和“明天”的叙述都是为强化“今天”,“今天”的不断意识形态化体现了时间的现实指向性。作者又写道,“‘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3](191)“曙光就在前面”是对未来时间的想象,这段话的时间序列是,“曙光——大时代——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随着时间序列的不断演进,自然时间不断地理论化、抽象化,意识形态内容不断深化。随着时间的不断意识形态化,时间的现实性也不断增强,作者叙述时间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现实,作者通过时间的逻辑演绎,最终回到现实,得出结论“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3](191),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礼赞。十七年散文对当下时间的叙述,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如刘白羽《日出》,作者在文中写到了观看日出的具体时间——黎明,黎明在文中是一个当下时间,它是具体的,客观的,黎明在结尾部分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针对性,“这时,我深切地感到这个光彩夺目的黎明,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我忘掉了为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高兴,而喜悦,我却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我在体会着‘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一句诗那最优美、最深刻的含意”[4]。结尾部分有着较为明显的时间序列,“日出——黎明——新中国——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作者把观看日出的黎明时刻理论化和抽象化,并且赋予黎明以重要的意识形态内容,认为黎明是新中国瑰丽景象的象征。黎明在散文中是一个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时间,黎明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它既是现实的象征(新中国瑰丽的景象),又要为现实服务,作者对“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的体会充分表现了时间的现实指向性。此外,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秦牧《花城》以及巴金、冰心等作家的散文也都体现了时间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第二,自然时间的崇高化。十七年散文习惯选择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以展示人物在自然时间中的语言与行为,人物的自然时间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互结合,以自然时间表现社会意识形态的崇高与伟大(历史意义),十七年散文的命名就集中表现了这种特征,如《车间里的春天》《屋里的春天》《古战场春晓》等之类的篇名,在这些散文中,“春天”是自然时间,散文的叙事以自然时间为线索,但自然时间并不是散文表现的主题,自然时间更多的是社会意识形态时间的象征或符码,表现社会意识形态时间才是散文的创作目的。在《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通讯中,自然时间与社会意识形态时间的融合方式为当代通讯写作树立了典范,文中写道,“十月一日这一天太伟大了,太丰富了。甚至在今天,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它的余风还在。 街上还是红红绿绿的跳舞队,秧歌队,游行队。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依然满街都是红旗,都是锣鼓。……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我不能不把这个伟大的日子这样繁琐地报告你们。这是由于我无能的笔没有法子把象昨天,乃至于毛主席领导建立的国家的这十天以来的历史时间恰如其分地向你们转述。”[5]在这篇通讯中,首先, 十月一日是一个自然时间,天安门广场的群众以自己的活动实现主体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秧歌、游行、红旗、锣鼓等是他们在自然时间内的实践方式。其次,十月一日更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时间,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太伟大、太丰富”集中表现了它的历史意义,散文的创作目的也是为了表现社会意识形态时间的崇高与伟大。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最后一段也集中表现了时间的意识形态化,前部分叙述“当你……的时候”,这是一种自然时间,后一部分叙述“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时间,自然时间的平凡体现出意识形态化时间的伟大和来之不易。又如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一九五五年秋天是一个自然时间,皇甫村的村民以自己的劳作实现对自然时间的把握,然而这种自然时间仅仅是一个铺垫,柳青的目的是表现一个伟大的历史时间,正如他在文中写到:“这是一九五五年秋天中国的乡村吗?这是我住了三年的皇甫村吗?我的祖国,你不是在前进,而是在飞奔!”[6]十七年散文对新中国的歌颂大都采取了上述方式,尤其是十七年时期流行的通讯和特写等散文作品大都把自然时间崇高化,赋予时间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
可以看出,在十七年散文中,尤其是在刘白羽、秦牧、魏巍、柳青等作家的散文中,时间负载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崇高的历史价值,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符码。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是特定时代的社会观念的集合,也可以被看作是观察或解释世界的方式,“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其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8]。因此,十七年散文中时间的意识形态化,也表现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时间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十七年散文中的时间与意识形态是统一的整体。
二、历史决定论与时间叙事
时间是历史的基础,在文学作品中,时间叙事也蕴含着一定的历史观念。众所周知,进化论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历史进化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心观念之一。十七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它不仅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也受到了历史进化论的影响,表现了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总体历史观念。在历史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一种以历史决定论为中心的历史观念,这在十七年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十七年散文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打上了特定时代的烙印。与十七年小说一样,十七年散文突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综合来说,十七年散文中的历史决定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十七年散文特别强调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具体到时间范畴来说,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紧密关系,遵行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规律。秦兆阳《老羊工》、唐克新《车间里的春天》、柯蓝《新的生活在等着》等散文体现了这种历史观念。《老羊工》在叙事时间范畴体现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变化,过去—现在—未来呈现线性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过去在散文中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过去与现在和未来形成鲜明对立,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进步,未来是现在的升华和超越。老羊工对时间范畴的叙述在十七年散文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啊!世界是怎么在变化呢?……我从十三岁起开始给财主放羊。财主吃白面,我吃糠饼子。冬天,财主在屋子里烤煤火,我想凑到厨房里去暖暖身子,说我是个穷放羊的,该在羊圈里待着,不该进屋进院,用脚踢我。夏天,一连三四个月不下山,在岩洞里睡觉,胆小得一哭哭半夜;财主派人给送粮食来,自个生一顿熟一顿的作了吃;怕狼怕豹,常爬到树上去待着;下暴雨,怕羊给山水冲走了往山顶上赶,雷在头顶上轰,雨打得我透不过气来……解放啦,我也老啦,不中用啦……可谁知道呢?谁知道我又有了用啦,也要到人们的世界里去露露脸啦!……”老羊工讲述过去遭受的苦难和侮辱,以体现现在的巨大变化,作者在结尾还要强调老羊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第二天天还没亮,老人就摸着黑动身回山;他更加惦念他的羊群了,他觉得自己虽然老了,生活的路子却反倒长远了宽阔了。”[9]在《老羊工》中,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界限分明,社会发展遵循线性规律逐层跃进,主体地位也遵循线性规律逐步提高,作者的创作目的就是通过社会和主体在过去—现在—未来的逐步变化,以表现新社会代替旧社会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唐克新《车间里的春天》叙述了过去—现在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表现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文中结尾写道,“春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用辛勤的劳动创造春天。”[10](72)揭示了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是历史的规律,作者在文中还揭示了过去—现在—未来之间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解放后,工厂的主人换了。这主人就是我们工人自己!”[10](67);另一方面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创造起幸福”[10](71)。柯蓝《新的生活在等着》揭示了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巨大变化,文中明确指出,过去“是指解放以前很长的一段黑暗历史时期”[11](118),现在“这是一切都要重生或新生的年代”[11](124),结尾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憧憬,“让我们爱吧,为了今天和明天。让我们生活得更有力吧,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为了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11](134)。此外,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萧乾《初冬过三峡》等散文作品都表现了这种特征。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俨然成为十七年文学的共同特征,十七年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小说,也都表现了这种历史观念。
另一方面,十七年散文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单就时间范畴来说,为了突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十七年散文采取了偶然时间必然化的操作方式。所谓偶然时间必然化,指的是强调偶然时间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束缚,以突出必然性在社会活动中的支配性地位,《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在柴达木盆地》《英雄列车》等作品表现了这种特征。王石、房树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讲述六十一个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有关人员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文中多次描写“就在同一时间内”的工作状况,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在同一时间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偶然时间,作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必然的事件,这是一种典型的偶然时间必然化的操作方式,作者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了全国的“阶级友爱、情深似海”[12]。李若冰《在柴达木盆地》讲述的是柴达木盆地在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作者在文章开头交待了时间范畴,“这是一九五四年早秋,一个特有的清朗的日子”[13](190)。作者在这一天去柴达木盆地是偶然的,在偶然的时间里,作者看到了柴达木盆地的巨大变化,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在文中把偶然时间转化为必然时间,“今天,也只有在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才真正赏识这丰饶的有待开垦的处女地”[13](192)。又如郭光《英雄列车》,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是一个偶然时间,但这个偶然时间发生的事件是必然的结果。列车在路途中被困,铁路路基出现了严重问题,行进中的列车被洪水包围,列车员和旅客在这个时间段里,充分展示了同舟共济的精神,相互帮助,共克艰难,苦战三昼夜,终于使列车胜利启程。作者在结尾集中表现偶然时间必然化的时间意识,“能在一发千钧的时刻,战胜洪水,化 险为夷,这气魄,这毅力,却绝不会是来自偶然”[14]。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的认识不足,表现了十七年作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高度信仰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必胜信念。
可以看出,在十七年散文中,尤其是秦兆阳、周立波、柯蓝、李若冰等作家的散文,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体现了鲜明的历史决定论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遵循客观规律而不断发展,社会历史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社会形态的演化过程,这是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既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又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因此,十七年散文虽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重要内容,但又陷入了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误区。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十七年时期的杂文写作对历史决定论有过一定的反思,表现了辩证法的思维特征,比如吴晗《说道德》。
三、历史化方法与时间叙事
中国自古就有在历史中理解时间的传统,“以史为鉴”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认识时间和处理事件的重要方法,中国文学叙事也大都运用了这种方法。杨义《中国叙事学》在讨论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时,就指出了中国文学叙事的“以史为鉴”的重要特征。十七年散文认识和处理时间的方式也表现出“以史为鉴”的特征,所谓“以史为鉴”,也就是一种历史化的方法,它具体指的是十七年散文往往把时间与历史结合起来,要么把时间放在历史中进行理解和认识,要么把时间与历史进行对比,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综合来说,十七年散文在认识和处理时间与历史的关系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十七年散文往往把时间作为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突出时间与历史过程的紧密关系,追溯日常时间的历史渊源。秦牧的《土地》《古战场春晓》等散文集中体现了这种方式。秦牧在《土地》中突出了日常时间中的土地与历史中的土地之间的紧密关系,追溯了日常时间中的土地的历史渊源,他在文中写道,“当你坐在飞机上,看着我们无边无际、象覆盖上一张绿色地毯的大地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倚着车窗,看万里平畴的时候;或者,在农村里,看到一个老农捏起一把泥土,仔细端详,想鉴定它究竟适宜于种植什么谷物和蔬菜的时候;或者,当你自己随着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地冒出脚缝的时候,不知道你曾否为土地涌现过许许多多的遐想?想起它的过去,它的未来,想起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为要成为土地的主人,怎样斗争和流血,想起在绵长的历史中,我们每一块土地上面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事迹,他们的苦难、忿恨、希望、期待的心情?”[15](164)在这段文字中,“当你……的时候”叙述的是日常时间,作者在日常时间的叙述中强调的是对过去历史的回忆或想象,日常时间只有在历史中才能显示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者在文章中追溯了世界历史中关于土地的斗争,强调“在我们看来很平凡的一块块的田野,实际上都有过极不平凡的经历”[15](168),土地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彰显出土地的价值和意义。在《古战场春晓》中,“一九六一年春天降临之前”是一个日常时间,作者在这个时间游览了广州北郊的三元里高地,即兴凭吊怀古,“一九六一年”这个日常时间就成为三元里斗争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作者回顾了一百二十年来的历史,在日常时间历史化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日常时间的重要性。此外,艾青《忆白石老人》、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贾植芳《黑夜颂》等散文作品也突出了日常生活与历史过程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十七年散文往往把日常时间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对比,以体现时间范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突出日常时间的价值和意义。《海南岛散记》《丽日南天》等散文主要运用了这种方式。陈窗《海南岛散记》使用了日常时间历史化的方式,作者在文章开头就追溯了海南岛的荒凉历史,重点讲述国民党政府对海南岛人民的压迫,然后描写海南岛在解放以后四年内的巨大变化,作者在讲述日常时间的所见所闻中,不断插叙海南岛的苦难历史,使日常时间融入海南岛的整个历史过程,日常时间又与历史中的海南岛形成鲜明对比,在日常时间历史化的过程中,突出了日常时间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我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人们正在使荒凉的山野变成繁荣的城市,正在使民族仇杀变成民族友爱,并且正在逐步消除昨天的黑暗而走向幸福的明天。”在这段叙述中,作者讲述了海南岛的历史变化,并以这种变化说明了当今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日常时间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显示出价值和意义。臧克家《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由一张照片引发对黄河的看法,在日常时间里,作者看到照片中的毛主席面向黄河笑,由此想起黄河悠久的历史,把日常时间中的黄河历史化,表现黄河在当今时代的巨大变化。韩北屏《丽日南天》记叙了十年时间里的巨大变化,回忆了黑暗时代的悲惨经历,作者在文中表现出明显的时间意识,“十年,就永恒的时间而言,它只是短促的一瞬间;就祖国的悠久历史而言,也不过是较长的一瞬间而已。我们亲爱的共和国,却在这十年中,创造了多少奇迹,成就了多少辉煌的功业!”作者把时间历史化,既突出了十年时间的短暂,又突出了十年时间的巨大变化。此外,杨朔《雪浪花》、方令孺《在山阴道上》、荒煤《阿诗玛,你在哪里?》等作品也突出了新的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
可以看出,十七年散文一方面把时间放置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把时间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对比,总体来说,十七年散文采取的是一种时间历史化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时间是历史的必然元素,时间与历史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时间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真正展示它的价值和意义,历史只有在时间中才能真正得到践行和建构,因此,如何处理时间意味着如何认识历史。时间历史化体现的是一种历史主义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这种历史化的方法在新时期散文中也有着重要表现,为了实现对新的时代的正名,一方面,新时期散文不断追溯历史,追溯中国革命的起源,以表现改革开放时代与20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新时期散文又不断反思历史,批判文化大革命,以突出改革开放时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断裂关系,表现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四、结语
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它不仅表现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而且表现了一种鲜明的历史观念。十七年散文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时间叙事方面具有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时间的意识形态化、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化策略三个方面。在十七年散文中,尤其是在秦牧、刘白羽、魏巍、柳青、秦兆阳等作家的散文中,时间承载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崇高的历史价值,负载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符码;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紧密关系,遵行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把时间放置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认识,或者把时间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对比,以历史化策略认识和处理时间,体现了一种历史主义态度。虽然,十七年散文在意识形态、历史决定论、历史化策略等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但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也存在一些误区。十七年散文的时间叙事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经验,又受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不仅与十七年文学组成了历史的大合唱,而且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积累了重要经验。总之,马克思主义时间理论对十七年散文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张清华. 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J]. 文艺研究, 2006(7): 4-16.
[2] 程慧敏, 李和平. 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内涵及其意义[J]. 理论学刊, 2011(8): 8-12.
[3] 刘白羽. 长江三日[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4] 刘白羽. 日出[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741.
[5] 杨刚.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C]// 散文特写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6.
[6] 柳青.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297.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50.
[8] 张国启, 李欣宇.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逻辑解读[J]. 湖北社会科学, 2013(1): 15-17.
[9] 秦兆阳. 老羊工[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12-117.
[10] 唐克新. 车间里的春天[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1] 柯蓝. 新的生活在等着[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2] 王石, 房树民.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91.
[13] 李若冰. 在柴达木盆地[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4] 郭光. 英雄列车[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84.
[15] 秦牧. 土地[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6] 陈窗. 海南岛散记[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54.
[17] 韩北屏. 丽日南天[C]// 散文特写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7.
The time narrating of prose in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YAN Shuisheng
(The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6, China)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is a brand-new historical period, which reflected a sharp time sense and history ideas. The time narrating of prose in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mainly for the time of ideology, historical determinism and historicized, etc. In the prose of the seventeen years, the time has strong practical orientation, loading rich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us becoming the social ideological codes. The works emphasiz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alk along the past-present-future linear developmen law and emphasize the inevitability and regularity of the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le ignoring the Contingency and twists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y place the tim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r compare the time with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 so as to understand and process time with historical strategy. Marx’s time theor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on the prose research.
seventeen years; prose; time; history; the time of ideology
I267
A
1672-3104(2014)06-0236-06
[编辑: 胡兴华]
2014-06-30;
2014-08-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关联研究”(08BZW057)
颜水生(1980-),男,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